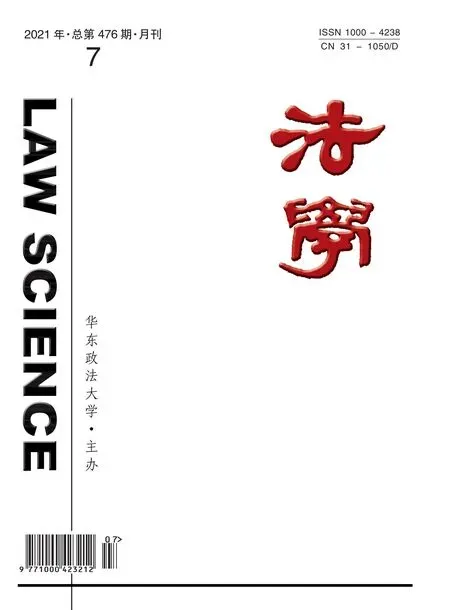論法律行為定性中的“名”與“實”
●于程遠
“名為……實為”原本僅為一種普通的表述方式,其意在揭示事物的本質(zhì)與其所宣稱的名號之間的差異。但是當(dāng)這樣一種表述方式頻繁地在裁判文書中出現(xiàn),并且經(jīng)常被作為判決說理部分的核心論據(jù)之一時,該表達似乎就在事實上形成了一種自身蘊含正當(dāng)性的獨特公式,不斷吸引裁判者訴諸該公式為自己的論證尋求正當(dāng)性支持。這一表達方式似乎已經(jīng)在事實上成為裁判者對法律行為作出定性以及適用法律時的重要理由。當(dāng)裁判者意圖適用有關(guān)B 的規(guī)則規(guī)制A 時,便可能聲稱該法律行為“名為A 實為B”,在該語境下,這樣一種聲稱通常就被作為說理本身。〔1〕參見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8)豫民終1074 號民事判決書。
實踐中“名為……實為”論斷的適用情形中交織著法律行為的內(nèi)容與目的、真實與虛假、當(dāng)事人的有意與無意、裁判者的自我謙抑與主動干預(yù)等多重矛盾。此時“名為……實為”的論斷似乎成為化解一切矛盾的“萬金油”,因為名不副實的情形是需要糾正的,這是正確適用法律的前提,此點在當(dāng)事人無意識地使用錯誤指稱時尤為明顯。在當(dāng)事人有意使用錯誤指稱時,如果裁判者基于自身判斷糾正此種名不副實的情形,實際上是對當(dāng)事人的意思自治施加了不同程度的干預(yù)。如果某法律行為的當(dāng)事人以明確的表達訂立A 類型法律行為,而裁判者卻宣告該法律行為名為A 實為B,并且以B 類型法律行為的相關(guān)規(guī)則予以評價,那么此時必然產(chǎn)生的矛盾是,當(dāng)裁判者認為當(dāng)事人進行了B 類型法律行為時,該行為性質(zhì)的認定實際上未必符合當(dāng)事人的意圖,甚至是當(dāng)事人所刻意避免的。
如果對相關(guān)案例作進一步的考察,便會發(fā)現(xiàn)這樣一種“名為……實為”論斷之下的“名”“實”關(guān)系可能遠比想象中的復(fù)雜。在法律行為的“名”“實”關(guān)系中,究竟何為“名”,何為“實”?當(dāng)法律行為的“名義”(指稱)與“內(nèi)容”遭遇時,名義為“名”,內(nèi)容為“實”;然而當(dāng)法律行為的“內(nèi)容”與“目的”遭遇時,內(nèi)容便成了呈現(xiàn)于表面的“名”,當(dāng)事人通過該法律行為所追求的經(jīng)濟目的便成為這一語境之下的“實”。當(dāng)人們以“名為……實為”這一論斷對法律行為作出定性時,究竟所指為何,解釋者能否以法律行為的內(nèi)容否定其指稱,又能否以法律行為的目的否定其內(nèi)容?若將觀察法律行為名實關(guān)系的視角從單純的“名”“實”二元結(jié)構(gòu)轉(zhuǎn)向法律行為的名義、內(nèi)容、目的的三層次結(jié)構(gòu)之上,便需要進一步回答三者在這一結(jié)構(gòu)體系中的作用問題。本文嘗試解決上述問題,澄清法律行為定性過程中的“名”“實”關(guān)系,探尋“名為……實為”這一在實踐中被普遍使用的說理論斷的正當(dāng)性基礎(chǔ)與邊界。
一、法律行為“名”“實”沖突的實踐考察與理論定位
(一)實踐中法律行為“名”“實”關(guān)系的沖突形式
1. 法律行為名義與內(nèi)容的沖突
實踐中“名為……實為”公式的運用可能首先出現(xiàn)在法律行為的名義與內(nèi)容發(fā)生偏離的情況中。所謂名義與內(nèi)容的偏離,是指當(dāng)事人為法律行為選取的名稱或在具體設(shè)定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時所使用的法律概念與該法律行為的實質(zhì)內(nèi)容不符。此時裁判者通常會以“名為……實為”的論斷否定當(dāng)事人對該法律行為的表面定性,從而揭示其真實性質(zhì)。
當(dāng)事人可能因為自身法律知識的缺乏而為其實施的法律行為選取了錯誤的指稱,然而事實上雙方當(dāng)事人對該法律行為的性質(zhì)并無爭議,例如,雙方當(dāng)事人錯誤地將“投資”稱為“借貸”的情形,〔2〕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終793 號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終1146 號民事判決書。以及錯誤地將“承包經(jīng)營合同”稱為“聯(lián)合開發(fā)合同”的情形。〔3〕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一終字第44 號民事判決書。此類情形下的錯誤指稱是當(dāng)事人無意導(dǎo)致的,對于法院在判決中轉(zhuǎn)變其定性而適用相關(guān)法律規(guī)范通常不存異議。但需要注意的是,雙方當(dāng)事人無異議并不意味著法院可以放棄對法律行為性質(zhì)的審查,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曾在判決中正確指出的:“合同的性質(zhì)和效力涉及合同當(dāng)事人法律關(guān)系的確定,影響當(dāng)事人權(quán)利義務(wù)的分配,關(guān)系到當(dāng)事人的訴訟主張能否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因此,人民法院在審理合同糾紛案件中,即使當(dāng)事人沒有爭議,人民法院也應(yīng)依職權(quán)對合同的性質(zhì)、效力進行審查。對于合同性質(zhì),應(yīng)綜合考慮當(dāng)事人的整體意思表示,根據(jù)當(dāng)事人約定的主要權(quán)利義務(wù)的性質(zhì)進行判定,而不能只審查合同名稱,不應(yīng)受個別條款的影響,亦不能僅根據(jù)當(dāng)事人在訴訟中的主張進行確認。”〔4〕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304 號民事判決書。
較為復(fù)雜的是當(dāng)事人有意選取錯誤指稱的情形,在此種情形下當(dāng)事人通常懷有規(guī)避某一特定法律禁令的隱藏目的,該禁令可能表現(xiàn)為法律在特定交易形式之下對主體資格、獲利程度的限制等。例如“名為投資,實為借貸”的現(xiàn)象極為普遍,當(dāng)事人將借款關(guān)系稱為投資關(guān)系,主要原因通常在于規(guī)避有關(guān)借款利率限制的法律規(guī)定。〔5〕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終1374 號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終881 號民事判決書。為了規(guī)避對借款合同的這一限制,當(dāng)事人不僅可能將借款合同偽裝成投資合同,還有可能將其偽裝成諸如“保證金有償使用協(xié)議”〔6〕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1667 號民事裁定書。、“承包經(jīng)營合同”〔7〕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111 號民事判決書。、“合伙協(xié)議”〔8〕參見廣東省深圳市龍華區(qū)人民法院(2019)粵0309 民初1915 號民事判決書。、“委托資產(chǎn)管理合同”〔9〕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二終字第83 號民事判決書。等其他形式,從而實現(xiàn)超過限額的利息回報。在此種情形下,法院通常會指出當(dāng)事人雖然有意選取其他名義,但其法律行為的內(nèi)容均表現(xiàn)為提供資金的當(dāng)事人不承擔(dān)經(jīng)營風(fēng)險,只收取固定數(shù)額貨幣,因此“實為借貸”。
2.法律行為內(nèi)容與目的的沖突
實踐中還存在大量依據(jù)法律行為的目的作出“名為……實為”論斷的情形。為了實現(xiàn)規(guī)避特定法律的目的,當(dāng)事人可能特意為法律行為設(shè)定紛繁復(fù)雜的內(nèi)容以加大法院對該法律行為作出定性的難度,此時法院則可能越過當(dāng)事人刻意選取的繁復(fù)手段,直接依據(jù)這些手段所達成的最終效果或可以探明的當(dāng)事人的實質(zhì)目的對該法律行為作出“名為……實為”的判定,從而使當(dāng)事人的規(guī)避行為失去意義。〔10〕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終1026 號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終940 號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183 號民事判決書。
此類論斷主要出現(xiàn)在原《合同法》第52 條第3 項“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這一規(guī)定的適用過程中。〔11〕參見江蘇省張家港市人民法院(2019)蘇0582 民初12771 號民事判決書;四川省華鎣市人民法院(2020)川1681 民初34號民事判決書;吉林省榆樹市人民法院(2019)吉0182 民初6268 號民事判決書。此種情形下法官的判斷并不受法律行為內(nèi)容的限制,只要當(dāng)事人意圖實現(xiàn)的目的或該法律行為客觀上可以達成的經(jīng)濟效果是非法的,那么該行為就有可能落入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規(guī)制范疇。從這一意義上看,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是對抗法律規(guī)避行為最為直接和有效的工具。但《民法典》合同編并未將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作為合同或法律行為無效的事由加以規(guī)定,因此這一案型被諸如虛假法律行為、惡意串通、類推適用等制度或方法分割與吸收。
由此,實踐中出現(xiàn)了一種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即在存在虛假法律行為的情況下,“名為……實為”論斷也得到了極為普遍的運用。法院經(jīng)常通過該論斷指出,當(dāng)事人之間實施的法律行為“名為”表面行為,“實為”隱藏行為。〔12〕參見吉林省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吉01 民再25 號民事判決書。例如當(dāng)事人為了避稅而實施的“名為買賣,實為贈與”的典型情形。〔13〕參見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16)京03 民終7576 號民事判決書;上海市浦東新區(qū)人民法院(2012)浦民一(民)初字第4122 號民事判決書。在此之外,法院在所謂“閉合循環(huán)買賣”中也通常會作出“名為買賣,實為借貸”的判斷,從而適用虛假法律行為制度認定表面上的買賣合同無效,轉(zhuǎn)而適用有關(guān)借貸的法律規(guī)范判斷當(dāng)事人之間事實上存在的借貸關(guān)系的效力。〔14〕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1247 號民事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終880 號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559 號民事裁定書。在這類案件中,雙方當(dāng)事人并無將表面上訂立的法律行為所規(guī)定的效果真正實現(xiàn)的意思,其通常只是希望借助表面行為應(yīng)付審批、登記、納稅、審查等法律行為外部的事務(wù),而其真正意圖實現(xiàn)的法律行為(隱藏行為)的內(nèi)容與其表面行為的內(nèi)容并不相同。〔15〕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終101 號民事判決書。此類情形本質(zhì)上不屬于法律行為定性的范疇,但經(jīng)常因“名為……實為”公式的運用與法律行為定性問題糾纏在一起,容易造成理論上的混淆和法律適用上的混亂。
(二)法律行為定性:意思表示的規(guī)范評價
撥開“名為……實為”這一籠統(tǒng)論斷之下的迷霧,不難發(fā)現(xiàn)法院無論出于何種理由運用這一公式,最終目的其實都在于為其裁判尋找合適的法律規(guī)范依據(jù)。通常而言,這一目標需要通過法律行為定性加以實現(xiàn)。法律行為定性的根本任務(wù)在于確定法律行為在法教義學(xué)上的歸屬類別,從而正確適用相應(yīng)的法律規(guī)范。例如,將“甲轉(zhuǎn)移標的物的所有權(quán)于乙,而乙支付價款”的合同定性為買賣合同,從而適用《民法典》第595 條以下的法律規(guī)范。又如,將“甲按照乙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乙支付報酬”的合同定性為承攬合同,從而適用《民法典》第770 條以下的法律規(guī)范。這一過程離不開對當(dāng)事人意思表示的解釋,法律行為定性的本質(zhì)是法律對當(dāng)事人的意思表示作出規(guī)范意義上的評價,唯有確定了當(dāng)事人通過意思表示構(gòu)建的法律行為類型,方能判斷法律針對該類型的法律行為所意圖采取的規(guī)制方式。
正如德國學(xué)者辛格(Singer)指出的,意思表示的本質(zhì)特征并非簡單地表達某種愿望或?qū)δ硞€行為進行宣告,而是一種“表述行為”,它是語言行為的一種,此種語言行為所產(chǎn)生的效力恰是其所表達的內(nèi)容。〔16〕Vgl. Staudinger/Singer, 2011, BGB Vor. § 116 Rn. 6.當(dāng)由此效力產(chǎn)生的法律后果符合當(dāng)事人的意愿時,當(dāng)事人的自治才能得到充分貫徹,即“根據(jù)自己的意愿對法律關(guān)系作出的終局性構(gòu)建”。〔17〕Vgl. Staudinger/Singer, 2011, BGB Vor. § 116 Rn. 8.基于意思表示而產(chǎn)生的法律關(guān)系并非構(gòu)筑于生物學(xué)意義上“自由的”、不確定的意志之上,某種允諾是否產(chǎn)生法律上的約束力,通過法律行為獲得的權(quán)利在遭遇阻礙時能否借助國家力量得以貫徹,事實上取決于法律上的特殊考量,并非僅僅基于允諾行為本身的性質(zhì)。究其實質(zhì),意思表示是一種對意圖構(gòu)建法律關(guān)系的人類行為的規(guī)范性劃分。換言之,買賣之所以為買賣,贈與之所以為贈與,并非因為當(dāng)事人稱之為“買賣”或者“贈與”,而是因為法律將此類行為評價為買賣(《民法典》第595 條以下)或贈與(《民法典》第657 條以下)。
因此,對意思表示內(nèi)容的確定在本質(zhì)上不僅屬于對事實的查明,其更是解釋者借助法律對該意思表示作出的法律評價,對當(dāng)事人特定行為意義的解釋更是如此。對意思表示內(nèi)容的解釋需要遵循人的客觀理性,這要求解釋者一方面應(yīng)當(dāng)盡量避免將合同的內(nèi)容解釋得前后矛盾,另一方面應(yīng)當(dāng)盡量對合同約定作出合乎成文法內(nèi)容與目的的解釋,從而盡量維持合同約定的法律效力。〔18〕Vgl. MüKoBGB/Busche, 2018, BGB § 133 Rn. 64.在諸多可能的解釋結(jié)果中,解釋者原則上應(yīng)當(dāng)采納能夠令合同約定具備法律意義的結(jié)果。〔19〕Vgl. Hager, Gesetzes- und sittenkonforme Auslegung und Aufrechterhaltung von Rechtsgesch?ften, 1983, S. 31 ff.例如,在“原告張某1與被告張某2、張某3、張某4、張某5 遺囑繼承糾紛案”中,被繼承人與自己的法定繼承人簽訂“遺贈扶養(yǎng)協(xié)議”,約定由該法定繼承人承擔(dān)對被繼承人生養(yǎng)死葬的義務(wù)并享有接受遺贈的權(quán)利。然而根據(jù)通說,遺贈扶養(yǎng)協(xié)議的扶養(yǎng)人須為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20〕盡管原《繼承法》第31 條第1 款僅規(guī)定:“公民可以與扶養(yǎng)人簽訂遺贈扶養(yǎng)協(xié)議。按照協(xié)議,扶養(yǎng)人承擔(dān)該公民生養(yǎng)死葬的義務(wù),享有受遺贈的權(quán)利。”但當(dāng)時學(xué)界普遍認為此處的“扶養(yǎng)人”應(yīng)為法定繼承人范圍以外的人,這一觀點在《民法典》第1158 條中得到確認:“自然人可以與繼承人以外的組織或者個人簽訂遺贈扶養(yǎng)協(xié)議。按照協(xié)議,該組織或者個人承擔(dān)該自然人生養(yǎng)死葬的義務(wù),享有受遺贈的權(quán)利。”這就導(dǎo)致該協(xié)議無法有效成立。于是法院在對該意思表示進行解釋時,將其解釋為“名為遺贈扶養(yǎng)協(xié)議,實為附義務(wù)的遺囑”,通過轉(zhuǎn)換的方式盡可能維持了該法律行為的效力。〔21〕參見江蘇省南京市棲霞區(qū)人民法院(2018)蘇0113 民初1913 號民事判決書。
法秩序?qū)Ξ?dāng)事人意思表示的價值評價從對該意思表示進行解釋時便已開始,而民法中對于意思表示瑕疵、違背公序良俗原則以及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強制性規(guī)定等更為直接的效力控制條款,實際上都建立在已完成意思表示解釋的基礎(chǔ)之上。例如,在“山西金暉煤焦化工有限公司、李蘇合同糾紛案”中,法院針對雙方當(dāng)事人“名為地質(zhì)災(zāi)害治理合同,實為煤炭資源開采合同”的情形作出了正確的認定。雙方當(dāng)事人以“昌華煤礦災(zāi)害治理內(nèi)部責(zé)任制承包協(xié)議”的名義約定由其中一方當(dāng)事人對礦區(qū)進行災(zāi)害治理,在治理過程中得到的煤炭資源歸己所有,并向另一方當(dāng)事人支付所謂“管理費”。這一合同既包含災(zāi)害治理的要素,又包含煤炭開采的內(nèi)容,從而造成合同定性上的疑難。法院結(jié)合合同約定的內(nèi)容以及地質(zhì)災(zāi)害治理合同的核心特征否定了“災(zāi)害治理合同”的性質(zhì),而將其認定為煤炭資源開采合同。其一針見血地指出:“鑒于人為活動引發(fā)的地質(zhì)災(zāi)害治理遵循‘誰引發(fā)、誰治理、誰承擔(dān)費用’的原則,本案作為已開發(fā)煤礦的地質(zhì)災(zāi)害治理,依法應(yīng)由昌華煤礦的權(quán)利人(采礦權(quán)人)作為責(zé)任治理主體,并承擔(dān)治理費用;若由第三人具體負責(zé)災(zāi)害治理,正常情況下責(zé)任治理主體應(yīng)向第三人支付治理工程費用,而不存在第三人向責(zé)任治理主體支付費用的問題,此應(yīng)為地質(zhì)災(zāi)害治理合同的核心特征。”針對合同中同時存在的關(guān)于所謂災(zāi)害治理相關(guān)義務(wù)的約定,法院則認為其“本來就是采礦權(quán)人法定的礦山地質(zhì)環(huán)境治理恢復(fù)義務(wù)”。〔22〕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終641 號民事判決書。由此,該協(xié)議形成了一個以災(zāi)害治理名義包裝的煤炭資源開采合同,應(yīng)當(dāng)受到以《礦產(chǎn)資源法》為首的一系列涉及煤礦資源開采的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規(guī)制。因此,意思表示解釋絕非單純地“探明”當(dāng)事人的真實意思,同樣蘊含當(dāng)事人意思自治與法律評價乃至司法干預(yù)之間的齟齬。在處理法律行為的“名”“實”關(guān)系時,裁判者本質(zhì)上是在“名”“實”之間選取某一標準對該法律行為進行評價,該標準的選取應(yīng)當(dāng)遵循法律在意思表示解釋理論之下作出的均衡考量,而不能逾越意思表示解釋理論設(shè)置的藩籬,純粹從外部規(guī)制的需求出發(fā)對法律行為進行定性。
二、意思表示解釋理論下的內(nèi)容決定論
(一)“經(jīng)驗/規(guī)范”二元方法體系下的意思表示解釋
1.自然解釋相較于規(guī)范解釋的優(yōu)先性
法律行為的定性本質(zhì)上屬于意思表示解釋的范疇,解釋者通過將待定性的法律行為與法律條文中的某一規(guī)則集合相對應(yīng)的方式完成對該法律行為的初步評價。在這一對應(yīng)歸類的過程中,意思表示的具體內(nèi)容是解釋者首先需要考量的決定性要素。
解釋者需要依據(jù)法律行為的內(nèi)容確定其性質(zhì),法律行為的內(nèi)容原則上應(yīng)當(dāng)依我國《民法典》第142 條加以確定。依據(jù)該條規(guī)定,意思表示的解釋方法因該意思表示有無相對人有所不同,然而無論是無相對人的意思表示還是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其解釋實際上都遵循所謂“經(jīng)驗/規(guī)范”(empirisch/nomativ)的二元方法體系(Methodendualismus),這意味著當(dāng)事人可以確定的真實意思(或合意)總是優(yōu)先于其表達得到法律的認可。〔23〕Vgl. Mittelst?dt, Falsa demonstratio: Und sie schadet doch! Eine Kritik der natürlichen Auslegung empfangsbedürftiger Willenserkl?rungen, ZfPW 2017, S. 175.
對于無相對人意思表示的解釋,我國《民法典》第142 條第2 款明確規(guī)定:“不能完全拘泥于所使用的詞句,而應(yīng)當(dāng)結(jié)合相關(guān)條款、行為的性質(zhì)和目的、習(xí)慣以及誠信原則,確定行為人的真實意思。”這是基于意思主義解釋立場的明確表達,即在確定意思表示的內(nèi)容時,表意人的真實意思是最重要的。如今被主流意見視為理所當(dāng)然的“誤載不害真意”規(guī)則,在羅馬法時期僅在遺囑解釋的領(lǐng)域得以適用,直到潘德克頓時期才開始有意見主張這一規(guī)則應(yīng)當(dāng)在契約領(lǐng)域同樣得到適用。〔24〕Vgl. Hans Josef Wieling, Die Bedeutung der Regel falsa demonstratio non nocet im Vertragsrecht, AcP 172(1972), S. 298.時至今日,在對無相對人的意思表示進行解釋時,我國法院已無須特意訴諸“誤載不害真意”規(guī)則,而可以直接依據(jù)《民法典》第142 條第2 款探明當(dāng)事人的真實意思,從而確定法律行為的具體內(nèi)容。
對于有相對人意思表示的解釋,《民法典》第142 條第1 款規(guī)定“應(yīng)當(dāng)按照所使用的詞句,結(jié)合相關(guān)條款、行為的性質(zhì)和目的、習(xí)慣以及誠信原則,確定意思表示的含義”。此時盡管規(guī)范解釋通常發(fā)揮更為廣泛的作用,但不容忽視的是當(dāng)事人的真實意思同樣處于最應(yīng)優(yōu)先考慮的地位。解釋者應(yīng)當(dāng)首先在經(jīng)驗層面上確定當(dāng)事人的真實合意,如果當(dāng)事人的合意內(nèi)容能夠清晰確定,那么無論表達如何,仍然均以其真實達成的合意內(nèi)容為準,這又被稱為“自然主義”的解釋方式。〔25〕參見紀海龍:《走下神壇的“意思”——論意思表示與風(fēng)險歸責(zé)》,載《中外法學(xué)》2016 年第3 期,第666 頁。換言之,如果雙方就法律行為的內(nèi)容實際上達成了真實合意,那么該法律行為便在該合意的范圍內(nèi)得以成立,而無須再借助規(guī)范解釋探尋一個“客觀受領(lǐng)人”的通常理解。例如,買賣合同的雙方當(dāng)事人已經(jīng)在談判中確定了所購汽車的價格為100000 元,那么在訂立書面合同時,合同書上所寫究竟是10000 元還是1000000元,其實并不影響合同在真實約定的100000 元價位上成立且生效。因此在法律行為內(nèi)容確定無爭議的情形下,當(dāng)事人的錯誤表達并不影響其性質(zhì)認定。〔26〕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終1146 號民事判決書。僅當(dāng)真實合意無法確定時,才需要在次級層面上尋求客觀受領(lǐng)人視角的規(guī)范解釋。〔27〕同前注〔23〕,Mittelst?dt 文,第177 頁。在規(guī)范解釋層面上,解釋者需要探尋的問題便不再是當(dāng)事人所達成的真實合意究竟為何,而是一個客觀的第三人處在意思表示受領(lǐng)人的位置上時,依據(jù)誠實信用原則與交易習(xí)慣會對該意思表示作出怎樣的理解。〔28〕Vgl. BGH NJW-RR 2002, 20, 22.因此,對有相對人意思表示的解釋并非自始就進入規(guī)范解釋的層面,在當(dāng)事人真實合意能夠探明的情況下,解釋者應(yīng)當(dāng)尊重此種合意,而不應(yīng)強行以客觀相對人的理解修正其意思。
2.規(guī)范解釋中的考量要素
規(guī)范解釋并不意味著解釋者被絕對束縛于意思表示的語義,而需要結(jié)合合同文本之外的、對意思表示受領(lǐng)人而言可獲知的全部情勢加以判斷。〔29〕Vgl. BGH NJW 2001, 1260, 1261.除了意思表示本身的文義之外,裁判者還需要綜合考量包括交易習(xí)慣、當(dāng)事人之間的利益狀態(tài)(Interessenlage der Beteiligten),〔30〕Vgl. Hoffmann/Schneider, Die Rücksendung der Ware als Widerrufserkl?rung, NJW 2015, 2529, 2532.以及當(dāng)事人通過實施該法律行為所追求的經(jīng)濟目的〔31〕Vgl. BeckOK BGB/Wendtland, 2021, BGB § 133 Rn. 25.在內(nèi)的諸多外在因素。這些外在因素盡管不能直接決定對意思表示內(nèi)容的理解,卻可以在對意思表示進行解釋的過程中發(fā)揮輔助功能。最高人民法院曾就合同定性的問題指出:“對于案涉合同性質(zhì)和效力,應(yīng)當(dāng)根據(jù)合同簽訂目的、約定內(nèi)容以及實際履行情況等予以認定。”〔32〕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終388 號民事裁定書。但是如果在第一步的判斷中結(jié)合全部的外部證據(jù)可以探明當(dāng)事人的真實意思,那么當(dāng)事人是否選取了正確的詞語對其意思進行表達就不再那么重要了。這也是所謂“誤載不害真意”規(guī)則所具有的價值。這一規(guī)則被比德林斯基(Bydlinski)稱為“合同法中最確實的律令”。〔33〕Vgl. Bydlinski, Privatautonomie und objektive Grundlagen des verpflichtenden Rechtsgesch?ftes, 1967, S. 119.
需要注意的是,規(guī)范解釋中對所有因素的綜合考量不應(yīng)導(dǎo)致意思表示解釋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完全忽略當(dāng)事人的明確表達而執(zhí)著于通過當(dāng)事人作出法律行為時的外部情勢探明隱藏在法律行為表達背后的真相。最高人民法院曾在判決書中通過肯認合同書的證據(jù)效力否定當(dāng)事人“名為買賣,實為借貸”的主張,并明確指出:“合同在性質(zhì)上屬于原始證據(jù)、直接證據(jù),應(yīng)當(dāng)重視其相對于傳來證據(jù)、間接證據(jù)所具有的較高證明力,并將其作為確定當(dāng)事人法律關(guān)系性質(zhì)的邏輯起點和基本依據(jù)……在兩種解讀結(jié)果具有同等合理性的場合,應(yīng)朝著有利于書面證據(jù)所代表法律關(guān)系成立的方向作出判定……透過解釋確定爭議法律關(guān)系的性質(zhì),應(yīng)當(dāng)秉持使爭議法律關(guān)系項下之權(quán)利義務(wù)更加清楚,而不是更加模糊的基本價值取向。”〔34〕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終字第78 號民事判決書。盡管最高人民法院從合同書的證據(jù)效力入手作出分析,但其觀點對意思表示解釋理論的運用同樣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在對意思表示進行解釋時,并非發(fā)掘越深入,解釋的結(jié)果就越正當(dāng),意思表示的文義始終是查明當(dāng)事人真實意思的首要依據(jù),而在證據(jù)層面上,固化于合同書上的意思表示文義相較于其他輔助情勢具有更高的證據(jù)效力。
在依據(jù)意思表示解釋規(guī)則對法律行為作出“名為……實為”的論斷時,不僅需要考察名義上該法律行為指稱是否錯誤,還需要考察實際上該法律行為是否具備另一法律行為的特征。例如,同樣是在房屋買賣合同中約定回購條款,在有的案件中會被認定為“名為買賣,實為借貸”,〔35〕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終490 號民事判決書。而在有的案件中則被認為“只是對購房人轉(zhuǎn)讓房屋權(quán)利的限制和對承租人權(quán)利的保障”,不導(dǎo)致該合同被認定為借款合同。〔36〕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終字第154 號民事判決書。其最主要的區(qū)別在于前者明確約定了在3 個月后以每平方米月息8 分的增幅回購該房產(chǎn),從而導(dǎo)致法院認為以購房為名支付款項、按月計取利息、到期還本付息等行為均符合借款合同的特征。而后者則無法從合同條款中解讀出符合借款合同特征的約定,甚至房屋沒有實際交接而是直接收取房租款的交易模式,也被法院認為屬于購房人對自有物業(yè)的經(jīng)營方式,雖然購房目的具有投資性,但購房的目的并不影響合同的性質(zhì)。這兩個案件的對比深刻地揭示出在以“名為買賣,實為借貸”對涉案合同進行定性時,重要的并非論證當(dāng)事人在買賣合同中作出的回購約定對“買賣關(guān)系”而言是如何“不典型”,而是論證該約定如何典型地符合了另一法律行為(即借款合同)的特征,從而證明其違反了法律有關(guān)借款合同的禁止性規(guī)定。若非如此則無法解釋在法律并未禁止當(dāng)事人作出“非典型”約定的情形下,為何非要強行將該法律行為納入“典型法律行為”的軌道。就如同法律既允許當(dāng)事人通過買賣合同以一個較高的價格約定購買空調(diào)附贈安裝服務(wù),也允許當(dāng)事人以較低的價格單獨訂立買賣合同與安裝合同,其原因不過在于當(dāng)事人并未觸犯任何禁令而已。至于究竟當(dāng)事人訂立的是一個合同還是兩個合同,則屬于當(dāng)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疇。從法律行為定性的實質(zhì)功能上看,即便法院依據(jù)其內(nèi)容轉(zhuǎn)變了對該行為的定性,也不意味著該行為直接失去效力,而是以同樣的內(nèi)容受到對應(yīng)其真實性質(zhì)的法律規(guī)則的審查。〔37〕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終286 號民事判決書。
意思表示解釋的任務(wù)不僅在于確定法律行為的內(nèi)容或含義,更在于為特定的內(nèi)容與含義找到與之對應(yīng)的法律規(guī)范。司法實踐中的這一過程并非易事,因為其中可能夾雜各種形式上的干擾因素,尤其是當(dāng)事人可能試圖以其他的合同名義干擾法院的判斷,法院此時便需要綜合各方面因素對合同性質(zhì)進行認定。例如在建設(shè)工程合同中,法律對分包和轉(zhuǎn)包行為的評價便截然不同。所謂分包,指的是承包人將其承包工程的一部分交由第三人完成,與第三人簽訂承包合同之下的分包合同的發(fā)包承包方式。對于分包行為,《民法典》第791 條第2 款第1 句規(guī)定:“總承包人或者勘察、設(shè)計、施工承包人經(jīng)發(fā)包人同意,可以將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而轉(zhuǎn)包指的是承包人將自己承包的工程全部倒手轉(zhuǎn)包給第三人,使第三人實際上成為這一建設(shè)工程的承包人。對于轉(zhuǎn)包行為,《民法典》第791 條第2 款第3 句規(guī)定:“承包人不得將其承包的全部建設(shè)工程轉(zhuǎn)包給第三人或者將其承包的全部建設(shè)工程支解以后以分包的名義分別轉(zhuǎn)包給第三人。”無論是轉(zhuǎn)包合同還是分包合同,從權(quán)利義務(wù)外觀上均表現(xiàn)為承包方將自身承包的工程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合同,其區(qū)別就在于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工作量占承包方自身總工作量比例的不同,而這一比例的不同便帶來了法律評價上的巨大差異。在“成都精建建筑勞務(wù)輸出有限責(zé)任公司、陳可建設(shè)工程分包合同糾紛案”中,一審法院便從合同的實際履行情況入手,正確地指出:“雖然陳茂源是以鴻盛公司的名義而非以個人名義或者九天公司的名義組織施工,但是由于陳茂源不是鴻盛公司的員工,鴻盛公司也不實際履行與發(fā)包方簽訂的建設(shè)工程施工合同義務(wù),因此《項目工程管理責(zé)任書》名為內(nèi)部承包、實為工程轉(zhuǎn)包,陳茂源是……工程的實際施工人。”〔38〕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289 號民事判決書。
因此,規(guī)范解釋的目標在于確定“意思表示的真實含義”(《民法典》第142 條第1 款),即確定意思表示的內(nèi)容。在確定意思表示內(nèi)容的過程中,當(dāng)事人的行為目的、履行中的實際行為以及當(dāng)事人之間的利益狀態(tài)等因素都可能被納入考量,但這些要素在整個邏輯鏈條上均屬于“輔助性情勢”(begleitenden Umst?nde),而非決定性要素。〔39〕Vgl. MüKoBGB/Busche, 2018, BGB § 133 Rn. 12.意思表示解釋規(guī)則致力于通過探明當(dāng)事人的行為目的確定意思表示的真實含義(內(nèi)容),而非直接決定當(dāng)事人應(yīng)當(dāng)通過何種方式和手段實現(xiàn)其目的。
3. 意思表示解釋的特別規(guī)范
(1)法律明文擬制或推定的意思表示含義
在特定情形下,法律可能以明文的形式對當(dāng)事人特定表達或行為的意義加以擬制或推定。在法律擬制的情形下,決定意思表示內(nèi)容的既非表意人的真實意思,也非客觀受領(lǐng)人對該表示的理解,而是法律對此的特殊考量。〔40〕Vgl. BeckOK BGB/Wendtland, 2021, BGB § 133 Rn. 30.而在法律推定的情形下,立法者允許當(dāng)事人通過證明自己與法律推定相悖的意思而推翻該推定。
例如,針對合同的定性問題,《民法典》第888 條第2 款規(guī)定:“寄存人到保管人處從事購物、就餐、住宿等活動,將物品存放在指定場所的,視為保管,但是當(dāng)事人另有約定或者另有交易習(xí)慣的除外。”這是立法者對到經(jīng)營場所從事“購物、就餐、住宿等活動”的民事主體作出的傾向性保護,意在終結(jié)司法實踐中保管合同與其他類型合同的定性之爭。例如,在“李杏英訴上海大潤發(fā)超市存包損害賠償案”中,雙方當(dāng)事人就消費者使用超市的自助寄存柜存物時與超市形成何種法律關(guān)系的問題發(fā)生爭議。消費者主張“自助寄存柜是超市為吸引消費者到其店內(nèi)購物,同時又要保證其店內(nèi)貨物安全而設(shè)置的,這是因購物而派生出來的保管服務(wù)”。而超市則主張其“為方便消費者購物而向消費者無償提供了自助寄存柜,雙方就此柜的使用形成的無償借用合同關(guān)系”。〔41〕《李杏英訴上海大潤發(fā)超市存包損害賠償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2 年第6 期,第199-201 頁。保管合同抑或借用合同的定性結(jié)果會直接關(guān)涉超市是否要為消費者包裹遺失負責(zé)的最終判斷。若法院將該合同認定為保管合同,則超市作為保管人負有妥善保管寄存物的義務(wù),若消費者在儲物柜中寄存的包裹遺失,則超市需要依據(jù)法律針對保管合同的相關(guān)規(guī)定承擔(dān)違約責(zé)任。然而若法院將該合同認定為借用合同,則超市作為儲物柜的出借人,只要保證儲物柜本身能夠正常使用即可,而無須對消費者寄存其中的包裹負責(zé)。由此,對消費者無償使用超市儲物柜寄存包裹這一法律關(guān)系的定性便具有了濃厚的法律評價色彩。若側(cè)重于“無償使用”的側(cè)面,則應(yīng)當(dāng)將其定性為借用合同,免除超市針對包裹安全的責(zé)任;若側(cè)重于“寄存包裹”的側(cè)面,則應(yīng)當(dāng)將其定性為保管合同,令超市對包裹負擔(dān)妥善保管的義務(wù)。
在該案中,法院并未武斷地判定此類型的法律關(guān)系一概屬于保管合同或借用合同,而是從原《合同法》對保管合同的定義入手,結(jié)合案件中包裹存放的具體操作步驟、超市在儲物柜處張貼的聲明等情形,證明消費者的物品沒有轉(zhuǎn)移給超市占有,超市也沒有收到消費者交付保管的物品,因此不成立保管合同。這是針對具體案件中當(dāng)事人意思表示內(nèi)容的解釋,它要求法官在個案中對當(dāng)事人意思表示的具體情形進行微觀考察,并且為之付出更高的論證成本。需要注意的是,盡管《民法典》第888條第2 款采用了“視為”的表述方式,但其并非對當(dāng)事人意思的擬制,而是推定,因為即便是在該款規(guī)定之下,裁判者依舊需要首先通過意思表示解釋理論確定當(dāng)事人的真實意思,僅當(dāng)該真實意思既無法查明又無可以依據(jù)的交易習(xí)慣時,才適用法律提供的推定規(guī)則。
(2)特別解釋規(guī)則的設(shè)置
在擬制與推定的規(guī)則之外,法律還有可能不直接確定當(dāng)事人意思表示的含義,而是通過在意思表示解釋的基本規(guī)則(《民法典》第142 條)之外設(shè)定特殊解釋規(guī)則的方式實現(xiàn)特定的法政策目標。例如《民法典》第498 條規(guī)定:“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fā)生爭議的,應(yīng)當(dāng)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yīng)當(dāng)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此類規(guī)定不能被理解為對《民法典》第142 條所設(shè)定的意思表示基本解釋規(guī)則的具體化,因為該條規(guī)定的目的并非“探尋”意思表示的真實含義,而恰恰是根據(jù)誠信原則“修正”(Korrektur nach Treu und Glauben)這一含義。〔42〕Vgl. MüKoBGB/Busche, 2018, BGB § 133 Rn. 65.因此,當(dāng)合同的定性問題與格式條款的解釋問題交織在一起時,根據(jù)《民法典》第498 條規(guī)定,若根據(jù)通常的理解不能得出唯一結(jié)論,解釋者應(yīng)當(dāng)作出對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當(dāng)事人不利的解釋,即通過對意思表示進行解釋作出對提供格式條款一方不利的定性。
(二)法律行為“名義”無價值的例外
如前所述,法律行為定性的主要依據(jù)是當(dāng)事人之間約定的權(quán)利義務(wù)構(gòu)造,即法律行為的內(nèi)容,而當(dāng)事人為法律行為選取的名義通常對法律行為的定性而言無足輕重。〔43〕參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6)京民終175 號民事判決書。其明確指出:“合同的性質(zhì)應(yīng)根據(jù)當(dāng)事人約定的合同內(nèi)容予以確定,合同名稱一般不影響合同性質(zhì)的認定。”但在司法實踐中,解釋者并非在所有情形下都能夠排除合同名義帶來的干擾,徑自依據(jù)法律行為的內(nèi)容對該行為進行定性,尤其是在臨界情形下,當(dāng)?shù)湫头尚袨橹g的界限自身不明時,當(dāng)事人選取的合同名義便可能重新具備了意義與價值。
例如,對于買賣合同與承攬合同而言,在通常情形下二者的界限是清晰的。買賣合同是“出賣人轉(zhuǎn)移標的物的所有權(quán)于買受人,買受人支付價款的合同”(《民法典》第595 條),而承攬合同是“承攬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支付報酬的合同”(《民法典》第770 條)。但是當(dāng)承攬合同中的“定作合同”與買賣合同中“預(yù)先訂貨的買賣合同”遭遇時,二者特征上的相似性便會導(dǎo)致定性上的疑難。所謂定作合同,指的是“承攬人根據(jù)定作人的要求,以自己的技能、設(shè)備和勞力,用自己的材料為定作人制作成品,定作人接受該特別制作的成品并支付報酬的合同”。例如家具、服裝的定制均屬此類。〔44〕參見黃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釋義·合同編》,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1421 頁。定作合同的特征在于制作標的物的材料由承攬人提供,與之相對的是加工合同,在加工合同中制作標的物的材料由定作人提供。而預(yù)先訂貨的買賣合同則是買賣雙方在標的物生產(chǎn)出來之前便約定賣方生產(chǎn)標的物并交付給買方,買方支付價款的合同。這兩類合同在特征上具有極高的相似度,因為二者均是一方當(dāng)事人應(yīng)另一方當(dāng)事人的要求生產(chǎn)(制作)標的物(成品)的合同,材料均由生產(chǎn)方自備,而且兩類合同中當(dāng)事人提出的要求可能都是“特殊要求”,從而導(dǎo)致標的物成為僅能供買受人(定作人)使用的專用產(chǎn)品。這就使得用以區(qū)分買賣合同與承攬合同的通常標準陷入“失靈”的尷尬境地。
然而,買賣合同與承攬合同的不同定性會在法律適用上造成重大差別。根據(jù)《民法典》第787 條,定作人在承攬人完成工作前可以隨時解除合同,而買賣合同中的買受人則不享有任意解除權(quán)。〔45〕被定性為承攬合同從而肯定任意解除權(quán)的例子,可參見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2013)渝高法民終字第00112 號民事判決書。針對此類情形,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貫徹實施工作領(lǐng)導(dǎo)小組主編的民法典合同編釋義書雖然依舊在原則上堅持內(nèi)容決定論的基本立場,但也同時指出在依據(jù)合同約定的權(quán)利義務(wù)內(nèi)容難以區(qū)分合同性質(zhì)時,則應(yīng)當(dāng)參照合同名義以及當(dāng)事人在合同中所使用的概念確定合同性質(zhì)。例如在當(dāng)事人使用“賒銷合同”等概念時,宜認定為買賣合同,而在其使用“定作合同”等概念時,宜認定為承攬合同。其理由在于:“之所以在此情況下不以合同的權(quán)利義務(wù)內(nèi)容定性,是因為從權(quán)利義務(wù)上不能作出判斷,無法探知當(dāng)事人的內(nèi)心真實意思,而合同所使用的概念才是當(dāng)事人真實意思的流露。”〔46〕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貫徹實施工作領(lǐng)導(dǎo)小組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 年版,第1806 頁。
因此,盡管單純的名義指稱通常對于法律行為定性而言并無價值,但是當(dāng)法院依據(jù)合同內(nèi)容無法確定合同性質(zhì)時,當(dāng)事人在合同中所使用的表達,甚至當(dāng)事人為合同選取的名義便可能成為當(dāng)事人真實意思的一種體現(xiàn),從而在合同的定性中發(fā)揮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時并非越過合同的內(nèi)容直接以名義對合同進行定性,而是在窮盡了對合同內(nèi)容的考察之后,不得已才將合同的“名義”作為查明當(dāng)事人真實意思的最終標準。
三、意思表示解釋中“目的”的意義
(一)“唯目的論”解釋的原則性否定
在裁判者對意思表示進行規(guī)范解釋時,因為需要考量的要素紛繁復(fù)雜,所以經(jīng)常采用的處理方式便是通過“名為……實為”的論斷直指當(dāng)事人訂立法律行為的目的或當(dāng)事人意圖借助該法律行為實現(xiàn)的經(jīng)濟效果,在探明當(dāng)事人目的之后,便可以排除紛繁的法律行為具體內(nèi)容的干擾,直接對該法律行為適用與當(dāng)事人目的相應(yīng)的法律規(guī)則。這樣一種越過手段直接考察目的的定性方式實際上強烈觸及了當(dāng)事人意思自治的領(lǐng)域,很容易對當(dāng)事人選擇不同形式組織自身私法生活的自由形成不當(dāng)壓制。因為在唯目的論的視角下,法律行為的內(nèi)容就不再是最重要的,當(dāng)事人意圖實現(xiàn)哪種典型法律行為的經(jīng)濟效果成為判斷其性質(zhì)的實質(zhì)標準。這使得當(dāng)事人只能老老實實地按照法律明文規(guī)定的典型行為所設(shè)定的“手段/目的”關(guān)系安排自己的私法生活,而無法在經(jīng)濟形式上作出有意義的創(chuàng)新。因此,必須慎重對待法律行為內(nèi)容與目的之間的關(guān)系,不應(yīng)輕易地對法律行為作出純粹目的論視角下的“穿透式”定性。
1.法律行為當(dāng)事人的構(gòu)造自由
法不禁止皆自由的基本原則意味著當(dāng)事人的法律行為雖然受到法律禁令的限制,但當(dāng)事人的自由也只受法律禁令的限制,“若不違反否定性規(guī)則,即聽?wèi){行為人完全自由,任其安排自己的生活、處理自己的事務(wù)、追求自己的利益”。〔47〕易軍:《“法不禁止皆自由”的私法精義》,載《中國社會科學(xué)》2014 年第4 期,第122 頁。這一原則需要通過當(dāng)事人自由訂立法律行為并自由安排法律行為的內(nèi)容得以實現(xiàn),前者被稱為“設(shè)立自由”(Begründungsfreiheit),后者則被稱為“構(gòu)造自由”(Gestaltungsfreiheit)或“內(nèi)容自由”(Inhaltsfreiheit),從內(nèi)容自由之中可以進而衍生出所謂“類型自由”(Typenfreiheit)的概念,即當(dāng)事人可以自行選擇法律行為的類型,無論該類型是否為法律所明文規(guī)定的典型。〔48〕Vgl. MüKoBGB/Busche, 2018, BGB Vorbemerkung (Vor. § 145), Rn. 24.盡管在諸如物權(quán)、婚姻、繼承等領(lǐng)域,當(dāng)事人訂立法律行為或多或少會受到類型強制(Typenzwang)的限制,但至少在合同領(lǐng)域,當(dāng)事人在極高程度上享有類型自由,法律對有名合同的規(guī)定并不意味著當(dāng)事人無法訂立有名合同之外的非典型性合同。〔49〕Vgl. Musielak, Vertragsfreiheit und ihre Grenzen, JuS 2017, 949, 952.當(dāng)事人既可以在典型合同類型的基礎(chǔ)上修修補補,也可以干脆自己創(chuàng)設(shè)新的合同類型。正因為如此,實踐中產(chǎn)生了大量的非典型合同及混合合同,它們的內(nèi)容、效力以及在定性問題上的獨立性同樣得到了法律的認可。在當(dāng)事人與裁判者的關(guān)系中,裁判者應(yīng)當(dāng)充分尊重當(dāng)事人的意思自治,不能輕易以自己的意思代替當(dāng)事人的意思;在不違背法律的強制性規(guī)定與公序良俗原則的前提下,當(dāng)事人既可以自由選擇通過法律行為所意圖實現(xiàn)的法律效果,也可以自由選擇欲通過何種手段實現(xiàn)該效果。
例如,在現(xiàn)行法下,被繼承人可能通過訂立“贈與合同”規(guī)避《民法典》繼承編關(guān)于遺囑必留份的規(guī)定。《民法典》第1141 條規(guī)定:“遺囑應(yīng)當(dāng)為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繼承人保留必要的遺產(chǎn)份額。”根據(jù)該條規(guī)定,如果被繼承人試圖通過遺囑剝奪一個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法定繼承人的繼承權(quán),那么此種意圖是無法完全實現(xiàn)的。〔50〕類似嘗試參見江蘇省南京市秦淮區(qū)人民法院(2006)秦民一初字第14 號民事判決書。但如果其選擇通過贈與合同的方式,在生前處分自己的財產(chǎn),便可以成功規(guī)避《民法典》第1141 條的規(guī)定。〔51〕該漏洞并非不存在,例如《德國民法典》第2301 條便針對贈與和遺囑之間的轉(zhuǎn)換作出了強行規(guī)定:“(1)關(guān)于死因處分的規(guī)定,適用于以受贈人在贈與人之后死亡為條件而作出的贈與約定。以贈與方式按這一條件作出的……債務(wù)約定與債務(wù)承認,亦同。(2)贈與人通過給付所給予的標的完成贈與的,適用關(guān)于生前贈與的規(guī)定。”面對此種規(guī)避行為,裁判者往往處于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面,對當(dāng)事人意思的完全尊重可能導(dǎo)致其利用法律漏洞造成個案中的不公結(jié)果;另一方面,如果直接從當(dāng)事人的目的出發(fā),要求該目的或法律行為的最終效果在所有觀察視角上均具備正當(dāng)性,又實際上抹殺了當(dāng)事人通過不同性質(zhì)的法律行為組織自身私法生活的自由。法律針對贈與和遺囑施加了不同的限制,如果僅因二者在現(xiàn)實中可能達成同樣的經(jīng)濟效果、滿足當(dāng)事人同樣的需求,就要求它們同時滿足彼此特有的限制條件,那么法律規(guī)定兩種“不同”性質(zhì)的法律行為就失去了意義,對不同性質(zhì)的法律行為施以差異化的限制條件也就失去了意義。
又如,父母要將房產(chǎn)轉(zhuǎn)讓給自己的子女,那么選擇買賣、贈與或遺囑繼承的方式,都屬于當(dāng)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疇,只不過當(dāng)事人在針對特定形式作出選擇之后,便也需要受到相應(yīng)法律規(guī)范的規(guī)制。在父母轉(zhuǎn)讓房產(chǎn)給自己子女的情形中,當(dāng)事人通過不同形式轉(zhuǎn)讓房產(chǎn)所需要繳納的稅費有所不同,如果當(dāng)事人選取遺囑的方式,那么訂立遺囑時還需要特別注意《民法典》繼承編對遺囑在法定形式(《民法典》第1134 條以下)與必留份(《民法典》第1141 條)等方面的限制。盡管上述法律行為實質(zhì)上可能指向同一目標,即以盡可能低的成本完成房產(chǎn)的轉(zhuǎn)讓,但并不意味著在這一目標之下,無論當(dāng)事人選擇何種具體的法律行為,都要受到同樣規(guī)范的規(guī)制。當(dāng)事人對不同法律行為的選擇,同時也意味著對相應(yīng)法律規(guī)范的選擇,在沒有特別理由的情況下,法院不應(yīng)以當(dāng)事人的最終目的輕易否定其對法律行為類型作出的選擇。而是應(yīng)當(dāng)從其他法學(xué)方法中尋求可能的應(yīng)對方案,同時也應(yīng)受到相應(yīng)法學(xué)方法適用條件的限制以避免司法的恣意。
因此,對法律行為的定性不能唯目的論,而應(yīng)當(dāng)立足于法律行為的內(nèi)容本身,借助法律行為解釋的基本規(guī)則,在充分尊重當(dāng)事人真實意思的基礎(chǔ)上判斷法律行為的真實性質(zhì)。這種性質(zhì)既非源自裁判者的主觀認定,亦非源自法律規(guī)制的便捷需要,而是源自基于當(dāng)事人真實意思所形成的法律行為的客觀構(gòu)造(內(nèi)容)。如果輕率地以當(dāng)事人的目的或法律行為的客觀經(jīng)濟效果給法律行為定性,則很容易壓制市場經(jīng)濟活動中主體的能動性和創(chuàng)造力,因為人們不知道自己所創(chuàng)造出的新的交易形式是否會被強行“對號入座”到既有的法律模型之中,從而在法律上徹底扼殺新的交易形式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簡而言之,在意思表示解釋規(guī)則之下,盡管當(dāng)事人不能“指鹿為馬”,例如不能強行將借款稱為投資而規(guī)避有關(guān)借款的法律規(guī)范,但享有選擇“鹿”或“馬”的自由,例如父母可以自由選擇通過買賣、贈與或遺囑等形式將房產(chǎn)移轉(zhuǎn)給自己的子女,并受到相應(yīng)的法律規(guī)制,承擔(dān)相應(yīng)的法律后果。
2.對濫用構(gòu)造自由的外部限制
盡管當(dāng)事人原則上享有法律行為的構(gòu)造自由,可以自由選擇通過不同構(gòu)造的法律行為實現(xiàn)特定的經(jīng)濟目的,但是如果此種選擇違背了強制性規(guī)范的規(guī)范目的,便可能形成對構(gòu)造自由的濫用(Gestaltungsmissbrauch),從而受到來自意思表示解釋理論外部的限制。〔52〕Vgl. MüKoBGB/Müller-Gl?ge, 2020, BGB § 613a Rn. 199.之所以是“外部”限制,是因為濫用構(gòu)造自由進行法律規(guī)避的后果并非導(dǎo)致法律行為的性質(zhì)發(fā)生變化,而是導(dǎo)致被規(guī)避的法律規(guī)范的直接適用或類推適用。換言之,在此種情形下,解釋者不應(yīng)簡單地對法律行為作出“穿透式”的定性,而是應(yīng)當(dāng)承認法律行為構(gòu)造上的特殊性,但須依據(jù)被規(guī)避的法律規(guī)范對該法律行為進行“同等對待”。〔53〕關(guān)于法律規(guī)避的討論參見張新:《論民法視域中的法律規(guī)避行為——以“民生華懋案”為例》,載《華東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2019 年第3 期,第90 頁;張新:《私法中法律規(guī)避的概念與本質(zhì)——兼論我國民法典編纂中的立法取舍》,載《江漢學(xué)術(shù)》2019 年第3 期,第13 頁。
在有些情形下,法律可能針對當(dāng)事人濫用構(gòu)造自由的情形作出明文限制。例如《德國民法典》第306a 條便明確規(guī)定:“即便本章的規(guī)定被以另外的構(gòu)造方式規(guī)避,它們也予以適用。”該條所指乃《德國民法典》關(guān)于格式條款的規(guī)定。類似的法律以明文規(guī)定不能被規(guī)避的條款主要出現(xiàn)在消費者保護領(lǐng)域,如《德國民法典》第312k 條規(guī)定了該章關(guān)于消費者保護的特殊條款:“以不另有約定為限,即使本目的規(guī)定被以另外的構(gòu)造方式規(guī)避,它們也予以適用。”此時,裁判者可以直接適用相應(yīng)規(guī)范,使當(dāng)事人規(guī)避法律的目的落空。
即便法條并未明文規(guī)定其不可被規(guī)避,裁判者亦可依據(jù)法律的規(guī)范目的對規(guī)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判斷,在當(dāng)事人的規(guī)避行為與法律的規(guī)范目的相悖時,類推適用相應(yīng)規(guī)范。〔54〕Vgl. MüKoBGB/Wendehorst, 2019, BGB § 312k Rn. 10-15.例如司法解釋對民間借貸利率的限制規(guī)定便屬于不可被規(guī)避的條款。《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法釋〔2020〕17 號)第25 條規(guī)定:“出借人請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約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應(yīng)予支持,但是雙方約定的利率超過合同成立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的除外。”盡管這一規(guī)定從文義上看僅針對民間借貸案件適用,而對于買賣、投資、合作等其他類型的協(xié)議不具有約束力,但從規(guī)范目的角度觀察,無論當(dāng)事人之間采取何種交易形式,只要最后呈現(xiàn)的經(jīng)濟結(jié)果表現(xiàn)為“一方提供資金,只是收取固定數(shù)額的回報,卻并不承擔(dān)經(jīng)營風(fēng)險”,便屬于該規(guī)范意圖調(diào)整的范疇。因此,即便借助法律行為定性規(guī)則無法將該法律行為定性為“借款合同”,也依舊存在將該規(guī)范類推適用的可能。
實踐中的此類問題經(jīng)常與虛假法律行為交織在一起,使得此種情形下法律行為的“名”“實”關(guān)系愈發(fā)復(fù)雜難辨。虛假法律行為實際上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名”“實”分離問題,因為當(dāng)事人不但有意識地選擇了不能代表其真實意思的指稱,而且也沒有真實執(zhí)行錯誤指稱所代表的法律行為內(nèi)容的意圖,只是在表面存在的法律行為之外另行訂立了獨立的法律行為并意圖使該法律行為發(fā)生效力。盡管從一般的語言習(xí)慣上看,法律行為名不副實的問題似乎同樣出現(xiàn)在虛假法律行為之中,即以表面行為為名,以隱藏行為為實,但如果對表面行為與隱藏行為進行單獨考察,二者的性質(zhì)都是清晰的。例如在“名為買賣,實為贈與”的情況下,合同雙方當(dāng)事人表面上訂立的法律行為性質(zhì)為買賣合同,實際上暗中實施的法律行為的性質(zhì)為贈與,在單個法律行為定性上并無疑難。〔55〕參見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16)京03 民終7576 號民事判決書。在虛假法律行為中,隱藏行為作為獨立的法律行為,與表面行為在本質(zhì)上不存在同一法律行為的“名”“實”關(guān)系,而是基于外在事務(wù)產(chǎn)生聯(lián)系的兩個獨立的法律行為。這一聯(lián)系停留在法律行為當(dāng)事人的動機層面,既非導(dǎo)致表面行為無效的原因,更不應(yīng)成為法院為表面行為定性的直接依據(jù)。
虛假法律行為的實質(zhì)功能并非對法律行為名不副實的現(xiàn)象施以外部的矯治,而是基于法律行為當(dāng)事人的意思自治,允許其自主決定是否令相關(guān)的表達發(fā)生意思表示的效力從而達到訂立法律行為的目的。《民法典》第146 條第1 款否定了虛假法律行為的效力,使之陷入無效的境地之中,但此種否定并非對當(dāng)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虛假法律行為之所以無效,是因為雙方當(dāng)事人一致同意該法律行為不發(fā)生效力,體現(xiàn)的是私人自治的消極側(cè)面,即當(dāng)事人自主決定不受哪些行為約束的自由;而隱藏行為在不違背法律強制性規(guī)定和公序良俗原則的情況下可以生效,則體現(xiàn)了私人自治的積極側(cè)面,法律依然尊重當(dāng)事人在法律規(guī)定的框架內(nèi)以真實意思建構(gòu)與自身相關(guān)的法律關(guān)系的自由。〔56〕Vgl. Staudinger/Singer, 2011, BGB § 117 Rn. 1.在此意義上,虛假法律行為的無效與法律行為因違背法律強制性規(guī)定或公序良俗原則而無效的情形存在本質(zhì)的不同。
因此,虛假法律行為制度中的核心議題并非法律行為的名不副實,而是當(dāng)事人在訂立表面行為時是否具備法律拘束意思。如果當(dāng)事人在訂立表面行為時具備法律拘束意思,則該行為是法律行為,可以產(chǎn)生法律約束力;但如果當(dāng)事人在訂立表面行為時不具備法律拘束意思,則其表示根本不是意思表示,也就無從成立法律行為。〔57〕關(guān)于法律拘束意思,參見于程遠:《論先合同信息風(fēng)險分配的體系表達》,載《環(huán)球法律評論》2020 年第6 期,第58 頁。法律拘束意思的判斷并非單純基于對該法律行為內(nèi)容的解釋,法院需要結(jié)合全部的客觀情況探究當(dāng)事人在訂立該法律行為時的法律拘束意思。〔58〕參見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8)鄂民終984 號民事判決書。在實踐中,法院既可能通過法律行為本身的構(gòu)造、〔59〕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終133 號民事判決書。法律行為締結(jié)時的情況、〔60〕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終260 號民事裁定書。給付與對待給付的等價性〔61〕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113 號民事判決書。以及交易習(xí)慣〔62〕參見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2018)渝民終269 號民事判決書。判斷法律行為的虛假性,也可能通過法律行為的實際履行情況反推當(dāng)事人是否具有真實的受該行為法律效果約束的意思。〔63〕參見廣西壯族自治區(qū)來賓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桂13 民終954 號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209 號審查與審判監(jiān)督行政裁定書。如果可以確定當(dāng)事人在進行某法律行為時不具有法律拘束意思,則根本不存在對其進行“名為……實為”認定的空間,而應(yīng)直接依據(jù)《民法典》第146 條第1 款判定其無效。此種無效的宣告并非對當(dāng)事人意思自治的干預(yù),而恰恰是尊重了當(dāng)事人“不使該法律行為生效”的意思。
(二)例外情形下的目的論解釋
1. 法律明文授權(quán)下的目的論解釋
法律行為的定性原則上應(yīng)當(dāng)立足于法律行為的內(nèi)容而非目的,但在法律明文授權(quán)的情形下,目的論視角下的法律行為定性路徑也可能例外地存在適用的空間。
例如,《民法典》第388 條第1 款規(guī)定:“設(shè)立擔(dān)保物權(quán),應(yīng)當(dāng)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guī)定訂立擔(dān)保合同。擔(dān)保合同包括抵押合同、質(zhì)押合同和其他具有擔(dān)保功能的合同。擔(dān)保合同是主債權(quán)債務(wù)合同的從合同。主債權(quán)債務(wù)合同無效的,擔(dān)保合同無效,但是法律另有規(guī)定的除外。”此條規(guī)定將“其他具有擔(dān)保功能的合同”納入擔(dān)保合同的范疇,采取了功能主義的定性方式,在法律行為解釋規(guī)則的框架內(nèi)直接排除了當(dāng)事人通過其他具體構(gòu)造規(guī)避擔(dān)保合同相應(yīng)限制的可能。只要該合同具有擔(dān)保功能,便有可能落入《民法典》第388 條第1 款第2 句規(guī)定的“擔(dān)保合同”的范疇,從而直接適用《民法典》物權(quán)編有關(guān)擔(dān)保合同的規(guī)定。這是法律以明文對裁判者進行授權(quán),使后者得以在更廣泛的范圍內(nèi)對當(dāng)事人的私人自治進行干涉,此時無論當(dāng)事人對其合同如何命名甚至如何構(gòu)造,都不能逃脫擔(dān)保合同的定性。
在沒有法律明確授權(quán)的情形下,目的論的考察方式不能普遍適用于所有法律行為的定性,而法律明確規(guī)定的僅為少數(shù)情形,在大多數(shù)情形下,法院依舊應(yīng)當(dāng)堅持以法律行為的內(nèi)容作為法律行為定性的核心標準。《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涉及國有土地使用權(quán)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法釋〔2020〕17 號,以下簡稱《國有土地使用權(quán)合同司法解釋》)第12 條規(guī)定:“本解釋所稱的合作開發(fā)房地產(chǎn)合同,是指當(dāng)事人訂立的以提供出讓土地使用權(quán)、資金等作為共同投資,共享利潤、共擔(dān)風(fēng)險合作開發(fā)房地產(chǎn)為基本內(nèi)容的合同。”這意味著所謂“合作開發(fā)協(xié)議”必須以“共同投資、共享利潤、共擔(dān)風(fēng)險”為內(nèi)容。如果當(dāng)事人訂立的所謂“合作協(xié)議”沒有約定共擔(dān)風(fēng)險的內(nèi)容,而是一方當(dāng)事人提供資金并收取固定數(shù)額回報,此時實質(zhì)上形成的是借款關(guān)系。這不是由當(dāng)事人的目的決定的,而是由雙方的權(quán)利義務(wù)內(nèi)容決定的。可能雙方確實想要如此投資,即一方投入金錢,享有固定收益,不承擔(dān)任何風(fēng)險,但這一關(guān)系在法律上的評價并非投資而是借貸,〔64〕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終1374 號民事判決書。后者則需要受到相應(yīng)的利率限制。在此類案件中,法院無須考察當(dāng)事人的真實目的究竟是投資還是借貸,而是應(yīng)當(dāng)從其法律行為的具體構(gòu)造出發(fā),考察合同雙方約定的給付與對待給付的具體內(nèi)容,并以此為依據(jù)對合同進行定性。〔65〕在此意義上,《國有土地使用權(quán)合同司法解釋》第21 條至第24 條以一系列定性規(guī)范為法律行為的區(qū)分定性作出了正面的示范。此處的“具體內(nèi)容”指的是當(dāng)事人在合同條款中約定的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的實際構(gòu)造,而非當(dāng)事人依據(jù)合同條款履行后可能達成的經(jīng)濟效果,而當(dāng)權(quán)利義務(wù)的具體構(gòu)造發(fā)生變化,導(dǎo)致該法律行為在內(nèi)容上不符合借款合同的特征時,即便當(dāng)事人內(nèi)心存有融資的動機,也不能將其認定為借款合同。通過不同的權(quán)利義務(wù)構(gòu)造實現(xiàn)同樣的經(jīng)濟目的,這是法律賦予法律行為當(dāng)事人的自由,解釋者依據(jù)意思表示解釋理論對法律行為進行定性,其實質(zhì)是將具體的權(quán)利義務(wù)構(gòu)造評價為某種法律關(guān)系從而正確適用法律。至于法律是否允許當(dāng)事人通過所選取的手段實現(xiàn)其背后隱藏的經(jīng)濟目的,通常而言不屬于意思表示解釋規(guī)則能夠評價的范疇。
2. 特定法律行為自身性質(zhì)要求的“目的論”解釋
在某些情形下,法律行為自身的性質(zhì)可能具有特殊性,從而要求解釋者在確定其性質(zhì)時更多地甚至主要對當(dāng)事人的內(nèi)在目的進行考量,此時可能成立一種非典型意義上的目的論解釋。之所以稱其為“非典型意義上”的目的論解釋,是因為此類情形下意思表示的內(nèi)容并非不重要,然而即便解釋者依據(jù)意思表示解釋的基本規(guī)則探明了該法律行為中的權(quán)利義務(wù)設(shè)置,也同樣無法對其進行定性,造成這一困難的原因并非在于意思表示含義的不明,而是在于該法律行為自身構(gòu)造的特殊性。
例如,對于混合贈與的定性而言,當(dāng)事人的目的便可能起到最終的決定性作用。混合贈與屬于一種形式上的有償合同,但其給付與對待給付之間的價值并不對等,而合同雙方對于給付與對待給付在價值上的不對等是明知的。〔66〕Vgl. Soko?owski, Die modale Schenkung als eine gemischte Schenkung nach deutschem und europ?ischem bürgerlichem Recht,BWNotZ 2013, S. 162.由此引發(fā)的問題是,對于這樣一種合同,究竟應(yīng)該適用有償合同(例如買賣、互易等)的相關(guān)規(guī)定,還是適用贈與合同的相關(guān)規(guī)定。盡管從原則上看,根據(jù)主觀等價性原理,合同一方當(dāng)事人可以就自身給付與對方當(dāng)事人約定客觀價值完全不相稱的對待給付,這并不會直接影響該合同被認定為有償合同。但只要合同雙方當(dāng)事人明知給付與對待給付在客觀價值上的不對等并且對于該價值差額部分的讓與形成合意,那么此種合意便至少部分具有了贈與的性質(zhì)。〔67〕Vgl. MüKoBGB/Koch, 2019, BGB § 516 Rn. 34.對于混合贈與的定性以及法律適用問題,德國法曾在“統(tǒng)一說”(Einheitstheorie)與“區(qū)分說”(Trennungstheorie)之間徘徊。〔68〕相關(guān)介紹參見MüKoBGB/Koch, 2019, BGB § 516 Rn. 37.而如今的通說則采所謂“目的評價說”(Zweckwürdigungstheorie),認為在此種情形下應(yīng)當(dāng)放棄此前對混合贈與進行統(tǒng)一定性的嘗試,而在個案中適用最符合法律行為目的或當(dāng)事人意愿的法律規(guī)范。〔69〕Vgl. Dellios, Zur Pr?zisierung der Rechtsfindungsmethode bei ?gemischten“ Vertr?gen, 1981, S. 118 ff.盡管解釋者從形式上依舊是按照意思表示解釋理論的相關(guān)規(guī)則對法律行為作出定性,但該法律行為的特點自始就決定了在諸多考量因素中“目的”會起到最終的決定性作用。
四、結(jié)論
法律行為定性的根本任務(wù)在于確定該法律行為在法教義學(xué)上的歸屬類別,從而正確適用相應(yīng)的法律規(guī)范。從本質(zhì)上看,這一過程屬于意思表示解釋理論承擔(dān)的任務(wù),解釋者需要確定當(dāng)事人作出意思表示的內(nèi)容,通過其內(nèi)容確定法律行為的歸屬類別。對意思表示內(nèi)容的確定不僅表現(xiàn)為對事實的查明,更表現(xiàn)為解釋者對該行為作出的法律評價。依據(jù)《民法典》第142 條之規(guī)定,意思表示的解釋方法因該意思表示有無相對人而有所不同,然而無論是無相對人的意思表示還是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其解釋實際上都遵循所謂“經(jīng)驗/規(guī)范”的二元方法體系,這意味著當(dāng)事人可以確定的真實意思(合意)總是優(yōu)先于其表達得到法律的認可。在對意思表示進行規(guī)范解釋時,解釋者并非被絕對束縛于意思表示的語義,其需要結(jié)合合同文本之外的、對意思表示受領(lǐng)人而言可獲知的全部情勢加以判斷。除了意思表示本身的文義之外,裁判者還需要綜合考量包括交易習(xí)慣、當(dāng)事人之間的利益狀態(tài),以及當(dāng)事人通過實施該法律行為所追求的經(jīng)濟目的在內(nèi)的諸多外在因素。這些外在因素盡管不能直接決定對意思表示內(nèi)容的理解,卻可以在對意思表示進行解釋的過程中起到輔助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規(guī)范解釋對所有因素的綜合考量不應(yīng)導(dǎo)致意思表示解釋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完全忽略當(dāng)事人的明確表達。
在依據(jù)意思表示解釋規(guī)則對法律行為作出“名為……實為”的論斷時,不僅需要考察名義上該法律行為指稱是否錯誤,還需要考察實際上該法律行為是否具備另一法律行為的特征。在特定情形下,法律明文設(shè)置的特別解釋規(guī)范也可能對解釋者的解釋結(jié)論產(chǎn)生直接影響。基于意思自治原則賦予法律行為當(dāng)事人的構(gòu)造自由,原則上應(yīng)當(dāng)對唯目的論的定性方式加以否定。因為在唯目的論的視角下,法律行為的內(nèi)容就不再是最重要的,當(dāng)事人意圖實現(xiàn)哪種典型法律行為的經(jīng)濟效果成為判斷其性質(zhì)的實質(zhì)標準。這使得當(dāng)事人只能老老實實地按照法律明文規(guī)定的典型行為所設(shè)定的“手段/目的”關(guān)系安排自己的私法生活,而無法作出有意義的創(chuàng)新。但在兩種情形下,解釋者的目的論解釋可以獲得正當(dāng)性,即法律明確授權(quán)如此的情形以及特定法律行為自身性質(zhì)導(dǎo)致目的論解釋為必要的情形。
總而言之,法律行為定性過程中的“名”“實”關(guān)系在本質(zhì)上并非單純的二元結(jié)構(gòu),而是“名義指稱”“內(nèi)容構(gòu)造”與“當(dāng)事人目的”的三層次結(jié)構(gòu)。在這三者之間,名義指稱在絕大多數(shù)情形下無意義,內(nèi)容構(gòu)造通常對法律行為的定性起決定性作用,當(dāng)事人目的通常僅為意思表示解釋的參考要素,僅在例外情形下可以對法律行為定性起決定性作用。意思表示解釋理論的評價功能原則上僅限于為特定內(nèi)容的法律行為尋找相應(yīng)法律規(guī)范的范疇,對于法律行為當(dāng)事人濫用構(gòu)造自由規(guī)避法律以實現(xiàn)非法目的的情形,裁判者不應(yīng)僅從規(guī)制的需求出發(fā),強行扭轉(zhuǎn)法律行為定性以適用法律,而是需要借助意思表示解釋理論外部的制度和方法加以限制,例如對強制性規(guī)范的類推適用。法律行為的定性應(yīng)該被嚴格限制在意思表示解釋理論的框架之內(nèi),區(qū)分真正意義上的法律行為“名”“實”關(guān)系和僅存在于當(dāng)事人動機層面的“名”“實”關(guān)系。例如,在虛假法律行為中通常不存在法律行為定性的疑難,因為無論表面行為還是隱藏行為的性質(zhì)通常而言都是清晰的。此時裁判者的主要任務(wù)是判斷表面行為的虛假性,并對隱藏行為的效力作單獨判斷,而不能簡單地以“名為……實為”的論斷扭轉(zhuǎn)表面行為的定性,因為其背后蘊含的法律問題是異質(zh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