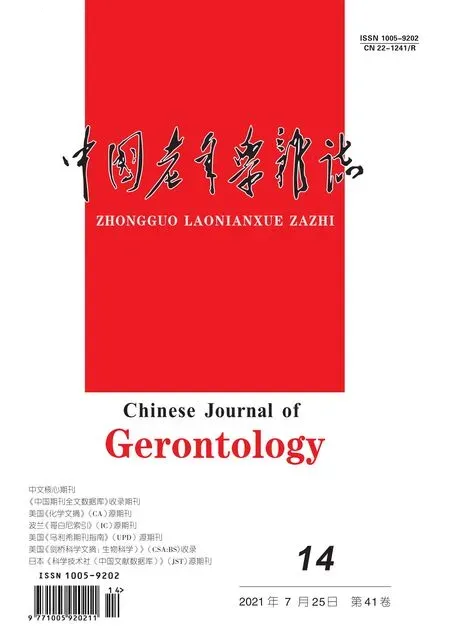老年髖部骨折患者術后下肢抬高方式與下肢深靜脈血栓的相關性
魏巍 吳國志 陳榮
(海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骨科,海南 海口 570311)
下肢深靜脈血栓(DVT)由于凝血功能異常,血小板、纖維蛋白原、紅細胞等血液有效成分在深靜脈腔內非正常凝結,且相較于上肢深靜脈血栓,DVT的發生率較高〔1〕。深靜脈血栓形成之后,其栓子脫落入血,伴隨血液循環到達身體各部位,誘發栓塞,其中尤以肺栓塞(PE)較多見,且病情兇險〔2〕。PE是DVT導致的較為嚴重的并發癥之一,也是導致臨床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病情隱匿、進展迅速、死亡率高〔3〕。臨床中諸多患者在原發疾病得到有效控制或排除威脅生命安全的情況下,突然發生劇烈胸痛、咳嗽、咯血,嚴重者出現心搏驟停、猝死,其最終死因分析結果常見為PE。諸多栓子來源于DVT,主要有空氣、脂肪、血栓、骨髓等,DVT形成后,導致肺動脈堵塞,誘發肺循環障礙;血栓脫落除誘發PE外,還可導致機體出現淺靜脈曲張、間歇性跛行、難愈性潰瘍等并發癥,極大降低患者的生活質量,甚至威脅患者生命安全〔4〕。老年髖部骨折是臨床骨科常見的疾病之一,針對該部位的骨折治療手段已相對成熟,但對于老年患者而言,其身體各功能呈不斷下降趨勢,術后并發癥相對較多,尤以深靜脈血栓較多見,嚴重降低手術效果,導致不良預后、致殘,威脅生命安全〔5〕。本研究通過探討老年髖部骨折患者術后采取不同下肢抬高方式,分析其發生DVT的情況。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海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骨科收治的105例老年髖部骨折患者的臨床資料,將采取“斜坡臥位”的33例患者納入A組;采取“三角臥位”的35例患者納入B組;采取“梯形臥位”的37例患者納入C組。3組一般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3組一般資料比較
1.2DVT診斷標準 根據中華醫學會外科學分會血管外科學組制定的《深靜脈血栓形成的診斷和治療指南(第三版)》〔6〕中相關診斷標準:癥狀:患肢疼痛、腫脹,活動后加重,患肢抬高時,癥狀好轉;體征:患肢遠端或整體出現腫脹,膚色正常或輕度淤血,嚴重者出現青紫;皮溫較正常肢體高,癥狀嚴重時皮溫偏低;當栓子堵塞動脈,肢體遠端捫不及動脈搏動或搏動減弱;若栓子堵塞小腿肌間動脈叢,病灶處壓痛明顯,查體Neuhof征與Homans征陽性;其中Neuhof征陽性:通過擠壓小腿腓腸肌與比目魚肌,小腿深部肌肉出現疼痛;Homans征陽性:受檢肢體伸直,踝關節背屈,比目魚肌與腓腸肌被動牽拉肌內病變靜脈,使其受到刺激,誘發小腿深部肌肉出現疼痛。超聲多普勒檢查診斷:①探頭加壓法:檢查時,使探頭加壓,靜脈管腔無法被壓閉或部分壓閉;②血栓回聲法:靜脈血腔探查無回聲或低回聲;③彩色血流法:病灶處管腔內未見彩色血流消失或充盈缺損;④脈沖Dopplar法:脈沖多普勒顯示頻譜不隨呼吸變化或缺乏自主性血流。
1.3入選標準 納入標準:①臨床經X線或CT檢查確診為髖部骨折;②手術指征明顯;③手術過程順利,效果良好;④排除病理性骨折;⑤患者及家屬均知曉本次研究目的并自愿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①伴其他部位骨折,如腰椎骨折、股骨骨折等;②凝血功能異常者;③術前即伴DVT者;④伴神經損傷者;⑤既往伴下肢手術史、血管疾病史;⑥伴嚴重基礎代謝性疾病,如高血壓、糖尿病等。
1.4針對性治療及護理措施 所有患者術后均給予低分子肝素鈣治療:入院當天即給予0.3 ml低分子肝素鈣(深圳賽保爾生物藥業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60191)皮下注射,術前1 d暫停注射,術后24 h繼續給藥,持續治療2 w。此外,給予患者“斜坡位”“三角形位”“梯形位”下肢抬高方式指導。“斜坡位”:抬高床位,保證雙下肢直腿抬高,軀干與下肢夾角為30°;“三角形位”:膝下墊軟枕,通過調整軟枕高度,保持軀干與大腿夾角分別為30°;“梯形位”:抬高床尾,使軀干與大腿夾角為30°,小腿與軀干平行。
1.5深靜脈血栓超聲檢查方法 由臨床經驗豐富、資歷較高的影像醫師,采用GE Voluson 730 EXPERT型彩色多普勒超聲儀對所有患者進行檢查,檢查時,探頭與股總靜脈呈60°夾角,探頭頻率5.0~10.0 MHz。分別于術前、術后7~10 d雙下肢彩色多普勒超聲檢查,若住院過程中患者出現深靜脈血栓的相關癥狀,及時進行排查,準確探查深靜脈血栓的形成情況,明確是否發生血栓及其形成部位,根據加壓試驗及血管內腔是否顯影,確認和排除是否發生DVT。檢查方法:患者仰臥位,下肢外旋、外展位,采用縱切面與橫切面相結合,探查股總靜脈、髂靜脈,沿著血管走向向下依次探查股淺靜脈、股深靜脈,之后協助患者俯臥位,探查腘靜脈、脛前、脛后靜脈小腿肌間經靜脈與腓靜脈。
1.6評價指標 分析給予老年髖部骨折患者術后不同抬高方式護理時,患者發生DVT的情況。
1.7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3.0軟件進行t檢驗、χ2檢驗及單因素方差分析。
2 結 果
術后7~10 d B組發生DVT概率較高〔12例(34.29%)〕,A、C組較低〔3例(9.09%)、3例(8.11%)〕,3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0.277,P=0.006)。
3 討 論
老年患者常合并骨質疏松、行動能力下降,不慎跌倒或髖部受到輕微的外力作用時極易導致患者發生髖部骨折,針對髖部骨折,手術治療效果顯著,能夠顯著縮短患者臥床時間,減少致死率〔7〕。深靜脈血栓形成后,血栓脫落入血循環,到達顱內或肺部等重要臟器組織導致栓塞,威脅患者生命安全;老年患者因血管彈性下降,且合并諸多基礎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壓等,加重血管損傷程度,導致老年患者骨折術后發生DVT的風險增加〔8,9〕。對此,需增強患者對深靜脈血栓的認知,及時采取有效的預防措施,對防治DVT具有重要臨床價值。
隨著醫療技術的發展與完善,針對DVT的治療取得了極大進步,尤其是微創技術的發展,使臨床患者罹患PE的風險顯著降低,與此同時,也極大改善了已經發生血栓患者的預后,但目前針對該病仍缺乏系統性、規范性的治療,特別是當諸多患者臨床表現不明顯甚至缺乏時,無法及時有效診斷,增加了血栓脫落、蔓延的風險,因此針對DVT的早期預防尤為重要〔10~12〕。
靜脈內膜損傷、血液淤滯、血液高凝狀態均是導致DVT的危險因素,老年髖部骨折患者易發生靜脈血栓,其主要原因為:①骨折導致骨質破裂、壓縮,營養骨干的血管及血管內膜受到嚴重損傷;②血管內膜組織暴露,導致凝血酶原釋放增加,激活血漿凝血系統,促進血小板凝集,使血液處于高度凝集狀態;③創傷、疼痛、麻醉、術中操作等均會引起機體應激反應,導致血小板聚集誘導劑——腎上腺素含量增加,血小板敏感性及其聚集功能增強;④老年髖部骨折,術后需長期制動臥床,導致下肢深靜脈回流速度降低;⑤老年患者常合并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壓等基礎代謝性疾病,導致血流動力學異常,機體血管彈性降低,管壁硬化、斑塊形成等;此外,血小板功能異常,易增加紅細胞黏滯度,導致機體處于高凝狀態;⑥手術器械侵襲、置換的骨水泥髖關節發生熱聚合反應等均會加重血管內膜受損程度,增加深靜脈發生的風險〔13,14〕。由此可見,老年髖部骨折患者術后發生下肢深靜脈風險較其他人群均較高。龔曉峰〔15〕研究結果顯示,老年髖部骨折患者術前DVT風險發生率較高,因此術前均需對其進行篩查;且對術前等待時間較長,合并周圍血管疾病、腦血管病、高脂血癥等患者應特別警惕DVT的發生。
目前,術后預防深靜脈血栓治療的有效方法即為藥物治療與物理療法,藥物治療主要為低分子肝素鈣皮下注射,其為普通肝素的衍生物,在不需要抗凝血酶Ⅲ的輔助下,能夠選擇性抑制抗凝因子Xa發揮作用,其具有與血管內皮細胞、血漿蛋白、血細胞結合少、生物利用度高、抗血栓作用明顯等優點,但該藥長時間使用容易增加患者圍術期出血風險,因此術前常不推薦使用該藥治療〔16〕。盡管低分子肝素鈣已逐漸成為骨折患者術后防治下肢深靜脈的首選藥物,可以有效降低臨床發生DVT的發生率,但老年髖部骨折患者術后發生DVT的概率仍然較高。本研究結果顯示,術后常規給予患者低分子肝素鈣皮下注射,此外,指導正確下肢抬高方式,發現“斜坡位”、“梯形位”兩種下肢抬高方式能夠顯著降低老年髖部骨折患者術后發生靜脈血栓的風險,“三角形位”抬高方式對降低DVT的作用相對較小。究其原因為,“斜坡位”、“梯形位”兩種抬高方式能夠促進股總靜脈血液流速,因重力作用加速靜脈血液回流;“三角形位”抬高方式對降低DVT的作用相對較小,其可能原因有:①其僅能夠促進膝關節以上靜脈流速,因受重力作用影響,膝關節以下靜脈血液回流減慢;②膝下墊軟枕,抬高患肢,軟枕容易壓迫腘靜脈,造成靜脈回流受阻,此外,該種抬高方式無法增加股靜脈流速,再加上腘靜脈受壓,導致DVT風險升高〔17,18〕。鑒于此,臨床上應盡量避免“三角形位”下肢抬高方式。
綜上,老年髖部骨折患者術后及時采取“梯形位”與“斜坡位”,能夠有效促進下肢靜脈血流速,從而降低DVT的風險;“三角形位”抬高方式無法有效預防DVT,臨床應避免采取膝下墊軟枕的方式使患肢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