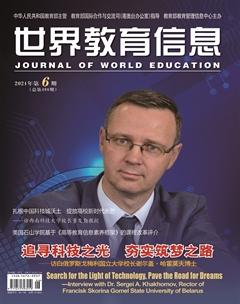以色列英語課程標準:內容、特征及啟示
程春松
摘? ?要:英語作為以色列的第一外語,有著與官方語言一樣的重要地位。以色列政府及教育部門十分重視英語教育,與時俱進地對英語課程標準進行修訂。通過對以色列現行中小學英語課程標準的內容分析發現:該課程標準體現了任務型語言教學大綱的特征、語言的實踐需求和信息時代的語言學習特點,注重吸收外語教育等相關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高階思維能力培養。這些特征對其他國家的英語課程標準制定和英語教育具有一定的啟示。
關鍵詞:以色列 英語課程標準 內容框架
以色列于1948年5月建國,地處地中海東南沿岸,總人口909.2萬,其中猶太人占74.4%(截至2019年9月)[1]。以色列是典型且較為特殊的移民國家,其官方語言是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在其國家語言體系中,英語擁有著獨特的地位,發揮著重要作用。雖然不是官方語言之一,卻在實際運用中有著與官方語言一樣重要的地位。英語不僅是國際交流的重要工具,也是以色列媒體、學術界、商界及公共領域主要使用的語言[2]。在中小學教育領域,英語被認為是以色列中小學生的“第一外語”,是“每個以色列人的第二語言”[3],是以色列所有學生從小學到中學階段的必修課程[4],是進入高等教育的“敲門磚”。以色列教育部十分重視英語教育,在全球范圍內招聘英語教師,在全國開展英語口語考試,頒布并且及時修訂英語課程標準。在英語教育過程中,課程標準發揮著重要作用,是英語課程開發、教學實施以及教學評價的指南。鑒于以色列政府和教育部門對英語教育的重視程度和英語在以色列國家語言體系中的重要地位,本研究從課程標準的產生與發展、核心內容、主要特征等角度對以色列中小學英語課程標準進行深入研究,以期為完善我國的英語教育和英語課程標準提供借鑒。
一、以色列英語課程標準發展歷程
以色列建國以后,中央集權的教育體制逐漸形成。由于對之前的英國統治存在仇視心理,一開始人們對英語學習的熱情不高。隨著英語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自1960年起,英語成為以色列五年級及以上學生的必修課,以文學教學為主[5]。當時以色列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與美國的聯系越來越緊密[6],以文學教學為主的英語教學受到語言教育專家的批評。因此,1968年頒布的英語課程標準發生了重大變化,英語教學開始注重語言的使用功能[7]。與其他課程標準一樣,英語課程標準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推廣,由當地英語教育官員對課程標準的實施進行監督。20世紀80年代,隨著英語在全球的推廣和交際教學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的興起,以色列對當時的英語課程標準進行了修訂。1988年,以色列教育部頒布了《公立學校和公立宗教學校五至十二年級英語課程標準》(English Curriculum for State Schools and State Religious Schools Grades 5—12)(以下簡稱《英語課程標準(1988)》)[8]。該課程標準指出:英語應作為一種國際性的“世界語言”來教授,以實際交流為目的,而不是為了文化融合[9]。與之前的課程標準相比,《英語課程標準(1988)》注重語言的實際交際功能,但仍屬于規定性課程標準,以綱要的形式規定課程教學的基本內容,并把語言習得局限于學校環境。
20世紀末,互聯網開始成為國際交流的重要工具,英語學習的網絡資源也越來越豐富。僅僅依托學校教育的傳統方式已經不能適應和滿足快速發展的社會對于熟練掌握英語人才的需求。2000年,以色列教育部頒布了《中小學英語課程標準:作為外語的英語學習原則和標準》(English Curriculum: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or Learn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for All Grades)(以下簡稱《英語課程標準(2000)》)。與《英語課程標準(1988)》相比,《英語課程標準(2000)》完成了從規定性標準到描述性標準的轉變[10],不再以綱要的形式規定中小學英語教學的基本內容,而是以描述性的話語描述學習目標,從社會交往(social interaction),信息獲取(access of information),陳述展示(presentation),以及語言、文學和文化欣賞(appreciation of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四個領域提出了中小學英語課程的目標[11],取代了以往聽、說、讀、寫四個方面的目標,以“能做某事”(can do)的方式描述語言能力。同時在課程目標上開始關注信息時代的語言學習需求,如在信息獲取領域的目標中將電子媒介的口頭和書面語考慮在內。
2013年,以色列教育部對英語課程標準進行了修訂,增加了詞匯語法列表、高階思維能力、整合信息交流技術的能力、文學教學的重要步驟等。同時考慮到英語作為國際通用語言的特征,以色列英語課程標準的名稱被改為《中小學英語課程標準:作為國際通用語言的英語學習原則和標準(修訂版)》(Revised English Curriculum: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or Learning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for All Grades,以下簡稱《英語課程標準(2013)》)[12]。2018年7月,以色列教育部再次修訂英語課程標準,頒布了現行的中小學英語課程標準《中小學英語課程標準:作為國際通用語言的英語學習原則和標準(修訂版,包含三級詞匯列表)》(Revised English Curriculum: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or Learning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for All Grades,Including Band III Lexis)(以下簡稱《英語課程標準(2018)》)[13]。與《英語課程標準(2013)》相比,《英語課程標準(2018)》名稱幾乎沒變,只是在內容上增加了熟練級詞匯列表。
二、以色列英語課程標準的內容框架
《英語課程標準(2018)》共有四部分內容:原則、課程總目標、分級目標和評價基準、教學建議。該課程標準首先根據外語學習、教育、評估,認知心理學,課程標準等研究領域的最新研究,提出有助于學習者英語學習的7個方面原則,為教師選擇教學材料、設計教學活動、開展教學評價等提供指導。在第二部分提出中小學英語課程的總目標,以及詞匯和語法的總體要求。在總目標的指引下,提出分級目標和每個分級目標下的評價基準(benchmarks),列出不同級別的核心詞匯表和語法知識內容。最后一部分是提供給教師和學校的具體的課程標準實施建議。
《英語課程標準(2018)》的核心內容是課程總目標、分級目標和評價基準。該課程標準將中小學生的英語水平分為三個等級:基礎級(Foundation Level)、中等級(Intermediate Level)和流利級(Proficiency Level)。基礎級是小學六年級畢業要達到的水平,中等級是初中九年級畢業要達到的水平,流利級是高中十二年級畢業要達到的水平。與總目標相比,分級目標更加具體,也呈現出層級性特征。以下是陳述展示領域的總目標和三個分級目標。
總目標:學習者能夠在印刷媒介和電子媒介中用英語進行口頭和書面觀點展示和信息陳述,思路清晰。
基礎級目標:學習者能夠就與個人有關的話題口頭或書面地組織和展示觀點和信息;能使用本級別所學的合適的詞匯和正確的語法。
中等級目標:學習者能夠就常見話題口頭或書面地組織和展示觀點和信息,語域和語篇類型符合交際目的和受眾需求;能使用本級別所學的合適的詞匯和正確的語法,并能使用話語標記(Discourse Marker)。
流利級目標:學習者能夠就廣泛的話題口頭或書面組織和展示觀點和信息,內容具有深度,語域和語篇類型符合交際目的和受眾需求;能夠使用本級別所學的合適的詞匯和正確的語法,并能廣泛使用話語標記。
從話題范圍來看,三個分級目標的話題從基礎級的“與個人有關的話題”拓展至中等級的“常見話題”,再到流利級的“廣泛話題”,話題逐漸擴大。對詞匯語法的要求也逐級提高。基礎級只要求學習者能使用本級別所學的合適的詞匯和正確的語法。中等級提出了語域、語篇類型和話語標記使用的要求。流利級在中等級的基礎上提出“內容有深度”,并能“廣泛使用話語標記”的要求。
該課程標準還在每個級別從四個領域提出了具體的評價基準。評價基準體系將每一個領域的二級目標分解成五個以上的評價基準。例如,基礎級社會交往領域的評價基準共有5個,分別是:能夠表達情感,如喜歡和不喜歡;能夠參與少量互動,如遵循基本的指示、要求和給出信息,提出和滿足簡單的要求;能夠參與簡短的對話或通過詢問的方式參與討論;能夠回答關于熟悉話題和日常情境的簡單問題;能夠創作或回復簡單的書面信息。與分級目標相比,評價基準更加具體,更加容易理解,而且可以被測量,所使用的動詞是表達、參與、詢問、回復、識別、鑒別、區分、歸納、描述等具體的詞匯。這樣能夠幫助教師更加準確地設定課堂教學目標,更好地開展課堂教學評價;幫助學生更好地評估自己的英語學習。
三、以色列英語課程標準的特征
與《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類似,《英語課程標準(2018)》以“能做某事”(can do)的方式描述語言能力,但是不同國家的課程標準具有不同的特征,《英語課程標準(2018)》也不例外,具有自己的獨特性。該課程標準體現了任務型教學大綱的特征,體現了對語言學習的現實需求,注重高階思維能力培養并展現出信息時代的語言學習特點。
(一)體現任務型教學大綱特征
語言教學課程標準(大綱)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結構教學大綱(structural syllabus)、情景教學大綱(situational syllabus)、主題性教學大綱(topical syllabus)、功能—意念教學大綱(functional-notional syllabus)、技能型教學大綱(skills-based syllabus)、任務型教學大綱(task-based syllabus)等不同的類型[14]。其中,任務型教學大綱基于以任務為主的教學思想。該類型的大綱并不描述學習者在完成課程的學習之后需要掌握的語言知識和語言技能,而是重點關注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應該操作或執行的任務[15]。任務型教學大綱不以詞匯或語法作為教學內容選擇的依據,也并非根據語言知識的難易程度確定教學內容的順序,而是羅列學習者在學習中應該執行或完成的多種任務,指導教師在教學活動中對任務進行設計,讓學生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學習和使用英語,通過任務來提升英語水平。
在《英語課程標準(2018)》中,無論是總目標、分級目標還是評價基準,均體現了任務型教學大綱的特征。例如,在社會交往領域,熟練級的評價基準包括:能夠表達思想和觀點,提供有深度的解釋;能夠使用適合語境、聽眾和交際目的的語言參與社會性或全球性話題的談話。這些評價基準的核心并非詞匯或語法,而是任務,不僅能夠使語言學習者更加明確語言的實際用途,而且有利于學習者鍛煉實際語言使用能力。《英語課程標準(2018)》為教師開展任務型教學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則:所有的任務都應該是有交際意義的,任務中要有需要通過語言來解決的問題,而且要同時關注形式和意義,教學材料要為有意義的語言交流創造機會。在真實的語言交際中,語言形式和意義同等重要,不存在只有形式沒有意義的交流,也不存在只有意義沒有形式的交流。該課程標準提出的關于“任務”的原則與應用語言學界提出的關于“任務”的特征一致,即任務要有交際意義[16],完成任務要涉及聽說讀寫其中的任何一項技能,要有真實世界的語言加工。[17]
(二)體現對語言學習的現實需求
《英語課程標準(2018)》強調語言與生活、文化的關系,以及語言學習的實踐性。社會交往,信息獲取,陳述展示,以及語言、文學和文化欣賞四個領域與學習者的日常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系。學習者不僅要學會使用英語進行社會交往,通過閱讀英語文章和聆聽他人話語獲取信息,使用英語展示自己的觀點和情感態度,還要學會欣賞語言的本質,欣賞英語文學作品,理解語言與文化之間的關系,理解語篇所處的歷史、社會和文化背景。
從語篇類型來看,學習者在中小學階段接觸的語篇類型非常豐富,并且符合其日常需求。除了學習文學作品,學習者需要掌握從報告、訪談、新聞、天氣預報、廣播節目、廣告、宣傳冊等口頭和書面語篇中獲取信息的能力;能夠獨立完成信件、電子郵件、博客等的撰寫;能夠完成講故事、陳述個人經歷、描述人物和事物等相對復雜的語言表達。學習者聽到的和讀到的語篇將成為他們創作和建構自己語篇的資源。在學習這些語篇之后,能熟悉該類語篇的詞匯、語法等語言特征,在將來的學習和工作中既能迅速理解該類語篇,又能寫出類似的語篇。
(三)注重高階思維能力培養
布魯姆教育目標分類法按照復雜程度,將認知過程劃分為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價和創造六個層次[18]。記憶、理解和應用通常被稱為低階思維;分析、評價和創造通常被稱為高階思維[19]。《英語課程標準(2018)》指出:“高階思維能力對學生有效獲取和應用知識非常必要,是學生必備的生活技能;掌握高階思維能力能幫助學生更好地應對21世紀的挑戰。”因此,教師需要在語言教學中融入高階思維能力的訓練,通過任務實施培養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同時將高階思維能力運用到語言學習和語言使用當中。
《英語課程標準(2018)》在提出了提升高階思維能力的原則,還提出了基礎級、中等級、熟練級的學習者應該掌握的高階思維能力與目標。基礎級學習者要掌握分類、比較、推斷、提出新想法、整合、關聯、預測等高階思維能力;中等級學習者要掌握分類、比較、區分不同視角、推斷、提出新想法、區分整體和部分、整合、證明合理性、關聯、預測、解決問題、排序、解釋動機等高階思維能力;熟練級學習者要掌握評價、解釋類型、勸說、綜合、遷移等高階思維能力。《英語課程標準2018)》指出:“教師設計的任務與活動應該幫助學習者將這些高階思維能力應用于語言學習及日常生活。”例如,針對“證明合理性”,教師設計的任務與活動就應該要求學生運用所學知識,結合自己的生活經驗,對該觀點進行分析和評價,判斷對錯,提出接受或者拒絕該觀點的原因,然后用英語表達出來。
(四)體現信息時代的語言學習特點
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增加了人們的交往與互動,并且改變了交往方式。為確保學習者能夠在語言學習中充分合理使用現代信息通信技術,需要對學習者的相關技能進行培養。《英語課程標準(2018)》充分考慮到學生現實的生活情境,結合信息化時代學習與信息獲取的新特點,提出了具有針對性和現代價值的目標與標準。
《英語課程標準(2018)》在總目標中規定:“學習者能夠在印刷媒介和電子媒介的各種口頭和書面語篇中獲取信息……通過這些媒介以不同的形式用英語進行口頭和書面的觀點展示和信息陳述”。同時,《英語課程標準(2018)》的第七章專門指出了不同級別的學習者需要掌握的語篇類型和媒介類型。語篇不僅包括文學作品,還包括新聞、廣告、信件、留言、報告、書評、影評、網頁等與我們日常生活工作相關的生活、工作語篇;不僅包括口頭的、印刷的語篇,還包括電子媒介中的語篇。其中,電子媒介語篇指的是通過計算機或多媒體等其他技術手段制作或傳播的語篇,既有口頭的又有書面的,如在Skype上的聊天、網站上的論壇發言、電子郵件、博客等。
根據系統功能語言學[20]的觀點,語言使用受情境因素的影響。語言使用方式會隨交際目的、題材、口頭還是書面的溝通方式、說話人的語言文化背景、印刷媒體還是電子媒體等情境因素的變化而變化。信息時代的語篇也會在詞匯和句法上具有自己的特征。學習者在語言學習中要學會注意交際目的、溝通方式、媒體類型等情境信息,要理解語篇和作者所處的歷史、社會和文化情境,并能解釋這些情境因素在語篇中是如何體現的,以及這些情境因素對作者寫作的影響。
四、啟示
英語課程標準是英語教材編寫、教學內容選擇、課程評價的重要參考,是影響整個國家學生英語水平提升的語言教育政策。通過對以色列英語課程標準的內容和特征的分析,發現該課程標準對英語課程標準制定和英語教育具有一定的啟示:英語教育要體現實踐需求,要將外語教育研究的最新成果與實踐教學相結合,對教師的指導意見要有可操作性。
(一)英語教育要體現實踐需求
以色列英語課程標準非常重視社會對語言學習的實踐需求,在多個方面得到體現。首先,在修訂課程標準的名稱時考慮到英語作為國際通用語的地位,以《中小學英語課程標準:作為國際通用語言的英語學習原則和標準》命名。其次,無論是課程的總目標、分級目標或評價基準,都注重英語作為國際通用語的地位,關注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中與來自不同語言和文化背景的人用英語進行口頭和書面交流,體現了英語使用者的國際化特征。
與此同時,課程標準的制定關注學習者所學習的語篇類型與社會生活的聯系。除了文學作品,教學材料還要有商品廣告、手冊、日記、說明書、通知、菜單、時間表、海報、天氣預報等多種類型的語篇。多樣化的教學材料一方面能引發學習者興趣,另一方面與學生的日常生活相關,對學習者在將來的國際交流很有幫助。
(二)將外語教育研究的最新成果與實踐教學相結合
以色列英語課程標準注重吸收外語教育等領域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將這些研究成果進行整合,以原則的形式呈現,以便一線教師將理論與教學實踐相融合。《英語課程標準(2018)》提出的原則吸收了外語學習、教育、評估,認知心理學,課程標準研究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具體包括:有意義的語言學習與教學的原則、入門級學習者的語言教學原則、教學材料選取原則、任務選擇與設計原則、課程評價原則、整合信息交流技術原則。
中小學教師具有一線教學經驗,但理論與實踐脫節是教師教育中普遍存在的世界性問題[21]。如果在課程標準中能夠用他們可理解的語言將外語教育研究的最新成果傳遞給他們,對他們的教學理念、教學設計、教學評價、教學材料的選擇與改編將有很大的指導作用,從而更加有效地開展英語教育。
(三)對教師的指導意見要有可操作性
《英語課程標準(2018)》為教師的教學提出了具體詳細,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導意見,如第八章“文學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讀前活動、語篇的基本理解、分析與解釋、為語篇和語境搭橋、讀后活動、反思、總結性評估七個方面為教師提出了教學建議。這些意見能夠指導教師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開展教學活動,有效達成課程目標。
教學建議概括性太強、不夠具體是諸多課程標準共同存在的問題。教師希望得到的是更加具體的指導意見。這樣的指導意見才具有可操作性。例如,僅僅建議教師在評價中要“體現學生在評價中的主體地位”,實施起來可能會存在困難。因此,如果把這條意見改成“建議讓教師參與評價標準的制定和評價工具的設計,讓學生開展生生互評”,教師能夠更好地理解學生在評價中的主體地位,從而更好地實施該教學建議。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以色列國家概況[EB/OL].(2020-10-10)[2021-03-25].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196/1206x0_677198/.
[2]SHOHAMY E. Language policy: hidden agendas and new approaches[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6: 72.
[3]SPOLSKY B, SHOHAMY E. The languages of Israel: policy, ideology and practice[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9: 156.
[4]SHOHAMY E. The weight of English in global perspective: the role of English in Israel[J]. 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2014(1): 273-289.
[5][7][9][10]OFRA I. English teaching in Israel: challenging diversity[C]//Teaching English to the world: History, curriculum, and practic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5: 192.
[6]OR I, SHOHAMY E. English education policy in Israel[C]//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2017: 66.
[8]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and Sport. English curriculum for state schools and state religious schools grades 5-12[M]. Jerusalem: Curriculum Development Division, 1988: 7.
[11]Ministry of Education. English curriculum: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or learn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for all grades[M]. Jerusalem: Pedagogical Secretariat, Israel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0: 16.
[12]Ministry of Education. Revised English curriculum: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or learning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for all grades[EB/OL].(2013-11-01)[2021-03-25].https://meyda.education.gov.il/files/HaarachatOvdeyHoraa/Englishcurriculum.pdf.
[13]Ministry of Education. Revised English curriculum: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or learning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for all grades[EB/OL].(2018-01-01)[2021-03-25].https://meyda.education.gov.il/files/Mazkirut_Pedagogit/English/Curriculum2018July.pdf.
[14]BROWN J. The elements of language curriculum: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program development[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7.
[15]程曉堂, 孫曉慧. 英語教材分析與設計(修訂版)[M].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11: 29.
[16]SKEHAN P.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learning[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95.
[17]ELLIS R. 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9-10.
[18]ANDERSON L, KRATHWOHL D R. 布盧姆教育目標分類學——分類學視野下的學與教及其測評(修訂版)[M].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9: 43.
[19]王帥. 國外高階思維及其教學方式[J].上海教育科研, 2011(9): 31-34.
[20]HALLIDAY M.?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3rd ed.)[M]. London: Hodder Arnold, 2004:67.
[21]CHENG M, CHENG A, TANG S. Closing the gap betwee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mes in Hong Kong[J].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Teaching, 2010(1): 91-104.
編輯 娜迪拉·阿不拉江? ?校對 呂伊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