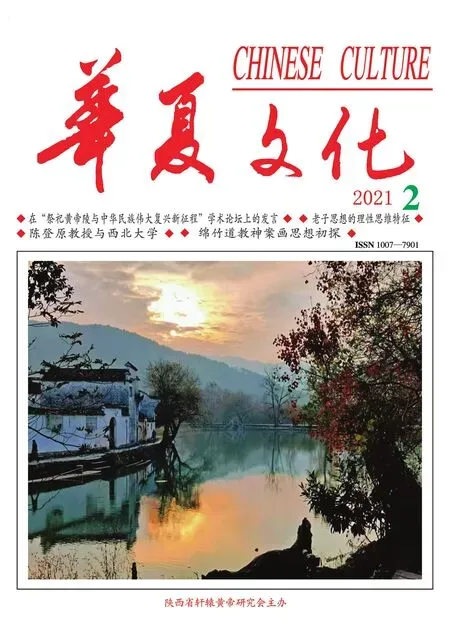老子思想的理性思維特征
□孫立舟

理性思維的出現(xiàn)標(biāo)志著人類的認(rèn)知由低級(jí)走向高級(jí)。在西方,古希臘的柏拉圖已明確提出了理性的概念。在近代啟蒙運(yùn)動(dòng)中,獨(dú)立思考的理性主義成為西歐社會(huì)的主要思潮。
有人認(rèn)為中國(guó)傳統(tǒng)思想文化僅限于道德說(shuō)教, 缺乏理性思維, 其實(shí)不然。中國(guó)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確注重道德倫理實(shí)踐, 但同時(shí)也不乏理性思維。其中,以“道”為核心的老子思想極具思辨性色彩,帶有明顯的理性思維特征。
老子思想支撐上的理性特征
在思想言說(shuō)上,老子注重言而有據(jù),具有理性思維的特征。老子說(shuō)自己“言有宗”(七十章),自己的學(xué)說(shuō)是有依據(jù)的。那么其依據(jù)是什么呢?是“道”,即客觀的規(guī)律。這些客觀的規(guī)律老子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在老子那個(gè)時(shí)代,當(dāng)然談不上科學(xué)實(shí)驗(yàn),他對(duì)客觀規(guī)律的認(rèn)識(shí)來(lái)自他對(duì)自然的觀察與思考分析。第十六章說(shuō):
致虛,極也;守靜,篤也。萬(wàn)物并作,吾以觀其復(fù)也。夫物蕓蕓,各復(fù)歸于其根。
萬(wàn)物競(jìng)相生長(zhǎng),紛紛紜紜,老子虛極而靜篤,細(xì)察它們變化、運(yùn)行的最終歸宿。最終他發(fā)現(xiàn),世間萬(wàn)物,無(wú)論其何等喧嘩、紛繁、異樣,最終都要復(fù)歸于各自本來(lái)自然應(yīng)有的樣子。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老子是以對(duì)事物冷靜地觀察而判斷出自然的規(guī)律的。當(dāng)然,老子反過來(lái)又以他所得到的自然規(guī)律,即“道”,去分析、評(píng)判事物。第五十四章說(shuō):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xiāng)觀鄉(xiāng),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
學(xué)者李零說(shuō):“這段話不是推己及人,不是說(shuō)用我的身觀你的身,等等。身、家、鄉(xiāng)可以有很多,但天下只有一個(gè),不能分彼此。”老子講,“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有余;修之于鄉(xiāng),其德乃長(zhǎng);修之于邦,其德乃豐;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以身觀身”,第一個(gè)“身”,指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這個(gè)標(biāo)準(zhǔn)就是修道之身,有真德之身;第二個(gè)“身”,指接受評(píng)判的每一個(gè)具體個(gè)人。這就好比檢查血壓,先在醫(yī)學(xué)上設(shè)立一個(gè)正常血壓的標(biāo)準(zhǔn)范圍,然后用這個(gè)標(biāo)準(zhǔn)去比對(duì)每個(gè)人的實(shí)際血壓,即可知道一個(gè)人的血壓是正常還是不正常。老子在明白了“道”之后,用修道的標(biāo)準(zhǔn)去判斷一個(gè)人、一個(gè)家、一個(gè)鄉(xiāng)、一個(gè)邦及一個(gè)時(shí)期的天下。
老子講五“觀”,啟示我們要用正確的標(biāo)準(zhǔn)去理性地判斷人與物,放在老子的思想體系里,這個(gè)標(biāo)準(zhǔn)就是“道”與“德”。放在我們今天,叫判斷人與事,要有正確的價(jià)值觀和世界觀。
老子思想表達(dá)上的理性特征
在思想表達(dá)上,老子在觀察與判斷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許多內(nèi)涵豐富、極具概括性的概念,具有理性思維的特征。請(qǐng)看第二十五章,老子提出了“道”這個(gè)核心概念: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dú)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強(qiáng)字之曰道。
有個(gè)東西,先于天地而存,寂而無(wú)聲,寥而無(wú)形,寓于天地萬(wàn)物,永不改自己獨(dú)立的本性;這個(gè)東西,健行不止,始終沒有危險(xiǎn)發(fā)生,是支配天地萬(wàn)物的根本。老子說(shuō),自己不知它究竟何狀何形,勉強(qiáng)將它稱之為 “道”。
除了提出“道”這個(gè)概念外,老子還提出了“德”“有”“無(wú)”“常”“無(wú)為”“自然”等概念。概念的提出,是把所感知事物的共同本質(zhì)特點(diǎn)加以高度概括并抽象出來(lái)的結(jié)果,是人類在認(rèn)識(shí)事物的過程中,從感性認(rèn)識(shí)上升到理性認(rèn)識(shí)的過程。《老子》一書諸多內(nèi)涵豐富概念的提出,表明先秦時(shí)中華民族理性思維已有發(fā)端并且達(dá)到了較高的水平。
老子思維水平上的理性特征
林崇德先生指出,辯證邏輯思維是人類思維的最高形態(tài)。在思維水平上,老子的思想具有強(qiáng)烈的辯證色彩,使其具有理性思維的特征。
老子思想是辯證的。老子認(rèn)識(shí)到事物中含有既相對(duì)立又相統(tǒng)一的正反兩面,在一定條件下這正反兩面是可以相互轉(zhuǎn)化的。在《道德經(jīng)》81章中,有74章都涉及正反變化的規(guī)律,就此而論,一部《道德經(jīng)》就是一部辯證的“正反經(jīng)”。如第二章:
有無(wú)之相生也,難易之相成也,長(zhǎng)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聲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隨也,恒也。
任繼愈指出,第二章這一部分論述了辯證法思想,提出一切事物都有對(duì)立面。陳鼓應(yīng)認(rèn)為,這種觀察事物的辯證方法,是老子哲學(xué)的最大成就。老子的辯證觀,啟示我們看待事物,要持理性的態(tài)度,不搞正反對(duì)立。如遇禍逢難時(shí)不悲嘆絕望,“禍兮,福之所倚”,積極樂觀面對(duì)艱難;順利得意時(shí)不驕橫狂妄,“福兮,禍之所伏”,居安思危,冷靜思考,以理性心態(tài)享受成功。
老子是有思想自信的,但是他的自信同樣是辯證的。如老子說(shuō),“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雖然我們知道自己在客觀上雄強(qiáng)居上,但在主觀上卻能取雌柔守下的姿態(tài),甘如天下的溪谷。老子教我們一面要做自強(qiáng)的雄者,一面又要做自謙的雌者,主張?jiān)谧孕胖凶灾t,在自謙中自信,否則自信就可能變成盲目自大。
老子思維模式上的理性特征
在思維模式上,老子從對(duì)自然和周圍事物的感性觀察中提煉出帶有規(guī)律性的認(rèn)識(shí),具有理性思維的特征。
老子在行文上多以天之道來(lái)述說(shuō)人之道,如第五章,先說(shuō)“天地不仁,以萬(wàn)物為芻狗”,后說(shuō)“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由此可知,老子把對(duì)自然的觀察與對(duì)人事的思考結(jié)合起來(lái),注重從大自然中獲得認(rèn)識(shí)。下面這段話顯示的是老子從暴風(fēng)驟雨中所獲得的啟迪:
飄風(fēng)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也。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第二十三章)
老子注意到,天地也會(huì)有反常的氣象,但是通常為時(shí)不長(zhǎng)。比如,狂風(fēng),通常刮不了一個(gè)早上;暴雨,通常不會(huì)整天一直下。狂風(fēng)暴雨是誰(shuí)造成的呢?天地。天地的力量,尚且無(wú)法長(zhǎng)久暴而狂,更何況人呢?老子是想以此警告統(tǒng)治者,不管你權(quán)力有多大,如果你暴虐囂張,很快都會(huì)滅亡的。象周厲王、商紂王等的下場(chǎng),就生動(dòng)地印證了這一點(diǎn)。下面再來(lái)看看老子從江海那里所悟到的統(tǒng)治之道:
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為百谷王。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第六十章)
老子看到,江海之所以能為百川之所歸,是因?yàn)榻L幱谙路剑@樣就自然成為百川之王。由此老子感悟出,那些高高在上的統(tǒng)治者對(duì)民眾講話,不要居高臨下地頤指氣使、盛氣凌人,應(yīng)該言辭謙恭溫和,貼近民心,才能得到民眾的衷心擁護(hù)。
老子還善于從對(duì)日常生活事務(wù)的觀察中得出深刻的規(guī)律性認(rèn)識(shí)。如老子從燒菜中也能思考出這樣的大道理:“治大國(guó),若烹小鮮。” 烹煮小魚,是不能頻頻翻動(dòng)的,否則魚就會(huì)碎得不成樣子。治理大國(guó),道理與之相似。如果統(tǒng)治者朝令夕改,政策沒有穩(wěn)定性,瞎折騰人民,國(guó)家就會(huì)動(dòng)蕩不安,弄得民不聊生。
老子思維方法上的理性特征
在思維方法上,老子比較多地運(yùn)用了推理的方法,使其思想具有理性思維的特征。以第十六章為例: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常”,是老子提出的一個(gè)特定概念,指事物發(fā)展變化的永恒規(guī)律。張岱年說(shuō):“常即變中之不變之義”,所謂常,就是“變化的不易之則”。老子在此作了一連串華麗的推理:知“常”,則大度包容;大度包容,則坦然大公;坦然大公,則天下歸從;天下歸從,則說(shuō)明統(tǒng)治合于自然;統(tǒng)治合于自然,則合乎大道;合乎大道,則可持久發(fā)展,始終沒有兇險(xiǎn)。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老子是極善于進(jìn)行推理的。
推理,是由一個(gè)或幾個(gè)已知的前提推出新結(jié)論的過程,是一種理性思維的方法與形式。這種思維方法,老子用得很多,如第五十九章也是一個(gè)比較典型的例子,在此不展開論述。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老子在觀察自然與客觀事物時(shí),運(yùn)用推理,冷靜思考,具有大局觀,多角度看問題,力圖透過現(xiàn)象來(lái)抓住事物的本質(zhì);在思想表達(dá)上,提出很多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這就使得其思想具有理性思維的特征。
2020年以來(lái)的新冠肺炎疫情,給人民生產(chǎn)與生活、學(xué)校教育、交通運(yùn)輸?shù)确矫娑荚斐闪撕艽蟮挠绊憽_\(yùn)用老子的辯證理性思維,我們從這場(chǎng)疫“禍”中,在政府治理、環(huán)境保護(hù)、法制建設(shè)、公共衛(wèi)生教育、醫(yī)療保障等方面都可以吸取許多深刻的教訓(xùn),從而變“禍”為“福”,化“危”為“機(jī)”,以更好地推進(jìn)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事業(yè)。
說(shuō)明:本文是安徽省2019年教育信息技術(shù)研究課題《新課標(biāo)背景下“歷史經(jīng)典著作選讀”微課程的開發(fā)與應(yīng)用研究》 (課題立項(xiàng)號(hào):AH2019379)階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