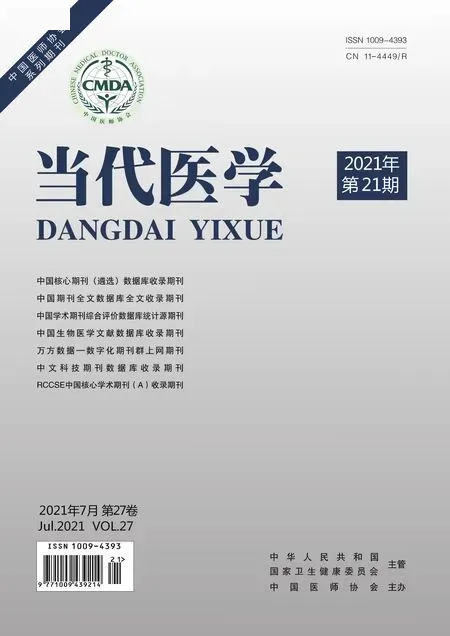罕見原發性肝結核1例和國內22例的臨床及病理分析
陳冰,程琦,徐斌
(1.江西省瑞金市人民醫院感染科,江西 瑞金 342500;2.復旦大學華山醫院感染科,上海 200040)
在傳統觀念中肝結核是肺結核或粟粒性結核病的一部分,隨著診斷技術的提高,越來越多肝內病變系由結核菌感染引起、而無其他臟器結核感染者被發現。根據結核菌感染肝的同時是否伴有肺結核或全身其他部位結核,可將肝結核分為原發性和繼發性兩種類型。原發性是指肝局部結核感染,其他器官無結核感染證據者[1]。原發性肝結核由于臨床表現無特異性,診斷十分困難。本研究回顧性分析本院病理確診的1例原發性肝結核患者的臨床資料并結合相關文獻進行復習,探討原發性肝結核的早期診斷方法及合理的治療方案,現報道如下。
1 病例資料
患者,男,45歲,浙江永嘉人,從事金融業,因發現肝臟占位3個月伴發熱20 d入院,于2017年5月24日收入復旦大學華山醫院感染科。患者于2月初無明顯誘因開始出現消瘦,至3月體質量下降近10 kg,稍感乏力,無納差,無發熱,無夜間盜汗,無咳嗽、咳痰等,初期未引起重視,未就醫。后患者于2017年4月22日至溫州永嘉市人民醫院進行健康體檢,查血常規、肝腎功能、電解質等檢查未見明顯異常;顱腦CT:未見明顯異常;胸部CT(見圖1):左肺舌段及右肺中葉可見散在少許條索狀密度增高影,邊界尚清,余肺未見明顯異常;肝臟B超:肝內多發低回聲團;肝臟MR(I見圖2):肝內多發占位性病變,肝周少量積液,肝門及腹膜后多發淋巴結腫大,雙腎多發囊腫,甲胎蛋白119 IU/mL。于2017年4月27日至溫州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就診,全身PET-CT(見圖3):①右肝6、7段多發軟組織及結節伴代謝活躍,大者中心區伴有壞死,反射性攝取值不均性增高,最大SUV值約7.7,考慮惡性腫瘤性病變,首先考慮膽管細胞癌伴肝內轉移,縱膈2R、4R、7/8/9R區、腹腔肝門胰頭及賁門癌。腹膜后腹主動脈及腔靜脈旁多發淋巴結腫大伴代謝活躍,均考慮轉移;②左肺舌段及右肺中葉少許炎性纖維灶,冠脈左支鈣化;③膽囊微小結石,右腎微小鈣化。于2017年5月2日于上海某三甲醫院住院治療,入院第2天行肝穿活檢,但肝穿后第1天患者開始發熱,腋溫峰值達39.0℃,午后出汗后可退,晚上體溫可再升,伴畏寒、寒戰,無咳嗽、咳痰,無鼻塞、流涕,無惡心、嘔吐,無腹痛、腹瀉,無尿頻、尿急、尿痛,行血常規,肝腎功能,自身抗體均正常。AFP:2.5 ng/mL,肝臟MRI:肝臟多發MT(轉移瘤機會性大),診斷為肝臟占位待查,予拉氧頭孢、頭孢他啶治療1周,仍發熱。2017年5月9日肝穿病理回報:為參考免疫組化及特染結果,壞死組織中未見真菌菌絲及孢子,抗酸陰性,傾向炎性假瘤伴大片壞死,繼續予甲硝唑、美羅培南、強的松等抗感染,抗炎等治療3周,體溫無好轉。于2017年5月24日轉入復旦大學華山醫院感染科,既往史:否認結核病史,否認肝炎病史,余無特殊,入院體格檢查:體溫38.5℃,神清,慢性消耗病容,全身淺表淋巴結未觸及腫大,頸軟,雙肺呼吸音稍粗,未聞及干濕啰音,心率95次/min,心率齊,心音尚可,各瓣膜區未聞及雜音,腹部平坦,軟,全腹無壓痛及反跳痛,未觸及包塊,肝脾肋下未觸及;墨菲氏征陰性,移動性濁音陰性,腸鳴音4~5次/min,余查體無特殊。入院輔助檢查:血常規正常,肝功能,T.B.NK細胞,腫瘤標志物均正常,免疫缺陷病毒抗體陰性,PCT:0.09 ng/mL,血沉:114 mm/h,CRP:74.9 mg/L,鐵蛋白:1 850 ng/mL,血TSPOT:抗原A孔>30抗原B孔>50,考慮到患者仍反復發熱,結合血T-SPOT強陽性,于2017年5月30日予診斷性抗結核治療,為減少肝功能損傷發生,抗結核方案為:異煙肼0.6 g,利福平0.45 g,乙胺丁醇0.75 g及左氧氟沙星0.5 g,均每天1次。抗結核治療第2天患者體溫平穩,同時積極尋找病理依據,在本院行2次B超引導下肝穿活檢病理報告均提示炎癥改變,未提示肝結核,于2017年6月12日外院借來初次肝穿切片至本院病理科會診病理回報(見圖4):送檢組織內見急慢性炎癥伴纖維組織增生,另見類上皮細胞反應及凝固性壞死,抗酸染色見少量陽性桿菌,提示結核,請結合臨床。最后確診為原發性肝結核,繼續予異煙肼、利福平、乙胺丁醇及左氧氟沙星抗結核治療,病情穩定后回當地醫院繼續規律抗結核治療并隨訪。

圖1 胸部CTFigure 1 Chest CT

圖2 肝臟MRIFigure 2 Liver MRI

圖4 肝臟病理示干酪樣肉芽腫及抗酸桿菌陽性Figure 4 Positive caseous granuloma and acid-fast bacilli in liver pathology
2 文獻復習
以“原發性肝結核”為檢索詞,通過萬方數據庫和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進行檢索(1984年1月至2020年1月),共檢索到國內發表的有關原發性肝結核的文章15篇,原發性肝結核22例,均符合病理確診標準。分析22例(包括本院收治的1例)患者的臨床資料,采用SPSS 22.0軟件進行描述性分析。
2.1 臨床資料 22例中男21例,女1例;年齡18~67歲,平均年齡(41.1±12.2)歲;平均病程(4.5±9.9)個月,既往病史:結核病史5例,其中肺結核病史3例,腹腔結核病史1例,頸淋巴結核1例,乙肝病史2例,肝內膽管結石病史1例,肝包吸蟲病史1例,白血病病史1例。
2.2 臨床表現 22例中發熱11例(50%),多以午后低熱為主,乏力9例(40.9%),消瘦8例(36.4%),肝區隱痛5例(22.7%),腹脹2例(9.1%),腹瀉1例(4.5%),納差4例(18.4%),盜汗2例(9.1%),肝肋下可觸及4例(18.4%),淺表淋巴結觸及腫大1例(4,5%),腹部壓痛4例(18.2%),無明顯癥狀及體征4例(18.2%)。
2.3 實驗室檢查 AFP:正常21例,陽性1例,輕度升高;PPD:陽性10例,其中強陽性4例,陰性7例,未測4例;血TSPOT:強陽性1例;肝功能正常18例,肝功能異常4例;血常規:白細胞及中性粒細胞升高4例,血沉升高4例。
2.4 影像學檢查 胸部CT:22例均提示未見明顯異常;腹部B超:22例中提示肝癌或轉移肝癌12例,肝膿腫5例,肝腫大2例,肝血管瘤1例,肝包吸蟲1例,肝膽管結石1例;上腹部CT:15例中提示肝癌或轉移性肝癌8例,肝膿腫4例,肝血管瘤2例,肝包吸蟲1例;增強肝臟MRI:4例均提示肝癌或轉移性肝癌;全身PET-CT:2例均提示肝癌或轉移性肝癌。
2.5 入院診斷及病理后診斷 入院診斷:肝癌或轉移肝癌8例(36.4%),肝占位待查5例(22.7%),肝膿腫3例(13.7%),肝血管瘤2例(9.2%),肝包吸蟲1例(4.5%),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1例(4.5%),白血病1例(4.5%),上呼吸道感染1例(4.5%)。
病理:22例均行病理檢查,其中5例為B超引導下經皮肝穿后病理,6例為剖腹探查后病理,11例為手術后病理。病理結果提示為干酪樣壞死、凝固性壞死、上皮樣肉芽組織結節、朗格漢氏細胞及淋巴細胞浸潤,抗酸染色陽性僅2例。病理后診斷:均修正診斷為原發性肝結核。
2.6 治療及轉歸 11例予肺結核方案抗結核治療,并延長鞏固治療時間平均為(11.7±2.0)個月,均治愈未復發;10例先行手術切除肝內病灶,再按2HRZE(S)/4~6HR方案抗結核治療,均治愈未復發;1例死亡,其直接死因為白血病誘發多臟器功能衰竭。
3 討論
肝結核較少見,屬于肺外結核,通常由肺結核通過肝動脈或腸道結核通過門靜脈播散造成[2]。肝結核可分為5種臨床病理表現:①粟粒性結核;②肉芽腫性結核性肝炎;③結節性結核;④導管性結核;⑤結節性結核[3]。50%~80%肝結核為普通粟粒型,而原發性肝結核所占比例不到1%,普通粟粒型由結核分枝桿菌通過肝動脈播散而來,而原發性肝結核往往由門靜脈途徑所形成,門靜脈血氧低,這也是原發性肝結核較少的原因之一[4],只有機體免疫力下降,或肝內屏障功能受損,當大量結核菌入肝后才能致病。故發病前多有免疫力低下等基礎疾病史,或既往結核史。本研究通過文獻復習表明,11例找到相關基礎疾病病史依據,占比50%,其中5例有相關結核病史,所以仔細詢問病史有助于找到診斷本病的一些線索。
3.1 臨床資料及臨床表現 本研究文獻復習中男性患者居多,但原發性肝結核是否以男性患者為主,需更多樣本量支持。患者全身癥狀同肺結核類似,有低熱、盜汗、乏力、消瘦等,其中發熱最常見;局部癥狀主要為肝區隱痛或絞痛,可伴有納差、腹脹、腹泄;體征主要可有肝肋下可觸及、淺表淋巴結腫大,右側腹部壓痛,但也有4例無明顯癥狀及體征,在臨床上結合影像學表現易誤診為晚期肝癌等,說明肝結核無特異癥狀和體征[5]。
3.2 實驗室檢查 18例行PPD試驗或血T-SPOT檢查,其中陽性11例,占比61.1%,低于相關文獻[6]報道肝結核PPD試驗陽性率,可能與本組樣本數量較少有關,也可能提示原發性肝結核PPD試驗或血T-SPOT陽性率較高,結合PPD試驗,尤其是血T-SPOT特異性較高,已被證明其特異性高于結核菌素皮膚測試,敏感性高達70%~90%[7-8],如為陽性則應考慮肝結核的可能,陰性亦需注意鑒別,故在臨床上應重視PPD試驗或血T-SPOT檢查。本組病例中AFP陰性21例,僅1例輕度升高,故AFP的定性及定量有助于與肝癌鑒別。本組病例僅4例表現肝功能異常,白細胞、中性粒細胞比例及血沉升高,說明肝功能,血常規及血沉亦無特異性[9],但持續高熱時合并白細胞、中性粒細胞比例大幅升高是肝膿腫的證據。
3.3 影像學檢查 本組病例行腹部B超22例,上腹部CT 15例,增強肝臟MRI 4例及全身PET-CT 2例全部誤診,其中肝癌或轉移性肝癌誤診率最高,腹部B超12例,占比54.5%,上腹部CT 5例,占比53.3%,而肝臟MRI及PET-CT全部誤診肝癌或轉移性肝癌,與有關文獻報道肝臟結核影像學無特異性一致[10]。肝臟感染結核菌后,隨疾病發展和免疫力變化,結核性肉芽腫有多種病理表現且可同時存在:干酪樣壞死、液化、纖維組織增生、鈣化;所以B超、CT及肝動脈造影特征性不強,無法區分結核瘤與肝癌、結核膿腫與肝膿腫等[11],加上原發性肝臟結核少見,影像學醫生易誤診,而外科醫生如過分依賴影像檢查結果,而忽視肝結核的可能,易造成術前誤診,因此,對原發性肝結核的確診需依賴于細菌學和病理學檢查。
3.4 入院診斷及病理后診斷 本組病例入院診斷為肝癌或轉移肝癌8例,占比最高為36.4%,肝占位待查5例,占比22.7%,肝膿腫3例,占比13.7%,肝血管瘤2例,肝包吸蟲1例,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1例,白血病1例,上呼吸道感染1例,因此,該病需與肝癌、阿米巴性或細菌性肝膿腫、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肝血管瘤等鑒別;病情進展速度、癥狀、血清甲胎蛋白水平、數字減影血管造影與CT檢查所見、肝臟穿刺活檢、剖腹探查、PPD試驗或血T-SPOT、結核抗體五項和診斷性抗結核治療等均有助于鑒別,其中肝穿刺活檢是最佳選擇[12]。22例病理結果提示為干酪樣壞死、凝固性壞死、上皮樣肉芽組織結節、朗格漢氏細胞及淋巴細胞浸潤,抗酸染色陽性僅2例,占比9.1%,這與文獻中[13]報道的肝活檢組織中發現抗酸桿菌的幾率不高(7%~59%)相符,但發光二極管顯微鏡已被證明是優于傳統的Ziehl-Neelsen顯微鏡,其使用現在被世界衛生組織提倡[14],可能會提高陽性率。病理后診斷:均為肝結核,因此,誤診率高達100%,提示誤診率極高,與國內龍新等[15]研究一致,由于肝結核的臨床表現和輔助檢查均無特異性,明確診斷很困難,迄今為止臨床確診率未見明顯提高。分析22例患者的診治情況,認為原發性肝結核的誤診及漏診可能的原因為:①少見,臨床表現缺乏特異性,部分病例無明顯癥狀和體征;②因缺乏肝外結核表現,對肝結核可能性的忽視;③影像學檢查缺乏特異性,但又過分依賴影像檢查結果,而PPD試驗或血T-SPOT陽性對提示肝結核診斷和AFP陰性對原發性肝癌鑒別診斷的重要意義卻未得到應有的重視;④肝結核與肝癌發病年齡段大體重疊;⑤術前及術后進行結核抗體檢測、PPD、痰涂片抗酸染色和痰培養陽性率低,也難以診斷原發性肝結核[15]。當診斷仍困難時應果斷采用B超引導下肝穿刺活檢,甚至多次活檢,這是除手術外早期確診的唯一方法,必要時可用腹腔鏡協助定位[16-17]。
3.5 治療與轉歸 本組病例有11例按肺結核方案抗結核治療,并延長鞏固治療時間平均為(11.7±2.0)個月,均治愈未復發,也有研究表明,為獲得最佳效果,應延長治療時間>12個月[18];10例先行手術切除肝內病灶,再按2HRZE(S)/4~6HR方案抗結核治療,均治愈未復發;1例死亡,其直接死因為白血病誘發多臟器功能衰竭。目前尚無專門針對肝結核的化療方案,本研究仍選用肺結核化療方案,但療程應與之相當或延長,治愈率高達95.5%。當然對已有肝損害,選用方案及藥物時需考慮肝的承受力,根據PK/PD理論,通過結合患者情況、治療藥物濃度監測及體外結核菌藥物敏感性試驗結果以制訂合適的劑量,優化給藥方案,提高療效,防止進一步損害肝功能[19-20]。同時,本研究發現,內科抗結核治療效果與術后再抗結核治療效果相當,但前者抗結核療程更長,可減少患者手術痛苦,因此,在臨床上優先肝穿病理確診肝結核后再行內科抗結核治療,只有當符合手術指征時才考慮手術切除病灶再行抗結核治療,有文獻報道[5]總結肝結核的手術指征:①結核瘤;②結核性膿腫;③引起梗阻性黃疸;④并發膽道出血;⑤多個病灶,但局限于一葉或一段;⑥局限性膽道損害,即使膽道整形亦可能影響其引流者;⑦病灶波及或可能波及膽囊時,應行膽囊切除;⑧可能合并腫瘤等需手術處理的其他病變。手術方式根據病變不同可采用肝葉或肝段切除、不規則肝切除(病灶切除)、膿腫引流和/或膽道引流、整形等。
綜上所述,臨床上需提高對原發性肝結核這一診斷的警惕性,原因為原發性肝結核診斷困難,誤診率高,其臨床表現及影像學檢查無特異性,PPD試驗或血T-SPOT強陽性及AFP陰性對診斷及鑒別診斷有重要意義,對疑診病例積極早期進行B超引導下肝穿活檢并作抗酸染色,可早期確診,從而使患者免于手術而獲得確診。原發肝結核的治療也應遵循規范的抗結核病治療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