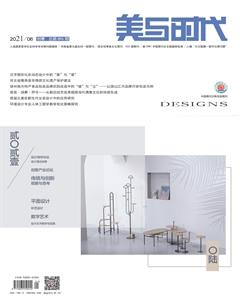荊州鉛錫刻鏤裝飾技藝研究
胡艷 彭蓉



摘? 要:2011年,鉛錫刻鏤技藝入選國(guó)家第三批公布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敖朝宗被評(píng)為國(guó)家級(j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傳承人。敖氏通過(guò)鉛錫刻鏤為青銅器中繁復(fù)紋飾及銘文的制作與修復(fù)提供了高質(zhì)高效的解決方案。2020年1月,湖北美術(shù)學(xué)院胡艷老師帶隊(duì)對(duì)鉛錫刻鏤傳承人敖朝宗進(jìn)行了專(zhuān)訪,在倡導(dǎo)保護(h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當(dāng)今,我們對(duì)這些珍貴的文化藝術(shù)遺產(chǎn)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有助于我們認(rèn)識(shí)那個(gè)久遠(yuǎn)的青銅時(shí)代及青銅裝飾藝術(shù)和制作工藝,并且在未來(lái)的設(shè)計(jì)中去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揮運(yùn)用。
關(guān)鍵詞:鉛錫;敖朝宗;青銅器;荊州
基金項(xiàng)目:本文系湖北省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研究中心(湖北美術(shù)學(xué)院)一般研究項(xiàng)目“荊州鉛錫刻鏤裝飾技藝研究”(FY-2020-06)研究成果。
在人類(lèi)文明進(jìn)程中,文化藝術(shù)遺產(chǎn)為文化的非物質(zhì)形態(tài),包含著人民大眾的智慧和創(chuàng)造,體現(xiàn)著地域文化傳統(tǒng)和特色,是整個(gè)文化體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其多樣性維系著文化生態(tài)的平衡。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從農(nóng)耕、游牧文明到工業(yè)文明,手工技藝和傳統(tǒng)文化的衰落,是全人類(lèi)面臨的共同命運(yùn)。19世紀(jì)上半葉在德國(guó)興起的浪漫主義,19世紀(jì)下半葉在英國(guó)興起的藝術(shù)與手工藝運(yùn)動(dòng),都是懷鄉(xiāng)、思鄉(xiāng)的一種體現(xiàn)[1]。當(dāng)我們步入現(xiàn)代社會(huì),許多傳統(tǒng)工藝美術(shù)品種正瀕臨“人亡藝絕”的失傳境地,造成工藝文化鏈的斷裂,進(jìn)而導(dǎo)致文化生態(tài)的失衡。隨著2011年荊州鉛錫刻鏤傳承人申報(bào)國(guó)家非遺保護(hù)成功,通過(guò)其獨(dú)特的技藝,將最典型的工藝美術(shù)視覺(jué)符號(hào)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出來(lái),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鉛和錫都是人類(lèi)最先利用的幾種金屬之一[2]。《說(shuō)文解字》“鉛,青金也。”“錫,銀鉛之間也。從金易聲。”[3]“青金”描述鉛自然狀態(tài)下表面附有一層青灰色氧化物的外觀特點(diǎn),“錫”從金從易,是一種容易變形的金屬。在科學(xué)尚欠普及的舊時(shí)常鉛與錫不分,統(tǒng)稱(chēng)“青元”。鉛錫刻鏤工藝即是利用鉛錫延展性好、熔點(diǎn)低等特性,通過(guò)打擊、扭曲、編織、擠壓、刻鏤等手法,歷經(jīng)20多道工序,把平面紋飾和立體、扭曲、鏤空等造型結(jié)合起來(lái),把器物形狀和動(dòng)物形態(tài)結(jié)合起來(lái),最終完成紋飾精致的原模。
獨(dú)立的鉛錫件文物在我國(guó)考古發(fā)掘中也有大量出土,如湖北隨州戰(zhàn)國(guó)曾侯乙墓出土的鉛錫盤(pán)、廣西賀縣鐵屎嶺北宋錢(qián)監(jiān)遺址出土的器皿中發(fā)現(xiàn)大量鉛錫成分等。直到近代,民間仍普遍使用鉛錫件。近年來(lái),隨著現(xiàn)代科學(xué)知識(shí)的普及,人們逐漸放棄了鉛錫作為生活用器,鉛錫器物制作也隨之淘汰,只保留了其加工技藝,作為對(duì)青銅器鑄造的技術(shù)支持,因此敖氏的鉛錫刻鏤技藝是沒(méi)有直接的鉛錫作品的。荊州地區(qū)在古代是南方青銅通往北方的重要通道,是楚國(guó)的核心地區(qū),也是楚式青銅器的重要出土地。楚式青銅紋飾在中原紋飾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出具有地方特色和時(shí)代特征的樣貌,其青銅冶鑄技術(shù)代表了當(dāng)時(shí)的最高水平。但相較于中原地區(qū)青銅器發(fā)現(xiàn)早、研究多而言,楚系青銅器的大量發(fā)現(xiàn)卻是近三四十年來(lái)的事,從歷史、紋飾到工藝仍有很多問(wèn)題尚待研究[4]。其中一些楚式青銅器的制造技藝曾一度被認(rèn)為失傳,但在民間的敖氏家族卻能借助鉛錫工藝復(fù)制出來(lái)。經(jīng)他仿制的馬踏飛燕、楚式云紋盒、狩獵紋壺等作品都達(dá)到了亂真的水平,其中楚式云紋盒入選中國(guó)當(dāng)代工藝美術(shù)雙年展,且是該屆青銅器門(mén)類(lèi)的唯一一件(如圖1)。因目前鉛錫刻鏤技藝依存于古代青銅器的復(fù)制和滿足國(guó)家文物單位修復(fù)古代器物的需要,故而技藝傳承較為艱難,保護(hù)和傳承鉛錫刻鏤技藝已迫在眉睫。
一、荊州鉛錫刻鏤技術(shù)簡(jiǎn)介
敖氏生活在荊江河畔湖北沙市的金屬加工工藝世家。荊州地區(qū)古來(lái)便是魚(yú)米之鄉(xiāng),較為富庶,具備民間貴金屬工藝加工的需求與物質(zhì)基礎(chǔ)。在舊社會(huì)的沙市,涉及五金工藝加工的有一百多家,而其中做得好的一二十家都與敖家有關(guān)聯(lián)。鉛錫刻鏤工藝用于青銅器制模與修復(fù)技藝,在敖家世代相傳,有家譜記載的已超過(guò)五代,是敖朝宗的曾祖父的雇工帶來(lái)的技術(shù),逐漸被吸納融合到貴金屬加工中。我國(guó)青銅器從夏代開(kāi)始到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其造型和紋飾從簡(jiǎn)到繁,也附加上更多的工藝,如:范鑄法(可細(xì)分為合范鑄法、填范鑄法、模印范鑄法和失蠟法4種)、嵌鑄法、卯接法、鑲嵌法、刻畫(huà)法、金銀錯(cuò)和鎏金等[5]。敖氏家族各類(lèi)金屬工藝加工技術(shù)的傳承使之具有復(fù)制青銅器的條件,尤其在表現(xiàn)青銅紋飾干凈有力、圓滑過(guò)渡、氣息逼真的特點(diǎn)上,發(fā)現(xiàn)了鉛錫具有的優(yōu)越性,并實(shí)踐出一套具體做法,使楚地青銅文化的瑰麗燦爛通過(guò)復(fù)制與修復(fù)呈現(xiàn)于我們面前。
二、鉛錫工藝與古代青銅鑄造工藝
鉛、錫和銅都是人類(lèi)發(fā)現(xiàn)和使用較早的金屬,僅次于金,其礦較金更易獲得,青銅即銅錫合金。《考工記》中對(duì)制作不同青銅器物所用銅錫比例已有詳細(xì)的規(guī)定;到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重要青銅器物如編鐘、銅劍和銅鏡等,合金成分配比已很?chē)?yán)格。可見(jiàn)在青銅時(shí)代,人們也已掌握了鉛錫的加工技藝。
所謂“制器先有模,無(wú)模難成器”。敖氏在祖輩習(xí)得鉛錫刻鏤技術(shù)后,逐漸將其融入到貴金屬加工中。經(jīng)過(guò)長(zhǎng)期實(shí)踐敖朝宗發(fā)現(xiàn)鉛錫輔助制模有著不可替代的優(yōu)勢(shì)。傳統(tǒng)制模主要有石、陶、蠟,由于材料的特性,在雕刻時(shí)石模容易出現(xiàn)崩裂,而陶范容易出現(xiàn)垮塌,達(dá)不到楚式青銅器紋飾的精細(xì)程度。而失蠟法中的蠟,一是性質(zhì)軟在表現(xiàn)紋飾力道上有所不及;二是久置易變形。面對(duì)一個(gè)比較長(zhǎng)的工期,尤其是在面對(duì)紋飾繁復(fù)的楚式青銅器,制作工期往往需要數(shù)月,很難在制模和澆鑄的全過(guò)程中保持原有挺立的形態(tài);三是由于范在澆鑄完畢之前是不打開(kāi)的,因此也無(wú)法判斷是否存在瑕疵,進(jìn)而導(dǎo)致廢品率極高,使得實(shí)際操作幾乎不可能。此外,從出土的古青銅上的焊縫推斷出復(fù)雜青銅器的制作使用了分鑄焊接技術(shù),然而由于銅的金屬特性,在沒(méi)有現(xiàn)代技術(shù)的情況下,銅的焊接實(shí)際上非常困難,條件要求極高而且易斷裂。而錫卻是我們最常使用的焊料,如果使用的是鉛錫模具,那么青銅器上的焊縫就有可能是對(duì)更容易進(jìn)行焊接的鉛錫模具進(jìn)行焊接而留下的痕跡。因而不禁讓人猜想,我國(guó)青銅時(shí)代的鉛、錫除了作為青銅的合金原料以外,是否還參與了青銅的制模呢?雖然目前還沒(méi)有足夠的出土證據(jù)來(lái)支撐這一想法,但從敖氏在青銅制作的實(shí)踐中,明顯感到有這樣的可能,即采用鉛錫刻鏤輔助制模可以規(guī)避傳統(tǒng)制模材料的缺陷,達(dá)到細(xì)如發(fā)絲和很高的繁密程度,并且在制作效率和降低廢品率都有出色的表現(xiàn)。此前曾有文詳細(xì)地討論過(guò)有關(guān)傳統(tǒng)青銅器鑄造方法在制作曾侯乙尊盤(pán)時(shí)的弊端,提出“漏鉛法”的可能性[6]。雖然在使用鉛和錫的方式上與敖氏不同,但值得一提的是都注意到了鉛、錫在楚式青銅器制模的可能性。筆者認(rèn)為,通過(guò)古今匠人之間的“對(duì)話”,對(duì)古代工藝的考證提出具有參考價(jià)值的看法,無(wú)疑也是手藝傳承的重要意義。
三、敖氏技藝與出土青銅器修復(fù)
青銅器修復(fù)是敖家工藝中非常重要的一項(xiàng)。由于在荊州地區(qū)青銅工藝中敖氏首屈一指,因此曾多次受湖北省考古所和湖北省博物館邀請(qǐng)參與文物發(fā)掘和文物復(fù)制工程。出土青銅器的損壞方式各不相同,為使出土青銅器恢復(fù)原貌,需依照每件具體器物制訂具體方案。2011年敖朝宗參與了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guó)墓出土青銅器的修復(fù)和整理工作,其中111號(hào)曾候犺墓是該墓葬群中出土青銅禮器最多的。其中有銘文的重要禮器“南宮簋”[7]受損嚴(yán)重,器物存在的凹陷變形,傳統(tǒng)的捶打方式有可能對(duì)器物造成傷害,敖朝宗提出使用靜壓的方式,并設(shè)計(jì)和制作了一臺(tái)修復(fù)青銅器的靜壓機(jī),可以在各角度進(jìn)行靜壓修復(fù)青銅器。經(jīng)由他修復(fù)的“南宮簋”最大程度地還原了器物原來(lái)的挺拔外形與精美紋飾(如圖2),其上銘文,解決了學(xué)界爭(zhēng)論了幾十年的“曾隨之謎”,確定了一個(gè)文獻(xiàn)上從未提及的曾國(guó)的大致歷史,將曾國(guó)的歷史推早500年到西周早期。葉家山的考古發(fā)現(xiàn)成為了改寫(xiě)歷史教科書(shū)的重要依據(jù)。
四、鉛錫刻鏤技藝中的傳統(tǒng)紋飾
藝人對(duì)紋飾的學(xué)習(xí)大都是從拓片中來(lái),比如在修復(fù)的器物上拓片。這些不同的紋飾是裝飾在不同的器皿上,既不是藝人的憑空創(chuàng)造,也不是受當(dāng)時(shí)權(quán)貴的要求下達(dá)的指示來(lái)制作,他們是有交流的,所以楚紋飾就非常活潑生動(dòng)。古人認(rèn)為“國(guó)之大事,在祀與戎”,青銅時(shí)代祭器與兵器主要為青銅器,其紋飾自是極度講究的。青銅器的紋飾是單面,一種花對(duì)稱(chēng)或分八片、六片,這樣看起來(lái)就比較繁華,這樣掌握一種花型就可以無(wú)限連續(xù)下來(lái)形成紋飾。在佛教傳入中國(guó)之前,同世界上其他早期文明一樣經(jīng)過(guò)了多神崇拜的階段,那些遠(yuǎn)古的圖騰和宗教通過(guò)紋飾成為祭器上的主要裝飾題材。同時(shí),青銅器也是權(quán)力和等級(jí)的象征。尤其到了東周時(shí)期等級(jí)森嚴(yán),中國(guó)古人尊九,天子“九鼎八簋”,再按公侯伯子男遞減。到了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有錢(qián)人也可以根據(jù)自己的要求來(lái)制作器皿,所以到了戰(zhàn)國(guó)末期,紋飾就百花齊放。敖朝宗注意到紋飾是人和大自然的相互認(rèn)識(shí)過(guò)程中產(chǎn)生的,楚國(guó)的青銅紋飾結(jié)合了大量自然物像,同時(shí)具有高度符號(hào)化的特征。比如卷云紋的內(nèi)卷外卷兩卷,代表天空云朵的變化,是人們觀察天空云彩的變化,逐漸形成程式化,定格下來(lái)反映到青銅器上。楚國(guó)紋飾最有代表的火裂紋,四個(gè)枝子加一個(gè)盤(pán)卷。楚人崇拜祝融,火裂紋就是他的圖騰,曾乙候墓出土的青銅器紋飾大都有火裂紋。又比如在我們看來(lái)神秘的夔龍紋、饕餮紋,他們來(lái)自蟲(chóng)鳥(niǎo),還有那些更抽象的雷紋、虹紋等都具有象征意義的[8],可以說(shuō)審美絕非青銅紋飾的第一目的。先秦青銅紋飾的裝飾特征主要是對(duì)稱(chēng)與連續(xù)。到了漢代,青銅工藝技術(shù)達(dá)到頂峰,再結(jié)合漢代對(duì)成仙的追求,其造型和裝飾更多變與流動(dòng)。掌握這些才能依據(jù)時(shí)代和器型特征來(lái)把握紋飾的整體效果,合理安排制作程序。
古人制造器物有嚴(yán)格要求,“劍面平整,劍鋒端正,五線歸一。”(如圖3)“萬(wàn)物有型,型則必實(shí),實(shí)則可鏤。”
關(guān)于制模:制器先有模,無(wú)模難成器;成模有尺寸,成模上鉛錫,刻鏤馳其中;制模有技巧,方圓刮削成模道;分劃分三四,六八方位出;宮格畫(huà)紋飾,上下高低皆有度,反復(fù)比較能安心。
關(guān)于刻鏤技法:挑刀指用勁,以免傷眼窩,用刀力必致,用針力上尖。
關(guān)于紋飾:?jiǎn)卧嗤桃粋?cè),花型相對(duì)刻一片,平起平走刻一排;每刀相連,前后相引,才能四平八穩(wěn);鏤花凝重,恒定心力,眼手一致,寧停不急,緊而不急,慢而不松,心氣平和,如有錯(cuò)寧可錯(cuò)不可亂。
五、鉛錫刻鏤技藝的傳承現(xiàn)狀
與其它很多“非遺”手藝一樣,敖氏鉛錫刻鏤及青銅器制作的手藝依然面臨著傳承的問(wèn)題。在申請(qǐng)“非遺”之前,敖氏作品主要購(gòu)買(mǎi)者是“文化商人”即文物販子,其制作自然也是不公開(kāi)的更無(wú)法進(jìn)行普及宣傳,除了一些行內(nèi)人士,基本是無(wú)人知曉。曾在荊州博物館館長(zhǎng)的鼎力幫助下,由敖朝宗自己出資在荊州市荊楚民俗博物館舉辦過(guò)一次展覽,第一次讓大家知道了荊州敖氏青銅器制作的存在。作品參加2010年上海世博會(huì)等各展會(huì),其中作品銷(xiāo)售情況非常不錯(cuò),缺憾是由于缺乏制作人手使得產(chǎn)品有限,存在供不應(yīng)求的狀況。這些經(jīng)歷更讓年過(guò)古稀的敖朝宗感覺(jué)到工藝瀕臨失傳的緊迫感,意識(shí)到必須打破家族傳承的脆弱性,打開(kāi)大門(mén),進(jìn)行不斷地交流,更多地走出去和讓更多人走進(jìn)來(lái)。他跨出了關(guān)鍵的一步申請(qǐng)成為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傳承人,將手藝公諸于世。“申遺”成功后,截?cái)嗔酥暗闹饕N(xiāo)售渠道而三年未開(kāi)張,全靠積蓄度過(guò)。后經(jīng)各方宣傳,以及國(guó)家提供了一個(gè)宣傳“非遺”文化的傳承園門(mén)店進(jìn)行宣傳與售賣(mài),生意才逐漸好轉(zhuǎn)起來(lái)。同時(shí)敖氏通過(guò)媒體向社會(huì)呼吁有志者前去學(xué)習(xí),而就目前來(lái)看,鉛錫刻鏤技術(shù)仍是以家族傳承為主,兩個(gè)兒子從2000年和2002年開(kāi)始學(xué)習(xí)技藝,從事傳承的工作。
我們?cè)诓稍L過(guò)程中了解到,鉛錫刻鏤技術(shù)有著特殊的傳承困難。首先想要將鉛錫刻鏤和青銅工藝學(xué)到精需要很長(zhǎng)的時(shí)間,因此前來(lái)學(xué)習(xí)這項(xiàng)技術(shù)的年輕人很少。再者由于金屬手工加工的特殊性,是火中求財(cái)?shù)墓に嚕霈F(xiàn)事故的幾率比其他如剪紙、木雕之類(lèi)的要高很多,并且制作工期長(zhǎng),在其中任何環(huán)節(jié)有疏忽,作為新手的學(xué)生可能會(huì)受到傷害,因此教方承擔(dān)的責(zé)任風(fēng)險(xiǎn)較大而很少開(kāi)展此項(xiàng)教學(xué)。敖朝宗認(rèn)為學(xué)校教學(xué)是傳承的重要途徑,前提是做好大量精細(xì)的準(zhǔn)備工作,從培養(yǎng)師資再到培養(yǎng)學(xué)生。一項(xiàng)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傳承,需要社會(huì)各方的努力,在多元渠道下實(shí)現(xiàn)工藝自身的社會(huì)價(jià)值則是最有力的傳承保護(hù)。
六、結(jié)語(yǔ)
隨著我國(guó)人民文化自信的增強(qiáng),對(duì)楚文化研究日益興盛,熱愛(ài)和研究傳統(tǒng)青銅文化的人增多。專(zhuān)業(yè)的技工對(duì)我們的文化和藝術(shù)研究提供著不可或缺的支持,兩者之間是可以相互促進(jìn)的。如果在這樣一個(gè)關(guān)鍵的時(shí)候,手工藝出現(xiàn)了失傳,將是莫大的遺憾,不知道要過(guò)多少年才能再找回,正如曾經(jīng)失落的青銅時(shí)代工藝經(jīng)過(guò)兩千多年才又一次隱約展現(xiàn)在我們面前一樣。
參考文獻(xiàn):
[1]陳岸瑛.時(shí)代轉(zhuǎn)折中的非遺傳承與傳統(tǒng)復(fù)興[J].裝飾,2016(12):16-20.
[2]李敏生.先秦用鉛的歷史概況[J].文物,1984(10):84-90.
[3]許慎.徐鉉,校訂.說(shuō)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shū)局,2019:295.
[4]劉彬輝.楚系青銅器研究[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4.
[5]陳振裕.中國(guó)古代青銅造型紋飾[M].武漢:湖北美術(shù)出版社,2001:10.
[6]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guó)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7]李志偉.有關(guān)曾侯乙尊盤(pán)鑄造方法的證明——論中國(guó)青銅時(shí)代的熔模技術(shù)[J].南方文物,2008(2):39-46.
[8]丁山.中國(guó)古代宗教與神話考[M],上海:上海書(shū)店出版社,2011:291.
作者簡(jiǎn)介:
胡艷,湖北美術(shù)學(xué)院講師。
彭蓉,湖北美術(shù)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