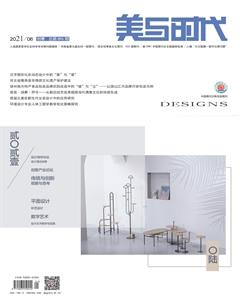“如一本小說”:馬蒂斯的書籍插畫研究
摘? 要:正如馬蒂斯所說,是藝術主宰了他的生命。從21歲拿起畫筆的到生命的終結,他一直堅持著藝術創作。但藝術巨匠馬蒂斯也有靈感枯竭的時刻,在缺乏靈感時他便從文學中攝取養分,獲得精神慰藉并為文學作品制作插畫。馬蒂斯的藝術離不開文學,2020年法國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舉辦的展覽《馬蒂斯:如一本小說》就是對馬蒂斯藝術生涯中鮮為人知的書籍插畫的探索與回顧。梳理馬蒂斯制作書籍插畫的歷程與其中包含的藝術思想,可以揭示馬蒂斯書籍插畫的現代價值。
關鍵詞:馬蒂斯;書籍插畫;藝術理念
一、馬蒂斯書籍插畫創作歷程
出生于法國南部勒卡多小鎮一個中產家庭的亨利·馬蒂斯,10歲時,在圣康丹鎮學習拉丁文和希臘文。18歲時,他前往巴黎學習法律。在巴黎讀書期間,馬蒂斯閱讀了許多文學類書籍并順利地完成了學業。畢業后,他在一家律師事務所擔任辦事員。這是一個只注重數量而不注重內容的工作,雇主要求他抄寫大量的存檔資料,但這些資料一般是無人去查閱的,于是馬蒂斯開始抄寫法國古典文學的代表作家拉·封丹的寓言故事來填滿這些枯燥的書寫紙。由此可知在21歲患病之前,馬蒂斯已經具有了一定的文化積累與文學修養。
正是馬蒂斯良好的文學修養讓他可以依據文學進行藝術創作并使作品時具獨特性。如1904年他創作的《寧靜、奢華、愉悅》,這幅畫絕對是他藝術生涯中的璀璨之作。《寧靜、奢華、愉悅》是馬蒂斯受到波德萊爾詩歌《西苔島之游》中的“在那里,一切如此美麗而秩序井然,豪華、寧靜,充滿歡樂”啟發進行的藝術創作[1]。雖然詩中描繪的是具有東方神秘色彩的室內場景,而馬蒂斯所繪的卻是一群裸女在南方的一個海灘上無憂無慮地消磨時間。
藝術大師馬蒂斯也面臨過靈感枯竭的階段,他認為“偉大的靈感來源是詩意的”,在靈感欠缺時他便轉向了文學的懷抱,從中吸取養分來進行藝術創作。20世紀30年代馬蒂斯開始創作書籍插畫,第一次嘗試是1930至1932年給象征主義詩人馬拉美的詩歌集做插畫,他每天清晨閱讀馬拉美的詩歌,愉快地閱讀完馬拉美的詩歌后才開始思考插畫的樣式。1935年他給意識流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的長篇小說《尤利西斯》制作插畫。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馬蒂斯的書籍插畫活動逐漸變多,如1936年他給法國作家亨利·德·蒙泰朗改編的神話《帕西法埃》制作插畫,并與亨利·德·蒙泰朗成為摯友,當馬蒂斯晚年臥病在床期間他們依舊保持著書信交流。1946年,他又為法國象征派詩歌的先驅夏爾·皮埃爾·波德萊爾的詩集《惡之花》制作插畫。從馬蒂斯的這些經歷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對圖像與文本進行了大量的混合與編排,并從中研習法國文學傳統。正是詩歌與書籍插畫將馬蒂斯從創造力的枯竭與脆弱中拉了出來并讓他在“二戰”期間尋求到了精神的慰藉,也激勵了晚年不便作畫的他以剪貼畫的形式于1947年制作了飽含他人生哲理的《爵士》一書。《爵士》生動地講述了他關于劇院和馬戲團的想法,書中包含色彩鮮艷的剪貼畫與閃耀著哲學火花的手寫文本。1941年至1948年,他為法國著名的愛情詩人龍薩的《情歌》制作插畫。1943年至1948年給中世紀法國宮廷詩人夏爾·德·奧爾良的《詩集》制作插畫。他是主動選擇給夏爾·德·奧爾良的《詩集》作插畫的,他在與魯維埃的通信中提到,“清晨閱讀夏爾·德·奧爾良的《詩集》讓他的肺里仿佛充滿了新鮮空氣”。他認為這位被英國俘虜的中世紀法國詩人的處境與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法國的處境相似,于是他以制作書籍插畫的形式表達他的反法西斯主義觀,并參加法國的文化抵抗運動。
二、馬蒂斯書籍插畫中包含的藝術理念
(一)藝術追求表現
馬蒂斯曾提出藝術可以通過兩種方法來表現:一是照原樣摹寫,一是藝術地表現。通過馬蒂斯的書籍插畫可以看到馬蒂斯追求的是“藝術地表現”[2]。他也曾說:“我所追求的,最重要的就是表現。”馬蒂斯認為不是所有的書籍都適合讓他去做插畫的,他需要書籍的內容具有一定的留白讓他去想象、去表現。
他第一次嘗試為書籍做插畫是給象征主義詩人馬拉美的《詩集》制作插畫。馬美拉《詩集》的特點在他所寫的《關于文學的發展》有著完美的詮釋,“詩寫出來原就是叫人一點一點地去猜想,這就是暗示,即夢幻”。馬拉美象征主義詩歌追求的不是客觀性質的描述,而是一種心靈狀態的傳達。馬蒂斯為《詩集》中的《牧神的午后》制作插圖(如圖1),這首詩描述的是在西西里島上的一個午后,半人半獸的牧神正在午睡,恍惚間他看到了水畔那美麗的精靈并與這些精靈度過了一段纏綿悱惻的時光,但當牧神醒來,他再分不清之前的浪漫究竟是夢境還是真實。馬蒂斯用簡單的線條勾勒了畫面右下角牧神半人半羊的形象,他正吹著雙管蘆笛對照詩中“哪有什么潺潺水聲?唯有我的蘆笛”,牧神身邊是六個動態各異的仙女。筆者認為,馬蒂斯是通過六個動態不同的仙女表達“是夢境還是真實”的寓意。畫面右上角的兩位仙女動態較為活躍是否是詩中所描述的“是仙女們倉皇逃奔”象征著“真實”,另外四個仙女在畫面中寧靜的或做或躺是否象征詩中所描述的“夢境”呢?馬蒂斯用最簡約的線條勾勒出詩歌中流動的身影,讓人們感受了詩歌中對美的追求與夢醒時分悵然若失之感。
筆者認為,正是馬美拉《詩歌》的中那含蓄微妙且帶有不確定性的朦朧意象可以賦予了讀者想象的空間,才讓馬蒂斯選擇了他的《詩歌》進行書籍插圖制作。在為馬美拉《詩歌》制作插圖之后也有出版商和作家邀請馬蒂斯來為他們的書籍制作插畫,但他回絕了許多,如蒙泰朗的《沙上的玫瑰花》。馬蒂斯認為蒙泰朗的《沙上的玫瑰花》已經描寫得包羅無遺了,已經沒有任何余地留給插畫去進行視覺補充了,蒙泰朗本人也承認了他所著作的《沙上的玫瑰花》已經把話說完了。他不喜歡“話都被它們說完了”的文學作品,他希望去表現內容有所留白的文學作品。
(二)引入符號
馬蒂斯在與他的朋友、詩人兼批評家阿拉貢的一次談話中提出:“一位美術家的重要性是由他引入美術語言的中的心符號數量多寡決定的。”[3]138從他書籍插畫也看出他注重在插畫中引入“符號”。
1947年出版的《爵士》是馬蒂斯用兩年時間創作的20張抽象剪貼畫。《爵士》里的作品大多題目具有詩意性和內容具有戲劇性。書中許多形象都是抽象的符號化的,具有不確定性,留給觀者想象的空間。如《爵士》中的《國王的悲傷》,畫題與作品本身對馬蒂斯來說并無什么聯系,它只是一種符號而已。畫面用三個不同的抽象色塊來構成人的形象,中間那個抱著提琴的黑色塊是否就是《圣經》中會彈琴的大衛王呢?馬蒂斯沒有解釋,留給觀者自己去思考想象。馬蒂斯通過鮮艷而明亮的色塊及不同形式的線條組合成能表達自己歡樂的心情的符號,如《爵士》中的《伊卡洛斯》(如圖2)。《伊卡洛斯》取材于希臘神話,伊卡洛斯借助蠟將鳥翼粘在雙肩來實現他飛行的夢想,但在他飛得忘卻自我時,離他越來越近的太陽將蠟融化了,他也不幸殞身大海。馬蒂斯所剪的伊卡洛斯,置身于明快的藍色背景中,他那舒展的身姿代表的是在天空飛行的歡樂,還是蠟融剎那間墜落大海的灑脫?畫面上黃色的星星賦予畫面輕快的韻律。而那顆紅色小點,則是整幅畫的點睛之筆,馬蒂斯仿佛將全部故事、所有精神都傾注在這一點上,讓它成為一個象征的符號,是灼傷伊卡洛斯的太陽還是伊卡洛斯那夢想飛行的心?
(三)撫慰心靈
馬蒂斯曾說:“我所向往的藝術,是一種均衡的、純粹的、寧靜的、不含使人不安或令人沮喪的成分的藝術。對于身心疲乏的人們,像一把鎮靜劑,或者像一把安樂椅,可以消除疲勞,享受寧靜、安憩的樂趣。”[4]1943年馬蒂斯便著手為夏爾·德·奧爾良的《詩集》做插畫,但是因為戰爭,直到1948年才完成。但正是這本《詩集》給了他心靈的慰藉。馬蒂斯認為這位被英國俘虜的中世紀法國詩人的處境與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法國的處境相似,他在閱讀這本《詩集》時感覺就像“草地上采到紫羅蘭一樣”。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馬蒂斯主動選擇給中世紀法國宮廷詩人夏爾·德·奧爾良的《詩集》制作插畫來表達他的反法西斯主義觀。同時他拒絕用丑陋的形式表現對戰爭的控訴,他選取了寧靜而優美的形象給法國人民以心靈的慰藉與鼓勵。在為奧爾良《詩集》做插畫時,他選取了“百合”這一符號來進行書籍插畫創作。他認為百合花最能表達夏爾·德·奧爾良的人品與他所處的環境和時代。在14世紀的法國,百合花已經成為了公認的法國君主政體的象征,是一個統一而強大的國家象征。同時百合在歐洲代表了“圣潔”與“復活”之意。馬蒂斯給夏爾·德·奧爾良的《詩集》里所作的百合花圖案(如圖3)都采取一種上升的姿態,配上各種顏色,對前后的書頁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
三、馬蒂斯對現代書籍插畫的啟發
(一)精確并非真實
1948年,在費城美術館舉辦了馬蒂斯作品的大型回顧展。馬蒂斯為這個展覽寫了兩篇短文,其中一篇就是《精確并非真實》。馬蒂斯指出,“藝術中具有說服力的并不是精確地復制自然或頗具耐心的細節的聚合,而是在于藝術家面對他選擇的對象時的深刻的感情,他對對象的專注和對其精神狀態的深入”[3]183。馬蒂斯書籍插畫中的作家個人肖像插畫不是憑空想象的,是他將作家的基本特征與精神特質結合后得來的。他會找作家的后裔進行調查,翻閱古老的法國史,參與油畫復制品創作。但他并不會完全依靠這些,他認為在那些作家的后代那里得到的都是外表特征,肖像插畫應當同時展露他們的精神風貌。于是他深入地閱讀作家的文學作品,從中感悟作家的精神風貌,然后再進行創作。無論是為15世紀的法國詩人夏爾·德·奧爾良還是19世紀的法國詩人波德萊爾作肖像插畫,他都是如此。
現代藝術家不應停留于表面的真實,應如馬蒂斯一樣該深入對象的精神狀態,并結合自己的藝術特色進行書籍插畫創作。藝術家可以從文學中攝取精華,但不能完全拘泥于原文。藝術家在接觸了需要作插圖的文學作品并對其有了深刻的認識后,就應放手大膽地創作。
(二)整體的平衡感
馬蒂斯在制作書籍插畫時追求整體的協調感與平衡感。他的第一本書馬美拉的《詩集》,插圖是銅版畫,所以他大多是用規則而纖細的線造型,不上陰影,他認為這樣印出來的插圖頁就如同沒有印刷過一樣干凈。讀者在打開書籍時,能夠得到一種干凈而輕盈的感覺,所以也有人稱馬蒂斯為“顏色與線條的游戲家”。馬蒂斯用雜耍演員手里的黑白球來比喻,圖文之間的關系,黑球是文字,白球是圖像,雖然彼此截然不同,但又交織在一起,藝術家應該讓他們成為一個和諧的整體。馬蒂斯在制作蒙泰朗的《帕西法埃》的書籍插畫時,插圖用的是膠版畫。黑底白線,用單線勾。插圖頁黑,文字頁面相對來說就白了。如何平衡?馬蒂斯通過畫面上的圖案把面對面的插圖頁和文字頁組合起來,使他們相互靠近,形成一個整體。然后,四周再用一條寬大的白邊把這兩個頁面都圈進去,把它們完全框在一起。馬蒂斯從書籍裝幀的角度認為黑白兩色的書籍給人一種陰郁不快的感覺。雖然,書通常都是如此的,但是,目前的情況是:很大的一頁紙,差不多滿版都是黑乎乎的。所以,馬蒂斯將篇首的大號字套紅。他又為這本書設計出一種格外莊重和典雅的字體,并且同文字和插圖這兩個已經確定的因素保持協調。
馬蒂斯的書籍插畫啟發現代書籍插畫與裝幀應該注重畫面整體的節奏與張弛,根據已經確定的因素,如文本內容與印刷形式等,進行書籍插畫創作與設計,使書籍整體達到和諧與統一。
四、結語
2020年法國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舉辦的展覽《馬蒂斯:如一本小說》的策展人維迪爾說:“在馬蒂斯的理解中,文字與繪畫的緊密關系就如同畫作與紙張。”文學作品揭示了人類精神世界,傳達了人類豐富的思想與觀念并給人以精神養分。馬蒂斯用流暢的線條來為文學作品制作插畫,插畫的內容已不單是文學的復述摹寫,里面蘊含了許多馬蒂斯個人的理解和主觀的現實。在制作書籍插畫過程中,馬蒂斯追求藝術的表現力,希望引入新的符號并認為藝術應給予人精神的慰藉。馬蒂斯制作書籍插畫的經歷啟發著現代書籍插畫時制作應該注意插畫的精確與真實,注重書籍的整體平衡感。
參考文獻:
[1]馬曉琳,李星明,田青雁.馬蒂斯[M].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43.
[2]伶俐.馬蒂斯藝術觀對設計的啟迪[J].西北美術,2015(3):98-100.
[3]弗拉姆.馬蒂斯論藝術[M].歐陽英,譯.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1987.
[4]何政廣.馬蒂斯[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64.
作者簡介:歐陽沁文,華中師范大學美術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