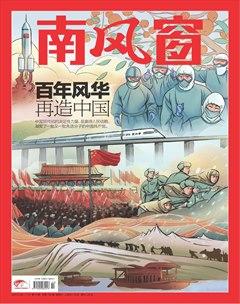好大學讓每個人找到適合自己的路
黃西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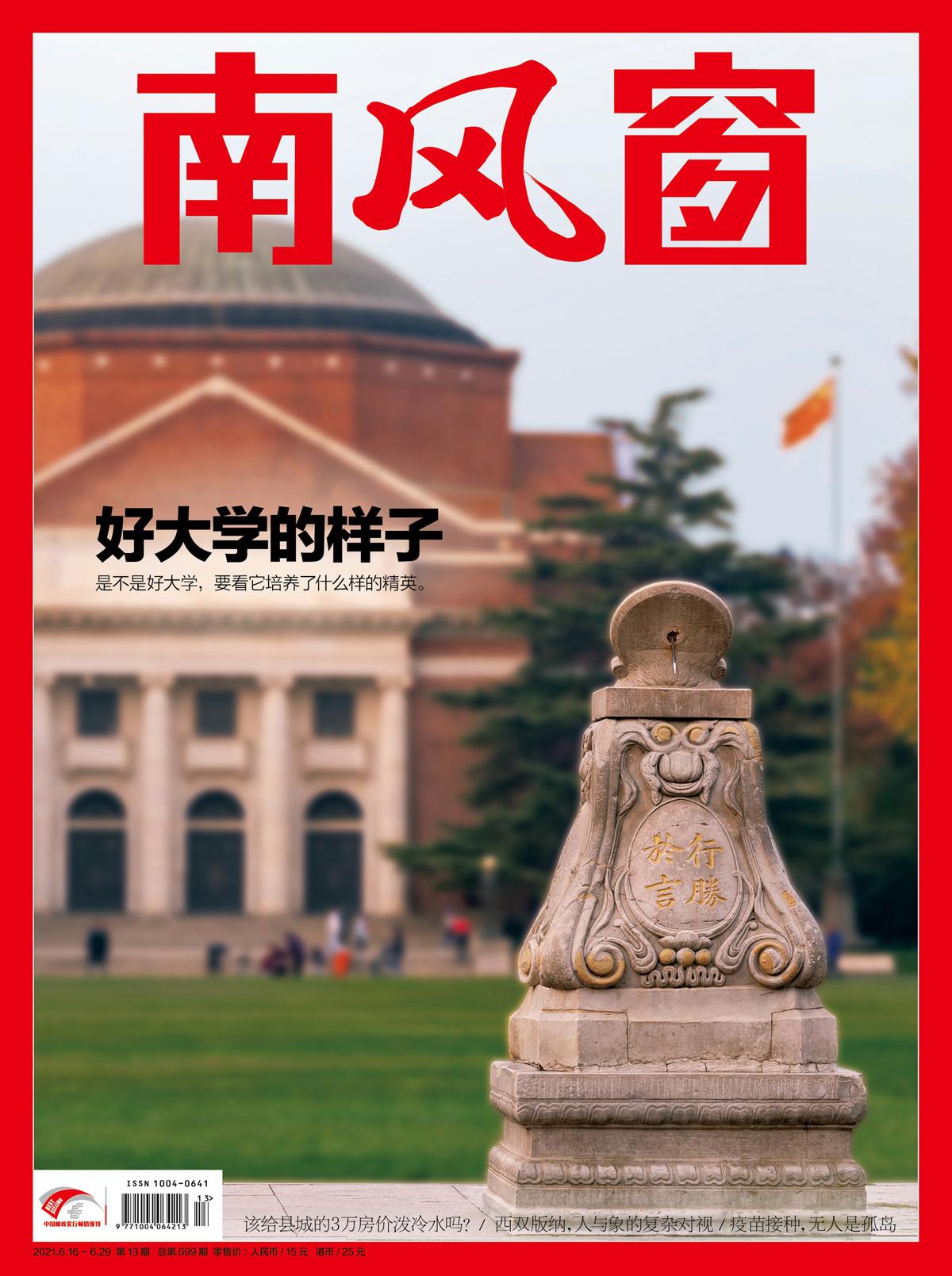
有兩點讓我覺得眼下探討“好大學的樣子”特別有現實意義。一個是眼下各地高考成績陸續放榜,考生們進入填報志愿階段,他們需要在選大學、選專業和選城市的靈魂拷問中,去嘗試著找到自己的答案,作出自己的選擇。二是好的大學如何對待教師和學生、教師和學生如何共同締造大學的文化和氣質,本身也值得關注。對于大學的定位和意義,我比較認同“科研往左,入世向右”的日本做法。雖然我們的現實不是以國立大學和私立大學來區分,但將大學分為科研方向和育人方向,大抵不會錯。
高中時,班主任兼語文老師給我們描摹的中文系學生的日常是,課業不多,社團活動豐富,有大把時間看小說、看電影,還可以自由談戀愛。這讓身處高三學習高壓的我們,充滿了期待。但等我上了大學,發現完全是另一種畫風:課程很多,大一要寫100篇作文,甚至還要學微積分和編程,看小說不是消遣而是任務,經常要熬夜刷書……唯一的好處可能就是“60分即過”。往后三年,也都有不算輕松的學習任務,主旨是磨練筆頭寫作、口頭表達,并初步體驗做學術的皮毛。畢業時,140多人的大系,談戀愛的屈指可數,大多數人都在為學業、實習、求職或考研忙碌。但回過頭來看,沒有一本書是白讀的,沒有一段路是白走的,所有的曾經才鑄就了現在的我。
我至今記得時任校長在一次接受采訪時,對“何為好大學”的闡釋。大意是,我們的大學,需要培養那些為人類命運、社會進步、科技發展不懈奮斗的年輕人,也需要容納那些孤獨的靈魂。我讀書的那幾年,雖然校園里隨處可見匆匆而過的忙碌身影,但那些青春的臉龐上,仍保留了與社會有一定距離的純粹和理想主義光輝,也時不時能在清晨或深夜的校園一角見到獨自徘徊的身影。十幾年過去了,據我對另一所大學的觀察,如今的學生越來越會為實際的、具體的事物忙碌了,這不能完全算是大學的“失靈”。大學本就是一個小社會,何況如今的社會發展更迅速,大學也更難“與世隔絕”,大學生們提前預演社會游戲規則,也沒什么不好。但我還是有些懷念我那個年代的大學。
另一個變化是,像我這樣本科畢業后直接工作,當年是主流,如今不是了。選擇讀研、讀博的學生越來越多,以至于有知名人士發文《本科值得一份好工作,不要失去就業欲》,這是一種善意而理性的提醒。不過越來越多學生選擇延長留在校園里的時間,不完全是大學和學術科研的魅力使然,也包含了許多復雜的現實因素,比如就業形勢對他們造成的壓迫感。要讓本科生有就業欲,需要以他們自身成熟的求職心態和扎實的求職能力打底,也需要充足的就業機會。這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大學和社會傾力協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