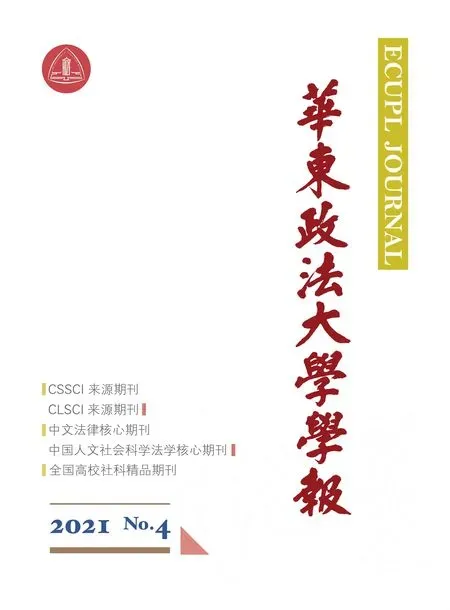論公民的疫苗接種義務——兼論《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第21 條的理解與適用
陳云良
一、問題的緣起
新冠肺炎疫苗的研發成功和附條件上市迎來了全球新冠疫情防控的轉折點,隨之而來的是如何依法依規有序規范地推進新冠肺炎疫苗接種工作。多份國內外調查報告顯示,各國民眾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疫苗猶豫(Vaccine Hesitancy)乃至反疫苗(Anti-vaccination)情緒。世界經濟論壇最新開展的一項針對全球15 個國家13500 名75 歲以下成年人對新冠肺炎疫苗接種意愿的調查研究表明,各國民眾雖然對新冠肺炎疫苗的接種意愿度均較高,但是在疫苗可獲得的前提下表示會立即接種或于一個月內接種的比例呈現較大差異,其中我國被調查民眾表示會立即接種的比例僅有23%,表示會于一個月內接種的比例僅有20%,在15 個國家中位居倒數第三位。〔1〕See Global Attitudes on A COVID-19 Vaccine, Ipsos survey for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March 11, 2021), https://www.ipsos.com/en/covid-19-vaccination-intent-has-soared-across-world.我國王志偉團隊對廣州市居民進行的新冠肺炎疫苗認知與接種意愿調研報告亦顯示,廣州市居民對新冠肺炎疫苗接種的知曉率高、接種意愿度強,但是即時接種的積極性并不高,更多出于對新冠肺炎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擔憂而持觀望態度。〔2〕參見王志偉等:《廣州市居民對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的認知與接種意愿調查》,載《現代預防醫學》2021 年第4 期,第732-737 頁。
在部分民眾出現疫苗猶豫的背景下,部分地區和單位采取強制接種辦法,強制接種引起了爭論,國家主管部門并不贊成這一做法。其實,強制接種在法律上并非不可取。美國馬薩諸塞州1855 年就通過了強制接種法,后來其他州也跟著仿效,對拒絕接種者處以罰款或拘役,有的甚至直接采取暴力手段進行強制接種。1902 年波士頓牧師雅各布森因為拒絕接種天花疫苗,被當地衛生局告上法庭,最后被法院判處有罪,并按接種法令被罰款五美元。后來,直至聯邦最高法院仍然維持了地方法院的判決,確認了州的強制接種權力。〔3〕參見李晶:《美國公共衛生管理權和民眾自由權利的博弈——基于“雅各布森訴馬薩諸塞州案”的解讀》,《世界歷史》2020 年第5 期,第35-39 頁。疫苗接種工作的推進需要在法治軌道上開展,新冠肺炎疫苗究竟應當作為免疫規劃疫苗成為公民之義務還是作為非免疫規劃疫苗交由公民道德自覺接種,應當交由法律來統一安排。
當下,我國學界對于疫苗接種的法律研究更多集中于疫苗相關權利的保障與救濟之上,而卻鮮少去審視公民疫苗接種的義務。然我國《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下文簡稱《基本醫療衛生法》)第21 條明確規定:“國家實行預防接種制度,加強免疫規劃工作。居民有依法接種免疫規劃疫苗的權利和義務。政府向居民免費提供免疫規劃疫苗”。因此,本文旨在通過規范分析方法,結合現有法律法規對《基本醫療衛生法》第21 條作出深度闡釋,以促進其正確適用,這不僅是當下依法有序規范推進新冠肺炎疫苗接種工作的重要前提,亦是后疫情時代我國依法實施公共衛生治理的重要任務。
二、何為“預防接種制度”?
《基本醫療衛生法》第21 條首句規定:“國家實行預防接種制度,加強免疫規劃工作”。為貫徹預防為主的指導方針,根據傳染病疫情監測和人群免疫水平,有計劃地實施疫苗接種,提高人群免疫力,從而達到控制和消滅某些傳染病的目的。雖然我國自古代便已有民間“種痘術”之記載,但現代意義上的預防接種制度建立時間相對較晚,自新中國成立之后才逐步形成。公共衛生學界通常以名稱為界將其劃分為計劃免疫前期、計劃免疫時期以及免疫規劃時期三個階段。〔4〕參見潘鋒:《國家免疫規劃有效保護廣大人民群眾健康和生命安全》,載《中國當代醫藥》2019 年第26 卷第29 期,第1-6 頁。然若以具體法律制度之形成為劃分基準,其可劃分為法制化前期與法制化后期。
在法制化前期,我國尚未建立統一的預防接種制度,更多是在中央政策指導下各地有針對性地推進預防接種工作。雖然原衛生部在這一時期亦發布了一系列指導性文件,但是并未形成統一的預防接種法律體系,缺少制度設計上的系統性、層次性。改革開放后,1980 年原衛生部發布的《預防接種工作實施辦法》是我國預防接種制度法制化的開端。《預防接種工作實施辦法》初步形成了我國現行疫苗分類制度、疫苗供應制度、疫苗接種制度以及疫苗損害救濟制度之基本框架,雖仍舊粗糙,但已初具總括式的體系化結構,并與隨后原衛生部發布的《預防接種后異常反應和事故的處理試行辦法》《關于試行預防接種證制度的通知》《全國計劃免疫冷鏈系統管理辦法(試行)》《計劃免疫技術管理規程》等規范性文件,初步構筑了一個涵蓋分類、供應、接種、損害救濟等多方面的預防接種法律體系。
1989 年頒布并實施的《傳染病防治法》于第12 條第1 款正式規定:“國家實行有計劃的預防接種制度。”這是預防接種首次被納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之中,從而使我國預防接種制度的法制化不再只是在規范性文件層面的橫向建構,而開始從縱向的法律層級中發展。隨后,國家不斷完善《母嬰保健法》《國境衛生檢疫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相關法律與預防接種制度的橫向銜接,并不斷制定和完善相關規范性文件。2019 年,《疫苗管理法》頒布,從疫苗的研發、上市、生產、流通、接種再到異常反應、損害救濟等方面形成更為全面和細化的制度框架,同年《基本醫療衛生法》亦將“國家實行預防接種制度,加強免疫規劃工作。居民有依法接種免疫規劃疫苗的權利和義務”寫進醫療衛生領域的“基本法”中。至此,我國形成以《基本醫療衛生法》為統籌,《疫苗管理法》與《傳染病防治法》為核心,各行政法規及部門規章為具體內容的兼具系統性和層次性的預防接種法律制度。
三、何以疫苗接種應成為義務?
《基本醫療衛生法》第21 條規定:“居民依法有接種免疫規劃疫苗的權利和義務”。為何需要將疫苗接種規定為公民之義務?在理論層面,為何免疫規劃疫苗的接種應成為居民之法定義務,可從道義主義與功利主義之中溯源其理論基礎。
(一)道義主義視角下的疫苗接種義務
免疫規劃疫苗的接種是一項護衛公共健康安全的公共衛生措施,這項法定義務首先源自道德義務或自然義務。道義主義所主張之道義,是以“義務和責任”為核心的道德理性,是一種先驗的自然理性。在這種自然理性的指引下,一個具備理性的人,即使在最原始的自然狀態亦會履行這種相互間的道德義務。而在社會契約的締結過程中,每個人為尋求一個更大的社會公意的庇護而對自身權利進行一定的讓渡,允諾政府為維護社會秩序之需要對其自由設置必要的限制,從而部分道德義務便轉化為法定義務而具備國家強制力。〔5〕參見 [法]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2009 年版,第28 頁。1905 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雅各布森案判決中就直接援用了這一社會契約理論來確認公民接種疫苗的義務。〔6〕參見 [美]勞倫斯?高斯汀、林賽?威利:《公共衛生法:權力?責任?限制》,蘇玉菊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 年版,第128 頁。對于個人而言,道義主義強調其行為應當立基于一種穩固、合理、克制之欲望,恰當處理自身與他人利益之關系。體現在傳染病防治情境之下,個人既有免于受他人感染之權利,亦有避免陷他人于傳染病危險之道德義務。在疫情流行期間,個人道義要求每個人遵守國家各類疫情防控措施,接受緊急行政權對公民自由的克減或者為公民所設立的新義務;而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觸者,則要接受隔離觀察、治療并接受流行病學的調查和追蹤;當疫苗研發成功后,國際社會均處于疫苗接種的賽跑之中,為避免落后于他國形成免疫落差,社會需通過大量個體的接種達至群體免疫從而形成社會保護屏障,此時道德義務亦要求符合接種條件的個體“應接盡接”,承擔起護衛國家、社會公共健康安全的公民責任。
而對于國家而言,道義主義強調國家在制定法律制度、分配公民權利與義務時應當符合正義規則,即所謂“惡法非法”。在國家公共衛生治理尤其是傳染病防治過程中,國家亦基于道義主義而具有特定之職責,國家應全力救治感染患者、拯救生命,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置于第一順位,不能因患者之年齡、身份、職業而存在差別對待,剝削他們獲得國家救助的權利。〔7〕習近平:《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載《人民日報》2020 年01 月28 日,第1 版。同時,國家道義亦要求國家應及時推動新藥、傳染病疫苗等產品的研發,并將其作為公共產品予以供給,不斷為更好保障民眾生命健康權創造條件。但是,公共衛生治理從來不是國家的獨角戲,公共健康的維護必然需要國家道義與個人道義的協同,國家道義在為保障公共健康創造條件,個體亦要接受來自公權力對其自由的必要限制并承擔起法律所賦予之特定義務。由此,本屬于道德義務的疫苗接種便開始逐漸被國家公權力所采納并通過立法的形式轉變為法定義務。
(二)功利主義視角下的疫苗接種義務
道義主義雖然解釋了免疫規劃疫苗接種義務成為法定義務的義理性來源,但是其在強調道德義務的同時,卻不可避免地會陷入“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8〕參見陳倫華:《論道德本質的功利與非功利二重性》,載《前沿》2005 年第10 期,第196 頁。道義主義天然有一個缺陷,即它只立足于行為本身是否正當,而對行為的實際效用卻鮮少考量。而實際上,國家在分配公民權利義務之時不僅需要義理性的支撐,亦需要對其社會效益進行考量。因為當一項道德上的權利或義務被法律所確立后,便意味著國家公權力需要付諸公共資源保障其該權利之行使或督促該義務之履行,而即使作為公共意志的國家,其所能配置的資源亦有其上限,這種有限性注定了即使再強大的政府也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能力去認知、應對一切風險。〔9〕參見謝暉:《COVID-19,透過“唯一知”“知無涯”看治理原則——基于“哈貝馬斯命題”的思考》,載《學術界》2020 年第7 期,第5-21 頁。從國家的角度而言,當資源總量一定時,有效地配置法治資源、合理分配權利義務無疑能使國家更好地應對各類風險,通過法經濟學之方法來選擇最有效益、最能增加社會最大幸福的那一部分義務往往是現代社會國家治理所追求的。因此,道德義務轉化為法定義務又需要功利主義的補正。
功利主義作為當代法經濟學的法理基礎,〔10〕參見金夢:《法經濟學基礎理論的新發展——以芝加哥法經濟學派為中心》,載《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6期,第155-161 頁。特別是在制度設計的論證中,得到了極為廣泛的應用。所謂功利主義,即以某一行為或措施對利益相關者所產生之實際效用或利益(增大幸福或減少不幸之傾向)來作為贊成或非難該行為或措施的標準。〔11〕參見 [英]邊沁:《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時殷弘譯,商務印書館2000 年版,第58 頁。功利主義是一種典型的結果論,它認為如果一項措施對個人而言符合“自利原理”,對社會而言又符合“最大幸福原理”,那么這項措施無疑是正當的。〔12〕參見 [英]約翰?穆勒:《功利主義》,徐大建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15 頁。在這個層面上,功利主義為國家預防接種制度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一方面,疫苗接種于個人而言,能使機體獲得相應疾病的抵抗力,從而減小了其患病之概率,有利于個體自身健康;而另一方面,免疫規劃疫苗是一種具備正外部性的公共產品,接種者在減少自身患病概率的同時,對其他人而言也是一種外部收益。同時,相較于其他傳染病防治措施,疫苗接種帶來的保護更具有徹底性和持續性,也具有更高的社會效益。哈佛大學風險分析中心曾對587 個有關于挽救生命的政府干預項目進行成本與收益評估,其中凈成本由低到高排序中,兒童免疫、孕婦產前保健、流感疫苗全民接種位居前三,兒童免疫的凈成本更是小于零,這足以證明疫苗接種本身是遠超越其他傳染病防控措施的最能有效配置國家傳染病防治資源的方式。〔13〕參見 [美]富蘭德,古德曼,斯坦諾:《衛生經濟學》,王健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74 頁。因而,在可負擔的前提下,將部分疫苗的接種作為一項法定義務予以確立,并由國家財政免費提供,無疑是既符合自利原則,又能促進社會最大幸福的增加之正當舉措。
(三)道義功利論下的疫苗接種義務
可以說,功利主義為將免疫規劃疫苗接種確立為法定義務奠定了經濟基礎并提供了效用機制,但是有時單純的功利論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在一種極端的自利原理下,功利主義的論證也不可避免地會導致自我挫敗,出現損害社會公平的現象,使之最終又必須以道義主義來作為其歸屬。在現代人類疫苗接種史上,不可避免地會因個體差異或是疫苗質量而發生小概率的疫苗損害事件,而另一層面,免疫規劃疫苗是一種具備正外部性的公共產品,而公共產品的這種正外部性是難以分割的,其由整個社會共同享有。群體免疫理論也表明,當足夠數量的個體通過預防接種而形成免疫屏障時,就會存在少數人無須接種而能夠享受群體免疫所帶來的保護,就是所謂的“搭便車”(free-rider)現象,〔14〕參見陳共:《財政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第23-26 頁。即不承擔成本和風險而免費享用公共產品的利益。因而在一個極致的利己主義者眼中,在不考慮其對他人和社會之責任時,不必承擔任何接種疫苗風險而能夠享用群體免疫之福利對其而言,將會比冒小概率的異常反應風險去接種疫苗更“利己”,因而如果不通過法律將免疫規劃疫苗的接種確立為普遍的法定義務而僅僅依靠民眾道德自覺地履行,無疑會有部分人企圖通過“搭便車”而逃避接種,損害社會的公平。
甚至有人同樣從后果論來為此尋求辯護,認為當已存在大量的個體主動接種疫苗時,單獨的個體不接種疫苗的行為對群體免疫的影響或對社會所增加的風險幾乎沒有統計學上的差異。〔15〕See Pierik R., “Mandatory Vaccination: An Unqualified Defence”, 35(2)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381-398(2018).這種辯護無疑是錯誤的。首先,其忽視了風險的累加性,忽略了無數個個體的自利行為所導致的風險累加將有可能從量變引發質變,使得群體免疫失效。其次,群體免疫雖然能為少數人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護,但是這種保護并不具備絕對性,雖然從人傳人的角度而言,接種者減少了其傳染給少數未接種者之機會,但是未接種者依舊有可能從其他渠道感染,而這個感染的未接種者依舊有可能傳染給另一個未接種者。再者,這種辯護所稱的統計學差異是將個人置于全國人口的比重而言,而相對的,每個人生活在不同群體之下,當對其所處之家庭、社區、學校、工作場所而言,更多是一種小范圍的群體聚集,隨著所處環境人數的減少,個人的比重亦隨之增加,因而僅僅從個人在全國所占之比重大小來忽視自身不接種疫苗所帶來的社會風險或是接種疫苗所增加的社會效益,是片面的、孤立的、不客觀的。最后,不接種疫苗而享用群體免疫利益的權利,其本質是一種社會稀缺性資源,依據羅爾斯正義理論中的“使最差者獲得最大好處”原則,〔16〕參見 [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年版,第8 頁。這種稀缺性社會資源所應當分配的對象,是不具備疫苗接種條件而被豁免疫苗接種義務的弱勢群體,他們或因年幼、年邁,或因疾病、體質而無法接種疫苗,因而他們需要獲得這種稀缺性權利去彌補他們不能自身產生免疫力之缺陷,也是他們,才是每一個主動履行義務接種疫苗的人所愿意和希望守護的人。而當一個符合疫苗接種條件卻拒絕接種的人竊取了這種稀缺性的社會福利時,無異于讓一個犯錯的人獲得利益,他刺痛了這個社會最基本的公平。一如阿爾貝托?朱比林尼(Alberto Giubilini)所指出的,拒絕履行疫苗接種義務而享受群體免疫福利的人和逃避稅收卻享受著公共財政帶來的一系列公共服務的人一樣,都違背了社會基本的公平正義。〔17〕Giubilini, A., “An Argument for Compulsory Vaccination: The Taxation Analogy”, 37(3)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446-466(2020).因此,將預防接種行為從一種道德義務引向法律義務,不僅是為了更好地配置公共健康資源,其最終仍舊回歸于守護社會的基本道義之上。所以,雖然功利主義在行為方式上為國家進行制度安排、有效配置權利義務提供了良好的法經濟學理論支撐,但最終仍應以道義主義為底線和歸屬,尤其在緊急情況下,道義動力遠大于經濟考慮。只有在堅持公平正義的前提之下,使用功利主義尋找最能有效配置權利義務的方式,形成兩者相結合的道義功利論,方能為免疫規劃疫苗接種成為法定義務提供良好理論支撐。
在著名的雅各布森訴馬薩諸塞州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正是使用了道義功利復合理論做出了劃時代的判決。該案主審大法官哈倫認為:“美國憲法所保護的個人自由并非任何時候、任何背景下不受限制的個人權利,個人在很多方面有必要服從社會公益。”聯邦各州有權力實施公共衛生措施保護所有成員免遭疾病侵害。〔18〕Jacobson v. Massachusetts. 197 U.S.26(1905).同時依據功利主義等原理對各州基于治安權而制定的疫苗強制接種制度做了一定的限制,該案的劃時代意義在于在美國這一推崇個人自由的國度確認了公民的疫苗接種義務和政府強制接種疫苗的權力,有利于人類應對傳染病疫情,對后世影響深遠,至今強制接種疫苗制度仍在發揮作用。2021 年5 月美國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員工起訴該醫院強制員工接種疫苗,被法院駁回。該判決仍然援用了1905 年雅各布森案判決所確認的強制接種并不違憲的原理。〔19〕Jennifer Bridges V.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4:21-CV-01174 (2021).
四、從“免疫規劃疫苗”的釋義看疫苗接種義務的類別與次序
“居民依法有接種免疫規劃疫苗的權利和義務”的第二層要義在于“免疫規劃疫苗”之理解,“有接種疫苗的義務”與“有接種免疫規劃疫苗的義務”是截然不同的,后者通過對疫苗本身的類型化進一步形成公民疫苗接種義務的類別與次序,因此,對疫苗接種義務的探討首先應建立在“免疫規劃疫苗”的法教義解釋之上。
(一)“免疫規劃疫苗”的法教義解釋
我國疫苗分類制度肇始于1980 年,最先于《預防接種工作實施辦法》中采用“基礎免疫制品與非基礎免疫制品”之分類,隨后伴隨著預防接種制度的發展,疫苗分類也相繼歷經“計劃免疫疫苗與非計劃免疫疫苗”“免疫規劃疫苗與非免疫規劃疫苗”之名稱變換,并且納入國家免疫規劃的疫苗種類也不斷增加。目前,國家免疫規劃所確定的疫苗已從4 種增加至14 種,可預防傳染病亦從6 種擴大至15 種。
但是,對于《基本醫療衛生法》中“免疫規劃疫苗”的理解,大多數人卻陷入其僅為上文所述的“國家免疫規劃確定的疫苗”之誤解中,認為其僅是一種明確的有限列舉的目錄。而事實上,《疫苗管理法》第97 條早已對“免疫規劃疫苗”給予了明確的界定,免疫規劃疫苗不僅包括國家免疫規劃確定的疫苗,還包括省級政府補充的免疫規劃疫苗、應急接種疫苗和群體性預防接種疫苗。而在此四類免疫規劃疫苗之中,又可因其適用情形之不同,進一步劃分為常規接種疫苗和緊急接種疫苗。
常規接種疫苗,是指我國已經建立起相應傳染病的群體免疫或目標接種率,僅需對后續適齡兒童或目標人群按常規程序予以接種以維持人群免疫率的免疫規劃疫苗,目前我國已確立了包括乙肝疫苗、卡介苗、百白破疫苗等14 種常規接種疫苗,同時,依照《疫苗管理法》第41 條第3 款規定,省級人民政府在執行國家免疫規劃時,根據轄區的傳染病流行情況、人群免疫狀況等因素,可以增加常規接種疫苗的種類和劑次。因此,常規接種疫苗可以歸納為“14+X”類,即國家免疫規劃確定的14 種常規接種疫苗和地方政府補充增加的常規接種疫苗。
而緊急接種疫苗,則是指在傳染病暴發、流行的緊急狀態下對特定范圍內的部分或全體人群進行的緊急接種的疫苗,包括應急接種使用的疫苗和群體性預防接種所使用的疫苗。“應急接種”與“群體性預防接種”既有相似亦有差別。相似之處在于兩者均是針對傳染病暴發、流行的緊急情況而生,疫苗接種均存在時間上的緊迫性。而差別之處在于,應急接種主要強調對“重點人群”進行接種,即對有可能暴露的對象或密切接觸者進行接種,而群體性預防接種的目標人群則比應急接種疫苗的“重點人群”更為廣泛,是指對某一行政區域(甚至跨行政區域乃至全國范圍)內的符合疫苗接種條件的全體居民進行的疫苗接種。目前我國僅在國家衛生行政部門發布的2016 年版《預防接種工作規范》中,列舉了三種應急接種疫苗,即在發生出血熱、炭疽和鉤端螺旋體病疫情時,可對重點人群進行相應疫苗的應急接種。而群體性預防接種僅僅是一種概括式的表述,并無列舉式規定,我國正在普遍接種的新冠肺炎疫苗即屬于群體性預防接種疫苗。因此,緊急接種的免疫規劃疫苗亦可歸納為“3+X”類,即三類已明確列舉的應急接種疫苗以及其他應急接種或群體性預防接種所使用之疫苗。
由此得出,“免疫規劃疫苗”是一個包含常規接種疫苗與緊急接種疫苗的合集,既包括明確列舉式的規定,亦包括概括式的規定,其并非一個完全封閉的法律概念,而是留存了面對紛繁復雜的現實情況而適時調整的空間。同時,除國家免疫規劃確定的疫苗是全體公民(居民)的共同義務外,其他三類免疫規劃疫苗均呈現明顯的地域性和對象性傾向,因此,免疫規劃疫苗的判斷也必然存在地域性和對象性,對于免疫規劃疫苗的判斷不能局限于其是否歸屬已明確列舉的14 種常規接種疫苗以及3 種應急接種疫苗范圍之內,還需要依據現實情況以及政府所做的補充接種、應急接種或群體性預防接種等行政決定中進一步研判。
而非免疫規劃疫苗,是指排除免疫規劃疫苗后的其他疫苗,屬于居民自愿接種的權利范疇,但是非免疫規劃疫苗對于傳染病防治也有積極的社會效益。非免疫規劃疫苗的接種在一般情形下只體現出一種弱道德義務,這種道德義務在無傳染病疫情時,其幾乎不伴隨任何道德上的可要求性。但這種道德義務會隨著傳染病疫情的出現而開始加強,甚至在緊急狀態下某些非免疫規劃疫苗的接種所產生的社會效益會大于常規疫苗的接種,從而被作為應急接種或群體性預防接種疫苗而納入免疫規劃疫苗之列,而如若該傳染病將長期存在,更有可能從緊急接種疫苗進一步轉化為常規接種疫苗。因此,任何一種疫苗并不固定歸屬于免疫規劃疫苗或非免疫規劃疫苗,其對應的義務亦非一成不變,無論是常規接種疫苗的“14+X”抑或緊急接種疫苗的“3+X”,“X”既是法律賦予政府及疫苗種類動態調整的空間,亦是法律調整公民疫苗接種義務范圍的空間。
(二)公民疫苗接種義務的類別與次序
疫苗分類之目的,實質上是形成居民疫苗接種義務的不同類別與次序,進而讓公民知曉不同情形之下其疫苗接種行為之輕重緩急,進而促進義務的履行(見圖一)。其中,免疫規劃疫苗與非免疫規劃疫苗分別對應著公民的法定義務與道德義務,而在免疫規劃疫苗之中,常規接種疫苗與緊急接種疫苗又分別對應著公民的常規義務與緊急義務。
緊急義務與常規義務的劃分是依照義務所設立之目的,其是在于調整常態下的公民行為還是調整非常態下的公民行為進行的。緊急義務是國家為應對法定的危險事由(災害、瘟疫、戰爭等)而對公民施加的必須實施或不得實施特定行為之要求,其與國家的緊急干預權相對應。〔20〕參見李昊:《緊急狀態的憲法實施機制與完善路徑》,載《法學論壇》2021 年第1 期,第103-112 頁。由于緊急狀態下,國家社會秩序屬于非正常狀態,國家權力的運行必然以恢復社會常態秩序為首要價值,國家緊急權力的運行不可避免會對公民權利義務產生重大調整。〔21〕參見程關松、方久:《防疫應急措施致困人員臨時救助的法律保障》,載《法治社會》2021 年第2 期,第111-119 頁。而此時所產生的緊急義務,具備如下三大特點。
其一,義務內容的臨時性。公民的常規義務往往由法律明確宣告,內容上具備明確性和可預見性,如遵守交通規則、依法納稅等義務,而緊急義務伴隨緊急狀態下的國家干預而生,其所面臨的突發情況往往只能預防卻難以預判,唯有當具體情況發生之時,才能“因地制宜”地采取緊急干預措施,進而確立公民需要配合履行之緊急義務,因此緊急義務的內容多具臨時性。
其二,義務履行的時限性。公民緊急義務的設立,乃因國家在緊急狀態下需要擺脫更多束縛,以獲得更高的社會治理效率,從而快速消除風險,恢復社會秩序,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促進公民緊急義務的履行本質上是國家行使緊急行政權的所欲達致的目的之一,因此該義務的履行也被限縮于更短的時限之內,甚至要求即時履行。
其三,義務沖突的優先性。社會的秩序是全體社會成員共同需要的,公民緊急義務是為維護社會秩序,保障公共安全而生,其背后是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根據整體利益優于個體利益原則,緊急義務的履行亦具有優先性,當其與其他公民常規義務發生沖突時,在不違背比例原則的情況下,應當優先履行公民的緊急義務。
由上可知,在義務的次序上,法定義務高于道德義務,而在法定義務之中,緊急義務又高于常規義務。當然,這種次序上的排列只是一般理論上的排列,并不排除特殊情形。并且,所謂義務之次序往往見諸兩種義務存在沖突且不可調和之時,此時方可依義務之次序進行必要的舍棄,而當不存在義務沖突之時,無論常規義務抑或緊急義務,都是公民應當依法履行之義務。

圖1 疫苗類別與義務屬性對應圖
五、公民疫苗接種義務與權利的調和
“居民依法有接種免疫規劃疫苗的權利和義務”的第三層要義在于“權利與義務”供述于一體。“居民依法有接種免疫規劃疫苗的權利和義務”在法律規范的分類中屬于權義復合性規范,其不同于單純的授權性規范或義務性規范。〔22〕參見謝暉、陳金釗:《法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第94-96 頁。當權利與義務復合于同一規范時,不可避免地會產生邏輯上之沖突,即權利的“可為”和義務的“必為”在行為模式上產生了矛盾,也因此,權利義務復合型規范自其誕生之初便不免承受了較多詬病,甚至有的學者主張取消此類復合性規范或將其表述為“公民不可放棄之權利”。〔23〕參見趙正群:《公民權利義務復合的憲法規范》,載《法學研究》1991 年第2 期,第92-93 頁。所以,對于“居民依法有接種免疫規劃疫苗的權利和義務”需要進行恰當的解釋,于本句之理解需結合《基本醫療衛生法》第21 條末句“政府向居民免費提供免疫規劃疫苗”來進行體系化解釋,明確其權利屬性,從而與義務進行調和。
(一)公民的疫苗接種權利是受益權而非自由權
“政府向居民免費提供免疫規劃疫苗”是從國家義務層面反向確證公民疫苗接種權利是一種受益權而非自由權。雖然作為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之一的預防接種,其權利屬性源于健康權。而健康權作為一項《憲法》所確立的公民基本權利,〔24〕《憲法》第21 條規定:國家發展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鼓勵和支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國家企業事業組織和街道組織舉辦各種醫療衛生設施,開展群眾性的衛生活動,保護人民健康。其本身體現著積極和消極的二元屬性。〔25〕參見陳云良:《健康權的規范構造》,載《中國法學》2019 年第5 期,第64-79 頁。在積極屬性上,公民的健康權表現為公民享有向國家請求健康相關服務給付的受益權,〔26〕參見曹艷林:《論健康權的受益性與國家的給付義務》,載《中國衛生事業管理》2009 年第1 期,第27-28 頁。其對應著國家負有為公民提供健康相關服務的基本義務;而在消極屬性上,公民的健康權則表現為個體具有選擇某些健康服務的自主權,其對應著國家及其他權利相對人的尊重和容忍、不干涉之義務,這種消極屬性更多體現在個體參與醫療服務的過程中,如在個體罹患非傳染性疾病時,自主選擇是否就醫,何處就醫,接受何種醫療服務等。
但是,疫苗接種的權利基礎不僅僅源于個體健康權,還包括公共健康權。公共健康權作為一種以社會全體成員健康保障為目標,由社會成員全體共享的健康利益,其與個體健康權不同之處在于,對于個體健康權而言,公民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責任人,〔27〕參見王晨光:《疫情防控法律體系優化的邏輯及展開》,載《中外法學》2020 年第3 期,第612-630 頁。因而在個體健康權之上,既有國家應予保障之受益權,亦有個體自主選擇之自由權,并依據“有效選擇理論”在具體情境之中發揮積極健康權或消極健康權之效力。而在公共健康權之上,強調國家主導,公民協同,國家是護衛公共健康安全的第一責任人,強調通過實施公共衛生監督、提供公共衛生服務等方式保障公共衛生安全,營造有利于全體社會成員生存發展的自然、社會、生活環境。因此,公共健康權的權益具備整體性,每個個體都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之下享受這種整體性利益,這種利益不可能具體地分割到每一個成員身上,并由該成員決定是否享有、是否放棄,因而其消極自由屬性被大量克減,而只表現出受益權的屬性。〔28〕參見呂成龍:《公共健康獲益權的法理探源及權利建構》,載《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5 年第3 期,第52-59 頁。因此,在《基本醫療衛生法》第21 條中,“疫苗接種的權利”是與“政府向居民免費提供規劃疫苗”的國家義務相對應的公民受益權,而不能將其理解為自由權,否則,就會陷入前文所述權利與義務的行為模式沖突。
(二)公民的疫苗接種義務必須以受益權為前提
“政府向居民免費提供免疫規劃疫苗”不僅揭示公民疫苗接種的權利屬性是受益權而非自由權,更表明這種受益權的享有或者說國家履行保障這種受益權的義務是公民負擔免疫規劃疫苗接種義務的必要前提。政府應當以公共財政來購買免疫規劃疫苗,免費向公民提供疫苗接種服務。但是更進一步需要思考的是,國家應當免費提供一種什么樣的疫苗接種服務或者說公民的受益權除了免費之外還應當在哪些層面得到保障?公民接種疫苗承擔著一定的不良反應風險,因此國家提供的疫苗接種服務,應當不僅僅是“免費”的,還應當是盡可能“安全”的。國家應確保疫苗質量的安全、有效,確保足夠疫苗數量的供應,確保接種人員接種技術水平的合格、規范,確保有適宜的場地和足夠的配套醫療物資,確保有成熟的應對不良反應的機制和應對異常損害的國家補償機制等等。通過上述條件,盡可能減少人為因素導致的接種風險,從而切實保障履行疫苗接種義務的公民的生命健康安全。
如此,當疫苗接種的權利和義務屬性復合于一體時,權利和義務的原本屬性分別在一定程度上發生變化,權利的消極自由屬性被義務的必然性所限制而表現為受益權屬性,而義務的負擔性也一定程度被權利的受益性所緩和,表現為國家提供免費、安全的疫苗接種服務為基本前提,從而產生一種全新的復合形態。
(三)權利和義務在法治實施中的調和
疫苗接種權利和義務研究也不能僅止步于對其屬性的探討,更重要的是要如何在更為具體的規范設計甚至是法治實施過程中通過對兩者的調和、運用來達到引導、促進公民主動進行疫苗接種的目的,從而提升其現實意義。因此,在推進疫苗接種工作的過程中,除了使用宣傳教育、行政指導等常規手段,在具體規范設計或實施之中,尚需運用權利與義務調和的手段來促進疫苗接種工作的開展。
其一,通過對權利的保障或促進來增加公民疫苗接種意愿。公民疫苗猶豫很大程度在于對疫苗接種風險的擔憂之上,因而政府除公開疫苗接種相關數據之外,尚可通過建立完善的疫苗異常損害的補償或救助機制,通過保障公民的救濟權利來緩解公民對異常損害的擔憂,減少接種遲疑。英美國家多通過以國家財政兜底的方式建立起新冠異常損害的補償或救助機制,以緩解公民的接種焦慮。〔29〕Se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ocial Care, Government to add COVID-19 to Vaccine Damage Payments Scheme, GOV.UK( Dec.3,202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overnment-to-add-covid-19-to-vaccine-damage-payments-scheme; Will the Countermeasures Injury Compensation Program provide compensation to individuals injured by COVID-19 vaccines? NRSA( January 2021),https://www.hrsa.gov/cicp/faq#covid.除此之外,亦可通過利益聯動機制,賦予積極接種新冠肺炎疫苗者其他領域的相關優待,如提高醫保報銷比例、稅收優惠等等,以促進公民接種意愿。
其二,通過施加不利益負擔來督促公民履行疫苗接種義務。目前,我國對拒不履行免疫規劃疫苗接種義務的公民所設置的法律責任較少,僅于《疫苗管理法》第92 條規定針對監護人不履行兒童常規接種義務,并且僅局限于訓誡罰,而對應急接種、群體性預防接種義務的違反目前尚未有具體規定。因此,亦可通過完善對在緊急狀態下拒不履行應急接種、群體性預防接種等義務的行政處罰來督促公民履行疫苗接種義務,比如在訓誡罰之外增設罰款等新的行政處罰類型。而在當下,隨著“疫苗護照”“疫苗健康碼”等國際或國內政策的實施,〔30〕參見張力:《國際旅游業蓄勢重啟 完全恢復仍前路漫漫》,載《中國文化報》2021 年3 月20 日,第3 版。接種新冠肺炎疫苗在可預見的未來許將成為國際出行、交流或從事特定職業、活動的必要前提,因此未接種者在相關方面之權利也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因此,在法治實施過程中,國家既可通過保障和增進公民相關權利的正向激勵,亦可通過施加不利益負擔或限制某些權利的反向懲戒等多種措施來促進公民履行疫苗接種義務。但是在各種措施的選擇過程中,亦要把握好正向激勵與反向懲戒之間的平衡,避免矯枉過正,使公民產生抵觸情緒。
六、有條件實施強制接種制度
在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背景下,新冠肺炎疫苗在世界范圍內本質上是一種稀缺性資源,在許多落后國家,甚至“一苗難求”。而我國通過不懈努力的自主研發,終于在疫苗研發的賽跑中搶占先機,多款疫苗在國內附條件上市,其中科興中維和北京生物兩款新冠肺炎疫苗被世界衛生組織納入緊急使用清單,且為緩解全球疫苗分配不均、促進發展中國家及落后國家疫苗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作出重大貢獻。
在國內,我國新冠肺炎疫苗的接種工作按照“兩步走”方案,第一步主要是針對部分重點人群開展接種,包括從事進口冷鏈、口岸檢疫、醫療疾控等感染風險比較高的工作人員以及前往中高風險國家或者地區去工作或者學習的人員;第二步,隨著疫苗產量的逐步提高,通過有序開展接種,符合條件的群眾都能實現“應接盡接”,逐步在各人群當中構筑起人群的免疫屏障,來阻斷新冠病毒在國內的傳播。〔31〕參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2020 年12 月19 日新聞發布會介紹重點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種工作”,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官網,http://www.nhc.gov.cn/xwzb/webcontroller.do?titleSeq=11359&gecstype=1,2021 年4 月18 日訪問。這“兩步走”方案實質上是先實行重點人群的應急接種,再逐步進行全面群體性預防接種,其本身便是“免疫規劃疫苗”法教義解釋所涵蓋之內容。同時,國家亦將新冠肺炎疫苗作為公共產品向民眾免費供給,也滿足了《基本醫療衛生法》第21 條“政府向居民免費提供免疫規劃疫苗”的前置性要求,以上可見,新冠肺炎疫苗在事實層面已然符合成為“免疫規劃疫苗”的實質要求。
新冠病毒變異速度越來越快,變異毒株的傳播力越來越強,死亡率越來越高,而至今仍然沒有找到有效的治療方法,也沒有開發出有效的藥物,接種疫苗是目前應對疫情最有效的手段。盡管我國目前的接種率大幅提高,人們的接種意愿越來越強,但是仍然有不少居民抱觀望態度,甚至有人抵制。需要通過法治手段提高接種率。我們論證了新冠肺炎疫苗屬于《基本醫療衛生法》和《疫苗管理法》所規定的“免疫規劃疫苗”,公民有接種疫苗的義務。借鑒美國強制接種制度,根據國家為了社會公共利益有權克減個人自由的基本原理,為了整個社會免受新冠病毒持續侵害,早日恢復正常工作生活秩序,我們可以有條件設立強制接種制度,推進《基本醫療衛生法》第21 條的實施。通過立法規定某些特殊(人員密集型)行業工作人員,高中風險區居民必須接受疫苗接種,不得拒絕。對于拒絕接種者可以設定罰款、隔離等行政處罰,同時限制拒絕接種者進入特殊行業工作。各地新冠疫情防控機構可以為新冠肺炎疫苗接種者的工作、生活、出行設定更多便利,引導更多居民主動接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