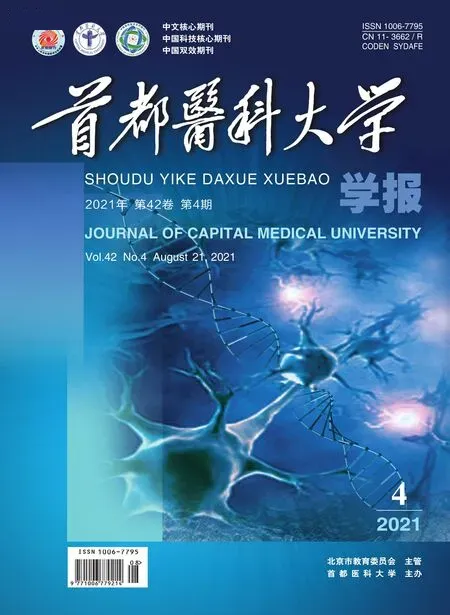老年髖部骨折患者圍手術期輸血和危險因素
岳 睿 李曉玉* 楊明輝 張 萍
(1.北京積水潭醫院干部科,北京 100035; 2.北京積水潭醫院創傷骨科,北京 100035)
2018中國死因監測數據集[1]顯示,跌倒是我國65歲及以上人群非故意傷害死亡的第一位原因。95%的老年髖部骨折是由跌倒造成的[2]。髖部骨折約占老年人骨折的23.79%[3]。預計到2030年,每年將有30萬例髖部骨折患者。這對患者和醫療保健系統來說,是一個顯著且迅速增長的經濟負擔[4]。目前治療髖部骨折的方法有保守治療和手術兩種,手術治療能減少臥床時間、讓患者早日下床,減少臥床相關并發癥,已被大多數醫師所采用[3]。老年髖部骨折患者圍手術期常合并貧血,糾正貧血最快速有效的方法便是異體紅細胞輸血(allogeneic red blood cell transfusions,ABT),約半數的髖部骨折患者接受了ABT[5]。老年髖部骨折患者圍手術期ABT常見的危險因素包括術前入院血紅蛋白(hemoglobin,Hb)低、高齡、女性、低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股骨粗隆間骨折、美國麻醉醫師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nesthesiologists,ASA)分級高、手術持續時間長等[4,6]。目前許多研究[5-7]已確認ABT存在許多嚴重的不良反應,如急性溶血性輸血反應、血源性感染(如肝炎、人類免疫缺陷病毒)、心血管風險增加、住院時間延長、住院費用增加、血源緊張等。由于老年人對輸血的耐受性差,更容易出現輸血相關并發癥。更好的術前規劃和評估患者ABT的需求,將有助于降低患者圍手術期ABT風險。因此,本實驗以老年髖部骨折患者作為研究對象,研究他們圍手術期ABT的危險因素,幫助臨床醫生識別高危患者,對可干預的因素進行早期干預,降低圍手術期ABT,對不可干預的因素早期識別,充分備血,以保證圍手術期用血安全。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從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因髖部骨折入住北京積水潭醫院老年創傷骨科病房的患者中納入1 112 例符合入選標準的患者,其中男性308例(27.7%),女性804例(72.3%),患者平均年齡(80.4±7.5)歲。所有入選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入選標準:①年齡≥65歲;②低能損傷所致髖部骨折(如站立高度跌倒、骨質疏松等);③受傷后3周以內的新鮮髖部骨折行手術治療;④無慢性肝病、血液系統疾病等出血性疾病病史。排除標準:①軟組織開放性骨折;②多發骨折;③病理性骨折;④合并其他部位出血。
1.2 方法
收集患者圍手術期的資料,包括年齡、性別、骨折類型、BMI、合并疾病(如高血壓、糖尿病、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腦血管疾病、慢性肺病)、圍手術期是否服用抗血小板藥物(阿司匹林和/或氯吡格雷)、入院Hb、血小板計數(platelet,PLT)、凝血酶原時間(prothrombin time,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血清白蛋白(albumin,ALB)、骨折至手術時間、ASA分級、麻醉類型(全身麻醉或椎管內麻醉)、手術持續時間、術中出血量(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IBL)(術中所用紗布增加的質量+引流瓶中出血量)和圍手術期ABT的情況。
基于限制性輸血政策,只給Hb低于80 g/L的患者或Hb低于100 g/L,但生命體征不平穩或有明顯癥狀[心率>100 次/分、收縮壓<90 mmHg(1 mmHg=0.133 kPa)、胸痛、大出血或極度虛弱]的患者輸血。患者是否需要輸血由臨床醫生決定。大多數患者在術后輸血,只有少數術前就滿足了ABT指征的患者才在術前輸血。所有患者圍手術期應用低分子肝素抗凝、術中使用氨甲環酸(tranexamic acid, TXA)治療。
1.3 統計學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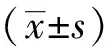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情況
1 112例患者中563例(50.6%)圍手術期有ABT記錄,其中僅有5例(0.9%)ABT在術前,絕大多數(99.1%)術后有ABT記錄,圍手術期平均ABT量為(3.3±2.0)U,其中64.2%的患者ABT≤2U,20.0%的患者為(3~4)U,15.8%的患者ABT>4U。股骨頸骨折的患者611例(54.9%),股骨粗隆間骨折的患者501例(45.1%)。
2.2 單因素分析
將患者根據是否有ABT分為2組進行單因素分析顯示,兩組患者在年齡(P=0.000)、性別(P=0.045)、骨折類型(P=0.000)、BMI(P=0.000)、入院Hb(P=0.000)、PT(P=0.000)、APTT(P=0.009)、ALB(P=0.000)、合并糖尿病(P=0.019)、ASA分級(P=0.000)、麻醉方式(P=0.012)、手術持續時間(P=0.007)和IBL(P=0.000)等方面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詳見表1。

表1 老年髖部骨折患者圍手術期ABT的單因素分析
2.3 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歸分析
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高齡(P=0.000)、股骨粗隆間骨折(P=0.000)、BMI低(P=0.017)、入院Hb低(P=0.000)、ASA分級≥Ⅲ級(P=0.022)、全身麻醉(P=0.049)和IBL多(P=0.000)是老年髖部骨折患者圍手術期ABT的獨立危險因素,其中入院Hb的Wald值最大,詳見表2。

表2 老年髖部骨折患者圍手術期ABT的逐步Logistic回歸分析Tab.2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erioperative ABT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hip fracture
3 討論
關于老年髖部骨折患者圍手術期輸血率,既往國內外文獻報道不一。本研究中圍手術期ABT率為50.6%, Smeets等[6]研究了388例手術治療的老年髖部骨折患者,其圍手術期的輸血率為41%。Arshi等[4]的研究中含8 416例老年髖部骨折患者,發現術后輸血率為28.3%。這可能與各研究中的研究對象的年齡、骨折類型、合并疾病、輸血政策等有關。北京積水潭醫院是以骨科和燒傷科為重點科室的三級甲等大型綜合醫院,所接診的患者很多是經基層醫院轉診而來的,患者一般情況差、病情相對復雜,這有可能造成本研究中ABT率相對偏高。
傳統意義上,輸血是為了維持Hb高于100 g/L和紅細胞壓積高于30%,這被稱為自由輸血策略[8]。近年來,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了術前多模式患者血液管理的概念,以減少輸血和輸血相關并發癥。基于此概念,制定了限制性輸血策略。在該策略中,當Hb低于80 g/L或有貧血癥狀時,患者需要輸血[8-9]。既往研究[10]表明,采用限制性輸血策略,在不增加術后30 d病死率和心肌梗死、卒中、肺炎、血栓栓塞和感染等發病率的情況下可明顯降低ABT率,而且在輸血后不良反應及節約用血方面顯著優于非限制性輸血[11]。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采用限制性輸血策略。
本研究結果顯示,老年髖部骨折患者圍手術期ABT與入院Hb、骨折類型、IBL、年齡、BMI、ASA分級和麻醉方式獨立相關。本研究中輸血組平均入院Hb為(108.3±16.5)g/L,顯著低于未輸血組(128.6±12.6)g/L(P=0.000)。此結果與既往許多研究[4,12-14]一致。且本實驗顯示,在所有危險因素中,入院Hb的Wald值最大,說明該因素對老年髖部骨折患者圍手術期ABT的影響最大。Desai等[15]研究顯示,術前Hb每增加10 g/L,圍手術期輸血風險降低約30%。這是由于Hb低本身就是ABT的指征,此外還跟術前Hb低的患者在面對手術和失血等應激的時候,免疫反應和代償能力低下有關。
造成術前貧血的原因很多,比如:①骨折出血、消化道出血等導致的失血性貧血;②造血原料缺乏所致的營養性貧血。③慢性感染、炎癥、腫瘤等引起的慢性病性貧血[7]。老年人由于常常合并多種疾病、對造血原料的吸收和利用減低,造血儲備減少,更容易合并術前貧血。
髖部骨折主要包括股骨頸骨折和股骨粗隆間骨折,股骨頸骨折為囊內骨折,股骨粗隆間骨折為囊外骨折[3]。與既往研究[4,15-16]結果類似,筆者發現股骨粗隆間骨折的患者,其ABT的風險明顯高于股骨頸骨折患者。分析其原因是由于囊內骨折后關節囊內壓力增加,造成填塞效應,整體失血少;囊外骨折后,無此填塞效應,且暴露的骨表面積更大,造成囊外骨折后失血明顯高于囊內骨折[17]。此外,本實驗中所有股骨粗隆間骨折患者均采用髓內針治療,在開放髓腔和擴髓過程中會破壞髓腔血管,增加失血量[18]。
筆者還發現IBL是ABT的獨立危險因素,輸血組IBL(200.6±119.1)mL,顯著高于未輸血組(151.8±103.5)mL(P=0.000)。與Wang等[12]的研究結果一致。一般情況下,患者的輸血需求與患者總失血量有關,包括IBL和圍手術期隱性失血量,IBL增多可能導致有效血容量減少,從而增加輸血風險[14]。有研究顯示,使用TXA能降低髖部骨折患者圍手術期出血量和輸血率,且不會增加術后血栓栓塞事件或其他不良事件的風險[19-20]。TXA是一種合成的抗纖溶劑,它通過阻斷賴氨酸結合位點來競爭性抑制纖溶酶原激活,進而抑制血塊分解,減少失血和輸血[19]。因此本研究中所有患者均于術前30min靜脈輸注TXA,行關節置換術的患者,在此基礎上加術中TXA關節腔內注射。
在本研究中,輸血組平均年齡為(82.9±6.9)歲,明顯高于未輸血組(77.8±7.2)歲(P=0.000),與既往研究[4,14-16]結果類似。年齡較大的人群器官功能減退,面對手術應激的代償能力弱,更容易在術后出現生命體征不平穩及急性失血相關癥狀,從而增加了ABT的需求。
與既往實驗[4,21-22]結果類似,本研究顯示,較低的BMI是圍手術期ABT的危險因素。Frisch等[21]研究了超過2 300例患者,發現全髖關節和膝關節置換術后,BMI高的患者輸血率較低。作者認為,BMI對輸血風險的保護作用可能是因為隨著BMI增加,總體血容量增加。雖然肥胖患者在手術過程中可能會因為較大的切口而失血較多,但與BMI低的患者相比,他們在特定手術過程中失血量占總血量的比例可能較低[21]。因此,相同的失血量對高BMI患者的影響要小于低BMI患者。
本研究顯示ASA分級≥Ⅲ級是老年髖部骨折患者圍手術期ABT的獨立危險因素。本結果與Wang等[14]和Sathiyakumar等[23]的研究結果類似。Sathiyakumar等[23]的研究表明,與ASA分級Ⅰ級患者相比,ASA分級Ⅳ級的患者接受輸血的可能性是前者的14.71倍。究其原因可能與ASA分級高的患者合并癥多、器官功能障礙和代償能力差有關。
本研究的數據顯示,全身麻醉的患者ABT的風險增加,此結果與Wang等[12]和何永軍[24]的研究結果一致。這可能是由于全身麻醉對血流動力學的影響更大,術中出現低血壓的風險高,為了糾正低血壓,除了必要的藥物治療外,很有可能會進行ABT,從而增加了ABT的需求[12,24]。
人們可能會認為,當患者等待手術時,骨折部位會持續失血,從而導致更大的失血和輸血風險。然而本研究卻并未發現骨折至手術時間延長會造成圍手術期ABT增加, Desai等[15]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這可能與骨折部位形成血腫有關。延遲手術有可能使骨折部位的血腫最終穩定,從而減少了活動性出血、IBL和圍手術期ABT[15]。Mattisson等[13]研究了987例髓內針治療的股骨粗隆間骨折和股骨粗隆下骨折的患者,發現與24 h內手術相比,延遲手術超過24 h,患者術前輸血率明顯增加,而圍手術期和術后輸血率方面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
本實驗中長期服用抗血小板藥物的患者,圍手術期均未停藥。這些患者因為心腦血管疾病的一級或二級預防長期服用抗血小板藥。這些疾病會損害血管內皮細胞,阻礙其分泌抗血小板因子,從而導致血小板聚集和血栓形成[25]。長期服用抗血小板藥者立即停藥有可能引起血栓形成和炎癥前狀態,使手術復雜化[25]。因此,這部份患者圍手術期未停用長期抗血小板藥。與Abdulhamid等[25]的實驗結果相同,筆者并未發現抗血小板藥物影響圍手術期ABT。
性別是否影響老年髖部骨折患者圍手術期ABT,目前尚無統一結論。Arshi等[4]的研究顯示,女性是髖部術后輸血的獨立危險因素。Desai等[15]的分析也發現,女性輸血的可能性是男性的1.54倍。原因尚不清楚,考慮可能與女性的基礎Hb低于男性有關。然而,也有研究者[6]認為女性并非老年髖部骨折患者圍手術期ABT的危險因素,本研究中單因素分析顯示,輸血組與未輸血組女性患者所占比例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75.0%vs69.6%,P=0.045),經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歸分析提示女性并非老年髖部骨折圍手術期ABT的獨立危險因素(P=0.611)。然而還需要多中心的較大的樣本量來進行進一步評估。
輸血增加了并發癥的發生率,并導致血源緊張、住院時間延長、住院費用增加等。對于老年髖部骨折患者,這些問題不容忽視[26-28]。針對年齡、骨折類型這些不可變的危險因素,醫務人員能做的唯有術前充分備血以保證圍手術期的用血需求。針對術前貧血、BMI、ASA分級這些因素則需要醫院和社區的共同努力,加強健康宣教,綜合制定慢病管理的合理方案,提高老年人的基礎健康狀況,改善其營養狀態。而針對麻醉方式、IBL等,則需要臨床各科室醫生緊密協作、綜合制定適合患者的手術和麻醉方式,降低老年髖部骨折患者圍手術期的ABT需求。
本研究有幾個局限性:首先,本研究是回顧性分析,不能排除其他潛在因素對結果的影響;其次,本研究所有數據均來自一家醫院;最后,缺乏長期隨訪數據,納入這些數據將有助于改善此類研究。因此,未來有必要進行前瞻性多中心的實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