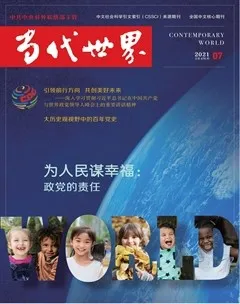中國的復興及對世界新秩序的影響
【伊拉克】阿迪勒·阿卜杜勒馬赫迪
法國學者阿蘭·佩雷菲特在1973年出版了名為《當中國覺醒時世界將為之顫抖》的著作,很多人對此不以為然。彼時中國是第三世界國家,民生凋敝,經濟社會發展困難重重、舉步維艱。眾所周知,早在1816年,在圣赫勒拿島流放的拿破侖一世就曾說過:“中國,還是讓他繼續沉睡吧,一旦覺醒,整個世界將為之顫抖。”
1972年,中國人均收入為132美元,世界排名第114位;美國當年人均收入為6094美元,世界排名第2位。2019年,中國人均收入達10262美元,世界排名前進至第68位;美國人均收入65118美元,排名跌至第9位。47年中,中國人均收入增長了約77倍,而美國僅增長了約10倍。1972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為0.114萬億美元,世界排名第七,美國則以1.279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一。2019年,中國GDP達14.342萬億美元,躍升至世界第二,逼近美國的21.374萬億美元。美國GDP在47年間增長了近16倍,而中國增長了約126倍。據估計,中國經濟將在2028年超過美國,而不是此前估計的2033年。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中歐貿易額高達5860億歐元,比歐美貿易額5550億歐元多出310億歐元。
實際上,因中國崛起而顫抖的不是整個世界,而是在過去幾個世紀長期掠奪中國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財富、損害他們權利、遏制他們發展、想方設法恢復殖民主義的那些國家。
中國復興與西方復興不同
亞洲人民、第三世界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視中國崛起為福音,他們可加以效仿并從中受益。既然中國能夠擺脫被殖民的命運和對殖民者的依附關系,不再積貧積弱,而且擁有發達的技術與先進的學術機構、經濟機構和管理機構,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那么為什么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不能從中國的發展經驗中獲得啟發呢?
中國的復興,靠的不是殖民和掠奪他國,中國也不熱衷于將自己的發展模式、文化、制度和標準強加于人。從根本上講,中國的復興靠的是艱苦奮斗和動員人民的力量。中國的復興走的是一條平衡之路,既從傳統思想和實踐探索中汲取營養,也學習借鑒他國,尤其是西方國家的經驗。據《全球經濟展望》(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數據統計,2019年中國的對外投資額占GDP的1.09%,而1993年中國對外投資額為零。既然中國能取得這樣的成就,能夠養活和教育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其他國家為什么做不到呢?
人們曾從西方文藝復興中受到啟發,試圖學習借鑒其經驗并從中獲益。但文藝復興之后,西方帶給世界的卻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西方優越論”和種族主義,不斷侵略、占領、掠奪、封鎖、剝削、制裁、打壓和歧視其他國家,導致這些國家歷史傳統中斷、社會撕裂、發展道路封閉,還因殖民者分而治之的理念和強加的邊界劃分而陷入戰爭。在此背景下,世界被分為北方現代發達國家和南方貧窮落后國家。
在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過程中,中國根據國內實際情況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并實現了全國解放。在發展的過程中,中國沒有完全摧毀舊傳統,也沒有完全西化,而是中西合璧,有意識地將傳統儒家文化和科學社會主義結合起來,實現了洋為中用、古為今用。中國付出鮮血和生命的代價、經歷痛苦和失敗的洗禮所取得的成功和積累的寶貴經驗為世界提供了一種不同于西方的發展模式。中國依靠強大的動員能力,不斷發展基礎設施和支柱產業,將廣袤的國土通過高效的交通網絡連接起來。中國根據本國國情和國力,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勞動生產方式,通過發展進步和公平競爭,而不是脅迫和征服為東方贏回了榮譽和勝利。
邁向世界新秩序的途徑是
融合、共生和競爭而非霸權
新的世界秩序除了融匯東西方文明之外別無選擇,它不應該是任何形式的霸權、控制和強加的價值觀。世界秩序既不是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也不是伊斯蘭教、基督教、猶太教或其他任何形式。世界秩序應將這一切融會貫通,多種制度和諧共生、彼此對話交流,制定公平標準,協調各方訴求,給予所有民族和國家平等機會。新的世界秩序應該是公正透明的,不應由秘密的或半秘密的以“國際社會”為幌子的團團伙伙把持。現在所謂的“國際社會”在某些領域只代表了少數幾個國家和團體,他們只想控制金錢、權勢和要害部門,利用壓制手段、媒體、網絡、銀行、軍事行動和情報等控制其他大多數國家,他們運作的方式缺乏透明度,而且以犧牲人類普遍利益為代價。
世界各國享有的權利和義務應該像一個國家的公民那樣,無論貧富都享有均等機會。國家不分三六九等,世界上不存在一個絕對善治、和平的國家,也沒有一個絕對無賴、恐怖主義的民族。當一個國家有侵略他國的想法和行為時,國際社會應該有能力界定這種侵略行為,并根據國際公認的標準采取統一立場。如果沒有界定侵略、恐怖、不義及自由和奴役相關概念的統一公認標準,某些國家就不應以國際社會的名義將這項權力據為己有,并剝奪別國權利。那些有過殖民他國、歧視他國和侵略他國歷史的國家,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這些遺產,并且夢想著“重操舊業”。占領巴勒斯坦領土的定居者和給予他們支持的國家就是最好的例證。聯合國譴責殖民主義和侵占他國權利的行為,并在《聯合國憲章》第十一章及一系列決議中都闡明了殖民地國家獲得獨立的重要性,強調民族自決,譴責種族主義、殖民主義、恐怖主義和跨大西洋奴隸貿易,承諾消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要求殖民者給予殖民地賠償,將殖民行為視作反人類罪行。
“一帶一路”是歷史實踐的
延續
歐洲人為了繞開“絲綢之路”進行了海上冒險,哥倫布為探尋香料產地印度的遠海航行就是一例。誠然,歐洲人在海上冒險的過程中證實了地球是圓的、發現了新大陸,為人類社會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部分貢獻。然而,啟蒙運動帶來的新科學和地理大發現帶來的成就,被西方用來推行殖民主義,并且這種殖民入侵的規模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必須看到,西方國家取得的任何一項成就,都是以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更大破壞為代價的。這就解釋了為什么當今世界存在北方和南方、西方和東方、發達國家和落后國家的差別。人類能力的提高以打破生活和環境平衡為代價。過去幾個世紀,各洲、各國的聯系被割裂,以攫取利潤、利己主義和享樂主義為核心的野蠻生活哲學代替了包括精神與物質、個人與集體、人類與自然的平衡哲學。“一帶一路”倡議正是要恢復被毀掉的這一切。
“一帶一路”倡議是對“絲綢之路”的復興。“絲綢之路”是由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德·里奇霍芬于1877年提出,用以描述連接亞非歐各國的關系網路。這張文明之網已延續千年,千年之前的東方和亞洲,無論在經濟、科學方面還是在管理或精神方面,都是世界文明的重要中心。隨著殖民主義興起,亞洲的中心地位衰落了。“絲綢之路”是古代世界的物流、文化、社會網絡,是文明互鑒、各國往來、人民交流的網絡,但西方殖民主義撕裂了這一網絡。
令一些國家感到恐懼的中國復興、東方復興和“絲綢之路”復興,是回歸平等和公平競爭,是對歧視、高傲自大和不公平發展的摒棄。轉向東方并不意味著放棄西方,而是東西方各自發揮所長,不以犧牲對方利益為代價來建立自己在歷史和現實中的地位,不再是讓自己富,讓他人窮;讓自己文明,讓他人落后;讓自己成為價值觀、標準的制定者,讓他人成為接受者。
中國復興了“絲綢之路”這一古老工程,回應了世界各國人民的根本訴求。過去是各國爭先恐后去中國,現在是中國積極擁抱世界各國。無論誰跟誰交往,目標都是互利共贏,有些國家竟然企圖歪曲這一事實。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東方各國、亞洲、西方甚至整個世界的復興都具有重大意義。
截至2021年1月30日,中國已經同140個國家和31個國際組織簽署205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從根本上說,古代“絲綢之路”為古代世界各國探索和了解中國提供了通道,為他們深入了解包括絲綢制作在內的中華文明奧秘打開了大門。東西方之間的貿易往來是東方和亞洲復興的一個重要因素,“絲綢之路”為雙方帶來了各自所需的商品,同時也促進了文化、宗教、習俗、經驗、精神和社會價值觀等的交流和傳播。經過幾個世紀不均衡、不公平的殖民主義秩序后,“一帶一路”倡議成為回歸均衡、公平的正常秩序的有效途徑。“絲綢之路”活力的回歸是東方、亞洲國家、非洲及整個世界活力的回歸。共建“一帶一路”是時代的呼聲,就像古代“絲綢之路”是歷史所需一樣。正如“絲綢之路”幾千年來服務于人類文明和交往,“一帶一路”倡議也是如此。“一帶一路”是世界各國的復興之路,其目的是促進世界各國交流互鑒,而不是毀滅其他文明或者竊取其財富。
中國的復興遵循
歷史發展規律
第三世界國家并沒有因中國的崛起而感到憂慮,中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給予第三世界國家多方面的幫助,如民族解放、國家發展以及對價值觀和傳統的保護等。中國尊重別國的主權、傳統和價值觀,不像西方國家那樣強推本國的制度、發展模式和價值觀。我們還注意到中國共產黨的經驗與其他國家共產黨的經驗不同,它無意讓別國效仿,而是讓各國根據本國國情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無論是社會主義道路、資本主義道路還是其他道路,沒有任何一條發展道路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中國遵循人民戰爭思想,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實現了民族獨立和解放。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遵循國內和國際市場規律,充分發揮市場力量,統籌考慮需求、質量、成本、競爭和優先事項等,不斷取得新的發展。不同于蘇聯注重數量先于質量、國家需求先于人民需求、中央需求先于地方需求、缺乏國內國際充分競爭的發展模式,中國尊重市場規律與消費者訴求,以此為基礎制定政策標準和生產規范,其生產的商品在質量和成本上甚至優于西方國家的產品。因此,西方國家只能通過貿易保護主義和“妖魔化”中國來抵消中國的影響力、阻止中國商品的出口。中國的發展模式擁有真實而強大的力量,不僅能夠幫助整個世界,而且能夠使自身實現永續發展并消除可能存在的一些缺點和不足。西方社會在福利水平和保護公民權利等方面達到了發達階段,但這些成就的取得并非一蹴而就,其前提是保持長期統一穩定并不斷積蓄力量,從而遏制各種矛盾和分歧。歷史已經證明,未來也將見證,如果國家能力被削弱,那么無論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還是其他任何模式,自由的范圍都會縮小,承受分歧的能力也會下降。
中國是包括伊拉克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伙伴和支持者
中國幫助第三世界國家制定發展規劃,在國際舞臺上支持第三世界國家追求民族解放、獨立和維護國家主權。中國直接或間接地幫助第三世界國家改善其中下層民眾的生活狀況,為他們提供質優價廉的商品,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和現實境遇。
就伊拉克而言,中國在所有問題上都和我們站在一起。中國尊重我們的主權和意愿,不會像其他國家那樣將自己的發展模式、價值觀或政策強加給我們。誠然,中國的確需要能源。但中國進入伊拉克之后與我們真誠合作。早在2008—2009年期間,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CNPC)就與伊拉克石油部簽訂合作協議,而其他國家的石油公司都猶豫不決。這些協議也是中伊雙方成功合作的開端,中國成功幫助伊拉克將石油工業產能和出口量從世界排名第八位和第十位分別提升至第四位和第三位。目前,伊拉克在歐佩克國家中石油工業產能和出口量都居第二位。中國公司在伊拉克石油工業中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通過技術人員交流將許多新技術新經驗帶給伊拉克。
伊拉克與中國建立了油貿收入擔保合作機制,即“伊中油貿合作協議”,這為伊拉克提供了復興動力。“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了強有力的合作框架,“伊中油貿合作協議”為伊拉克經濟、政治、安全和社會等各方面可持續發展提供了金融、科技、制度和法律等方面的工具,使伊拉克能夠完成復興所需的大型項目。協議使伊拉克一勞永逸地擺脫了食利制度,擺脫了國家財政預算因國際石油市場波動而搖擺的局面,擺脫了只能造成爛尾工程和成本浪費的充滿腐敗的執行框架。這種合作模式可以推廣到其他國家。
西方“妖魔化”中國的行為證明了東方的勝利和西方的失敗
當前,西方“妖魔化”中國的行為與他們之前“妖魔化”其他任何尋求發展、進步、經濟多元化、不按其既定統一決策行事的國家并無二致,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對西方而言,制裁異己是那么容易,而決定對異己是嚴厲制裁還是寬大為懷,依據的是他們自己利益得失或者對象國是否接受他們充滿偏見的單方面觀點。21世紀第二個十年后期,中美友誼隨著特朗普上臺及“美國優先”政策的提出而終結。在美國采取一系列單邊主義政策后,中美分歧不斷擴大,隨之而來的是西方“妖魔化”中國行為的不斷升級、范圍不斷擴大。世紀之交時,大多數西方民眾(超過60%)對中國持肯定態度。然而,由于西方不斷“妖魔化”中國的行為和其他一些原因,西方民眾對中國的看法變了。
中國的復興、經濟高速增長和取得的偉大成就震撼世界。世界見證了中國偉大的成就、現代化的能力和適應現代社會工作生活方式的速度。過去,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通過在中國大量投資獲益,他們的公司進入中國后開始取得創新和成就。但當中國開始在西方投資獲益、在全球貿易中占有越來越大的份額,建立通信、貿易和工業體系并在高科技領域(如月球和火星發射探測器)取得突破,政治影響力和存在感開始在其周邊甚至世界范圍內上升的時候,西方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他們開始“妖魔化”中國并渲染中國“崛起”的威脅。
無論是出于恐嚇目的還是陳述現實,很多人都在談論中國超越美國,東方超越西方;還有人在談論西方的失敗。但事實上,沒人要打敗西方,摧毀西方及其文明、成就、科學和能力不符合人類的利益,就像毀掉東方不符合人類的利益一樣。目前,西方仍然是強大的,擁有強大的能力和創新的動力。誠然,一切地區和國際的殖民政策、侵略政策和種族歧視政策都已被打敗或將被打敗,這不僅僅針對西方,而是針對所有國家。外部力量既無意愿也無能力打敗西方,西方只能被自己擊敗。若西方國家繼續抱殘守缺,堅持以有形或無形的方式稱霸世界,為了少數國家的利益犧牲大多數國家的利益,堅持雙重標準,黨同伐異,就會不戰而敗。人們越來越相信,破壞性的沖突不符合人類的利益,相互合作、彼此接納才符合人類的利益,而且是大勢所趨。西方國家曾經為人類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如果不重新審視自己的歷史、經驗以及與其他國家的關系,不在世界體系中重新定位自己,將會失去所獲得的一切以及整個世界的信任。令人欣慰的是,西方有很多領導人、社會人士和青年力量對此抱有同感。
未來,各國將會獲得平等發展的權利,不再被掠奪、制裁和壓迫,不再使用暴力,不會產生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壓迫者將會被自己打敗。無論壓迫者是來自何方,被壓迫者都會跨出反抗的第一步,這雖然只是最初的反應,但會為未來的勝利奠定基礎。
作者系伊拉克前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