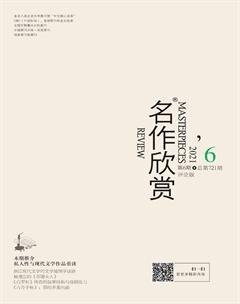論張棗詩(shī)歌的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
摘 要:詩(shī)人張棗有相當(dāng)多的詩(shī)歌中出現(xiàn)了對(duì)話(huà)式結(jié)構(gòu)的嵌入。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如何展開(kāi),在詩(shī)歌中嵌入話(huà)結(jié)構(gòu)的意義都將張棗詩(shī)歌的對(duì)話(huà)研究推向一個(gè)高潮,從而引導(dǎo)人們思考張棗創(chuàng)作背后的意圖。
關(guān)鍵詞:張棗 詩(shī)歌 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
一、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的異見(jiàn)
2000年,蘇姍娜·格絲在文章中提道:“此詩(shī)是張棗對(duì)他的另一首短詩(shī)《云雀》(迄今只存德譯本,未見(jiàn)有原文發(fā)表)的大幅度改寫(xiě),最顯眼的不同之處是將一個(gè)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重新嵌入,比如‘云雀被賦予了一個(gè)自己?jiǎn)我坏臄⑹雎曇簦谑潜3至艘粋€(gè)主體姿態(tài)的形式。”a從蘇姍娜·格絲的話(huà)中我們可以大膽提取她對(duì)于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定義的關(guān)鍵詞:?jiǎn)我粩⑹雎曇簟⒅黧w姿態(tài),即說(shuō)明在蘇姍娜·格絲理解的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中這兩個(gè)條件缺一不可。單一的敘述聲音即存在一個(gè)聲音在說(shuō)話(huà)。難于理解的是“主體姿態(tài)”,這是附著在“單一敘述聲音”這一條件之上的,它要求不僅僅保持一個(gè)人說(shuō)話(huà),同時(shí)這個(gè)人的說(shuō)話(huà)方式必須是出于他(她、它)本人,而不是作為某一個(gè)其他人的轉(zhuǎn)述工具,這一條件即賦予了說(shuō)話(huà)人自主的話(huà)語(yǔ)權(quán),也成為理解和判定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的關(guān)鍵。
通過(guò)對(duì)張棗詩(shī)歌中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研究的整理,筆者發(fā)現(xiàn)很多“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的理解與此區(qū)別很大,但很少有研究者關(guān)注到這一點(diǎn)。在復(fù)旦大學(xué)孫婕的畢業(yè)論文《論張棗詩(shī)歌的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b一文中,她將《那使人憂(yōu)傷的是什么》《桃花園》等在內(nèi)的四首詩(shī)歌歸入“具有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的詩(shī)歌行列中。她理解的“對(duì)話(huà)”和蘇姍娜·格絲理解的“對(duì)話(huà)”顯然有所不同,而《那使人憂(yōu)傷的是什么》真的具有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所要滿(mǎn)足的條件嗎?
《那使人憂(yōu)傷的是什么》一詩(shī)共有四節(jié),除開(kāi)頭和結(jié)尾沒(méi)有用第二人稱(chēng)“你”開(kāi)頭,中間兩段均以“你”開(kāi)頭,表面上看起來(lái)非常符合對(duì)話(huà)的定義。“那使人憂(yōu)傷的是什么?/是因?yàn)闊o(wú)端失落了一本書(shū)?”開(kāi)頭這兩句看似是一種問(wèn)答的形式,但提問(wèn)人和被提問(wèn)人都隱退,實(shí)際上并沒(méi)有辦法判定提問(wèn)人和被提問(wèn)人是否達(dá)到單一發(fā)聲和主體姿態(tài)這兩個(gè)條件。當(dāng)繼續(xù)往下讀時(shí),所謂詩(shī)歌的“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則蕩然無(wú)存。全段是以“你”的人稱(chēng)展開(kāi)回憶,但在寫(xiě)法上卻以一個(gè)隱于背后的“我”用極其肯定的語(yǔ)氣,甚至帶一點(diǎn)脅迫式的味道使“你”記起以下書(shū)寫(xiě)的經(jīng)驗(yàn)。大部分詩(shī)歌中都有涉及“我”“你”“他”等人稱(chēng)轉(zhuǎn)換的問(wèn)題,有時(shí)候會(huì)造成一種“對(duì)話(huà)式”寫(xiě)作的錯(cuò)覺(jué)。對(duì)話(huà)是兩個(gè)聲音平等地交談,甚至兩個(gè)聲音談?wù)摰牟皇且粋€(gè)主題和事件,但它必須出現(xiàn)以自我主體說(shuō)話(huà)的姿態(tài)。《那使人憂(yōu)傷的是什么》則更像是作品中的“我”用陳述句轉(zhuǎn)述“你”的內(nèi)心想法,始終只存在一個(gè)聲音,而沒(méi)有構(gòu)成對(duì)話(huà)。
蘇姍娜·格絲所謂的“對(duì)話(huà)”除了強(qiáng)調(diào)單一發(fā)聲和主體姿態(tài)外,也強(qiáng)調(diào)多種聲音的存在。在對(duì)《今年的云雀》解讀中,蘇姍娜·格絲將詩(shī)分成了三個(gè)部分,從而拎出了兩個(gè)對(duì)話(huà)主體,即云雀和“我”。而上述孫婕論文中歸類(lèi)的《那使人憂(yōu)傷的是什么》除了不滿(mǎn)足“主體姿態(tài)”以外,更沒(méi)有兩個(gè)及以上聲音的交流,筆者認(rèn)為不能算作是對(duì)話(huà)式結(jié)構(gòu)。
雖然有部分敏銳的研究者注意到這一點(diǎn),但相關(guān)探討淺嘗輒止:“張棗詩(shī)歌中的‘對(duì)話(huà),并非嚴(yán)格意義上的‘主體和‘他者之間遵循特定主題的對(duì)話(huà),而更多的是一個(gè)由頭、一個(gè)起跳板、一種言說(shuō)方式。” c國(guó)內(nèi)大部分研究張棗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的文章均出現(xiàn)了上述分析的問(wèn)題,只要詩(shī)中出現(xiàn)人稱(chēng)的轉(zhuǎn)換,或者說(shuō)有一個(gè)聲音對(duì)著隱藏不發(fā)聲的一個(gè)事物抒情、控訴或說(shuō)話(huà)都會(huì)被認(rèn)為是嵌入了一種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這對(duì)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在張棗詩(shī)歌中的表現(xiàn)和發(fā)展及意義研究產(chǎn)生了分析樣例失真的問(wèn)題,導(dǎo)致這一部分的分析并不能令人信服。
二、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的形式和標(biāo)志
張棗在處理嵌入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問(wèn)題時(shí)還利用了人稱(chēng)轉(zhuǎn)換、關(guān)節(jié)詞插入、語(yǔ)氣停頓等方式賦予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不同的形式。根據(jù)插入方式的不同,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的形式表現(xiàn)出顯性與隱性的特征。
最為明顯和簡(jiǎn)潔的方式是通過(guò)詩(shī)中人稱(chēng)變換表現(xiàn)出來(lái)的。這一類(lèi)的例子有很多,例如《燈芯絨幸福的舞蹈》和《骰子》。《燈》詩(shī)節(jié)選部分為1(5—6)d和2(2—3)。
詩(shī)中人稱(chēng)的奇妙之處在于兩段都是以“我”為發(fā)聲主體,但兩個(gè)“我”所代表的身份是不同的。第一節(jié)的“我”代表著一個(gè)觀(guān)看者和評(píng)論者,第二節(jié)的“我”則代表著燈芯絨舞者。而這種“我”“我”的迷魂陣卻并不對(duì)讀者造成閱讀障礙,張棗把握其中不變的物體——舞臺(tái)、影子、衣服等,并圍繞主體發(fā)聲者與這些不變之物的關(guān)系做文章,使這種人稱(chēng)的變化看似不變實(shí)則變換,又不似平常轉(zhuǎn)換得那樣庸俗,提升了閱讀體驗(yàn)感。讀者很容易明白這是觀(guān)看者與舞者圍繞著“對(duì)彼此的印象”這一個(gè)話(huà)題在展開(kāi)對(duì)話(huà)或者說(shuō)辯駁,不會(huì)產(chǎn)生《那使人憂(yōu)傷的是什么》所帶來(lái)的那種猶疑。李倩冉在《被懸置的主體——論張棗》一文中指出:“人稱(chēng)的選擇往往意味著言說(shuō)視角的選擇,‘我包含更多的內(nèi)心活動(dòng),‘你則帶有語(yǔ)調(diào)的親密性,選擇以什么角色為‘我本身就包含了抒情主體的態(tài)度。”e對(duì)話(huà)式結(jié)構(gòu)的嵌入可以引發(fā)讀者關(guān)于詩(shī)人與作品中的“我”關(guān)系之思考,以便可以發(fā)現(xiàn)嵌入式結(jié)構(gòu)是詩(shī)人在以怎樣的方式進(jìn)行言說(shuō)或者抒情。
三、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的背后
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的插入讓主體意圖的表達(dá)有了些許障礙,多種聲音的混入讓主體聲音很難突出。關(guān)于詩(shī)人嵌入對(duì)話(huà)的猜測(cè)有許多,廣受認(rèn)同的有兩種:一種即對(duì)話(huà)方式反映了詩(shī)人對(duì)中國(guó)古代“知音”觀(guān)的思考,一種即對(duì)話(huà)嵌入反映了詩(shī)人現(xiàn)實(shí)生活中與人溝通的經(jīng)驗(yàn)書(shū)寫(xiě)。蘇姍娜·格絲的文章對(duì)張棗關(guān)于“知音”觀(guān)書(shū)寫(xiě)的實(shí)驗(yàn)進(jìn)行了細(xì)致的分析,明確指出張棗詩(shī)歌中的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投射成了一種對(duì)理想傾聽(tīng)者的找尋。同時(shí),他把日常對(duì)話(huà)經(jīng)驗(yàn)投射到詩(shī)歌中的書(shū)寫(xiě)也不容忽視,根據(jù)現(xiàn)實(shí)對(duì)話(huà)結(jié)果的成功和失敗,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在詩(shī)中的表現(xiàn)和引發(fā)的思考也不同。成功的經(jīng)驗(yàn)或許從心理上給他的非母語(yǔ)環(huán)境創(chuàng)作注入了信心和激情,畢竟他會(huì)相信:人和人之間是可以通過(guò)語(yǔ)言成功交流和互相理解的。他的很多作品都是這樣對(duì)話(huà)成功經(jīng)驗(yàn)的書(shū)寫(xiě)。但這種對(duì)話(huà)經(jīng)驗(yàn)也有很多失敗的案例,例如前文提到的《今年的云雀》《骰子》…… 現(xiàn)實(shí)對(duì)話(huà)經(jīng)驗(yàn)的失敗又猶如一劑毒藥推翻了他關(guān)于“人和人能夠有效溝通”的判斷,從而陷入如何平衡語(yǔ)言豐富的表意功能與人的理解力的泥淖中。
根據(jù)陳冬冬等友人的整理,《燈芯絨幸福的舞蹈》寫(xiě)作時(shí)間不遲于1988年,是張棗對(duì)日常溝通成功經(jīng)驗(yàn)的書(shū)寫(xiě),也是研究張棗“知音”觀(guān)最重要的文本。但若不細(xì)致深入地理解這首詩(shī),很容易將它歸為“對(duì)話(huà)失敗經(jīng)驗(yàn)書(shū)寫(xiě)”的一類(lèi)。首先從兩節(jié)開(kāi)頭進(jìn)行一個(gè)對(duì)比:“我看見(jiàn)的她,全是為我/而舞蹈,我沒(méi)有在意”和“我看到自己軟弱而且美/我舞蹈,旋轉(zhuǎn)中不動(dòng)”。兩段中的“我”,即 “內(nèi)我”與“燈芯絨舞者”此時(shí)是處于一種相互觀(guān)察觀(guān)看的狀態(tài),彼此都認(rèn)為兩者融為一體,絲毫不見(jiàn)下面即將產(chǎn)生的分歧。但越往下走就越會(huì)現(xiàn)出二者的分歧。
在節(jié)選的1(7—13)中,開(kāi)頭一句“她大部分真實(shí)”是很耐人尋味的描述,潛臺(tái)詞即是:她看起來(lái)基本上真實(shí),但是還有小部分的她不真實(shí)或者沒(méi)有表現(xiàn)出來(lái)讓“我”看到。而“我”對(duì)她的觀(guān)察結(jié)果來(lái)源于兩個(gè)事物的對(duì)比——影兒和面目。作對(duì)比的兩個(gè)對(duì)象在選擇上本就具有一定的對(duì)立性。影子作為本尊的派生物,在文學(xué)解讀中常暗示內(nèi)心真實(shí)的一面或者隱藏的自我,而面目則是正式場(chǎng)合外人了解本尊的直觀(guān)途徑,一虛一實(shí),一暗一明,在對(duì)比中極顯張力。而“我”對(duì)這兩者的態(tài)度也是注入了很濃厚的感情色彩。影子是“退舍身后”,面目是“姣美”,單獨(dú)來(lái)看兩個(gè)形容沒(méi)有問(wèn)題,都是平常的說(shuō)法,但當(dāng)聯(lián)系到對(duì)比對(duì)象是對(duì)立的關(guān)系,且出現(xiàn)了一個(gè)肯定前者否定后者的連接詞“不像”時(shí),這兩種形容的感情色彩就完全不同了。“我”肯定了她影子退舍身后的默默無(wú)聞和清高,卻否定了她刻意展現(xiàn)“姣美”式樣的虛假與做作,更多了一種譏諷與不屑。第二節(jié)燈芯絨舞者則從自己的角度反駁了第一節(jié)“內(nèi)我”對(duì)于她的評(píng)價(jià),“我并非含混不清”是一個(gè)很重要的表明單一主觀(guān)姿態(tài)發(fā)聲的詞語(yǔ),它明顯是對(duì)第一節(jié)“內(nèi)我”認(rèn)為她將真實(shí)的自我與虛假的表象混合在一起,給人一種假象的反駁。燈芯絨舞者以強(qiáng)烈的姿態(tài)為自己正名:在她那里,她很珍視“真”,并且認(rèn)為世界是真實(shí)的,一切都需要真實(shí)。至于為什么會(huì)給他留下她不真實(shí)的假象,是因?yàn)樗跒樗囆g(shù)獻(xiàn)身時(shí)的確會(huì)專(zhuān)心致志到忘乎自我,使之呈現(xiàn)出來(lái)的自我似乎符合前段“內(nèi)我”的控訴——她大部分真實(shí),小部分虛偽。這樣的爭(zhēng)辯持續(xù)著跟進(jìn),甚至愈加劇烈。燈芯絨舞者開(kāi)始覺(jué)得第一段的“內(nèi)我”似乎完全不理解她。
在1(18—12)和2(15—23)的比較中,兩人的分歧看似更厲害了。第一節(jié)的“內(nèi)我”認(rèn)為燈芯絨舞者的衣裳磨損了,第二節(jié)卻收到了反駁:衣裳沒(méi)改,且影子也是熱騰騰充滿(mǎn)生命活力的。“可他,不會(huì)明白這番道理”“他才不會(huì)那樣挑選我”披露了燈芯絨舞者責(zé)怪“內(nèi)我”的兩個(gè)主要原因:1.沒(méi)有理解真實(shí)的燈芯絨舞者;2.“內(nèi)我”把自己和燈芯絨舞者放置在兩個(gè)不同的階層上來(lái)進(jìn)行觀(guān)察、比較甚至評(píng)判。燈芯絨舞者認(rèn)為自己被“內(nèi)我”所物化,將一個(gè)具有獨(dú)立生命力的人當(dāng)作一個(gè)可供自己玩賞的物件,這是對(duì)燈芯絨舞者一個(gè)極大的侮辱。至此,在溝通的意義理解層面上是一次失敗的對(duì)話(huà),因?yàn)閮扇烁鲌?zhí)一詞。但是轉(zhuǎn)變深藏于第一節(jié)和第二節(jié)結(jié)尾。燈芯絨舞者苦于“內(nèi)我”對(duì)自己所思所想并不理解而發(fā)出了無(wú)奈和遺憾的嘆息,但這些辯白她自然并未告知第一節(jié)的“內(nèi)我”,嘆息自然也沒(méi)有實(shí)在地讓“內(nèi)我”聽(tīng)見(jiàn)。但第一節(jié)末尾“內(nèi)我”卻聽(tīng)見(jiàn)了燈芯絨舞者的嘆息。某種意義上代表著燈芯絨舞者所想的,實(shí)際上“內(nèi)我”也十分清楚,即驗(yàn)證了一個(gè)道理:人與人之間是可以溝通的。得出這個(gè)結(jié)論對(duì)于張棗來(lái)說(shuō)不容易,但是相當(dāng)值得。他已經(jīng)離開(kāi)母語(yǔ)創(chuàng)作環(huán)境多年,在非母語(yǔ)語(yǔ)境中他的創(chuàng)作會(huì)遇到頗多困難,例如:如何令非母語(yǔ)讀者領(lǐng)悟和體驗(yàn)到母語(yǔ)寫(xiě)作的意義,如何平衡非母語(yǔ)創(chuàng)作和內(nèi)思想斗爭(zhēng)的矛盾以及如何用語(yǔ)言將兩個(gè)完全獨(dú)立的個(gè)人思想聯(lián)系到一起……他提到確認(rèn)這種經(jīng)驗(yàn)對(duì)于他有多么重要:“它傳給我一個(gè)近似超驗(yàn)的詩(shī)學(xué)信號(hào):另一個(gè)人,一個(gè)他者知道你想說(shuō)什么。也就是:人與人可以用語(yǔ)言聯(lián)結(jié)起來(lái),對(duì)我而言,證實(shí)了這點(diǎn)很重要。” f
然而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對(duì)話(huà)實(shí)驗(yàn)也并不總是能收到令人欣喜的結(jié)果,談話(huà)也有失敗的時(shí)候。在寫(xiě)這類(lèi)經(jīng)驗(yàn)時(shí)(例如《骰子》),張棗詩(shī)歌的語(yǔ)調(diào)顯然沒(méi)有《燈芯絨幸福的舞蹈》這類(lèi)詩(shī)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那種輕松愉悅,更多的是一種沉重與無(wú)奈,也正代表了他在其中的思考……
《骰子》中“ 內(nèi)我”以一種命令式的語(yǔ)氣讓“內(nèi)你”說(shuō)一句話(huà)——“沒(méi)有我”,即“內(nèi)我”立于“內(nèi)你”的言說(shuō)角色上的直接敘述。而“內(nèi)你”則理解成了“沒(méi)有我”是“內(nèi)我”立于“內(nèi)我”本身立場(chǎng)上的發(fā)聲,于是用了轉(zhuǎn)述說(shuō)出了“沒(méi)有你”。而顯然,“內(nèi)你”的舉動(dòng)并沒(méi)有理解“內(nèi)我”的意圖,于是“內(nèi)我”對(duì)“內(nèi)你”下達(dá)了第二次命令。此時(shí)為了避免產(chǎn)生誤解,“內(nèi)我”直接站在了自己的立場(chǎng)角度要求“內(nèi)你”復(fù)述,而“內(nèi)你”再一次誤解。
這種繞口令似的詩(shī)歌看似是詩(shī)人與我們開(kāi)的一個(gè)玩笑,在主語(yǔ)人稱(chēng)的迷宮中始終沒(méi)有走出來(lái),但是沒(méi)有人在意到底“沒(méi)有的是誰(shuí)”。我們從中看到了語(yǔ)言的豐富卻又無(wú)力的現(xiàn)實(shí)。即語(yǔ)言豐富的表意功能在人與人能夠合理溝通的基礎(chǔ)上自然能夠發(fā)揮出它的光亮,但是在人與人溝通失敗的基礎(chǔ)上,語(yǔ)言的豐富只能是“縛腳”的那根繩子。因此,詩(shī)人可能不禁要問(wèn):語(yǔ)言何用?溝通交流何用?
通過(guò)上述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張棗在使用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表達(dá)日常溝通經(jīng)驗(yàn)時(shí)是痛苦的。一方面,成功經(jīng)驗(yàn)驗(yàn)證的真理給了他從語(yǔ)言上尋求突破的定心丸;另一方面,失敗的經(jīng)驗(yàn)讓他對(duì)語(yǔ)言的處理陷入迷茫之中。語(yǔ)言本身是很神奇和美妙的媒介,但如果沒(méi)有辦法達(dá)到心意共通,語(yǔ)言似乎也失去了一定的意義。但是無(wú)疑,無(wú)論是成功對(duì)話(huà)經(jīng)驗(yàn)的書(shū)寫(xiě),還是失敗對(duì)話(huà)經(jīng)驗(yàn)的書(shū)寫(xiě),張棗為我們展現(xiàn)了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嵌入詩(shī)歌中的種種魅力。在鐘鳴看來(lái),張棗的這種試驗(yàn)是成功的:“在詩(shī)歌敘述中機(jī)智成為‘對(duì)話(huà)者,也只有張棗君等一二人,其余無(wú)神無(wú)形,做出來(lái)的派,混點(diǎn)名頭,不過(guò)爾爾,莫能望其項(xiàng)背。”g或許客觀(guān)的評(píng)價(jià),張棗的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嵌入詩(shī)歌的處理水平并沒(méi)有鐘鳴所說(shuō)的那么高,但他畢竟為當(dāng)代及后面的詩(shī)歌創(chuàng)作者提供了一個(gè)可參考學(xué)習(xí)的向度,于詩(shī)歌的多樣化發(fā)展來(lái)說(shuō),是功不可沒(méi)的。
a〔德〕 蘇姍娜·格絲,商戈令:《一棵樹(shù)是什么?──“樹(shù)”商戈令譯,“對(duì)話(huà)”和文化差異:細(xì)讀張棗的〈今年的云雀〉》,《當(dāng)代作家評(píng)論》2000年第2期。
b 孫捷:《論張棗詩(shī)歌的對(duì)話(huà)結(jié)構(gòu)》,復(fù)旦大學(xué)2012碩士學(xué)位論文。
ce 李倩冉:《被懸置的主體——論張棗》,《文藝爭(zhēng)鳴》2020年第3期。
d 文章出現(xiàn)(5—6)表示《燈芯絨幸福的舞蹈》的第一節(jié)第5—6句,其他同理。
f 黃燦然:《張棗談詩(shī)》 (訪(fǎng)談錄,原載于《飛地》 第三輯) https://site.douban.com/106369/widget/notes/134616/ note/311097045/?dark_mode=0
g 鐘鳴:《詩(shī)人的著魔與讖》,《西部》2012年第13期。
作 者: 鄧縈夢(mèng), 云南大學(xué)文學(xué)院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碩士生,研究方向:當(dāng)代詩(shī)歌。
編 輯: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