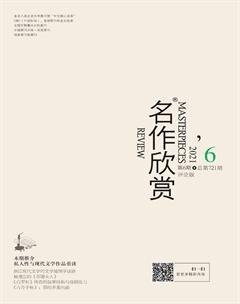《謫仙怨》的反諷敘事
摘 要: 白先勇小說《謫仙怨》通過多重反諷敘事,取得了別具魅力的藝術效果。從情節、話語、主題三個層次觀察其敘事特征,不難發現其中的反諷意涵,其反諷敘事策略對小說主題的揭示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白先勇 《謫仙怨》 反諷
《謫仙怨》是白先勇頗負盛名的短篇小說,寫于20世紀60年代白先勇赴美留學時期,收錄在其短篇小說集《紐約客》中。和《紐約客》中其他小說一樣,《謫仙怨》的故事也發生在紐約,講述了官宦小姐黃鳳儀家道中落后舉債留學,到了紐約不久,便在學業、愛情、生活的多重壓力下淪落風塵的故事。《謫仙怨》的故事簡短,卻不簡單,作者通過多重反諷敘事,深化了故事內涵,取得了別具魅力的藝術效果。
一、情節反諷
“‘反諷一詞在大多數現代批評的使用中仍然保留了其原意,即不為欺騙,而是為了達到特殊的修辭或藝術效果而掩蓋或隱藏話語的真實含義。” a在《謫仙怨》中,最易察覺的是情節反諷,作者通過敘事結構的安排,隱藏了敘述的真實含義,從而達到反諷的效果。《謫仙怨》是《紐約客》中最短的一篇,全文不到四千字,作者卻規劃了兩個相對獨立又有機結合的敘事段落,對結構的重視可見一斑。事實上,小說的反諷結構,正依賴于這兩部分敘事段落的并置。
孤立來看,兩部分篇幅相當,無論從敘事內容、敘述視角看,都具有相對獨立性,甚至將其割裂開來做兩個故事閱讀也未嘗不可。第一部分題為“給母親的一封信”,信件一開頭,她便開始了對母親關懷的“責備”,“你一個人在臺北,不小心保重,弄出了毛病來,我又不能回去照顧你,豈不是給我在國外增添煩惱嗎?” b儼然一個母親責備孩子的口吻。她輕松幾句交代了自己失敗的感情生活,仿佛在談論別人的事情。她表達了對紐約的熱愛,讓媽媽相信她實在過得很開心。在黃鳳儀的口中,她完全理順了她的生活,獲得了完全的自洽狀態。
第二部分題為“LOWER EAST SIDE,NEW YORK”,采用全知視角。在紐約的一個風雪夜,黃鳳儀在風月場化身“蒙古公主”,無比老練地周旋于各色人等之間,和四五十歲的“糖爹爹”打情罵俏。在玫瑰色的氣氛中,黃鳳儀似乎依然是一個自洽的存在。
在《紐約客》首篇《謫仙記》 中,強力矯飾如李彤,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她的疲憊和孤獨在小說敘述中外化出來,但在《謫仙怨》中,就兩部分敘事的字面而言,我們并不能進入黃鳳儀的內心深處。而一旦我們將這兩部分并置、對比,情節反諷便立刻形成了。小說構建了“書信—現實”這個情節反諷結構,它們像兩塊對立的鏡子,互相補遺,互相掩飾,更互相拆穿,當兩個自洽的黃鳳儀站到一起,我們看到了一個不自洽的黃鳳儀。
二、話語反諷
“新批評”派的布魯克斯認為反諷就是“語境對一個陳述語的明顯的歪曲”c。孤立地看《謫仙怨》的兩部分敘事,我們很難發現有什么話語被明顯歪曲了,或者說,哪怕我們對一些話語感到懷疑,也并不能立刻確定這就是反諷,只有情節反諷模式浮出水面后,兩部分敘事在各自內部的話語反諷才得以成立。簡而言之,在我們讀完小說之前,我們并不會發現話語里面的反諷意味,而當我們發現了兩部分敘事的巨大矛盾后,再回頭一看,就會發現,許多話語都變得詭異起來。
在“給母親的一封信”中,黃鳳儀使用了許多問句,尤其是反問句,帶著一種不容辯解、斬釘截鐵的口吻,以致形成身份倒置——母親如此“不懂事”,幾乎要惹惱了強勢的女兒。然而,她的反問句越是決絕,就越讓人懷疑,越讓人想追問一句“是嗎?”——
“其實我已經二十五歲了,難道還不懂得照顧自己嗎?”是嗎?
“其實你掛來掛去,還不是擔心我一個人在紐約過得不習慣,不開心。怎么會呢?人人都說美國是年輕人的天堂。”是嗎?
“我想通了,美國既是年輕人的天堂,我為什么不趁著還年輕,在天堂里好好享一陣樂呢?”是嗎?
在那些看似坦蕩的陳述句中,話語反諷更是比比皆是。第二部分充斥著風月場的行話,“Rescue Me”“乖乖”“寶貝”“沒長毛的小狗兒”“四五十歲的‘糖爹爹”,這些語句都極不可靠,在濃烈的玫瑰色氛圍中,巨大的孤獨感被抽離出來。更有“蒙古公主—老蜜糖”形成強烈反諷,中年嫖客沉浸在情色的異域獵奇里,黃鳳儀則沉迷在甜與苦的混淆中。我們能感覺到,她不愿被拆穿,她希望沉浸在“蜜糖”一般的錯覺里,求得片刻的遺忘,因為“蜜糖”的背后,恰恰是最苦澀的生活。這也正如她對待紐約的態度,她需要紐約,并非要召喚自我,而是要召喚對自我的遺忘。吳福輝認為,白先勇小說“仿佛是白頭宮女在述說天寶遺事,但用的是一顆純粹現代人的心靈,敘述中國人在20世紀被放逐的悲劇……” d如果說“紐約客”是對“臺北人”的引申或再放逐,那么,在黃鳳儀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被放逐”“再放逐”的結果,是引領被放逐者走向自我放逐。
三、主題反諷
看完前文的論述,也許你會質疑,在“給母親的一封信”中,難道她的敘述一定不可靠嗎?我們為什么不能選擇全然相信黃鳳儀呢?難道我們不能認為,她的口吻只是性格使然嗎?畢竟,她講起母親去舅舅家打麻將的往事時,我們甚至感到了無比真摯、不加矯飾的情感。這種情感沒有一貫性嗎?對于第二部分,你還可以踩著道德選擇和生活方式的界限如此質疑:是的,黃鳳儀是淪落風塵了,可這有什么問題嗎?淪落風塵就一定是精神的不自洽嗎?
如果沒有主題上的反諷,以上所有質疑都將成立。我們可能掌握了許多黃鳳儀的心靈事實,但它們無法形成證據鏈以供我們從總體上把握其心靈實質。但《謫仙怨》主題反諷赫然存在。
在《謫仙怨》中,主題反諷從整體上統攝著情節反諷和話語反諷,成為串聯證據鏈的最重要線索。它赫然存在于標題當中——“謫仙怨”。據《說文解字》:謫,罰也,“謫”和“仙”兩個字就構成了主題上的反諷,這一反諷的結果是“怨”。黃鳳儀的心靈實質是什么?當然就是“怨”。如此一來,前文所假設的質疑便不攻自破了。黃鳳儀之“怨”從何來?借反諷視角,可以“身份焦慮”為核心解讀《謫仙怨》的主題。“謫—仙”反諷的本質就是身份焦慮,黃鳳儀的身份焦慮可借幾個經典的哲學問題來歸納。
我是誰?——“最多有時有些美國人把我錯當成日本姑娘,我便笑而不答,懶得否認,于是他們便認為我是個捉摸不透的東方神秘女郎了……”
我從哪里來?——“你看,媽媽,連我對從前的日子,尚且會迷戀,又何況你呢?”“以后不必再寄中國罐頭來給我,我已經不做中國飯了,太麻煩。”
我在哪兒?——“抬起頭看見那些摩天大樓,一排排在往后退,我覺得自己只有一點丁兒那么大了。”
我要到哪里去?——“現在全世界無論什么地方,除了紐約,我都未必住得慣了。”
只需以反諷視角去看黃鳳儀給母親的信,就會感受到她巨大的身份焦慮。無論是身份認同、文化根底、現實處境、人生方向,黃鳳儀都到了進退失據的地步,正如劉俊談及李彤、黃鳳儀的命運所說:“從上海到紐約, 她們跨越的不僅是太平洋, 更是天上人間的界限——在天上她們是主人,到了人間她們卻成為消費品。” e黃鳳儀“謫仙”之“怨”,由此而來。
《謫仙怨》是《紐約客》的第二篇,從集子的共同主題的角度,我們同樣能夠發現反諷色彩。與“謫—仙”的反諷結構類似,“紐約—客”同樣是一個反諷結構,黃鳳儀不是“紐約人”,而只是“紐約客”(在這里,“New Yorker”的中文諧音奇妙地顯示出宿命色彩)。黃鳳儀說她喜歡紐約,“在紐約最大的好處,便是漸漸忘卻了自己的身份。真的我已經覺得自己是個十足的紐約客了”。在紐約這樣的大城市中,她失去了全部的主體性(作為“紐約人”的可能),紐約將她放逐,將她客體化。當她喪失身份認同,喪失前路也喪失退路時,她渴求的是被淹沒和被遺忘,城市的價值無奈地體現在其冷漠和吞噬性上。而通觀《紐約客》,遭此處境的又何止她一人呢?克爾凱郭爾如此強調主題反諷:“在更高的意義上,反諷不是指向這個或那個具體的存在,而是指向某個時間或情狀的整個現實……它不是這個或那個現象,而是經驗的整體……”f在這個意義上,《謫仙怨》甚至可以看作是對《紐約客》的點題。
四、結語
通過情節的對置、話語的語境歪曲和主題的深度反諷,《謫仙怨》的故事在悍然的撕扯中成立,人物的身份焦慮得到了貼切的展現,這種展現尤具焦灼感和幻滅感。反諷越深,“謫仙”之“怨”越深,相對于“怨”而言,“謫仙”無疑成了一場盛大的自我嘲弄。將這樣深切的反諷結構推延至《紐約客》中,“紐約”又何嘗不是對“客”的嘲弄與放逐呢?
a 〔美〕艾布拉姆斯,哈巧姆:《文學術語詞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84頁。
b 《謫仙怨》原文均引自《白先勇文集第一卷》,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不再一一另注。
c 〔美〕布魯克斯:《反諷—— 一種結構原則》,轉引自趙毅衡編選:《“新批評”文集》,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376頁。
d 吳福輝:《背負歷史記憶而流離的中國人——白先勇小說新論》,《文藝爭鳴》1993年第3期。
e 劉俊:《從國族立場到世界主義——論白先勇的〈紐約客〉》,《揚子江評論》2007年第4期。
f 〔丹麥〕克爾凱郭爾:《反諷概念》,轉引自趙毅衡編選:《“新批評”文集》,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頁。
作 者: 陳凱,云南大學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編 輯: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