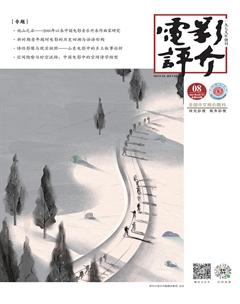分形·疊加·間隙:《沒有過不去的年》空間敘事美學詮解
但愿


《沒有過不去的年》(以下簡稱《過》)于2021年1月初上映,作品體現了以導演尹力為代表的中國第五代導演對中國現實主義美學的追求。導演使用大量快切、錯位和長鏡頭,聚焦當代中國多子女家庭的人倫關系與社會變化,介紹以王自亮為主敘述者的王氏一家在春節前15天里的點滴生活,通過王自亮“被裹著走”的狀態綴連其不同階層、不同職業、不同群體間的“清明上河圖”。
尹力導演并未將重點落到宏大敘事的議題變化中,而是“把節日變成一個載體,在這個載體之上展覽眾生相,把社會的各個階層都放到這上邊”[1]。導演采用中國敘事學中獨有的“綴段(episodic)式空間化敘事”方式,將視角集中于各種不同空間的多項周旋(multiple periodicity)[2],通過向內延展的分形空間、向外并置的疊加空間和與空間之間的事隙營造的方式,形成獨特的空間美學。
隨著不同空間的轉換和彌合,關切民生的醫療、養老、環保、腐敗、民俗、群體性心理癥候、出國、出軌等諸多社會議題也隨著過年這一橫截面漸次呈現在觀眾眼前。
一、分形空間:未完成的戲中戲
早在中國戲曲藝術中,就有穿插進戲劇情節的表演片段,被稱為戲中戲(playinplay)。這些戲中戲的上演通過劇情的相似性與嵌套的隱喻創造出一種美學結構,即“不僅包含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相似性,即作品每一個小部分在延展開之后和整體的結構協調一致,不同句子間的長度變化還呈現出一種級聯性的長程動力學(the dynamics of a cascade)關聯”[3]。從文字塑造的作品到能呈現影像的視覺性媒介的轉化,內戲(Innerplay)對外戲(Outerplay)的“元文本的異度空間,以一種確然的文化內涵輔助元文本的敘事向度”[4]變得越來越立體化。
本片中出現了4次戲中戲分形空間,分別是合唱曲《青春舞曲》、話劇《全家福》、古本故事《王氏家譜》和導演的原定結尾置景。每場戲中戲都是未完成的片段,故事發展越到后面,戲中戲的未完成狀態就越明顯,《青春舞曲》尚且有完整歌曲,《全家福》只有出演畫面,《王氏家譜》的內容處于不可知,置景則直接被導演砍掉,不在正片出現。這種結構上的彌散,象征著“媽在家就在”這一元敘事的逐漸失效。
(一)王向藜的《青春舞曲》:循環的隱喻
影片里首次出現的戲中戲,是王家大姐王向藜指揮的G大調合唱曲《青春舞曲》,作為該片的插曲,也是該片唯一一個被完整性嵌入的戲中戲(但依然被切成了碎片)。該歌曲是王洛賓改編的新疆民歌,其歌詞和曲調都有強烈的魚咬尾特點,使歌曲的節奏在播放過程中顯得異常歡快且明亮。
處于片頭的《青春舞曲》與片尾的農村老家歡樂的除夕節慶儀式形成首個分形敘事的呼應空間,繼承了中國詩歌古典美學營造意境的“樂景寫哀”手法。
王向藜在指揮過程中維持著優雅精致,與之合唱的青年成員們亦以和諧的多聲部在不斷切換的特寫鏡頭下與之共鳴,王自亮與情人一閃而過的各種畫面則是中景,副歌中歌詞“我的青春小鳥一樣不回來”的3次重復的調子越來越高,然后戛然而止,所有人重新回到一地雞毛的日常生活。
在王向藜指揮下的循環復唱與王自亮和情人在轟鳴的火車聲掩蓋下的畫面交錯形成的蒙太奇切片,給人帶來了強烈的錯亂感。《青春舞曲》也通過循環和歡快構筑出一種強烈的景觀隱喻,即富足、歡愉、歌頌的超平面現代生活并不是生活的真相,而是被粉飾的話語,這些話語本身也喪失了宏大敘事特性,而是依賴于不斷重復的情緒性曲調進行。被現代性異化的人們被困在這種循環著的故事的內部,不管是永無止境的日常[5],還是枝葉旁逸的瑣事。
(二)王自亮的《全家福》:完整的喪失
王自亮在《過》中是成名編劇,片中穿插了他的數個編劇出的作品,幫名演員改一年多的劇本、為暴發戶寫人物自傳,連妻子李思杰都說“你什么時候能寫自己想寫的東西”。他擔任編劇并上映的《全家福》是片中唯一證明“他想寫”的東西,但也正如二弟王自健所說“你寫的那個人就是我”,盡管王自亮回應說“藝術創作不能對號入座”,但王自亮也已經陷入到“人戲不分”的狀態。他必須以編劇的視角觀察世界,才能保持繼續創作的可能,而不是“一廂情愿地把客觀現實當成被有意組織起來的戲劇”[6],但逼仄局促的現實生活,讓王自亮除了借話劇演出的殼,已經失去了完整表達情緒和意圖的能力。他必須依靠短平快的方式應對身邊的所有事情。
《全家福》只是王自亮對理想生活的烏托邦想象,是他所處的現實生活的鏡像投射,但如何展開《全家福》,王自亮沒有具體的藍圖,觀眾也看不到具體的展開,于是只能通過劇場內觀眾的反應和一掃而過的演員表演來揣測。該劇并沒有得到觀眾與演員的認同,大家都像王自亮對待生活那樣,想盡快應付過去,母親宋寶珍也在觀劇時昏昏欲睡。
最后王自亮的大段獨白,似在對母親訴說,卻更像是以演員的身份對第四堵墻外的觀眾訴說,以補充他的人物設定。這段獨白之后,王自亮再度回到只能用短平快的方式和人交流的狀態,在與美國的妻女相處時也沒有改善。
(三)宋寶珍的《王氏家譜》:被觀看的古本
王自亮在去往美國的飛機上關閉了一切通訊設備,也不再看任何影像視頻,而是打開了母親給他的《王氏家譜》,此時鏡頭逐漸向前搖,前座的外國女子正在手舞足蹈地看著視頻。此本家譜在之后的劇情里沒有再出現,直到電影最后,在老家與塵封已久的相冊放在一起。當王家的4個子女翻開相冊時,似乎之前成年之后的所有矛盾都不復存在。《王氏家譜》以一種梳理非當下生存者的譜系成為了王家的修復型懷舊,“距離通過親密體驗和所渴求對象在場得到補償”[7]。在《王氏家譜》營造的懷舊情景下,盡管宋寶珍并沒有任何容貌上的改變,但王自亮重返了孩童時代,似乎與“依舊爬上來”的明天(明年)進行了時間切割,仿佛“花兒謝了明年還是一樣的開”。
在《王氏家譜》的結尾,李思杰和兩個女兒正在念著家譜里的內容,受到片尾信息和片尾曲的干擾,讓觀眾難以分辨其具體信息。但這個畫面與前述劇情里李思杰和女兒與王自亮因為出軌的矛盾相沖突,似乎《王氏家譜》真的將那些疏離、無奈和隱忍的困境進行了消弭,但這或許亦只是王自亮的幻念,是作為孩童的王自亮對于成功中年男人的未來想象。
(四)尹力的置景:未出現的片尾
在原本的電影結局中,導演尹力還想加入一個戲中戲的置景。“一家人終于和解,坐在一起吃團圓飯。但是鏡頭拉遠,視野出了廳堂,讓觀眾看到這里原來不是鄉村,而是在城市里一座高樓的樓頂上——一切僅僅是一場戲或一臺演出。因為我不滿足現在這種虛假的溫情……鏡頭越拉越遠,可以看到這臺演出的前排全是觀眾,再越拉越遠,北京CBD整個盡收眼底……形成一個間離效果……從導演的個人表達上是有藝術性的,我們能夠找到整部影片作為寓言的提綱挈領的形而上學。”[8]
盡管最后放棄了,但這也說明尹力對“過年”主題并不只是停留在大團圓式的結果上,而是轉移到“過不去”這一難題中。在尹力看來,“沒有”并不是修飾“過不去”,而是與“過不去”一樣,是對“年”的形容。
尹力想通過對各種未完成的戲中戲的設置,形成對年節的儀式感的反思:是否只要坐在一起就是團圓,就是溫情?過年只是對現實僵局的一種想象性解決,在導演看來,這種行為景觀只是將煩瑣、局促、撕裂的生活進行了懸置,使之更像是流俗的鏡像烏托邦,“在鏡子中,我看到自己在那里,而那里卻沒有我,在一個事實上展現于外表后面的不真實的空間中”[9]。
二、疊加空間:并置的異托邦
在時代裹挾下,現代社會的空間原本就復雜而多變,《過》背后還折疊了改革開放40年的巨變,將不同時間與空間的生存境遇在一部電影中進行并置。我們可以在片中看到各種似乎不應該共存的場域,高度現代化的林立高樓、一片嘈雜的拍戲現場、流水屠宰的一線工人,以及儺戲慶祝的農村民俗。
福柯認為,這些“外在于所有場所的,盡管它們實際上是局部化的”[10]位所,就是異托邦。“異托邦有權力將幾個相互間不能并存的空間和場所并置為一個真實的地方”[11],并將違和的邊境模糊起來。
在本片中有3處重要的異托邦,分別是手機及其訊息的媒介、安徽徽州老家農村和王家的老房子。手機是以王自亮等中年人高度依賴的虛擬現實異托邦,大部分沖突與劇情發展由手機畫面完成;農村是宋寶珍等老年人心心念念想回去的鄉土異托邦,但該異托邦正在不斷受到現代社會的侵蝕;老房子是銜接中年與老年人的地緣共同體異托邦,具有強烈的懷舊性。這些異托邦都呈現出共有的特質,碎片化與幻象化。
(一)手機:生存幻象
現代人的生活已經牢牢地依附在手機上,似乎失去手機就與世界失去聯系,手機作為可移動的媒介,將不同人的生活碎片銜接起來,并成為全景敞視主義(panopticism)的必備空間。福柯在異托邦的第六特征里提到,“異托邦有創造一個幻象空間的作用,這個幻象空間顯露出全部真實空間簡直更加虛幻,顯露出所有在其中人類生活被隔開的場所”[12],就是對手機的完美注腳。
王自亮的生活從來都是被手機填滿,導致他不得不焦灼于應對手機帶給他的一切大小事務。王自亮的所有工作建立在手機上,為成功老板寫的自傳、給大腕兒寫的改了一年多的劇本,以及看了一眼手機之后又翻身開始編劇寫作。王自亮與妻子女兒的溫馨生活片段,被拍進照片里,也只是拍進照片里——我們現在仍不知道這些照片究竟拍于何時,導演將這些拍照片的場景亂序插入到劇情之中,營造出記憶碎片似的混亂感。王自亮關心的鄉村污染問題,來自微信轉發朋友圈,后來引來一連串的官司、律師援助、與二弟的博弈。王自亮被發現出軌,還是因為手機。妙果從父親的舊手機中發現了他與情人的合照;妻子說王自亮給情人刷卡時,她是副卡,總會收到短信提醒。
在《過》中,手機營造的生存幻象更是以超真實的狀態而呈現,在要不要陪老太太一起過年的幾兄弟姐妹的扯皮中,導演通過一次又一次的電話,如視頻電話、手機電話、短信、微信將其呈現。
(二)農村:鄉土幻象
費孝通在《鄉土社會》中將農村鄉土描述為“不是以個人為單位,而是以住在一處的集團為單位”[13]的孤立和隔膜,農村以低流動性和有機的團結形成禮俗社會。圍繞著徽州鄉土地區,即母親口中的“老家”,也似乎完全不受到高速發達的現代社會的侵蝕,而是保留了古色古香,無論是建筑風格還是人文地理,都有著強烈的世外桃源感。到了大年三十的晚上,這片鄉土上演慶祝新年歌舞節目,把過年從一個單薄的詞語變成了一個動態的場域,可是這種美好的幻想注定只是枉然。一直照顧老太太的元能兄弟摔斷了腿,同時查出他早已因企業排放的污水患上了疾病。整個鄉村留存的鄉民們,都患上了疾病——整片土地,整個農村老家也都被現代化生產的工業以非常破壞性的方式裹挾著進入了現代社會。
作為鄉土幻象的農村與宋寶珍似乎是一體的異托邦。她最開始不愿意看病,也不懂現代技術;后來進了醫院檢查得知生命只剩3個月時間(她自己不知情),盡管身體早已被侵蝕,但依然努力成為治愈在現代社會中疲于奔命的中年人們。
(三)老房子:懷舊幻象
在整部影片中,老房子直到故事最后才出現,從電影一開始到結尾,宋寶珍一直念叨著要去的只是老養院。宋寶珍回老家所在的老房子,有王家的舊照片,有她真正認可的“兒子”,還有能隔絕現實紛亂的功能,是一個懷舊的烏托邦。
老房子最后也只是成為懷舊用的擺件,除了“外人”元能和老太太以外,其他人想要的只是一個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但可以裝作掛念著的空屋。“他們拋棄了抱負和期望,開始返回到那種具有欺騙性、自我觀照和自我參照的安全庇護所中”[14],但對于老房子這一庇護所到底應該如何維護,王家的中年人沒有任何真正的行動。
在故事的最后幾幕,過于幻想的場景再度復現出來,一家人其樂融融地圍在一起看老照片,仿佛從來沒有任何矛盾一般,仿佛現實里的生活壓力從來就不存在一樣,仿佛下面一直等待著抓捕王自健的警察也并不存在。
有治愈之地在此處,所有的故事都可以從頭再來。《假如還有來生》的重點,不是來生,而是假如,是將所有的故事停留在童年時分。
三、空間之間:中國式敘事的“事隙”
麥克勞德認為,敘事無法窮盡所有信息,人類的思維接收經驗是將“觀察到的一部分理解為整體,這種方式被稱為知覺的封閉性”[15],整體通過聲、畫、字塑造為敘事空間。浦安迪在《中國敘事學》對中西方的敘事空間作出了詳細的分別:在西方的敘事空間中,事件是一種實體的時間化設計,在中國敘事學里,則是綴段式的空間化敘事。中國式敘事空間的重點并不在對于事件或情節的推進,而在于“事與事的交疊處之上,或者是放在事隙之上,或者是放在無事之事之上”[16],在中國美學中將其成為留白或意境。
造成這樣的差別,是因為中國式敘事受到中國哲學“天人合一”的思想影響,不將敘事過程以離散的單元塊組合,而是將敘事作為一個完整的空間進行處理。在《過》中,除了明確的故事主線外,導演尹力還通過大量看似與主題無關的事隙在空間之間進行填補,與王家故事形成更寬廣的中國式共時性空間。
本片導演采用了毛邊、切片和汽車空間3種主要的事隙手法,個人和家庭在時代下的輾轉變化為更具有集體記憶的心路歷程。毛邊是和與主線完全無關的與他人相遇的畫面形成的群像交響效果;切片是對不同角色故事線的共時性交代;汽車空間是不同人物在其他大的敘事空間中不斷轉移過渡的空間。
(一)毛邊:社會角落的閑筆
與西方敘事學打破第四堵墻的思路不同的是,尹力導演的做法,是通過這些毛邊,把現實生活中人們所遭遇到的狼狽與困境,和影片中的主線敘事進行復調式銜接,從而模糊真實與虛假之間的關系。
電影最開始的醫院場景中就有大量毛邊,導演尹力在接受采訪時談到有“院里吵架的姐妹,大街上不會玩微信的老頭,舉著個烏龜敲車窗的販子,向編劇推銷男性保健品的,樓上的七個不服,八個不忿的鄰居”[17]等。不僅如此,導演亦不避諱現實中可能出現的不宜場景:王自亮與情人在廉租房內的行為,屠宰場內生豬被現代流水線肢解,以及律師開車突逢車禍等被納入到電影之中。
這些看似零碎的毛邊,形成了大大小小不同空間之間的對話,鏡頭的推移自然流暢,似乎是不經意的行為,但豐富的細節將故事構筑出多重結構,最后演變為“看似互無關聯,卻是統一在一種概念性的主題思想上”[18]:現代社會的失序發展與精神迷茫。
(二)切片:共時性情感
“人物所展開的故事都是對話性的,也就是一切負有意味和含義的事物當中所存在的”[19],電影進入尾聲后,一晃而過的切片開始增加,并形成與主敘事的強烈對話性。盡管導演通過切片看似給出了結局,但這些切片反而更加模糊了可能的走向,使電影產生了強復讀性。
在《過》中,被切片影響的可復讀場景讓觀眾陷入迷惑,很難判斷到底哪一處敘事是真實的。電影一開始,王自亮究竟知不知道污染企業的罪魁禍首是他的弟弟?他所謂的道歉,是對誰道歉?他的弟弟王自健究竟有沒有動手解決律師?他在美國的妻子,來美國機場接他和他見面時候的模樣,以及他們一家四口在后續的日常歡樂氣氛中的相處,是否真實?妻子當時是否知情?妻子所謂的副卡,是為了維護女兒編造的謊言還是真實存在?情人染了頭發之后在候機室等待的究竟是誰?
這些疑問在片尾的切片輪放中逐漸升騰起來,成為電影的開放式謎團。它們存在于不同的事隙之間,散點化的敘事消解了確定的敘事邏輯,同時也消解了對現代性社會宏大敘事的運行。
(三)汽車空間:被裹著走
電影里的汽車空間是一個極易被忽視的空間。作為事隙,汽車空間雖然不具有完整展開敘事的能力,但依然起到了銜接其他敘事空間的作用。在影片中,王自亮有將近三分之一的時段在汽車空間里,從電影一開始駕車送母親去醫院,一直到輾轉于律師事務所、話劇社、電影片場、徽州老家、機場和洛杉磯妻子的家。
同樣的,汽車空間里發生的種種細節,讓王自亮要面臨的情況愈發復雜,手機與汽車空間亦出現高度重疊。王自亮與兄弟姐妹商量如何與母親過年的場景大部分發生在車上;情人在車上告訴他“我媽媽來了,要見你”,牽扯出吃飯的戲;妻子打來的視頻通話,王自亮能不接就不接,妙果說“你不是在路上,就是在寫劇本”,埋下夫妻失和的伏筆;成功老板的秘書在車上和王自亮聯系,希望取消他的署名權。
無論是汽車在車水馬龍的道路上前行,還是汽車里的人的心緒,都體現著如王自亮好友肖凡所說“人不都是裹著走的嗎?”的內卷化進程。人被汽車裹著向前走,汽車被更急速的現代化裹著向前走,現代化則被更宏大的時代漩渦裹挾著前進。學者趙軍就認為這個看似圓滑的生活哲理,“是一個喪失了信仰和是非觀的社會最為悲哀的寫照”[20]。
最后出現的汽車空間是車禍現場,當律師的自駕車撞上運輸煙花爆竹的貨車時,因為突然裹進車禍而引爆的煙花爆竹的聲音不斷響起,象征著現代性生活驟然迎面撞上再也無法逃避的年節。
結語
電影作品塑造了眾多不同的空間,這些空間之間的內互文性形成的解釋學循環最后形成獨特的空間美學表達。《過》所形成的空間感,形成了魚咬尾式的多重闡釋空間,一如主題曲《假如還有來生》的頂真式結構與循環式內容,融入了尹力導演的心理現實主義風格,成功彰顯了中國式敘事對空間美學的獨特魅力。
參考文獻:
[1][8]尹力.《沒有過不去的年》現實主義的銳度和溫度——尹力訪談[ J ].電影藝術,2021(01):79,83.
[2][16][美]浦安迪.中國敘事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95,46.
[3]Stanis?awDro?d?,Quantifying origin and character of long-range correlations in narrative texts[ J ].Information Sciences,2016.Volume 331,2016.2,pp32-44.
[4]俞曉紅.論戲曲文本在非線性敘事中的構成——以《牡丹亭》為考察中心[ J ].戲曲研究,2018(02):242.
[5][日]上北千明.擬日常論[EB/OL].新·批評家育成サイト,https://school.genron.co.jp/works/critics/2015/students/kamikita/1065/.
[6]劉紹禹.反對廉價雞湯,真正的團圓電影應該像這樣[EB/OL].虹膜,https://mp.weixin.qq.com/s/VrPzhB_B7BkrqlOD8qoG4w.
[7][美]博伊姆.懷舊的未來[M].楊德友,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50.
[9][11][12][法]福柯.另類空間[ J ].王喆,譯.世界哲學,2006(06):54,55,57.
[10][法]福柯.不同的空間——激進的美學鋒芒[M].周憲,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22.
[13]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4.
[14][英]齊格蒙特·鮑曼.懷舊的烏托邦[M].姚偉,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169.
[15][美]麥克勞德.理解漫畫[M].萬昱,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10:63.
[17]王諍.專訪導演尹力:灼熱之后才知道什么叫生活[EB/OL].澎湃新聞,(2021-01-16)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805040.
[18]李明,林潔.論電影的復調敘事結構[ J ].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8(02):83.
[19][英]阿拉斯坦泰爾·倫弗魯.導讀巴赫金[M].田延,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7:101.
[20]趙軍.什么原因讓我們過不去了?——琢磨《沒有過不去的年》[N]中國電影報,2021-01-20.http://chinafilmnews.cn/Html/2021-01-20/552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