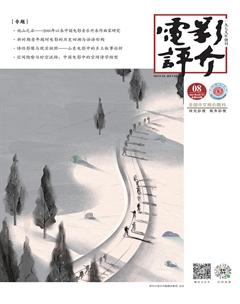歐美畫家傳記電影的繪夢審美之旅
蔣蕾蕾
一、敘事斷想:藝術靈魂的沉睡與蘇醒
傳記電影是“有關文學與電影、歷史與虛構、記憶與想象等跨界的藝術。”[1]歷史真實與合理的藝術虛構,共同組成了傳記電影的情節內容,受到大眾客觀認可的記憶和創作者的自由想象,二者的比重則決定了傳記電影的敘事方式。我國藝術家的傳記電影,如陳凱歌執導的傳記大片《梅蘭芳》,基本遵照梅蘭芳先生的真實生平,以史實為根基,敘事主線清晰、段落分明,如同梅蘭芳一生的編年史般娓娓道來。影片涵蓋了梅蘭芳少年、青年、中老年三個不同的人生階段,分別以舊派京劇代表人十三燕、紅顏知己孟小冬、戲迷邱少白三個人物串聯起梅蘭芳先生各個時期對京劇的重要貢獻。而西方傳記片脫離了“演史”傳統的束縛,得以不拘泥于歷史原貌、相對隨性地演繹主人公的傳奇人生。與《畫魂》《八大山人》等中國畫家傳記電影相比,西方畫家傳記片少有甚者皓首窮經式地苦心創作,更注重描寫靈感迸發的瞬時力量,鏡頭下的畫家自由徜徉在藝術的伊甸園中,近乎狂熱地獻身于藝術,而影片往往截取人物的特定經歷,用倒敘、插敘的方式代入其他片段,由此突出情節本身的引人入勝。
西方藝術家傳記影片的主旨是藝術精神的恒久與偉大,主人公在片中儼然是行走于塵俗間的藝術化身,代表著人類對美與真情的孜孜以求。他們大多反叛傳統、特立獨行,影片情節也因此變得曲折離奇,主人公時而靈光一現、藝術源泉噴涌奔流,時而窮困潦倒、成為世俗任意踐踏的對象。一如電影《莫迪里阿尼》中的藝術雙星——畢加索與莫迪里阿尼。出身于猶太貴族家庭的莫迪里阿尼在經歷家族沒落后,變得行為放誕、性情古怪,片中重復閃回莫迪里阿尼童年時的債主上門的驚心場景,側面揭示人物內心時常惶恐不安的原因。而片中的畢加索則站在莫迪里阿尼的對立面,他卓有才華,更能輕松搞定客源和展覽,以藝術為捷徑成功躋身上流社會。影片對二人的形象進行了大刀闊斧的藝術改編,側重描寫兩種不同的藝術態度,畢加索的入世與莫迪里阿尼的出世,在20世紀初巴黎的咖啡館中雙星閃耀,二人跨越貧富階層的惺惺相惜,更是浪漫情結與人文關懷的相生相融。電影更用大量筆墨渲染了莫迪里阿尼的愛情,填補了許多歷史宏觀視角無法觸及的細節。莫迪里阿尼畫作中那些擁有修長脖頸、緊閉雙眼的神秘女子,是一個藝術天才與情癡的情感噴發,片中那句“只有當我了解你的心靈深處時,我才會畫上你的眼睛”,成為對莫迪里阿尼作品最富有浪漫氣息的詮釋。電影虛構了莫迪里阿尼在領結婚證的路上被劫匪襲擊等情節,一紙被鮮血染紅的證明,是他送給珍最后的愛情箴言。他在巴爾克扎雕像下頑童般縱情舞蹈的鏡頭,又在此刻猛然閃回,呼應著畢加索筆下的莫迪里阿尼肖像。影片以多層次的、漸進性的敘事展開人物的復雜內心,同時肯定了兩種不同的藝術追求——出離于時俗是一種勇氣,而適應時代同樣是一種能力。借助大量的細節想象與情節虛構,影片大膽描繪出這一獨立于莫迪里阿尼生平事跡之外的題旨,并以此升華影片的思想內涵,體現了傳記電影敘事多元化的重要性與必要性。電影對故事核心矛盾的一再渲染,讓觀眾得以在短時間內抓住莫迪里阿尼真正的一生所求與藝術精神的精髓。
二、浪漫情懷:藝術在繽紛色彩間川流
畫家傳記電影融合了傳記片歷史再現的功能和繪畫藝術的視覺感染力,畫面中川流不息的繽紛色彩,是對主人公創作理念與藝術精神的絕佳表達。色彩賦予了繪畫永恒的生命力,對于電影而言,配色、色調、色塊的運用同樣也是影片抒情達意不可缺少的手段。西方畫家傳記影片大多色調秾麗絢爛,與使用大色塊相比,更注重利用色彩的微觀漸變與細節渲染來表現流動性的氛圍。這類電影還擅于運用高飽和度、高對比度的場景畫面表現藝術噴薄而出的能量,讓繪畫成為主人公宣泄情緒的最佳突破口。
世界影史上第一部油畫電影《至愛梵高·星空之謎》將色彩的運用技巧推向了頂峰,得益于油畫這一特殊的表現形式和主人公梵高的知名度,影片能夠動用龐大的畫家團隊精雕細琢,6萬余張作品、5年的全手工繪制和百余幅梵高原作,編織出梵高奇幻不羈的精神世界。片中表現梵高早年經歷的片段幾乎只有黑白灰三色,他因與世不容的傳教方式被人們無情奚落,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黑白色調暗示著人物灰暗不堪的心理空間,他的思想被困束在單調、沒有色差的房間。而梵高逃離故鄉后,藝術源泉的噴涌讓他迎來了創作巔峰,《向日葵》《羅納河上的星夜》等名作以動態的方式展呈在銀幕上,絢麗的畫面色彩和流動的生命力映襯著主人公失而復得、死而復生的藝術追求。由此可見,色彩對于畫家傳記電影的意義遠不止場景的構建、鏡頭語言的表達,還能夠直接折射出主人公的心理狀態與生存境遇。
獲得奧斯卡獎、金球獎雙料提名的電影《弗里達》更是色彩運用的典例。墨西哥城熱烈奔放的異域風情,本就給予了觀眾充分的色彩想象,而《弗里達》最初的鏡頭恰好是一座被漆成寶藍色的房子。寶藍色如夜空般璀璨奪目,驚艷而又神秘,是對女畫家弗里達性情和人生軌跡的絕好隱喻。她在47年生命中接受了32次手術,最后不得不穿上皮革、石膏與鋼絲做成的胸衣來支撐脊椎。死亡、病痛是弗里達人生的常客,而少女時期的她就在胸口的石膏上作畫,繪出色彩耀眼、翩翩欲飛的蝴蝶,蒼白的石膏與彩色的蝴蝶是影片對痛楚與美麗共生的隱喻。
“影視創作利用人對色彩的情緒反應來選擇符合劇情、場景氣氛、人物心情需要建立畫面的主色和重點色。”[2]《弗里達》作為一部以主人公愛情經歷為主線展開的影片,它用繪畫中的繽紛色彩來詮解愛情。弗里達在教堂邂逅了比她年長21歲的丈夫迪亞哥,二人結為終生的藝術伉儷與靈魂伴侶。在迪亞哥離開時,弗里達在憤然與自暴自棄中創作了享譽世界的名作《兩個弗里達》,身著白色服裝的她和身著金色服裝的她,通過一根鮮紅的血管將兩顆心臟相連。畫作中深愛迪亞哥與失去迪亞哥的兩個自我,就像影片中的那所藍房子一樣。一度失去了精神支柱的弗里達每日以淚洗面,房子的墻壁是灰白的、庭院是頹敗的,當迪亞哥提出復婚二人重新找回愛情后,房子才再次出現了明麗絢爛的色彩。藍色墻壁搭配紅綠相間的窗欞,顯得恣意而浪漫,庭院中有蓬勃生長的仙人掌和拖著翠綠長尾的孔雀。
對比度、明度較高的空間,象征著人物內心熾烈燃燒的愛情與揮灑得淋漓盡致的生命,這便是弗里達人生的主色調——一個有著連心濃眉、敢于挑戰世俗目光的女人,同樣也是一個飽受肉體與愛情的苦痛折磨,依然燦爛綻放的靈魂。恰如片中迪亞哥在畫展上對弗里達作品的評述:“犀利又溫和,柔美如蝶翼,堅硬如鋼鐵,討喜如微笑,殘忍如人生……”片中絢麗璀璨的色彩意在突顯生命的殘缺與藝術精神的無瑕,在一片濃墨重彩的漸變中繪出這位傳奇女子的人生態度。色彩是繪畫與電影兩種藝術形式的交點,也是作為電影主人公的畫家與影片創作者跨越時空的深層共鳴,色彩能夠在光影變幻中找到比視覺藝術更為深刻的內涵,這也正是畫家傳記片的獨到之處。
三、悲美內蘊:創作個性與生活個性的背離
傳記片以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為原型進行藝術加工,片中人物形象始終無法完全脫離歷史真實,卻又要盡可能地完成藝術審美上的升格化,塑造比主人公的歷史原貌更為動人的銀幕形象。這就需要電影人在創作劇本、分析角色的過程中,將主人公的創作個性與生活個性暫時剝離。換言之,西方藝術家傳記電影認可平凡是生命的常態。
“創作個性是指在一定生理基礎上并在社會實踐中形成的藝術家個人獨特的較穩定的全部心理特征的總和。生活個性在生活實踐中形成,并在實際生活中起作用……生活個性不是創作個性,生活個性要通過創作實踐的審美的升華,才能變成創作個性。”[3]西方傳記片中的藝術家,其創作個性與生活個性并不總是合一的,相反,二者的背道而馳反而能夠強化戲劇效果,人物在藝術殿堂的長駐和在人間的彷徨逡巡,象征著精神的永恒與生命的轉瞬即逝,呈現出動人的悲劇色彩。法國電影《花落花開》以樸素畫派代表人物薩賀芬的繪畫生涯為故事主線。薩賀芬只是一名家貧如洗、身材臃腫的女仆,靠幫傭和朋友救濟生活,片中的她多數時候只能吃主人家的剩飯,甚至不舍得浪費一丁點面包屑;因為買不起顏料,也只能用動物血液、蠟油和綠植自己動手調制。沉浸于繪畫創作中的她完全不是身份卑微的女傭,儼然是藝術世界的主人。薩賀芬在與野草、大樹、花鳥的心靈對話中汲取靈感,繪出她心中的大自然。畫作中恣意盛開的繁花像燃燒的眼睛,照亮曠野四周的茫茫長夜。當畫界經紀人幫她拍照時,薩賀芬的目光始終避開鏡頭望向天空,她堅信是天空與自然賦予了她敏銳的藝術觸覺。《花落花開》的開篇是基于薩賀芬地位與藝術才華的反差來構寫故事的,與許多畫家傳記片一樣,主人公極力排斥被凡庸的人海所同化,卻又不得不耗費大量精力鉆營現實的生存問題。抓住其中繁華憔悴的強烈落差,是建構影片悲美內蘊的前提。
《花落花開》更將創作個性與生活個性的對立融進了情節發展中。畫評人伍德的出現終結了薩賀芬的幫傭生活,靠著賣畫的豐碩報酬,薩賀芬從拖欠數月房租到出手租下整層房子,從買不起取暖的炭火到買空了商店的銀器。薩賀芬遇見“伯樂”伍德,是影片敘事基調的轉折點,他的到來,讓她的后期創作遠離了自然、走向為附庸風雅的上層人士服務,但薩賀芬也因伍德的消失而精神失常。當她不能夠重拾畫筆而被牢牢捆在病床上時,伍德再次到來,為她安排了一棟推開窗便能看到曠野和藍天的房子,影片也在此刻戛然而止。
自然的失落與復歸讓觀眾感受到,當人物安守清貧寧靜、從心所欲地創作時,她的心靈同樣了無羈絆;當她將藝術作為改變低微出身的附加手段時,她對名利的熾熱渴望反而灼傷了自我。影片最初,以原野、微風與低垂的天幕營造出詩意的美與沖淡的哀愁,隨著自然景象的隱去、薩賀芬的自我迷失,她一次次神經質的舉動放大了令人癡狂的藝術之美,突顯了作繭自縛的人性之悲。最終告別了繪畫的薩賀芬再次坐在曠野的大樹上俯瞰村莊草甸、眺望遠方的濃云,此時與彼時景色的一致與人物境遇的落差,烘托出悲美的情感氛圍。觀眾站在薩賀芬藝術生涯與人生道路的盡頭回望,更能領略創作個性與生活個性無法合一時畫家內心的煎熬。影片表面以凄婉哀愁的語調敘述了主人公一生的遭際,實則是為了喚起觀眾對藝術與人生的無盡思索。
四、時代困局:一場遲到的精神自贖
藝術家在不同社會時期所處的位置也各不相同,畫家的社會地位與生活境遇也因此成為傳記電影爭相描寫的主題。繪畫對于他們究竟是最基本的謀生手段還是精神世界的支柱,抑或是優越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點綴,影片大多從畫家與繪畫的關系著手,探討人物出身、社會地位與性格所帶來的差異,以此表現主人公藝術人生的曲折傳奇,以及對藝術極致境界的不懈追求。電影往往采取相對抽象的表述方式,所要突顯的是繪畫與電影帶來的雙重感官效應,而非直接言明特定時代的歷史背景,借由藝術的浮光掠影引導觀眾去感悟歲月洪流中美學情懷的不朽。
大部分畫家傳記電影都在試圖營造內外交困的環境氛圍。一方面,主人公受制于藝術嘗試得不到主流社會認可;另一方面,外界挫折加劇了他們與生俱來的敏感情緒,讓他們在無數次自我懷疑與靈魂迷失中踏出一條通向藝術的坦途。如電影《梵高傳》,通過多種視角表現了繪畫對于梵高的意義,一個青年懷揣著不合時宜的藝術思想,承受著大眾不入流的批評質疑,只有提奧是他藝術樂園的忠誠衛士。片中的梵高試圖將繪畫作為單純的謀生工具,卻又下意識地承認繪畫是自己宣泄情感的唯一出口。這樣的矛盾讓他的靈魂與畫作愈發緊密地貼合,像轉瞬即逝的曇花般,在歷史的一瞬迸發出耀眼的浪漫主義情懷。而他的畫作與靈魂二者殊途同歸,都在冷言冷語和褻瀆的目光中完成了對自我的救贖。
傳記電影主人公與社會環境、歷史進程的錯位構成了影片最重要的視角,西方畫家傳記片也因此出現了一個必不可少的角色——畫作經銷商。他們是畫家與買主間的紐帶,象征著繪畫作為生存工具的經濟職能,他們或許能夠成為畫家的伯樂,又或許只是世俗奴役畫家生命的影視表征。影片《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借由一幅世界名畫的誕生講述了畫家維米爾的困境,他不但寄人籬下,每日要忍受岳母和妻子對自己藝術創作的誤解,還要受到畫作經紀人的多重牽制,經濟上的困窘讓他不得不完全按照對方的要求作畫。他與女仆葛利葉于世難容的愛情雖是電影的杜撰,卻頗具象征意味。葛利葉擦拭窗戶讓陽光照進畫室,隱喻著維米爾精神世界中繪畫靈感的闖入,而經紀人信口雌黃,要求維米爾創作一張葛利葉與他的畫像,則代表著世俗力量對藝術精神的綁架。最終,維米爾和經紀人各自妥協,為葛利葉創作單人肖像,又暗示著藝術與社會共同訴求的統一。維米爾偷來妻子的珍珠耳環、葛利葉脫下頭巾露出金色長發,這些必不可少的細節,表現了藝術對世俗壓迫的輕蔑與種種反抗。電影通過構想一系列藝術家生存境況與外界環境間的矛盾,表現了以維米爾為代表的許多畫家的真實心態。他們中的大多數生前窮困潦倒、身后揚名立萬,藝術的先鋒性使他們注定不能在正確的時間獲得大眾認可。但無可否認的是,恒久的審美應是一種情懷,一度湮滅在歷史浪潮中的滄海遺珠,仍舊會在百年乃至數百年之后以另一種方式被現代人所發掘。盡管時代的局限性限制了藝術家的個性自由,但畫家傳記片中所傳達的種種反思,足以證明當下西方電影人對于人文精神的肯定。社會歷史的發展不具備先驗性,但我們仍不妨保留長遠的眼光看待藝術的發展、看待藝術家的個人選擇,以悲憫的情懷燭照塵世間眾多靈魂對藝術境界的追求。西方傳記電影的哲思性正在于此,它們不僅是藝術形式上的創作,更是藝術精神上的生命寫作。
結語
畫家傳記電影是兩種藝術形式最完美的跨界,它以銀幕為畫布、以鏡頭作畫筆,讓畫家本人成為自己畫作的一部分。西方畫家傳記片在敘事風格上偏向于描寫矛盾沖突,通過構寫主人公拿起藝術之盾抗爭時俗的故事,表現人物求而不得、內外交困的生存境況,以此反襯他們在歷史洪流中的心靈掙扎以及對藝術的不舍追求。這類影片分別透過藝術殿堂和現實社會的兩個空間維度重審人物,在天賦異稟、聲名顯赫、命運坎坷的傳奇性之外,電影再現了每個生命個體都具備的凡俗性,讓主人公的銀幕形象更為血肉豐滿。西方畫家傳記影片前衛的色彩運用、多元的敘事手法,均為我國藝術家傳記片的創作與研究提供了啟示,指引我們更好地探索繪畫、影視、文學三者的跨界共鳴。
參考文獻:
[1]張英進.傳記電影的敘事主體與客體:多層次生命寫作的選擇[ J ].文藝研究,2017(2):86.
[2]張菁,關玲.影視視聽語言[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6:42.
[3]童慶炳.藝術創作與審美心理[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