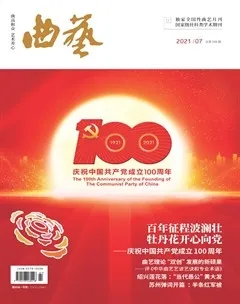記憶與思考
田連元
人們的記憶往往始于4到6歲,那時你還是孩子,發生的事情會在你的腦海里產生印記,但并無思考。思考往往是在你上學讀書之后,產生了思維模式、是非觀念、邏輯定理,便有了“事件為什么要這樣,而不是那樣”等自我提問。
我的記憶,應該是在6歲左右,“遼沈戰役”的時候。血戰四平時,我在四平城內,常見變換入城的隊伍,鬧不清正反、對錯。1948年,我到了天津南郊,又趕上了“平津戰役”。那時我8歲,天津解放了,也有成年人的喜悅和高興。
抗美援朝時,我已在天津上學。學會了歌曲,“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覺得中國很了不起。
真正有了思考,應該是加入本溪市曲藝團,成為一名專業曲藝演員后。那時,經常學習的就是毛主席1942年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明確了文藝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為了貫徹執行這個方向,我們團經常下兵營、去軍部、赴礦山、到煉鋼爐前,為士兵、為工人同志們服務;也經常下鄉,去公社、下大隊為農民演出。為了服務到位,有一次,我下到馬塘公社最遠處的施家大隊演出,那里離火車站還有50里路。我聽說一位軍屬老大娘住在密林深山,獨門獨院,一輩子沒看過節目,便請公社文教助理陪同,又步行15里路,為這位沒看過文藝節目的老太太一個人,說了一段《程咬金賣耙子》。老人家聽得津津有味,臨走時還在問:“后來那個人怎的啦?”我說:“下次來再給您說。”由于當時那里沒電,我們只好趁天黑之前快往回趕,不然怕遇見狼。
“文化大革命”之后,文藝事業復蘇。在黨的政策的感召下,我們又擴大了為人民服務的范圍和地域。為貫徹和弘揚傳統文化,我的評書《楊家將》首開了電視評書的欄目;并為中央電視臺策劃、主持,開播了《曲苑雜壇》的專題設置;我還多次參加中國文聯的萬里采風活動,最高曾到過海拔5300米的“紅其拉普”口岸,中巴邊界界碑,慰問邊防戰士,最低曾到徐州礦務局“豎井”地下1300米巷道“掌子面”,為一線工人現場演出。
在黨的文藝方針指引下,為了宣傳時代楷模、道德模范,我參加了6次由中央文明辦、中國文聯聯合舉辦的“全國道德模范故事匯巡演團”的演出。巡演大力宣揚軍中的見義勇為的盧家勝、勇斗歹徒的廈門三兄弟、文藝界的“好漢”金漢、影星田華等典型的先進事跡。在建黨百年之際,我要寫錄一部評書《話說黨史》(1919—1949),作為獻禮節目。這就需要我了解建黨初期的往事和經過。我沒有當時的記憶,只有靠閱讀和看資料,這叫作“閱讀記憶”和“觀賞記憶”。這種“記憶”,把我帶到了“想當年”和“那時候”。
寫黨史、說黨史,讓我在學黨史的同時更受教于黨史。當大革命失敗后,蔣介石掌握了全國軍政大權,對共產黨斬盡殺絕、斬草除根的時候,不少意志薄弱者脫黨而去;也有不少意志堅定者,死于敵人的屠刀之下;更有堅定信念者,擦干了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體后,挺身而立、繼續戰斗。此后產生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全國無數次的起義,乃至“上井岡”“反圍剿”“萬里長征”,哪次革命活動都是無數先烈的生命和鮮血換取來的。僅以陳毅元帥描寫贛南游擊戰爭的一首詞,便可見當時斗爭環境之艱苦。“天將曉,隊員醒來早,露侵衣被夏猶寒。樹間唧唧鳴知了,滿身沾野草。天將午,饑腸響如鼓,糧食封鎖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數,野菜和水煮……”
尤其是1936年冬,游擊隊被困20余日,最后到了無米下鍋的地步。傷病在身的陳毅,面對死神的即將到訪,他仍有革命者視死如歸、斗志不減的氣勢,寫下流傳千古的《梅嶺三章》:“斷頭今日意如何?創業艱難百戰多。此去泉臺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南國烽煙正十年,此頭須向國門懸。死后諸君多努力,捷報飛來當紙錢。投身革命即為家,血雨腥風應有涯。取義成仁今日事,人間遍種自由花。”這是一個面臨死亡的革命者的豪言壯語,這里包含著“創偉業、建新國,圖復興、為人民”的偉大抱負。如今我們學黨史,就要“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識崇德、學史力行”,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
在我們的學習記憶當中,再思考新的征程。
(作者:評書表演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