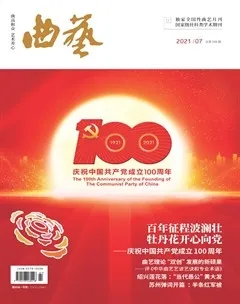毓秀鐘靈 天津瑰寶
佀童強

天津時調一代名師王毓寶是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天津時調)代表性傳承人,天津市藝術研究所(原天津市表演藝術咨詢委員會)國家一級演員,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員,中國曲藝牡丹獎終身成就獎獲得者,中國金唱片獎獲得者。2021年6月10日16時21分,王毓寶在天津去世,享年96歲。她的去世是天津時調的損失,也是中國曲藝界的重大損失。
王毓寶先生逝世后,文化藝術界眾多組織和個人均發來唁電和慰問信,表達了對王毓寶先生沉痛的哀悼之情。先生仙逝,后生晚輩傷感之余,卻不能徒然涕零而無其他作為。筆者謹以此文略述她的生平和藝術成就,以期大眾能深入了解她的一生,并以她為榜樣,努力推動中國曲藝事業的繁榮發展。
王毓寶的父親王振清(1880—1963)是一名油漆匠,同時也是一位酷愛曲藝的票友,自幼拜天津著名曲藝教師劉萬魁(天津時調名家二毓寶之祖父)為師,學習時調,在天津曲藝票界享有盛譽,也開啟了王氏家族四代從藝的序幕。
據王毓寶先生回憶,她的父母一共生了11個孩子,由于舊社會醫療條件有限,前面的5個孩子都陸續夭折,成長起來的手足6人中,有王殿元、王殿英與她本人從事藝術工作。
王殿元生于1914年,自幼受家庭影響,學習四胡,曾經為京韻大鼓名家林紅玉及多位鼓曲名家伴奏,并且與馬三立、祁鳳鳴等曲藝前輩交情甚篤。
王殿英(1923—2010)16歲時拜天津古典戲法“五大文”之一的王文韶為師,后又師從郭壁臣。新中國成立后,王殿英先后加入天津市和平區曲藝雜技團和天津市實驗曲藝團,是中國戲法界的一代大家。王殿英的長子王天明、長孫王淮、次孫王迎目前都從事曲藝事業。
王毓寶是王振清最小的女兒,丙寅年(1926)十一月十五日出生。當時他們居住的紅橋區關上一帶,正是天津民間藝人聚集的地方。家庭因素和周圍環境的影響,讓她與民間藝術有了不解之緣。王毓寶是聽著大鼓、時調的旋律長大的,調門旋律似乎已經融入了她的血脈。從能記事時,王毓寶就會哼唱。其實,王毓寶的二姐王毓儒(1919—2004)比她學藝早,嗓子也特別好,但是一上臺就憷場,后來就沒有繼續從藝。由于家庭比較困難,王毓寶很早就開始分擔養家糊口的重擔。開始是跟著父親上茶樓走票,后來隨著名氣的增長,她開始趕園子,至20世紀40年代時,王毓寶已經聲名鵲起,成為天津時調界的后起之秀。小梨園、大觀園、群英、燕樂、玉壺春、大觀樓等曲藝場所都留下過她的身影。當時有報刊經常刊登各界對王毓寶的藝術評論。如1948年8月4日的《天津中南報》認為,“王毓寶中行電臺播音,有秦翠紅風味”“此次王毓寶中行電臺播音……連日歌來,頗有秦翠紅之風味,嗓音較以往尤為洪亮,頗好此調者,屆時收聽”。
天津時調是天津地方曲種,或名為時新小曲。天津時調歷史上的較為著名的演員、票友、樂師,如趙寶翠、秦翠紅、王紅寶、高五姑、趙小福、姜二順、新婉華、屈振庭、朱文良(小朱佬)、謝韻秋、魏墨香、侯玉鳳、許成友、孫文林、李玉花、岳小霞、張子清、梁慧珠、王麗云、王寶寅、辛德林、盧成科、阮文祿、陸桐坡、李默生、馬鳳儀等,為時調聲腔的改革創新和藝術的傳播發展作出較大的貢獻。而王毓寶從小就觀摩學習眾多前輩名家的藝術風格,加上自己的表演實踐,很快對時調藝術有了自己的認識和觀點,并為日后鍛造出自己的特色奠定了基礎。
1948年冬,天津群英戲院裝修,就想把曲藝演員推薦給小梨園,讓他們在那里演出一陣子。但小梨園當時是天津頗有聲名的雜耍園子,所以小梨園的經營者對這批“臨時工”有些挑剔,特別提出不要時調等當時被認為有些不上臺面的藝術形式。群英戲院的負責人郝祥金說,“我們的時調不是你想象的那樣,我們的演員唱的都是能登大雅之堂的段子,咱們先試演3天如何?”在郝祥金的擔保下,時調演員也被允許登臺。年輕的王毓寶抓住機會,在3天的演出中先后表演了自己父親傳授的《七月七》《悲秋》《踢毽》曲目,她超群的演技、端莊的形象和文雅的唱詞均備受關注。3天演出完畢,小梨園經營者一改之前的態度,“群英修好了你還得給我再趕一場”。從那時起,小梨園成了王毓寶較為重要的演出場所之一。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王毓寶繼續在天津各大曲藝場所演出,她1950年加入紅風曲藝社,與白云鵬、常寶堃、趙佩如、陳亞南、陳亞華、王寶霞、馬三立等名家同臺,后來又參加了孫書筠任團長的群聲曲藝社,與郭全寶、全長保、周文如、石連城、張壽臣、石慧儒、劉靜雯等名家同臺。她不僅演唱時調,還與孫書筠、桑紅林、司馬靜敏、郭榮起、朱相臣等合作演出了曲藝劇《柳樹井》《劉巧兒》等,并嘗試用【靠山調】演唱新節目。
王毓寶真正展示藝術才華是在1953年。這一年,她在馬三立的推薦下加入了天津人民廣播電臺曲藝團,成為了國家劇團的演員,開始著手對時調進行有針對性的改革。在著名琴師祁鳳鳴、李元通、王文川、王海門,著名作家王焚、姚惜云等人的幫助下,她以一曲《摔西瓜》名響津門,并且把叫了多年的“時調”“小曲”定名為“天津時調”,并初步奠定了自己質樸、爽朗、甜潤的藝術風格。
20世紀50年代中,王毓寶的表演總體呈現出新節目與傳統節目新唱的“雙軌并行”態勢。在她經常演出曲目中,傳統的有《放風箏》《踢毽》《七月七》等,現代的有《提意見》《想心事》《摔西瓜》《糊花燈》等。同時,她還培養和影響了一批專業或對天津時調有較深造詣的演員,如郭菊蘋、陳富貴、邢慧琴、王萍、邱鳳蘭等。
1958年是王毓寶帶著天津時調走向全國的一年,她在撼人心魄的《翻江倒海》(天津市曲藝團創作室集體創作,紀希、高天執筆)中,用激昂聲腔和生動的內容立體展現了勞動人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戰天斗地的英雄氣概。這個節目在北京舉辦的首屆全國曲藝會演中廣受好評,全國的曲藝工作者也從此知道了天津有一個唱“女高音”的王毓寶。匯演過后,她與高元鈞、駱玉笙、蔣月泉、朱慧珍、李錦田、楊海荃、郭文秋等曲藝名家一起進行了全國巡回演出,把天津時調唱遍了大江南北。
20世紀60年代初,王毓寶積極響應“挖掘傳統、繼承傳統”的號召,開始以自己的方法整理藝術。老藝人姜二順能演唱很多瀕臨失傳的小曲、小調,但老人年壽漸長,王毓寶擔心這些小調失傳,所以就拜在姜二順的門下,用心學習整理老人的藝術成果,并將之化用到天津時調中,收獲了較好的效果。
20世紀60年代,王毓寶等與作者、樂隊們又創作出了贊頌革命者大無畏精神與高尚情懷的《紅巖頌》《換崗哨》《毛主席來到咱農莊》等作品,這些作品夾敘夾議,為拓展天津時調的內容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豐富了天津時調的曲本庫。同時,她還嘗試創作了以“數子”增強敘事性的《賣椰子的老大娘》等曲目,并且接受解放軍戰士的建議,嘗試在天津時調的演唱中增加表演動作,有效改變了天津時調“沒有表演”的傳統面貌,豐富了藝術的舞臺表現力。
正當王毓寶頻創佳作,努力攀登新的藝術高峰時,“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她被扣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帽子,關進了“牛棚”。據她后來回憶,身體和精神上的折磨尚在其次,對天津時調的攻擊才是她最感痛心的。天津時調是她的生命,是她絕不會舍棄的精神之魂。在恢復演出后,她的創演熱情迸發出了巨大的能量,“誰也不能說天津時調不行”幾乎成了她的執念。一曲由王濟創作的《大寨步步高》迅速風靡全國,那個年代的人們,幾乎都能哼唱出“虎頭山喲,高又高喂……”的曲調。
她與著名作家朱學穎、著名弦師馬滌塵合作創演了《軍民魚水情》,這個詞意清新、韻律爽脆的曲目成了那個時代的“流行音樂”。專業曲藝團體中,部隊和地方的業余宣傳隊里,群眾的口耳之間,都縈繞著《軍民魚水情》的旋律。這個講述了一個做軍鞋、送軍鞋故事的作品,不僅貼合了當時的時代需求,生動地表現了軍民之間的深情厚誼,在唱腔上更有突破。王毓寶合理借鑒京劇《打龍袍》中“報花燈”的數板方式,在這個作品中運用了1/4拍的新板式,為唱腔平添了旋律變化。同時,還在韻誦和念白中交錯運用京津方言,使人聞之倍感親切。而【老鴛鴦調】長腔的巧妙運用,更讓人拍案叫絕。

這一時期她還為天津市曲藝團培養出了賈立青、王桂玲、王榮芬、高輝等演員,為天津時調在寒冬后的復興積蓄了力量。
粉碎“四人幫”之后,張俊作詞的《心中的贊歌向陽飛》是她的代表作,也是她一吐胸中塊壘的抒情詩。在這個作品中,她既道出了群眾對“四人幫”的深惡痛絕,也吐露了文藝工作者對黨的好政策、人民的好領袖的期盼與懷念。其中一段懷念周總理與文藝工作者聚會的唱腔,巧妙地糅進了《洪湖赤衛隊》中《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調,每當她唱到“我唱洪湖水,總理拍手隨;我唱南泥灣,總理來指揮;再要往下唱,總理怕我累,站起身讓我坐在他周圍”時,王毓寶總會情不自禁地流淚。
20世紀80年代初,她與作者李光、著名琴師馬滌塵一起改編創演了孔繁青的《夢回神州》,又一次獲得巨大成功。在這個作品中,王毓寶采用【老鴛鴦調】作為基本唱腔,以表現臺灣同胞思念大陸,懷念家鄉的哀傷抑郁之情。作品詞曲情緒一致,韻律深沉感人,但又在低回傷懷的“水窮處”恰到好處地轉向激越奮昂的“云起時”,慢板的【老鴛鴦調】轉為【二六板】,直至結尾形成高潮,很好地表達了臺灣同胞渴望祖國早日統一的真摯心愿。
1986年,中國北方曲藝學校在天津成立,王毓寶與自己的師妹二毓寶共同擔任天津時調的教師,從1986年到21世紀初,她們先后培養出梁淑華、劉迎、劉文紅、劉渤揚、陳美美等一批優秀的天津時調繼承人。而王毓寶更是不顧自己年事已高,在專心課徒的同時還不斷創演新作品,如《津門老字號》《津城美如畫》《十美放風箏》等,都是她在20世紀90年代創作出來的。
2000年之后,王毓寶逐漸減少了登臺的次數。但只要參加演出,她總會爭取把最好的一面呈現給觀眾。
2015年12月25日,劉小凱主編的《天津有個王毓寶》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本書用扎實的資料和生動的語言詳細介紹了王毓寶的從藝經歷和天津時調的作品曲譜,而多位文化名人撰寫的文章,更可以幫助讀者立體地了解天津時調中的王毓寶。
2019年9月13日,由天津市曲藝團、天津市曲藝促進會、天津市曲協共同主辦的慶賀天津時調大師王毓寶從藝85周年理論研討會在天津同悅興茶社舉行,孫福海、趙玉明、靳學東、籍薇、張蘊華、種玉杰、岳長樂、王力揚、李伯祥、魏文亮、崔琦、趙振嶺、王永良、宋勇、宋東、楊妤婕、劉小凱、劉迎、劉渤揚等多位京津兩地的曲藝藝術家和學者都出席會議,并對王毓寶的人品藝德進行了精到分析與高度贊揚。
王毓寶不僅是一位藝術家,還是一位謙和的長者。在曲藝界的舊俗中,“名角兒”“大腕兒”是演出的核心,樂隊弦師則只是“角兒”的附屬,演員可以對弦師招之即來,揮之即去。新中國成立前,弦師的報酬要靠“角兒”賞。演出分紅,依然是由“角兒”按比例分給樂隊,但不論是三七開還是二八開,哪怕是看著比較公平的四六開,樂隊所得仍然少于“角兒”。但王毓寶從來都是與樂隊平均分紅。她從藝以來,對長輩弦師禮敬有加,對平輩或者晚輩則是平等相待,不管是演出還是排練,甚或是弦師在臺上出現差錯,她從未有過指責、呵斥等“耍大牌”的表現。更可貴的是,在她所有的節目中,哪位弦師參與了唱腔設計,她就會主動在相關的出版物或宣傳中標明弦師的名字,而不會急吼吼地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顯眼的地方,哪怕弦師是她的學生或者晚輩也一樣。久而久之,一些不明就里的觀眾就覺得:“王毓寶不會裝腔!”她聽到后也只是微微一笑,“沒有這些老師就沒有王毓寶的今天”。不爭不辯,云淡風輕。“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以藝動人而以德服人,王毓寶真正做到了德藝雙馨。
在幾十年的藝術生涯中,有一位幕后英雄一直在默默地支持著王毓寶,那就是她的丈夫劉志凱。劉志凱1923年生于天津,為人熱情,性格豪爽,酷愛曲藝,尤其喜愛天津時調。解放初期,經人介紹,還在天津紡織管理局工作的劉志凱與王毓寶相識相戀。1954年劉志凱調到石家莊工作,1956年春,兩人結為連理。婚后,劉志凱常年在外,每年只能回來近一個月的時間,這樣兩地分居的生活一直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初,劉志凱才被調回天津,夫妻二人才算得以團聚。劉志凱全力支持王毓寶的藝術事業,參與創作《拷紅》《小燕學藝》《劉少奇來到花明樓》等唱段。二人琴瑟協調,但天不作美。一向身體健康的劉志凱,在1984年11月24日8時出門后,在天津火車站的天橋上突發心臟病,雖有好心人把他及時送到天津第一醫院,但為時已晚。
老伴去世后,王毓寶就一直與次子劉小凱、兒媳王麗萍生活在一起,兒子、兒媳非常孝順,小孫子也已經成家生子,一家四代同堂,其樂融融。劉小凱1983年進入天津曲藝團,專攻四胡和大提琴,是國家一級演員,幾十年來曾經為王毓寶、史文秀、趙學義、張秋萍、籍薇、王莉、王喆、劉迎、劉渤揚等曲藝名家伴奏,并且能夠幫助母親設計唱腔、課徒傳藝,現在已成為天津市曲藝團樂隊中的骨干和天津時調重要的傳承者之一。
王毓寶的長子王大海,1968年下鄉至內蒙古呼倫貝爾盟科右前旗,1972年考入吉林曲藝團,與演員劉威搭檔說相聲,1987年正式拜董湘昆為師,開始學習京東大鼓,現已成為東北著名的京東大鼓表演藝術家,國家一級演員。他在董湘昆的唱腔基礎上大膽突破,發展出的“滑稽京東”在曲藝界頗有影響。王大海雖年逾七旬,但依然活躍在白山黑水間,為百姓演出。
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隨王毓寶學習天津時調者不計其數,正式拜在她門下的有劉迎、劉渤揚、陳淑萍(已故)、楊麗玲、史琳、房玉霞、王勝霞、志淑嬿、禹美茹等,筆者也列于門墻。此外,在南開大學薛寶琨教授的推薦下,她還與陸倚琴共同收過留學生弟子白卓詩,為傳統文化的廣域發展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