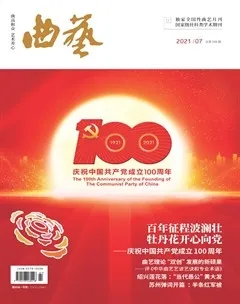圈外介入 別具洞天
《曲藝》雜志:非常感謝孫教授能撥冗接受我們的采訪。您是《曲藝》的忠實讀者,從2016年至今,近5年來筆耕不輟,在《曲藝》和其他文藝界姊妹刊物上發(fā)表了50余篇與曲藝相關的文章,在曲藝界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更拿到過中國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的“啄木鳥杯”。但據(jù)我們所知,您的研究領域是航海交通,是什么推動您年逾古稀時,跨界投身于蘇州評彈的研究中呢?
孫光圻:周恩來總理有句名言,“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保持對知識的好奇心,我認為應該是我們大家共有的一種素質(zhì)。但你剛才還是過譽了,“影響”云云,我自覺還是擔當不起。如果一定要為目前我的“曲藝狀態(tài)”標定一個“身份”的話,那就是一個“半瓶水晃蕩的‘老年新兵”,充其量只能算是文藝的業(yè)余愛好者,遠遠談不上是“專業(yè)人士”。但這種跨界,并不是我一拍腦袋后的決定,而是一種長期受特定環(huán)境影響后自然而然的反應。
美國學者露絲·本尼迪克特認為:“個體生活歷史首先是適應由他的社區(qū)代代相傳下來的生活模式和標準。從他出生之時起,他生于其中的風俗就在塑造著他的經(jīng)驗和行為。到他能說話時,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創(chuàng)造物,而當他長大成人并能參與到這種文化的活動時,其文化的習慣就是他的習慣,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事實上我的跨界根源就在這段話中。蘇州評彈是江南地區(qū)的代表性曲藝曲種,它的根深扎在江南文脈和社會基礎之中,江浙滬地區(qū)的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地會受到它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它影響下的“小小的創(chuàng)作物”。
在青少年時期,我父親就常帶我去上海的書場聽書,收音機中的評彈說唱聲也是我們家重要的“背景音效”,聽過《三國演義》《英烈傳》等評話,我又開始對《三笑》《楊乃武與小白菜》等彈詞作品產(chǎn)生了興趣,就此一發(fā)而不可收拾,甚至有次為了不誤過特定時間段的彈詞節(jié)目,我沒去參加親戚的婚宴,真可謂“一近評彈如入海,從此俗事如路人”。后來雖然到外地讀大學,但仍是千方百計利用各種機會回上海購買各種彈詞的音像制品。大學畢業(yè)后留校工作,我也時常在教學與科研之余,以聆聽、哼唱彈詞自娛。日積月累,從“聽”到“品”,而入“思辨”,想更深入地了解彈詞的藝術構造。所以,我今天跨界深入到彈詞的研究中,不是心血來潮,而是一種長久積累以后自然而然的反應。明代大儒王陽明夜間練氣,倏忽沛然而不能御,引氣長嘯,聲震十里,也是一種長久修煉后的反應。事殊異而理相同,浸淫彈詞若久,我也想要引氣而呼。

《曲藝》雜志:如您剛才所言,您對彈詞的興趣是從小培養(yǎng)起來的。從心理學的角度而言,興趣和愛好,是一個人力求接近和探索某種事物,并從事某種活動的積極心態(tài)和行為傾向。這種心理狀態(tài),可以使一個人對某種事物和活動觀察敏感,記憶牢固,思維活躍,情感深厚,從而使其行為具有特殊的進取性和創(chuàng)造性。正如莎士比亞所說,“學問必須合乎自己的興趣,方可得益”。那您有沒有想過以興趣為師,把彈詞當作自己的事業(yè)呢?您會不會對沒有以彈詞為事業(yè)而感到有些遺憾呢?
孫光圻:你這個問題問到點子上了,說實在的,我高中畢業(yè)后,一度很想報考戲劇類專業(yè)。但因在20世紀60年代初,理工科是一般家庭和社會認同度較高的專業(yè)方向,“學好數(shù)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即此之謂也。而不謙虛地說,我當時的數(shù)理化成績比較好,因此很遺憾的,我與藝術的“飯碗”失之交臂了。因為最近中高考臨近,我想額外就“興趣”多說一點。“興趣是最好的老師”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想要真正明了自己的興趣是什么,可能也需要很長的時間,有的人的興趣會抵不住時間的消磨而失去光彩。就此而言,我還是認為,均衡補充知識營養(yǎng),有計劃地發(fā)掘自己的興趣,有助于健康發(fā)展。等到身體的底子打好后,再進一步向自己的興趣傾斜精力,為時也不晚。就以我來說,雖然學了航海交通專業(yè),沒端上藝術的“飯碗”,但對從小喜歡的文史知識和蘇州評彈始終念茲在茲,沒有放棄。
遺憾的話,肯定有一些。在參加工作的幾十年中,我雖然也曾想多在彈詞上傾注一些精力,但用北方方言來說,我這人稍微有些“軸”,就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nèi),把本職工作做到最好。一來二去,時光荏苒,紅了櫻桃,綠了芭蕉,直到70歲時,我的延聘期結束,正式退休,這才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彈詞中來。但畢竟不是年富力強的小伙子了,聽說讀寫,漸漸有了些不方便。我偶爾會想,如果當年我真的成了一個文藝工作者或者相關領域的學者,現(xiàn)在又會是什么樣子?或許在某個平行空間中,真有一個彈詞演員孫光圻或者文藝理論家孫光圻呢?不過想象結束后,還是得回歸現(xiàn)實,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通過這幾年的實踐,我真切地認識到,跨界和從事本職工作一樣,都要付出巨大的時間成本和精力成本,想要做出個模樣的話更是如此。天上不掉餡餅,一分耕耘一分收獲,跨界參與,必須心所往之,時以付之,力而用之。所以,當前我是拿出了以往搞專業(yè)的勁頭,主動給自己立項目、定任務,經(jīng)常沒有什么休閑日,有時還夜以繼日地干。家人和朋友一開始感到很不理解,“你既已退休,自應頤養(yǎng)天年,何必還要去自討苦吃?”其實他們并不知道,在我內(nèi)心深處,跨界不是討苦吃,而是自尋樂子,盡可能去實現(xiàn)自己的精神抱負和人生價值,從某種角度來說,這也是我別樣的“養(yǎng)生之道”。
《曲藝》雜志:以一個晚輩而不是記者的身份,我還是想懇勸您,一定要注意休息。曲藝是說唱藝術的統(tǒng)稱,包括彈詞在內(nèi),它目前共有500多個曲種。您研究彈詞已經(jīng)頗有心得,今后是不是會考慮再研究其他的曲種?
孫光圻:這個問題本質(zhì)上牽涉到“精”與“博”的辯證關系。《莊子》有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法國數(shù)學家笛卡爾也認為,人類的已知是一個圓的面積,我們知道得越多,圓的面積越大,但圓之外的面積始終會大于圓的面積。如果長期東摘一鱗西取半爪,只能稀釋時間與精力的濃度,不利于出成果。所以,我在曲藝方面的主要精力還是集中在彈詞上,由鑒賞而評論而創(chuàng)作,逐步深化我對它的了解,力求做到一個“精”字。但精研不是“只此一家,別無分號”,這會遮斷自己的目光,束縛自己的思維。就如明清時期皓首窮經(jīng)的舉子們,畢生鉆研八股時藝,作詩作文,真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但論及其他,往往就目僵舌硬,茫然無知,訥訥無言,“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曲藝是一個集體概念,所有曲藝曲種都是它的子集,而如揚州彈詞、長沙彈詞等,與蘇州彈詞可謂同根共生,在藝術特點和表演形式上都非常相似。旁征博引,透過姊妹曲種看彈詞,能對它的藝術概念有更為立體的認識。所以我認為,在豎著挖蘇州彈詞這個“井”的基礎上,還要考慮“橫著開河”,有針對性地加深對曲藝藝術的整體理解,做到“精”與“博”的辯證統(tǒng)一。
《曲藝》雜志:您對“精”與“博”的論述是中肯之談,頗能給人啟發(fā)。您對航海交通的研究應該是最精的,而跨界則也是一種形式的“博”。就此而言,您認為應該如何將原有的專業(yè)知識和彈詞藝術有機地整合在一起,在跨界過程中達到“精”與“博”的辯證統(tǒng)一呢?
孫光圻:唐代文豪韓愈在《師說》中認為,“聞道有先后,術業(yè)有專攻”。就學科分類而言,航海與曲藝一個是理工類,一個是文藝類,確實如風馬牛不相及。但是,任何一門學問都必須符合從實踐到理論的認識過程以及從理論到實踐的應用過程,這種研究方式是共通的,航海與曲藝也不例外。我在原專業(yè)領域曾寫過10余部專著,發(fā)表過200篇左右的論文,這個治學經(jīng)歷對于我從事彈詞理論研究,撰寫相關評論文章是很有幫助的,因為不論是哪一類行業(yè)的評論分析或理論探討,其基本套路還是大體相通的,差異只是在資料和素材方面。
我們一直在說,曲藝是最接地氣的藝術形式,是時代動向的“風向標”和社會發(fā)展的“晴雨表”。我還認為曲藝是老百姓接受知識的“識字簿”。在“上智與下愚不移”的那個時代,黎民黔首要靠什么來獲取知識,擁有最基本的是非觀呢?曲藝就是一種很好的媒介,布巾短衣與引車賣漿者能聽著各種曲藝故事,懂得一些道理,擁有基本的判斷。“說書唱戲勸人方”,這是曲藝社會功能的一種。即使到了現(xiàn)在,信息爆炸,教育水平提高,但大眾依然需要曲藝。“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本身就可以看作一種提純機制,在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現(xiàn)代信息社會中尤其具有特殊的導向意義。同時,曲藝作品還可以有效拓展內(nèi)容的邊界,普及一些可能相對“冷門”的知識,“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大約是曲藝作品表現(xiàn)最多的兩個主題,但航海知識可能就比較新鮮了。所以我希望把我的專業(yè)知識化入曲藝作品中,讓航海文化與曲藝文化水乳交融。因此,我在2016年創(chuàng)作了《海上絲綢之路評彈演唱開篇集》,力圖用評彈去表演航海文化的內(nèi)涵。12個開篇中的6個后來由上海評彈團演出,頗受大學生和評彈粉絲的肯定和歡迎。在此之后,我又從中選擇了《徐福東渡》《鑒真與法顯》《媽祖?zhèn)髌妗?個題材,擴充改寫成為有故事、有情節(jié)、有人物的短篇彈詞,并由江蘇省演藝集團評彈團的青年演員演出了十余場,也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曲藝》雜志:航海曲藝確實是個有趣的新概念,以往的傳統(tǒng)書目,如《三笑》《怒碰糧船》等,也有一些涉及水上航行的內(nèi)容,但底材都是江河湖泊,很少涉及遼闊的海洋和滔天的巨浪。通過您的介紹,我認為這類“海味”濃郁的評彈,對增強和豐富曲藝的表現(xiàn)力不無裨益。如果從評論或理論角度來說,您認為航海交通與曲藝藝術又該如何整合呢?
孫光圻:在這方面我還在做嘗試,不敢妄言成果。目前的想法是,要適度運用航海歷史文化和交通運輸戰(zhàn)略的研究思路和寫作方法,爭取將定性概念與定量分析結合起來。一般來說,傳統(tǒng)的曲藝研究方法側(cè)重于文史背景和藝術表達的實證性研究,較少有細化或量化的解剖式分析。而在航海交通領域,這種研究方法是常用手段,它的最大好處是可以避免研究的主觀隨意性或模糊性。因此,我在撰寫中篇書目評論和進行彈詞藝術樣式研究中,就力求從書目的獨特的表演內(nèi)容和形式出發(fā),重點揭示和闡論其個性化的藝術設計和審美特征。如對《林徽因》的評論著眼于都市評彈的藝術魅力,對《蘆蕩槍聲》的評論著眼于人物塑造的獨特性,對《醫(yī)圣》的評論,著眼于對“評彈劇”藝術指標的評估。
在對彈詞藝術樣式傳承與創(chuàng)新的理論研究中,我嘗試通過拆分其基本藝術信號,界定其自身的結構指標體系,進而提出新的論證方法。我在中國曲協(xié)與蘇州評彈學校主辦的學術研討會上,對彈詞提出了兩級指標的理論概念,為判別評彈的傳承創(chuàng)新以及對彈詞本體樣式的認定,架構了一套客觀的評價指標體系。當然,這只是我基于自己觀察研究所闡發(fā)的概念,疑惑或是評判的聲音不會少,但我始終將太史公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奉為圭臬,這是對“研究—成果”最科學精到的總結。我也期待著大家能對我的“一家之言”提出更多更中肯的意見。
《曲藝》雜志:您剛才的介紹有些概念化,還是想請您結合自身的鉆研經(jīng)歷,更深入地闡發(fā)一下,如何將本身專業(yè)作為“源頭活水”引入曲藝研究的“方塘”中。
孫光圻:首先應該明確,立足于曲藝或者說是評彈研究,就要有意識地推動本身專業(yè)的“去中心化”,將之提煉為一種能夠為撰寫曲藝相關文章提供增益的方法論。而了解、熟悉曲藝的知識結構與理論體系是當務之急。感性體驗是跨界的路標,但跨界之后就不能單憑愛好和喜歡行事,如果想要出成果,那就要對所跨入的某種藝術樣式的基礎知識和前沿發(fā)展,有必要和充分的認知。近些年來,我雖然跨界介入鐘愛的蘇州彈詞,但在真的要動筆寫稿時,卻時感心中空蕩蕩,筆下無物。為之,我在實踐和理論上同步“惡補”了蘇州彈詞的一系列功課,如這門藝術的基本理論和文史資料,相關的文獻匯編和各種詞典,各種藝術流派代表性人物的傳記及其談藝錄,各種主要的經(jīng)典書目的演出臺本等。同時,如前面提到的,我還在孜孜不倦地“橫向開河”,積極學習評彈以外的知識體系,從中國曲藝概論和發(fā)展歷史,世界戲劇和中國戲曲的教科書,世界主要表演藝術理論體系,以及各種相關的報刊、年鑒、報告中汲取必要的研究養(yǎng)分。同時,實際觀聆現(xiàn)場表演和各種音視頻資料也是重要的功課。我體會到,只有通過對彈詞藝術樣式進行全面認識和補充,才能從宏觀與微觀上同時對彈詞有較為廣泛和深入的理解,從而為跨界研究和創(chuàng)作奠定必要和堅實的基礎。例如,布萊希特表現(xiàn)派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驗派的戲劇表演理論,對于我們理解彈詞藝術乃至曲藝藝術“跳進跳出”“一人多角”的藝術定位是極具好處的,這也能使我在評估彈詞的傳承和創(chuàng)新時,有更多的理論底氣。
《曲藝》雜志:您說得很有道理,真正想跨界進入曲藝的領域,就必須對曲藝有較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不能浮光掠影,淺嘗輒止。我想就此再請教一下,對于跨界后的學習和探索,您覺得還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問題?
孫光圻:您說得很對,跨界不能浮光掠影,淺嘗輒止,也不能是去湊熱鬧、抬轎子、捧明星,而是要對彈詞發(fā)展中存在的現(xiàn)實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供業(yè)內(nèi)人士參考。因此,力求全面和深入地介入進去,盡可能去發(fā)現(xiàn)當代曲藝藝術在傳承和發(fā)展中的熱點、重點和焦點問題,力求談出一點個性化的理論體會和創(chuàng)新思考,是我一直以來的追求。比如,為嘗試解答“彈詞如何在守正傳承的基礎上創(chuàng)新發(fā)展”這一問題,我集中力量撰寫了一系列文章,從非遺文化傳承的本真性、動態(tài)性和活態(tài)性角度,對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的保護非遺文化的倫理原則和國家制定的“雙創(chuàng)”戰(zhàn)略等,談了一些不成熟的意見和體悟。與之同時,還具體聯(lián)系近年來演出的重要書目,如《林徽因》《徐悲鴻》《繁花》《大浪淘沙》等,作了有針對性的實證論述。“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嘗試著創(chuàng)作,在“研究者—創(chuàng)作者”的身份轉(zhuǎn)換間,能對自身的研究有更深的感悟。以自己的切身的創(chuàng)作體會破譯彈詞的美學密碼,這可能是我接下來一段時間的跨界重點。
《曲藝》雜志:您從跨界從事曲藝研究和創(chuàng)作的角度,談了一些自己的體會,這對于我們曲藝界利用和引進圈外的人才和知識來強化和拓展曲藝藝術是很有好處的。實際上,跨界不僅是曲藝愛好者的自身需要,更是曲藝發(fā)展的需要。“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一些具有研究和創(chuàng)作能力的圈外人士跨界加入,對于曲藝事業(yè)的立體發(fā)展,是很有好處的,這大概可以稱為“旁觀者清效應”。
孫光圻:您說得很對。我是一個曲藝界的“老年新兵”,現(xiàn)在仍然是,時不時地還會講一些外行話。但我認為,我是能在專業(yè)人士未曾留意的縫隙間,發(fā)現(xiàn)一些似乎習以為常,但細想頗費思量的問題的。再說,任何一個專業(yè)界域都有各種不同的派別和復雜的人事關系,有時往往容易產(chǎn)生不便講或不能講的某種心理制約,例如學生不好批評老師,部下不好批評領導,熟人之間不好互相批評。而跨界介入的圈外人因為以前與圈內(nèi)人士大都不認識,學術人格相對獨立,在理論研究或是寫評論之時,思想上的負擔和顧慮相對較少,所以一般比較敢于坦誠相見,秉筆直言,說出自己內(nèi)心的見解和真話。
《曲藝》雜志:實際上,曲藝評論和其他文藝評論一樣,其主要功能是引導創(chuàng)作,助力打造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如您所言,有的放矢的跨界評論可能真的會成為推動曲藝事業(yè)發(fā)展的源頭活水。再次感謝您能撥冗接受我們的采訪,祝您身體康泰,并一如既往地參與到跨界的事業(yè)中,為曲藝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提供更多的“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