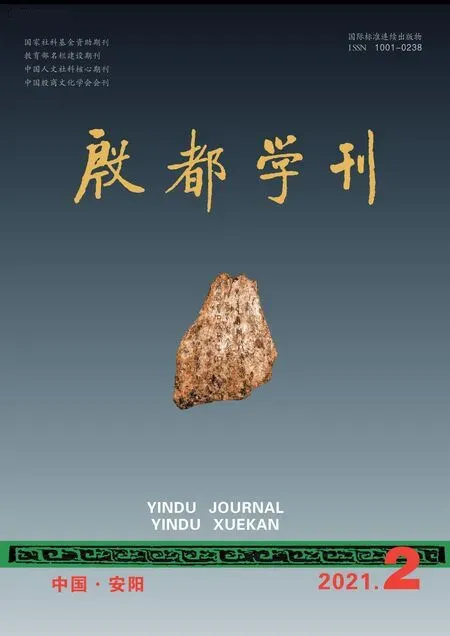卜辭所見“芻”“牧”及相關問題研究
王建軍,戚耀斐
(鄭州大學 歷史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0)
畜牧業是殷商時期重要的經濟部門,比較發達的畜牧業,也給殷人帶來了相對富足的生活水平,對此傳世文獻亦有記載,如《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馬”,“胲作服牛”。《管子·輕重戊》謂:“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越絕書吳內傳》與《孟子·滕文公》也分別記載了商湯在伐桀之前,曾用牛羊拉攏荊伯和葛伯。郭沫若先生在談及甲骨文使用大量祭祀用牲時,曾說:“殷代的牧畜業應該是相當蕃盛的。”(1)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郭沫若全集歷史篇》(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此說符合實際。下面我們結合賓組甲骨文的辭例,分別探討“芻”“牧”及其相關問題。
一、“芻”“牧”的構形及其含義
二、卜辭所見“芻”材料的分類系聯
《合集》中賓組各類卜辭共計19753片,其中反映“芻”的辭例約有116片,或卜問貢納的犧牲和數量,或卜問“芻于某地”,還見有反映商代畜牧奴隸逃跑事件的辭例。
(一)貢納的犧牲和數量
卜辭有諸多關于貞問貢納牲畜及數量的記載。請參下列辭例(為排印方便,釋文盡可能用通行字,文中所舉的辭例按不同性質排序):
(1)己丑卜,殼貞:即以芻,其五百隹六?
(《合集》93正賓一類)
(2)貞:古來犬?古不其來犬?/古來馬?不其來馬?
(《合集》945正賓一類)
(3)…茲以二百犬□昜?
(《合集》11274正賓二類)
上揭辭例中的“以芻”,指進獻或貢納牲畜之意。上揭例(1)貞問貢納牲畜的數量,單次就達506之多。可見,貢納牲畜的牧場應當具有一定的規模。眾所周知,由于先民謀生的方式不同,因而就造成了其生活環境的差異,或從事農業,以種植谷物為生;或從事畜牧業,靠蓄養羊、牛為生,從事畜牧業的人不可避免地需要牧場。(5)[突尼斯]伊本·赫勒敦:《歷史緒論上》,李振中譯,寧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在牲畜飼養方面,或“野放”,或人工放養。“野放”即把牲畜趕到野外,任其自由覓食與活動,既無圈欄,也無人照管。因此,此類牲畜很容易野性化,捕捉時需用獵殺的方式。但商代放牧的牲畜已遠遠走過了這一階段,而是常靠人工放牧。(6)王宇信、楊升南:《甲骨學一百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545頁。這一點,可從上舉卜辭所見的“牧”字構形得到進一步地證實。例(2)是卜問古地是否會進供犬和馬,可見古地當設有畜牧業場地。昜稱為昜伯(《合集》6460賓一類),例(3)中的昜伯一次向商王室進貢200只犬,可見昜伯境內有發達的養犬業。另外,卜辭見有關于“羌芻”的記載,請參下列辭例:
(4)丁未卜,貞:令戉、光又獲羌芻五十?
(《合集》22043)

(《合集》39496)
上揭例(4)卜問商王是否命令戉與光抓獲羌芻五十人?知“芻”為羌族(地)人充任。例(5)正面卜問臿“致”的是否為“羌”?反面驗辭記載臿所“致”的是“羌芻”,即從事畜牧牲畜的羌人。《說文》謂:“羌,西戎牧羊人也。”此正說明羌乃西北一游牧民族,擅長畜牧,商王將抓獲的羌人用其所長,從事畜牧業生產勞動。這是促進商王國經濟發展的一項有利舉措。
(二)芻牧的地名及相關問題
研究商代的畜牧業離不開對商代芻牧地名的系統整理與考察。對此,賓組各類有大量關于芻牧地名的記載,這些地名應是當時飼養或放養牲畜的一些牧場。請參:
1.卜“以芻于某”

(《合集》96賓一類)
(7)貞:矦以冎芻?
(《合集》98賓一類)
(8)貞……奠灷以芻于丂?
(《合集》101賓三類)
(《合集》104賓一類)

2.卜“取某芻”
(10)取竹芻于丘?
(《合集》108賓一類)
(11)勿取夫芻于隹?
(《合集》109賓三類)
(12)庚辰卜,賓貞:乎取芻于扶□?
( 《合集》110正賓二類)
(13)貞:乎取羞芻?
(《合集》111正賓一類)
(14)甲戌卜,□:曾角取逆芻?
(《合集》112師賓間類)
(《合集》117師賓間類)
(16)丁巳卜,爭貞:乎取何芻?
(《合集》113正甲賓一類)
(17)貞:取克芻?
(《合集》114賓一類)
(《合集》115賓一類)
(19)乎取生芻于鳥?
(《合集》116正賓二類)
(《合集》118賓一類)

3.卜“某芻于某”或“芻于某”
(21)貞:雝(雍)芻于莧?/貞:雝芻于秋?/雝芻于雇?
(《合集》150正賓二類)
(22)弓芻于悖?
(《合集》151正賓一類)
(《合集》152正賓二類)
(《合集》249正+《合集》232正=《補編》24正賓二類)
(《合集》11408正賓二類)
(26)貞:芻于旬?
(《合集》11407賓二類)
(27)貞:芻〔于〕奠?
(《合集》11417正賓二類)
上舉(21)-(27)諸辭中的“某芻于某”,意為商王武丁是否派某人去某地采芻。例(21)連續貞問了三個地名,此系選貞卜辭。例(26)(27)兩辭,未顯示商王究竟派誰到旬、奠兩地采芻。
(28)戊子卜,王貞:來競芻?十一月。
(《合集》106正賓二類)
(29)弓芻隹……
(《合集》685正賓一類)
(30)乎前光芻?
(《合集》1380賓一類)
(31)貞:于敦大芻?
(《合集》11406賓二類)
(32)貞:令辳圓雝芻?
(《合集》119賓一類)
(33)□□卜,古貞……工芻?
(《合集》127賓三類)
(34)……唐芻……
(《合集》146賓二類)
上揭諸辭貞問的形式比較復雜一些。前文已指出,芻有割草或飼養牛羊之草料的含義。例(28)中的“來競芻”,當是卜問競地之芻是否到來。其他辭例中的“某芻”都是指商王派遣畜牧官員到某地征取草料,或要求某地(族)貢納草料。另外,卜辭也有關于某地之“芻”逃亡的辭例。如:
4.關于幾個芻牧地名的探討

A.殷都南部

關于“奠”之地望,彭邦炯先生認為,卜辭中的奠地即西周時期的鄭國地,其地望在今陜西華縣。(14)彭邦炯:《甲骨文農業資料考辨與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583頁。此說似有可商。今陜西華縣境,乃鄭國初封之京兆,這是西周時期最早的鄭地。《左傳·隱公十一年》鄭莊公曰“吾先君新邑于此。”杜預注:“此今河南新鄭,舊鄭在京兆。”位于京兆的舊鄭,乃為桓公東遷之前的封地,而非卜辭所載殷商時的奠(鄭)地。據研究,卜辭中奠族的地望,恰與桓公所遷之“鄭父之丘”相重合。對于桓公東遷之事,近出《清華簡(陸)》中的《鄭文公問太伯》則云:“昔吾先君桓公后出自周,以車七乘,徒卅人,鼓其腹心,奮其股肱,以協于庸偶,攝胄擐甲,擭戈盾以造勛。戰于魚羅(麗),吾乃獲函、訾,覆車襲介,克鄶迢迢,如容社之處,亦吾先君之力也。”(15)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中西書局,2016年,第119頁。簡文明確指出,桓公在攻克函、訾、介三邑后滅鄶,并在鄶國故地立社建國。據《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載:“(晉文侯)二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16)(清)朱右曾輯,王國維校補,黃永年校點:《古本竹書紀年輯校》,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6頁。吳良寶先生考證清華簡中函、訾的地望在今新鄭附近。對于鄭國建都“鄭父之丘”的具體地望,學界有不同觀點,(17)其一“陜西說”見:a.李峰:《西周金文中的鄭地與鄭國東遷》,《文物》2006年第9期;b.李峰:《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c.邱奎:《今本〈竹書紀年〉所載西周鄭國史地問題考辨》,《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7年;其二“望京樓說”見:d.郭瑋:《新鄭望京樓城址與鄭父之丘》,《中原文物》2012年第2期;其三“鄶國故城說”見:e.邵炳軍:《鄭武公滅檜年代補證》,《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f.李宗寅:《鄭國的東漸與鄭城三遷》,《黃河科技大學學報》2007年第9期。其中持“鄭韓故城說”者認為,“鄭父之丘”當為現今新鄭的鄭韓故城,西周末期鄭桓公已遷都至此,(18)鄭杰祥:《鄭韓故城在中國都城發展史上的地位》,《黃河科技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其地應位于城內東南部即今雙洎河和黃水河交匯處附近,據《古本竹書紀年》《清華簡》等文獻及考古資料可知,鄭桓公在幽王三年(前779年)已攻滅鄶國,定都“鄭父之丘”(即今鄭韓故城東南部),實現了東遷建國。(19)韓國河、陳康:《鄭國東遷考》,《鄭州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鄭杰祥先生亦認為桓公所遷之“鄭父之丘”位于今新鄭市一帶。(20)鄭杰祥:《商代地理概論》,第257-260頁。綜上,我們認為卜辭中的奠(鄭)地位于殷商時期王畿以南的今鄭州地區,桓公所遷之“鄭父之丘”當在今新鄭市一帶。

B.殷都北部

C.殷都東部
“悖”之地望,鄭杰祥先生認為:“卜辭悖地,丁山《殷商氏族方國志》以為當在后世的貝丘一帶,茲從丁說。卜辭悖地或即古貝丘。古代貝丘當位于今臨清縣東南20余公里,此地西南距卜辭捍地100余公里,它或即卜辭中的悖地。”(27)鄭杰祥:《商代地理概論》,第175頁。“何”的地望,鄭杰祥先生認為在今山東省魚臺縣西南。(28)鄭杰祥:《商代地理概論》,第160頁。“専”之地望,張秉權先生認為位于今山東省郯城。(29)張秉權:《殷虛文字丙編考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7年。此三處地名位于殷東。
D.殷都西部
位于殷西的地名有“唐”“羞”“工”“昜”等。“唐”之地望,陳夢家先生認為“唐在安邑一帶”,安邑即今山西省夏縣以北安邑鎮(30)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科學出版社,1956年,第274頁。。鄭杰祥先生則認為:“《大清一統志·山西平陽府》古跡條下:‘唐城在翼城縣南,《括地志》:在縣西20里’……清代翼城即今山西省翼城縣,位于唐代翼城縣東北約7公里,因此故唐城在唐翼城縣西今翼城縣南。此地西北距卜辭吉地約100公里,它應當就是卜辭中的唐地。”(31)鄭杰祥:《商代地理概論》,第293頁。“工方”的地望,陳夢家先生認為工方位于今山西安邑與河南濟源西之間,(32)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第274頁。鐘柏生認為應在晉陜兩省交界偏南地區。(33)鐘柏生:《殷商卜辭地理論叢》,(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其他芻牧地名的地望皆不可考,故不納入統計范圍。從統計中可以看出,位于殷都以南的芻牧地名較多,可見武丁時期在殷都以南設置的牧場較多。
我們利用“分級劃類”法,(34)王建軍:《賓組卜辭研究·分類卷》,科學出版社,2019年。對《合集》賓組所見的40個芻牧地名進行了分類系聯,從中可以看出這些地名多見于武丁執政的中晚期,其中賓一類數量最多,賓二類次之,賓三和師賓間類較少。
三、卜辭所見的“牧”及相關問題探討
前文已經指出,殷人的牧區具有相對固定的位置,卜辭對牧場有“牧鄙”的記載,如:
(《合集》11003賓二類)
“牧鄙”即牧地的邊鄙,(35)王宇信、楊升南:《甲骨學一百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550頁。也就是邊沿地帶。卜辭也有諸多牧場單位的記載,請參以下諸辭:

(《補編》4145賓二類)
(38)乙丑卜,賓貞:二牧又……
(《甲編》1131賓二類)
(39)……曼茲三牧……于唐……
(《合集》1309賓三類)
(40)丙止鹿……允丙止三[牧]……或鹿一 ?
( 《合集》10321賓一類)
(41)辛未貞:三牧告?
(《屯南》1024)
(《天理》519)
上揭辭例中二牧、三牧和九牧皆指牧場的具體單位,也可指牧場的數量。辭中之“告”是報告的意思,即牧場管理者向中央王朝報告牧場經營的相關情況。卜辭顯示,商王國的牧場設置于王畿內外。在王畿內分設南北、左右四大牧區,在王畿之外,都有具體的名稱。如:
(43)貞:于南牧?
(《合集》11395賓二類)
(44)其北牧擒?
(《合集》28351)

(《合集》28769)
以殷都為中心,左右即指東西方位,“北牧”當是殷都以北的牧區。
(46)貞:莧牧?
(《合集》5625賓三類)
(《合集》11396賓一類)
(48)分……牧?
(《合集》11398賓三類)
(《合集》13515賓三類)
(《合集》11274正賓二類)
王宇信先生認為這是設置在侯專境內的養豬場。(36)王宇信、楊升南:《甲骨學一百年》,第551頁。此說比較合理。
四、卜辭所見的芻牧職官
牧場的管理者,在王畿四大牧區內設有職官,小臣、芻正、牧正、亞牧、馬亞、多馬亞、馬小臣以及小多馬亞臣等。請參:
(51)貞:乎芻正?
(《合集》141正賓二類)
(52)貞:多馬亞其有禍?
(《合集》5710賓三類)
(53)貞:叀翌乎小多馬亞臣?
(《合集》5717賓三類)
(54)貞:其令馬亞射麋?
(《合集》26899)
(55)丙寅卜,叀馬小臣……
(《合集》27881)
(《合集》35345)
(《屯南》2320)

牧還有一個意思就是負責管理畜牧業的官員,裘錫圭先生說:“牧、亞牧、牧正應當是同類官職的官吏,為王室畜牧業的主管者。”(37)裘錫圭:《甲骨文所見“田”“牧”“衛”等職官研究》,《文史》1983年第19期。這在賓組卜辭中也有體現,如:
(58)戊戌卜,賓貞:牧匄〔羌〕,令冓以曼?
(《合集》493正賓二類)
王宇信先生認為,羌即為羌芻,是畜牧業的實際生產者。“匄羌”是求取羌的意思,牧求取到從事畜牧業生產的奴隸,讓冓送到曼地去。可見牧可以調配勞動人手,當為主管畜牧之官。(38)王宇信、楊升南:《甲骨學一百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而在賓組卜辭中我們可以見到關于牧官的一些常見活動。請參:
(《合集》7424賓三類)
(《合集》7343賓二類)
于省吾先生說:“爯謂述說也,冊謂冊命也。”(《駢績·釋爯冊》第13頁)。可見卜辭中的“爯冊”就是獻冊儀式,即雙手舉冊向商王述命,在卜辭中多與征伐有關。上述兩辭中言牧爯冊,可見牧當是具有一定權力的官職。再看下面一版卜辭:
(61)戊戌卜:雀人芻于教?
(《合集》20500)
上揭例(61)卜問是否讓雀負責教地的芻牧之事。雀在甲骨文中是個重要的人物,既主持商王朝的祭祀典禮又經常帶兵出征,可見其地位之高。這樣的人物,被商王委派負責某地芻牧之事,可見商王對放牧之事的高度重視。(39)王建軍、杜佳浩:《殷卜辭所見的雀族及其相關問題》,《中州學刊》2020年第4期。
“牧”又稱“亞牧”,在一些銅器銘文中,記載有“亞牧”之職,如出土于河北省豐縣的一件商代柱足鼎的鼎口內就銘有“亞牧”。(40)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郭旭東先生認為“亞牧”也是一種不尋常的官職,其職責范圍應該是在負責牧養牲畜方面。(41)郭旭東:《從甲骨文字“芻”“牧”論及商代的經濟生活》,《華夏考古》2009年第1期。林歡先生認為,牧官以管理地區行政與邊境安全為主,商人通過任命牧官達到控制邊境的目的,牧是中央王朝對諸侯之長的尊稱。商代的賜封牧官大概也有承認其地位的意思,其實就是以牧官的名義加強諸侯強族與大邑商之間的聯系,在諸牧與商人之間結成一種不對等的聯盟關系。(42)林歡:《甲骨文諸牧考》,收入宋鎮豪主編《殷商文明暨紀念三星堆遺址發現七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除牧之外,賓組卜辭中還能見到其他許多有關畜牧業的職官,比如“司羊”(《合集》19863)、“司犬”(《合集》20367)、“豕司”(《合集》19209賓三類)、“羊司”(《合集》19210賓三類)、“彘司”(《合集》19884)、牛臣(《合集》1115反賓二類)。《說文》:“司,臣司事于外者,從反后。”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引《周禮》注云:“凡言司者,總其領也。”由此可知,司犬、司羊、豕司就是管理養犬、養羊和養豬事務的官員。也就是說商代畜牧業已經具有相當專業化的分工合作,專人司專職,可見其畜牧業已經比較發達。
農業具有穩定性,固定人口所需農業生產用地波動較小,隨著人口激增,才會大面積增加農業用地,農業經濟下,人口增長緩慢,故對農業用地需求增長緩慢。而畜牧業受生產成本的波動而波動,牧場的規模受牲畜數量的影響。牲畜數量增加就要擴大牧場的規模。甲骨文中有如下辭例:“作芻。”(《合集》13793反)。“作芻”應指新建的牧場或擴大飼養牲畜的場所,此亦表明商王朝在這一時期牲畜的數量有所增加,且需要擴大一定規模的牧場,才能滿足日常生活以及祭祀用牲等方面的需求。
五、結語
殷人的祖先擅長畜牧,前文已述“相土作乘馬”“胲作服牛”。相土作為傳說中的商族祖先善長馴服馬匹,至盤庚遷殷后,商代的畜牧業有了長足的發展,這些我們從卜辭以及考古發現中都能得到證實。通過對賓組各類芻牧材料的系聯整理與研究,從中可以看出,殷商時期的畜牧業比較發達。商王朝在王畿和諸侯國等一些地區開辟了專門的牧場,而且有專門從事畜牧業的生產勞動者。可以說,殷商時期的畜牧業達到了一定的專業化程度。這些都充分反映了畜牧業在商代社會經濟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附錄:《合集》賓組各類卜辭芻牧地名一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