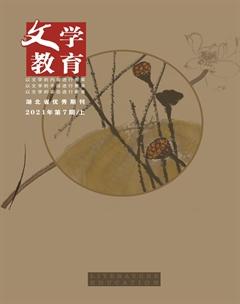東西小說里的都市與鄉土空間
趙立田
內容摘要:廣西作家東西的小說通過書寫城鄉文明的對撞,對鄉土世界和鄉村生活進行了省思,也對都市文明和都市日常生活進行了審視。同時,作家通過記敘因為生存空間的遷移給人類帶來的困擾與抉擇,從而揭開了人類豐富而復雜的情感世界,以及由此帶來的心靈激蕩。
關鍵詞:東西小說 批判 審視 都市 鄉土
改革開放后,隨著中國社會逐步加快的現代化進程,城鄉文明的對位與對話也日漸緊密。作為時代的親歷者之一,小說家們用藝術的眼光,觀察社會生活,記錄社會生活,并通過這些文字傳達他們對社會生活的思考。作為廣西文學界的領軍人物,東西的小說作品常常通過寓言式的書寫來反映時代生活,深刻地思考并闡釋著城鄉文化空間里人們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這些作品,有些涉及到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傷害,有些涉及到命運的思考,有些又和人物對生活的反省息息相關。無論是從個體的角度,還是以家庭為切入點,東西的小說都為我們揭開了歷史與人性的豁口,再現和反思社會前進的腳步、個體掙扎的靈魂以及愛恨交織的情感體驗,為城鄉文化空間的構筑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一.被批判的鄉土
小說家東西出生于多山環繞的桂西北農村,不便的交通環境、靜謐的山鄉風情,造就了現實版的“沒有語言的生活”。鄉村的文化空間給予東西生活的身體和臂膀,也給予了他小說創作時的精神底色,在作品里,就表現為作家所關注和反應的是個體、家庭在與命運搏斗時的激烈與悲壯。解讀東西的鄉土題材小說,要把它們放在廣西,乃至中國鄉土社會劇變的時代氛圍里觀察,才能審視主人公們在追求物質財富的時候所面臨的情感、家庭裂變與愈合的辯證,才能透視社會轉型時期城、鄉文化空間的位移與流轉,才能把握在社會的風云激蕩時期,生命個體的吶喊、彷徨與掙扎,甚至于極端的逆天改命。
小說《沒有語言的生活》選取了鄉村文化空間里小人物的生活遭遇作為書寫的題材,展示了在地域偏僻和物質極端匱乏的條件下,人們極度貧困的生活狀況和幾近赤貧的精神面貌,將小人物為贏得生存空間而做的努力和掙扎展現人前。人感知外部環境的基本依靠就是五官,可是小說在描寫盲人王老炳、聾子王家寬和啞巴蔡玉珍組合的非常家庭的貧困生活時,卻將他們的失明、失聰、失語作為與環境保持相對獨立的生存狀態,并在“劃河而居”之后,贏得了自如的生存空間。我們不妨把作家對這三個角色的設定理解為人對社會和自我關系的一種判斷。他們最初和普通人是一樣的,感知這個世界和其他人沒有什么不同,但是,生活的殘酷性就在于,它不斷地蠶食了人物的生活空間,以語言的傷害漸漸地把人逼到角落里,正如論者所言,“由聾子、啞巴和瞎子組成的家庭,表達的正是在言語的機鋒面前保持的沉默和相對的隔絕,以期達成個體在傷害前的弱勢自保,這是惡托邦里的人性捍衛,也是道德的自我堅守。”[1]荒謬的生存選擇背后竟然流蕩著合理的生存規則,小說人物以不斷收縮的生存空間闡釋了生活的艱辛與不易。為了避免繼續騷擾他們最初是搬到了河的對岸離群索居,后來干脆拆掉了過河的小橋,以至于斷絕了他們與“文明世界”的聯系。當他們自以為擺脫了人世間的傷害之時,小孩子王勝利上學之后,第一天學會的竟然是辱罵父母的歌謠,在沉默中生活的一家人再次過上了沒有語言的生活。
由此可見,如果說“聾”、“啞”、“盲”在小說內的家庭組成是作家對生存境遇的極限展演,那么,“你”、“我”、“他”恰巧三人的人生指稱則顯露出東西對人際關系的細察程度。在書寫王老炳一家的困窘生活之時,東西以他悲天憫人的心懷,批判了鄉村中普遍存在的精神貧困現象——貧困與苦難絕非僅來自于自然界的風不調雨不順,人心深處所潛藏的貪婪才是毀滅人性的根本因素。《目光愈拉愈長》里,在村子里生活的母親劉井常常站在家門口不斷地眺望遠方,她渴盼著兒子能夠早日平安歸來;但是,當兒子馬一定從城里回家之后,不斷地埋怨母親,不停地嫌棄農村的生活,終于有一天逃出了村莊。母親的目光愈拉愈長,但是,那個在都市里生活的兒子也越走越遠,終于消失在日落后的群嵐之外。年輕人的出走,使鄉土文明迅速地衰敗。在風云激蕩的城鄉文化空間位移時期,東西對社會變革進行的細致體察,清晰地勾勒出時代浪潮里的人物形象,引起了讀者深刻而又廣泛的共鳴。
二.被審視的都市
在新時期的歷史條件下,大量從土地生產里解放出來的農民涌進都市,客觀上也為都市文明與都市生活注入了新的元素,而這些都市新移民對都市的情感介入過程,則是“光明與黑暗相共”的。易言之,都市新移民的“進城”,串聯起了差異性較大的城、鄉文化空間,也使城鄉之間的敘事空間得以構筑。小說《篡改的命》就以汪長尺的“進城悲劇”作為敘事的線索,闡述了農民對“進城”的渴求與艱辛,不斷地在“篡改”中思索著人生與命運的糾纏。
主人公汪長尺,從父親汪槐到他,都在孜孜以求地完成一項光榮而艱巨的任務,那就是要盡早完成從農民到市民的身份轉變。然而,命運只是不斷地捉弄著汪氏父子。在執著,甚至是近乎變態的偏執念想里,他們最終決定自己家族的傳人過繼給仇人,從而完成所謂的“身份轉變”,殊不知,完成身份轉變后的兒子汪大志卻決意要割裂他與鄉土家族的血脈聯系,這不啻為極大的諷刺。小說的最后情節,是汪大志去追查自己的身份,然而追查的結果卻指向了自己本身。同樣是追尋身份之謎,最后查明自己身份的俄狄浦斯,因為殺父娶母的罪名無法抹煞,加上他治下的國家已經飽受多年瘟疫之苦,唯有承擔起亂倫的罪責才能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因此他刺瞎了不能識別自己身份的雙眼,流浪他鄉。反觀《篡改的命》里的汪大志,當他知道自己身份的秘密后,卻把所有的檔案丟到江里,實際上也顯示了他對鄉村文明的棄絕和對都市文明的熱烈擁抱。都市文明以巨大的優勢攬懷了年輕人的期許和夢想,也暗示著物質社會里人對血緣、親情等精神欲求的屏蔽和抹殺。這個戲仿了俄狄浦斯故事的故事,終于將作家對命運的省思推向高潮:當人無論如何都不能逃脫命運的擺布之時,他是選擇繼續抗爭,并最終承擔責任,還是選擇妥協,甚至是逃避事實?兩相比較之下,更能顯示出古希臘神話里的英雄的崇高感,因而燭照出當代都市人的卑微,甚至是猥瑣。而作家在刻畫城鄉文化互動(懟)的過程中,深刻地揭露了這樣的窘境:在都市與鄉土文明的罅隙里,都市新移民寄希望于改變自身生存困境所做的努力是如此艱辛。有論者指出,“關于三代人進城的故事,看似悲憫,亦含批判,表面嘻哈,內里沉重。東西寫出了一個具有喜劇精神的悲劇,并用這個悲劇有力地祭奠了一個荒謬的時代。”[2]在社會缺乏足夠的上升平臺的背景下,對命理的如此“篡改”,用當下的流行語來說,體現了一種“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扭曲、悲壯的搏殺,正如論者所言,書寫了都市新移民的“作品寫出了鄉土社會遷徙者與都市文化發生碰撞時靈魂世界的至深悲劇”[3],而悲劇之所以出現的原因,是值得我們每一位讀者深思的。
通過父子進城的故事來審視都市生活的寫作姿態在東西的其他小說里也時有出現,在《我們的父親》、《保佑》等等小說里還有較為精彩的展演。《我們的父親》里,父親出走了,因為他進城之后發現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發生了異變,兒子“我”最后連父親的葬身之地都無從尋覓,那么,“對父親的死或失蹤的真相的追尋刺痛了我們,刺穿了冷漠的堅冰。在這個世界上,誰敢說自己是無罪的?”[4]《保佑》則是《目光愈拉愈長》的父親版,那個在村口眺望兒子的人,從母親劉井變成了父親李遇。如果父親是歷史,那他必須是鄉土文明的歷史。當兒子作為第一代的都市新移民,將自己的生存空間移植進都市里,那么,父親的歷史,也就是鄉土的歷史就已經斷裂了。當兒子馬一定、“我”所掌控的新秩序終于在都市里逐漸地建立起來,父輩的舊秩序也日漸蒼老。無論是兒子對父親的逃離,還是他對父親的尋覓,都將在父親的出走或者是眺望里完成隱秘的交接。
綜上所述,廣西作家東西的小說通過書寫城鄉文明的對撞,對鄉土世界和鄉村生活進行了省思,也對都市文明和都市日常生活進行了審視。同時,作家通過記敘因為生存空間的遷移給人類帶來的困擾與抉擇,從而揭開了人類豐富而復雜的情感世界,以及由此帶來的心靈激蕩。在都市化進程中,都市新移民不得不面對諸如離散、挫折、失敗、認同危機等心理問題,并在這些情感矛盾中不斷地走向個體精神世界的深處,不斷地思考處于雙重文明夾縫中的命運走向。他們從鄉土中來,卻融入都市里去,深刻地展示了都市文化與鄉村文化之間的共生關系。都市給鄉村文化搭建了更大的活動平臺和生存空間,而鄉村文化又維系了都市人內心對生命本真的終極信念,而東西小說以寓言式的書寫,不斷地叩擊著人類內心世界普遍而共通的情感體驗,更重要的是,它以一種批判的眼光,為我們審視都市、鄉村的生活提供了一種基本的姿態與路徑。
參考文獻
[1]潘頌漢:《在人性凌遲的現場——東西小說論》,《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8年第1期。
[2]謝有順:《有喜劇精神的悲劇——讀東西的<篡改的命>》,《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1期。
[3]丁帆:《論近期小說中鄉土與都市的精神蛻變——以<黑豬毛白豬毛>和<瓦城上空的麥田>為考察對象》,《文學評論》2003年第3期。
[4]張柱林:《撕破面紗,擊穿堅冰——東西小說論之一》,《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基金項目:2018年廣西高校中青年教師基礎能力提升項目“新世紀廣西小說城鄉敘事主題研究”(2018KY0574)。
(作者單位:廣西梧州高級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