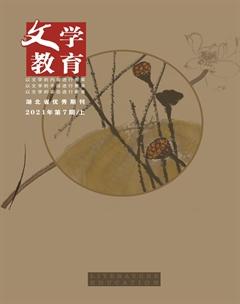《受戒》:詩化小說傳統的一次復歸之旅
李能
內容摘要:汪曾祺在1980年發表的小說《受戒》是他宣告“復歸”文壇的信號,也是其“京派”傳人地位的再次確認。《受戒》也因其蘊含的多重復雜的內涵,成為當代文學史上不可忽略的存在。本文以小說中顯露的鮮明的詩意化審美特征為視角,主要從汪曾祺詩性的審美追求與文學信念、文本中生活圖景的詩性顯現以及悲劇性內蘊的詩化消解三個方面對汪曾祺的“詩化文體”作進一步理解與論述。
關鍵詞:汪曾祺 《受戒》 詩意化
1980年10月的《北京文學》雜志上刊登了一篇“另類”①的短篇小說《受戒》,其作者正是在文壇銷匿了近四十年的“京派”作家團體在當代的遺珠汪曾祺。其時,文學必須服務于政治這一文學創作規范的合法性地位開始受到學界的質疑,“解放”的氣氛稍有活泛。盡管如此,文學話語仍受制于政治權力話語,而新的文學創作規范還未建構,局勢也尚未明朗。汪曾祺發表這篇與現實政治或意識形態相去甚遠的小說《受戒》無疑是向沉寂已久的文壇投下的一顆深水炸彈,人們普遍為小說中似夢似幻、和諧寧靜的桃源世界所震驚。《受戒》將讀者拉回了四十年代“京派”小說的文學傳統中,讓已經被深埋在地表之下的詩化抒情小說破土重生。本文從汪曾祺小說的詩性審美追求出發,對文本中的詩性表達進行細致地研讀,力圖找出其中潛在的新的研究點,從而對汪曾祺其人及其作品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文人氣”與詩意化審美追求
汪曾祺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中文系并師承“京派”著名作家沈從文,二人因為志趣相投,所以感情頗深且惺惺相惜。汪曾祺作為沈從文的得意門生,其創作理念與文學實踐方式深受沈從文的影響,是傳承接續沈從文文學風格與美學理想即“京派”文學傳統的最佳人選。他們始終堅持用自己的筆端書寫故鄉清新美好的風俗人情、和諧寧靜的鄉土風景以及單純平淡的日常倫理生活,二人的小說都具有鮮明的詩化特征。自1940年代末開始,由于建立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以及救亡圖存的時代需求,“京派”所主張的自由主義和審美本位主義的文藝觀已經不合時宜,所以逐漸在大眾的視野中隱去身影。而汪曾祺憑借《受戒》中樸實雋永、清新淡雅的詩化文體風格,讓人們看到了“京派”文學之火復燃的可能性,也讓人們對這一文學傳統的文學史意義與審美價值予以重新評價和認可。
與沈從文“鄉下人”的氣質不同,汪曾祺由內而外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儒雅明道的文人氣。有評論者認為他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后一個士大夫”,這樣的說法不無道理。汪曾祺家境殷實,從小熟習繪畫、書法,對文學寫作與閱讀興趣濃厚,并且夢想成為一名作家,且素以詩人身份自居,②他說:“我的氣質,大概是一個通俗抒情詩人。我永遠只是一個小品作家。我寫的一切,都是小品。”③汪曾祺的文人氣質決定了他的文學創作風格的詩化特征,即重抒情而少情節。他的創作只能是脫離現實政治與社會歷史的“私人寫作”,是文化人特有的孤寂隱逸的游吟獨唱。對于20世紀的中國文學進程而言,汪曾祺是一個孤獨且固執的過客,他始終與主流文學保持距離,以平和的心態默默地守衛著自己心中的文學信念與審美理想,在生活的積淀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理念與文體風格,且日趨成熟。
當代小說作家畢飛宇曾對汪曾祺的這種“文人氣”有過明確的論說:“汪曾祺是文人,深得中國文化的精髓。”“他講究的是腔調和趣味,而不是彼岸、革命與真理。”“他平和、沖淡、日常,在美學的趣味上”追求一種“雅”與“正”。④這無疑是對汪曾祺個人氣質及其創作旨趣的頗為中肯的見解。
從汪曾祺1940年代創作的第一部小說集《邂逅集》到1980《受戒》的發表,我們可以明顯地感受到作者始終如一地堅持把小說當作詩來作的文學信仰與審美追求。不論是文人、詩人還是小說家,汪曾祺集這三種身份于一身,最終外化為一種平淡、幽遠的抒情性的詩化小說風格,而《受戒》正是其對這一文學理想的典型實踐。
二.兩種生活圖景中的詩性美
在《受戒》中,汪曾祺用充滿詩意的筆觸為讀者描繪了兩種與詩意不甚相關的生活圖景——廟宇生活與世俗生活。在他的筆下,寺廟不像寺廟,世俗不夠世俗,可它們卻都是詩的,由內而外地散發著詩的韻味與情致。
《受戒》講述了一個叫明海的小和尚在與鄰居小姑娘英子相處的四年時間里雙方互生情愫并私定終身的純美的初戀愛情故事。明海與英子的愛情讓掙扎在現代工業文明環境下的讀者心向往之,人們不禁為六十歲的汪曾祺仍能保持內心的純真與無邪而震撼與感動,而他的純真與無邪讓他對文學詩意的追求變得順理成章、合情合理。在汪曾祺的筆下,不論是日常社會的世俗生活還是遠離塵世的廟宇生活,都滿溢著和諧、溫情的詩性韻味。
小說在第一部分描寫了明海所在的寺廟即菩提庵里神職人員的廟宇生活。在讀者的閱讀期待中,廟宇生活應該是肅穆、莊重、神秘的,可展現在讀者眼前的有關寺廟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反常。在明海的家鄉,和尚是一種職業,無關宗教信仰,只因當和尚可以享受到很好的福利待遇:可以吃現成飯;可以攢錢。那些曾一直存在于我們想象中的整日吃齋念佛、守著清規戒律的和尚被驅逐出去了,寺廟的神秘與莊嚴被汪曾祺用隨意且戲謔的語言完全消解了。
明海所在的寺廟加上明海,總共五個和尚。他們在庵里的日常就是打牌、吃肉,佛教里的基本戒律如不殺生、不飲酒、不妄語等在這里形同虛設。文章名為“受戒”,其實一直都在“破戒”。小說試圖將廟宇生活世俗化與人情化,正如有些論者所述:“荸薺庵里有佛像,有和尚,但卻沒有虔誠的信徒。”⑤他們只是享受著世俗生活的美好的普通人。汪曾祺并不贊揚和尚的這種世俗化的生活方式,但同時他也沒有否定與排斥,他持中立態度,正因如此,讀者在這里只能讀到戲謔與玩味,而不是諷刺與挖苦。這其中內蘊著深厚的文化意味和生活情致,是汪曾祺“人間梵天的美好愿望”的詩意表達。⑥
廟宇生活充滿世俗味,那真正的世俗生活會是如何?小說在第二部分描寫了英子一家以及庵趙莊整個鄉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他們整日里為生活操磨,卻并不覺得日子很苦,像栽秧種稻、打場等重活兒,自己家忙不過來時,就會換工。他們過的完全是與世無爭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富有詩意和夢幻的色彩,讓人心向往之。他們不受倫理道德的束縛,享受著自然的饋贈與生活的詩意美。作者將人指向了詩性的美麗和生活的自適中。汪曾祺用八十年代的感情來描寫“解放前”的中國鄉村,這個鄉村富足、美好,簡直就是人間天上。在讀者的認知中,“解放前”的社會應該是黑暗恐怖的,怎么會是汪曾祺所描述的人間仙境呢?汪曾祺的膽量與魄力正在此處。不論是在“十七年文學”期間還是“文革”時期,他像是有意地自覺地回避主流意識形態對文學意味的消解,他的寫作從來都是非政治的,是文化的,人性的,詩意的。
三.“哀而不傷”:悲劇內蘊的詩化消解
《受戒》中明海與小英子唯美清新的懵懂之戀蘊含著悲劇性的審美意味。但是這種悲劇意味并沒有被作者明顯地展示給讀者,而是用詩意化的外衣包裹隱藏了起來,是要讓讀者自己去玩味感受。這是汪曾祺詩化文體對其悲劇意蘊的掩埋與消解,是其詩化小說的獨特之所在。
在小說的末尾,明海受完戒后,小英子按照約定劃船去善因寺接明海回荸薺庵,在回庵的途中,他們的情感關系發生了質的變化,而對這一過程的敘述,無疑是整個小說的爆破點。盡管作者為我們描繪的懵懂少年的戀愛畫面那么唯美、有意境,但讀者仍不能不為明子和小英子的結局而擔憂:明海將來是否要做方丈、又是否要做沙彌尾,小英子的決定根本不能改變什么,而明海更不能決定什么。小英子到底能否如愿以償地嫁給明海當老婆,這是作者為我們設下的一個懸念,而這個懸念的答案或許作者自己也無從知曉,所以,小說到這里就結束了,剩下的內容只能靠讀者自己去領悟與體味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受戒》的內涵其實是悲劇性的。它不是蕩氣回腸或國破家亡的時代大悲劇,而是唯美輕逸的、小家碧玉的愛情小悲劇。在小說的最后,作者不止描寫了小鳥擦著蘆穗飛遠的畫面,還有正迎接著它的憂傷的、無邊無際的天空的畫面,像故事的結局,或許根本不會有結局。
明海與小英子沒有結局的愛情故事雖然傷感,但卻不會讓讀者感到痛徹心腑。相反,這種傷感是悠揚的、輕飄的,是回味無窮的。這便是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對汪曾祺悲劇意識的不自覺地滲透。儒家對悲劇意蘊的表現方式頗強調“哀而不傷”與“溫柔敦厚”的審美原則。在這種“中庸”文化精神的影響下,汪曾祺在表現悲劇人物與悲劇情節時,沒有發出如魯迅般的陰冷與深刻,而是極力把生活與人性寫得溫情柔美,他追求的是一種和諧與樸素之美。他刻意地保留一點,掩飾一點,平淡一點,使得痛苦和悲情弱化,努力讓每一個不幸的靈魂都能找到屬于自己的慰藉與歸屬。正如明海與小英子的愛情,命運將他們捆綁在了一起,卻也可能又將他們分開,可是不論結果如何,都無法抹煞他們內心的那份純真與天然,是生活的詩意美讓他們可以無所顧忌、隨心而行。從此種意義上來說,《受戒》的詩意性審美韻味將其本身所內蘊的悲劇性色彩消解與融合了。
汪曾祺曾明確指出,沈從文筆下的那些農村少女,三三、夭夭、翠翠,是促成他產生小英子這樣一個形象的潛在的因素。而他也對自己是廢名、沈從文之后的京派傳人這一身份表示認同并以這一身份自許。我們或許可以說,正是汪曾祺對詩化或散文化這一“京派”文體的堅守,使得“京派”這一現代文學傳統得以在當代文學史上再次占有一席之地。不過,以沈從文為代表的“京派”文學傳統在1980年代興起的“重寫文學史”浪潮中,其文學史價值與意義是否真的得到充分的呈現與挖掘尚有待于研究者去鉤沉探索。
參考文獻
[1]錢振文.“另類”姿態和“另類”效應——以汪曾祺小說〈受戒〉為中心[J].當代作家評論,2006(2):30-37.
[2]季紅真.游吟的珠湖人——汪曾祺全傳[J].新文學史料,2009:11-36.
[3]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
[4]畢飛宇.小說課[M].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
[5]王本朝.瀆神的詩性:〈受戒〉作為1980年代的文化寓言[J].當代文壇,2012(2):22-25.
[6]周泉根,楊潔.歸去來兮朝花夕拾——試探汪曾祺小說意象中的童年情結[J].當代文壇,2011(6):93-96.
(作者單位:西安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