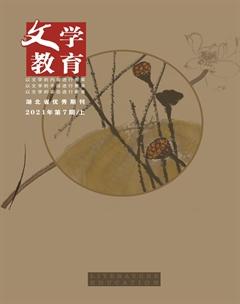從《春光乍泄》看王家衛電影的追尋命題
束品慧
內容摘要:在王家衛的電影中,追尋是永恒的命題。影片中的人物往往內心孤獨封閉,又一刻不停地追尋溫暖。王家衛通過視聽密碼、對物傾訴等手法映射出孤獨追尋的港人群像,展現出工業時代港人的生存狀態,并給港人指出了一條發泄情緒和紓解思想的出路。
關鍵詞:王家衛 追尋 孤獨群體 工業時代
縱觀王家衛的作品,我們不難發現王家衛一直在圍繞“追尋”這一主題進行創作。影片中的人物渴望溫暖又拒絕接近,向往親密又不愿敞開心扉,而這正是后工業時代港人精神圖景的映射。在孤獨的煎熬下,他們不斷追尋溫暖,試圖擺脫“無根感”,卻又往往感到迷茫和失落。王家衛在《春光乍泄》中如以往一般用獨特的表現方式講述追尋主題,并在經過一系列的探索后終于給出了有關“追尋”主題的答案,讓人感到耳目一新。
一.王家衛“追尋”主題影片的主要特點
“追尋”主題一直貫徹在王家衛的電影中,“敞開心扉——受傷——封閉自我——迷失——追尋”可視為王氏電影中普遍的心路歷程。主角們往往歷經痛苦,面對殘酷的現實,他們緊閉內心,不愿表達,轉向尋找內心世界的答案。而這并非王家衛刻意塑造特立獨行的人物形象。無數個體追尋背后,映射的是整個港人群體的追尋狀態。
1.聚焦人物內心
王家衛的電影以獨樹一幟的個人風格著稱,他敏銳捕捉人物內心,聚焦孤獨感。孤獨是傷害的果,同時是傷害的因。“也許,黎耀輝的夢魘從來不是一個外間世界強加于他的,而是一個個傾心付出卻回報寥寥的傷痕所建構的。”[1]影片中的人物常在冰冷的環境中受傷,為避免進一步受到傷害,他們轉而將自己包裹。但封閉內心的后果是,自我封閉者被孤獨籠罩,他們無比向往溫暖,又拒絕敞開心扉,因此傷害到他人。《春光乍泄》中,黎耀輝希冀與何寶榮有安定的生活,但他從不對何寶榮表達這一想法,而是試圖通過限制何寶榮的行動,藏起他的護照來達到目的。其結果必然是陷入惡性循環,兩人產生矛盾,人物感到困頓,無法掙脫,更加封閉。
為擺脫孤獨感,渴求心靈歸屬感,影片中的主人公們不斷追尋。影片《春光乍泄》以黎耀輝的敘述展開。他敏感、孤獨、渴望溫暖,與父親關系冷淡,家庭名存實亡。因此,出逃、追尋,成為黎耀輝唯一的選擇。他與何寶榮相愛、羨慕小張,對溫暖的渴求都是動因之一。在王家衛的一系列影片中,“敞開心扉——受傷——封閉自我——迷失——追尋”成為普遍的心路歷程,主人公永不停歇地追尋,希望掙脫孤獨感的桎梏。
2.個體背后的追尋群像
王家衛的影片中,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春光乍泄》中的黎耀輝許久不與父親交談,何寶榮和黎耀輝直到分手也沒有對彼此吐露內心。《墮落天使》中,殺手拒絕情感交流;《東邪西毒》的歐陽鋒在與大哥大嫂沖突后逃避。但是,這并非王家衛刻意塑造特立獨行的人物形象。恰恰相反,這在某種程度上映射出后工業時代港人的生存狀態,影片著眼的個體背后,是整個港人群體的追尋狀態。
在步入工業時代的香港,四顧冰冷,每天與陌生人擦肩,不是漂泊,勝似漂泊。《重慶森林》著眼快餐式都市愛情,幾位主人公唯一的共同交集就是奶茶店。不是固定的誰,不是特定的故事,這樣的情節可能在同一城市的不同角落同時發生。這在某種程度上暗示,影片中的主人公們代表的不是具體的某個人,而是后工業時代的港人群像。
利奧塔在《后現代狀況》中說,“壓抑是文明不可逆轉的代價”。這正是后工業時代的人們精神狀態的典型特征。在后工業時代,人們的聯系微薄化,內心封閉荒涼者占大多數。城市的冰冷困擾生活在城市的人們,他們試圖尋求自我排遣的方法,其結果就是出走、追尋。影片描摹一個個追尋者的形象,通過對孤獨個體的描繪展現后工業時代港人的生存狀態。
二.王家衛追尋主題作品的表現方式
王家衛的影片極具獨特氣質,以個性化的影像風格聚焦主人公內心,多種形式表達追尋這一貫穿影片的主題。他擅于通過解鎖視聽密碼進行氛圍渲染,表露人物沉默中的心緒,亦或用鏡頭追蹤人對物的傾訴畫面,展現主人公以傾訴的方式打開心門,在追尋中找到一線曙光。
1.視聽結合的氛圍渲染
“在整個影像表意系統中,鏡頭語言是空間造型和營造視覺節奏的手段。在電影中,王家衛擅長用鏡頭來表達影片主題。”[2]而通過畫面和音樂的巧妙搭配精準傳達人物心理,引起觀眾情感共鳴,更是王家衛電影作品的一大特色。影片中人物大多內心封閉,因而音樂是極佳的表現形式。“當音樂MilongaforThree響起,緩慢的節奏隨著水波流淌,黎耀輝側躺在甲板上,鏡頭的拍攝使他仿若置身浮萍,無所依傍。這正是王家衛想表達的效果——黎耀輝一個人孤獨地面向無邊無際的大海,在蒼涼的畫面里,他的形單影只被無限放大。”[3]前路何在?去向何方?皮亞佐拉的探戈曲中,水波緩緩起伏,人物追尋過程中的迷茫心緒在視聽密碼里展現得淋漓盡致。
影片中,人物追尋過程出現轉機仍然以音樂配合畫面形成一種張力效果。何寶榮被打傷是黎何二人感情修復的轉折點,兩人坐在出租車里,燈光明滅,伴隨著音樂WATER FALL淌落——他們在那一刻極近,身體和心——這也許是黎耀輝一直追尋的溫暖。同樣是封閉空間,舞曲“Milonga for 3”搭配黎耀輝與何寶榮共舞的橋段營造氛圍。在電影結尾,從離港到返港,黎耀輝的追尋終于有了結果,此時,“電影的畫面終于恢復生氣,‘Happy Together的樂聲響起,暗示著黎耀輝找到回家的路。”[4]
2.人對物的傾訴
影片中,若即若離的獨白、似近實遠的人物關系,無不昭示著后工業時代的冰冷,人與物的交流勝于人與人之間。主人公在追尋中的痛苦難以排遣,往往轉而對物的傾訴。在王家衛的影片里,我們經常可見到這樣的場景——主人公獨自來到某一處地方,開始吐露內心,留下秘密,然后轉身離去。《春光乍泄》中,小張只身一人前往烏斯懷亞,“聽說那里是世界的盡頭,有個燈塔,失戀的人都喜歡去,把不開心的東西留下。”他請黎耀輝對著錄音機錄下自己的不開心,幫他帶去烏斯懷亞。
人對物傾訴是人內心釋放的過程,傾訴者在吐露過程中重新審視自己的內心,做出選擇。《春光乍泄》里,小張終于來到烏斯懷亞,把黎耀輝的不開心留在了世界盡頭。黎耀輝自己也前往瀑布,見到尋找已久的伊瓜蘇,鏡頭在瀑布上空停留了兩分鐘。傾訴,是把封閉心理轉為外放形式,人物在對物傾訴的過程中達到內心自洽的狀態,逐漸走出追尋無路的困境。
三.王家衛追尋主題作品的回答
在王家衛的“追尋”主題系列影片中,從《旺角卡門》到《阿飛正傳》、《重慶森林》,王家衛影片中的主人公一直走在追尋道路上,結局卻并不樂觀,或死亡、或迷失。《旺角卡門》的阿華在追尋中找不到出路,最后死亡。《重慶森林》里警察223在都市迷失。而在《春光乍泄》中,人物的追尋終于有了一個相對的結果——由頭來過。
后工業時代,香港社會發展迅速,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聯系變得淡薄脆弱。影片中的主人公們在受到傷害后自我封閉,因此與周圍環境產生極深的隔膜,又“因其與社會、家庭的疏離而凸顯出其邊緣人狀態,但潛意識中渴慕著情感與撫慰,這種渴慕由于人物之間的拒絕否定而受到阻礙。《春光乍泄》一定程度上沿襲了這種人物塑造模式,但卻強化了人物對情感的渴慕與追尋成份,對追尋做出了新的回答。”[5]從香港到阿根廷,一路上,黎耀輝與何寶榮分分合合,他渴望從何寶榮那里得到溫暖,而何寶榮不甘束縛。兩人爭吵、冷戰,卻鮮少交流內心。稍有緩和,便互相試探,繼而又是爭吵。追尋不到出路,黎耀輝被孤獨圍困,他在甲板上凝望,對著收音機哭泣,站在瀑布前,他覺得“站在這里的應該是兩個人”。面對無法治愈的傷痛,黎耀輝選擇遺忘,敞開心扉去擁抱世界,與過往講和。或許,我們可以將其視為王家衛早就拋出的“追尋”主題的答案——遺忘、回歸、由頭來過,新生的人走向新旅途。
昆德拉提出,“忘卻是絕對的不公正,也是絕對的慰藉。”[6]并非所有的忘卻都可恥,過去無法改變,但能忘卻。爭吵、被拒絕、邊緣化,如果這一切傷害導致個體的自我封閉、困頓迷失,何妨遺忘。唯有忘卻,方能真正重啟心門,由頭來過。正是認識到這一點,黎耀輝遺忘過去的傷害,主動敞開自我,重新開始。王家衛的影片中,遺忘往往通過傾訴的方式呈現,以這種方式遺忘,或許可以證明,遺忘不是怯懦的逃避,是遇到痛苦后不斷追尋,終于直視內心的釋懷。于是,“對‘無根感的困惑從所有象征、比喻、暗示中解脫出來,做了一次直白的點破,仿佛是對‘無腳鳥人生難題的明確答復。”[7]封閉的內心其實渴望傾訴,孤獨的人追尋溫暖。選擇遺忘,主動交流,擺脫心靈的無所歸依,忘卻使人在追尋中愈合傷口,與自己、與世界和解,找到新的意義,然后——“不如我們由頭來過”。
注 釋
[1]《凝視中的“看”與“被看”——電影《春光乍泄》的身體敘事研究》王祎顏;四川戲劇2009年06期;99-100.
[2]《王家衛電影中的后現代主義風格研究》王可、王潼;新聞研究導刊2020年19期;116-117.
[3]《王家衛電影音樂圖鑒》羅展鳳;《王家衛的映畫世界》80.
[4]《<春光乍泄>電影音樂品析》陳心;電影文學2009年16期;123-124.
[5]《飄零與復歸:現代人的精神之旅》何建平;電影藝術1998年05;3-5.
[6]《小說的藝術》米蘭·昆德拉著 董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7]《無根的漂泊與冷漠的疏離——論王家衛電影的母題系統》白玉紅;四川戲劇2009年06期;99-100.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