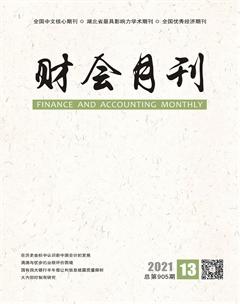企業金融化與盈余持續性
和麗芬 張丹 王巧義



【摘要】伴隨著企業金融資產投資與獲利的不斷增加, 金融活動能否提升盈余持續性成為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 以2012 ~ 2019年滬深A股非金融和房地產行業上市公司為樣本, 構建不同金融化動機下的計量模型, 實證分析企業金融化與盈余持續性的內在關系。 研究表明: 出于“市場套利動機”配置金融資產, 企業金融化對盈余持續性具有抑制作用; 出于“資金儲備動機”配置金融資產, 雖能增加企業內源現金流, 但并未對盈余持續性產生促進作用, 反而證實部分企業存在“以錢生錢”投資現象。 進一步研究發現: 創新能力下降是金融化行為對盈余持續性產生抑制作用的部分中介因子; 機構投資者可以發揮緩解二者負相關關系的調節作用; 相比國有企業, 金融化行為對盈余持續性的抑制作用在非國有企業中更明顯。 該結論為合理定位金融化動機提供了經驗證據, 對于引導企業“脫虛向實”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關鍵詞】企業金融化;盈余持續性;創新能力;機構投資者
【中圖分類號】F275.1?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4-0994(2021)13-0028-8
一、引言
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平衡發展是防范經濟運行風險的關鍵, 然而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卻呈現出金融化的特征: 實體經濟占GDP的比重從2011年的71.39%連續下降至2019年的62.40%①, M1同比增速2018年以來始終低于M2且差距逐漸增大, 最大差距達8%②, 四大國有銀行結構性存款也不斷攀升。 微觀層面, 由于實業投資利潤率下降, 很多企業轉而投資金融資產。 國泰安數據庫的數據顯示: 2012年配置金融資產的企業占比50.68%, 2018年該比例上升為82.39%, 且金融資產占總資產比重近8年上漲了近2.5倍。 以上數據說明, 在資本逐利驅動下, 大量產業資本流向高收益的金融領域, 企業金融資產投資與金融渠道獲利占比不斷提高[1] 。 從短期看, 大量金融資產投資能增強公司資金的流動性, 防范資金短缺風險, 但同時也會擠占企業的長效技術創新資源, 進而可能影響盈余可持續性, 危害公司實業的長遠發展。 那么, 實體企業金融化與盈余持續性之間到底存在何種關系? 該關系的傳導路徑又是什么? 考慮到企業金融化行為與盈余狀況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外部治理的影響, 哪些因素會對二者的關系產生調節作用? 本文試圖解答以上問題。
本文的貢獻包括: 第一, 從資產結構與現金流量兩個角度構建反映市場套利動機的存量指標與反映資金儲備動機的流量指標, 分析不同動機下企業金融化對盈余持續性的影響, 證實了金融化行為對盈余持續性的抑制作用; 第二, 采用中介效應模型證實了“企業金融化——創新能力——盈余持續性”傳導路徑, 對大多關注“金融化影響技術創新”的現有文獻進行補充; 第三, 從機構投資者治理視角, 證實了機構投資者的調節作用, 結合產權性質分析企業金融化與盈余持續性之間關系的差異,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內外部環境與企業行為之間的聯系。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企業金融化是指企業的金融資本運作越來越頻繁, 且利潤主要來源于金融渠道而非貿易和生產商品[2] 。 盈余持續性是指企業當期或前期盈余業績持續到下一期的可能性[3] 。 現有文獻對企業金融化與盈余持續性的研究多集中在金融化對企業實業投資、技術創新的影響, 并產生了“擠出”與“擠入”兩類效應觀點。 “擠出”效應認為, 實體企業金融化主要源于市場套利動機[4] 。 金融行業的高收益助推企業依靠金融渠道獲利、降低技術研發投入[5] 。 在資產組合權衡取舍下, 企業會減少用于實體投資的資金尤其是減少對固定資產的投資[1] , 進而對實業投資率[1] 、經營性業務生產效率[6] 產生抑制作用。 另有部分學者認為, 金融化與實體投資、技術創新的關系表現為“擠入”效應, 認為金融化行為的動機是建立資金儲備[7] 。 相較于外部融資環境的改善, 企業內部資金積累更能持續地推進其技術創新等長效投資[8] , 而金融產品一般具有較強的流動性, 當企業面臨經營風險時, 可以將金融產品迅速變現以減輕對外部融資的依賴[9] , 從而降低財務困境成本[10] 、緩解實業投資壓力并保持創新活動的長期性與穩定性[11] , 有利于維持公司主業的長期競爭力[9] 。
通過文獻回顧可以發現, 市場套利動機與資金儲備動機均為企業金融化行為提供了理論依據, 但不同動機下企業金融化作用于盈余持續性的方式存在差異。 從市場套利動機看, 資本逐利驅使企業金融化行為越來越頻繁, 企業不斷提高金融資產配置比例[4] , 越來越依賴金融渠道獲利, 導致管理層追逐“以錢生錢”的投資模式, 降低對生產經營活動特別是技術創新的資金投入, 從而對盈余持續性造成不利影響。 尤其在委托代理沖突下, 相比周期長、見效慢的實業投資(特別是技術創新投資), 市場套利動機會驅使管理層將資金投向能夠獲得短期現金流的金融資產, 以獲得管理權私利, 致使企業投資戰略短期化, 經營決策轉向金融領域而偏離業務, 損害企業盈余持續性。 從資金儲備動機看, 企業金融化是管理層為緩解融資約束而做出的適度投資, 企業配置的金融資產能夠憑借較強的變現能力發揮“準貨幣”功能, 避免因資金不足而導致企業投資中斷, 并緩解外部經營不確定性對主業的沖擊[9] 。 此外, 合理的金融資產配置有利于提高企業資金使用效率[12] , 產業資本參與金融市場也更有助于資本市場為技術創新投資者提供長期激勵、分散風險和共享機會功能[11] , 提升全社會創新活動的長期性、穩定性與風險承受度。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 從市場套利角度看, 金融化行為會擠占企業實業投資資源, 抑制盈余持續性。
H2: 從資金儲備角度看, 金融化行為會創造企業內源現金流, 促進盈余持續性。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及數據來源
以滬深A股2012 ~ 2019年非金融及房地產行業上市公司為樣本, 并對數據進行如下處理: 剔除ST、?ST公司; 剔除相關數據缺失公司; 剔除數據異常公司; 剔除在2012年上市的公司。 此外, 為減少極端值的影響, 對連續變量進行上下1%的縮尾處理, 最終獲得1044家上市公司共7308個平衡面板樣本觀測值。 企業專利申請數目來源于CNRDS數據庫, 其余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 運用Stata 16.0及Excel 2010進行處理。
(二)變量選取
1. 因變量: 盈余持續性(Croa)。 借鑒肖華等[13] 的研究, 采用主營業務資產收益率(主營業務利潤/期初期末總資產賬面均值)衡量企業盈余持續性。
2. 自變量: 企業金融化(fin)。 包括存量指標(fin1)與流量指標(fin2)。 存量指標來自資產負債表, 以金融資產/總資產表示, 反映金融資產投資對企業實物投資的擠占程度, 用于檢驗金融化行為的市場套利動機。 本文借鑒杜勇等[9] 的統計口徑, 定義fin1=企業配置的金融資產③/期初期末總資產賬面均值。 流量指標來自現金流量表, 反映金融資產投資創造現金流的能力, 檢驗企業金融化行為的資金儲備動機。 借鑒嚴武等[14] 的研究, 本文定義fin2=(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期初期末總資產賬面均值。
3. 中介變量: 企業創新能力(invest), 采用專利申請數目度量。 當前對企業研發創新能力的衡量指標主要包括研發投資占主營業務收入比[5] 、無形資產凈額增量占總資產比[15] 、專利申請數目[9] 等。 鑒于研發支出無法反映人力資本開發以及新技術引進、消化和吸收[8] , 無形資產包含無法體現創新能力的項目(土地使用權), 本文采用能綜合反映企業對各種創新投入利用能力的專利申請數目衡量企業創新能力, 定義invest=Ln(專利申請數目+1)。
4. 調節變量: 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inst)。 以機構投資者持股數占公司總股本的比例作為機構持股的計量指標。
5. 控制變量。 參考現有文獻, 本文設定控制變量包括公司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成長能力(Q)、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企業上市年齡(age)、高管貨幣薪酬水平(mpay)以及公司內部控制質量(index), 并控制時間效應。 此外, 考慮到資產負債率與盈余持續性的關系[16] , 將資產負債率的平方(lev2)也納入控制變量范圍。 具體變量定義如表1所示。
(三)模型構建
當前學術界多采用一階線性自回歸模型估計企業的盈余持續性, 基本模型為: Earnt+1=α0+α1Earnt+εt。 該模型的邏輯是: 盈余持續性越高, 以企業當期盈余預測未來時期盈余的準確性越高。 α1為當期盈余對未來時期盈余的敏感程度, 即盈余持續性。 若α1為正且越大, 表明盈余持續性越好。
借鑒程敏英等[17] 、彭愛武等[18] 的計量模型, 將企業金融化存量指標(fin1)、t期盈余持續性與企業金融化存量指標的交乘項(Croat×fin1)及相關控制變量納入上述基本模型構建方程(1), 將fin2、Croat×fin2及相關控制變量納入上述基本模型構建方程(2), 分別驗證H1與H2。 具體方程如下所示:
交乘項的系數α3(或β3)代表企業金融化對盈余持續性產生的影響。 若α3顯著為負, 則說明在市場套利動機下, 金融化行為通過對實業投資的擠占削弱了本期盈余與下期盈余的關系, 對盈余持續性具有抑制作用, H1得以驗證; 若β3顯著為正, 則說明在資金儲備動機下, 金融化行為能夠通過增加企業內源現金流的方式“反哺”經營業務, 對盈余持續性具有促進作用, H2得以驗證。 為消除不可觀測因素的影響, 本文采用排除公司個體差異的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列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由表2可以發現: Croat+1和Croat的均值分別為18.8%與15.8%, 說明樣本公司主營業務資產收益率的平均水平較高, 但從標準差來看, 企業間差異較大; 企業金融化存量指標(fin1)的均值為2.7%, 表明金融資產在總資產中的平均占比為2.7%, 最大值為88.2%, 說明不同樣本公司的金融化水平懸殊, 部分企業金融資產配置比例過大, 存在過度金融化現象; 企業金融化流量指標(fin2)均值為9.2%, 說明樣本公司通過金融渠道獲取的現金流較高, 標準差為0.296, 說明各公司的金融渠道獲利能力差距較大; 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inst)的均值為7.3%, 最大值為55.2%, 說明我國機構投資者平均持股比例較高。 觀察其他變量, invest、size、mpay、Q與age的標準差較高, 表明企業創新能力、公司規模與成長能力、上市年齡以及高管貨幣薪酬水平在不同公司間差異較大。 lev均值為43.3%, 表明樣本公司資產負債率較為合理。 其他變量的中位數與均值基本一致, 說明其基本服從正態分布。
(二)多元回歸結果
表3第(1)、(2)列是對方程(1)、方程(2)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的結果。 結果顯示: 方程(1)與方程(2)中Croat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 表明企業盈余持續性較強; 方程(1)中Croat×fin1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 表明市場套利動機下的金融化行為削弱了本期盈余與下期盈余的關系, 抑制了盈余持續性, H1得以驗證; 方程(2)中Croat×fin2的回歸系數雖為正, 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表明資金儲備動機下的金融化行為盡管能為企業創造一定的現金流, 但不能起到促進盈余持續性的作用, H2未通過檢驗。
其他控制變量對盈余持續性的影響與現有研究結論基本一致。 需要說明的是, 結合資產負債率(lev)與資產負債率平方(lev2)的回歸系數可知, 資產負債率與企業盈余持續性呈“倒u型”關系, 盈余持續性會隨著負債水平的提高先上升后下降。 top1與mpay的回歸系數也表明, 盈余持續性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高管貨幣薪酬水平負相關, 為企業提升盈余持續性水平提供了一定的參考價值。
(三)回歸結果分析
由方程(1)與方程(2)的回歸結果可知, 市場套利動機下的金融化行為擠占了實業投資資源, 對盈余持續性具有抑制作用; 資金儲備動機下的金融化行為盡管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融資約束, 增加了企業現金流, 但并沒有起到促進盈余持續性的作用。 其原因可能是在資本逐利性驅使下, 金融渠道獲利進一步強化了企業金融化行為傾向, 誘使管理層投資偏好與企業經營模式改變, 導致企業陷入“金融投資——獲取現金流——金融投資”的惡性循環。 這驗證了我國部分企業追逐“以錢生錢”投資模式的客觀存在, 逆向證明了H1的理論推演。
(四)穩健性檢驗
1. 替換相關變量。 方程(1)、(2)的解釋變量采用滯后項形式, 已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內生性問題, 但為進一步保證回歸結果的可靠性, 本文參考肖華等[13] 、李常青等[19] 的研究, 將方程(1)中盈余持續性指標由主營業務資產收益率(Croa)更換為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的總資產收益率(Roa), 計算公式為: Roa=(凈利潤-非經常性損益)/期初期末總資產均值。 參考劉貫春[15] 等的研究, 將方程(2)中現金流量表下的金融化流量指標(fin2)更換為利潤表下的金融化流量指標(fpr2), 計算公式為: fpr2=(投資收益+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其他綜合收益-營業利潤)/營業利潤絕對值。
表3第(3)列、第(4)列分別是對方程(1)采用Roa、方程(2)采用fpr2進行穩健性檢驗的回歸結果, 可以發現交乘項Roat×fin1的回歸系數仍顯著為負, Croat×fpr2的回歸系數為負但不顯著, 與主模型(2)回歸結果存在差異但未改變原結論, 依舊無法證實企業金融化行為對盈余持續性的促進作用。 穩健性檢驗結果表明, 本文結論具有較強的可靠性。
2. 更換回歸模型。 前文涉及的檢驗主要采用面板數據的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 為檢驗回歸結果在不同回歸模型下是否依然成立, 本文采用Tobit模型對方程(1)、(2)進行二次回歸, 并控制時間與行業效應, 回歸結果見表3第(5)、(6)列。 主要變量的回歸結果與原結果基本一致, 表明本文的研究結論具備較強的穩健性。
五、進一步分析
(一)創新能力的中介效應
根據前文的分析, 企業金融化行為在市場套利動機下會擠占技術創新等實業投資, 這不僅會弱化企業創新動機, 也會影響企業對創新項目的持續性投資, 進而對盈余持續性造成不利影響。 因此, 為檢驗創新能力是否在金融化影響盈余持續性的過程中發揮中介作用, 根據中介效應的檢驗模型[17] , 構建方程(3)、(4), 并對方程(1)、(3)、(4)采用Baron等[20] 的中介效應檢驗程序來考察是否存在 “企業金融化——創新能力——盈余持續性”這一傳導路徑。 鑒于本文采用專利申請數目對企業創新能力進行度量, 而專利申請數目具有非負整數特征, 故采取計數模型(Poisson模型)對方程(3)進行回歸[21] , 并控制時間與行業效應。 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對方程(1)、(4)進行回歸。 檢驗方程如下:
借鑒溫忠麟等[22] 的方法,? 按照以下程序進行檢驗: 首先, 檢驗企業金融化對盈余持續性的影響, 觀察方程(1)中回歸系數α3; 然后, 檢驗企業金融化對創新能力的影響, 觀察方程(3)中的回歸系數ω1; 最后, 同時檢驗企業金融化、創新能力對盈余持續性的影響, 觀察方程(4)中回歸系數γ2、γ4。 具體需要滿足以下條件: 其一, α3顯著, 否則中介效應不存在。 其二, 在ω1、γ4都顯著的基礎上, 若γ2顯著, 則存在部分中介效應; 若γ2不顯著, 則存在完全中介效應。 其三, 若ω1、γ4至少有一個不顯著, 則需要通過 Sobel 檢驗判斷中介效應(ω1×γ4)的顯著性。
表4列示了“企業金融化——創新能力——盈余持續性”傳導路徑的檢驗結果, 方程(1)列是不納入中介因子(invest)的檢驗結果, 交乘項Croat×fin1顯著為負; 在方程(3)的檢驗結果中, fin1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 說明企業金融化行為降低了創新產出; 在方程(4)的檢驗結果中, 交乘項Croat×invest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 表明企業創新能力越強, 盈余持續性越強。 由此可知, 企業金融化行為降低了企業創新能力, 進而抑制了盈余持續性。 另外, 方程(4)中交乘項Croat×fin1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依然顯著, 依照中介效應的檢驗程序可知, 創新能力是企業金融化影響盈余持續性的部分中介因子, 證實了金融化行為通過對創新資源的“擠占”, 對盈余持續性造成不利影響。 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與前文基本一致。 將主營業務資產收益率(Croa)替換為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凈資產收益率(Roa)(下同), 對方程(4)進行替換指標的穩健性檢驗, 得到與主模型一致的結論, 結果如表4所示, 表明本文結論具有較強的可靠性。
(二)機構投資者的調節作用
有效的外部監督能夠削弱經理人攫取管理權私利動機, 減少大股東利益侵占行為, 加大企業研發支出[23] 。 作為獨立于大股東與內部人的外部投資者, 機構投資者有能力發揮外部治理機制的重要作用。 首先, 相比個人投資者, 機構投資者進入目標企業時伴有巨額投資, 在參與公司治理時能夠憑借其強大的資金實力享有更大的話語權, 一旦控股股東或管理層做出不利于企業長遠發展的投資決策, 機構投資者就能憑借其較高的持股比例進行決策干預, 這不僅能減少大股東謀取控制權私利的行為, 還能起到對管理層的監督約束作用, 遏制管理層短視行為, 促進管理層與股東的利益趨同。 其次, 機構投資者比一般投資者專業水平更高, 可以憑借其信息搜集與處理、建立聯系等優勢幫助企業進行資源整合, 降低技術創新等長期價值導向投資活動的風險水平, 并為創新活動提供更為豐富的行業信息, 使得管理層投資偏好向具有長期潛在收益的技術創新過渡, 進而增加企業未來產出。 總體上, 機構投資者有能力通過監督治理機制與知識溢出機制減少管理層短視投資行為, 促使企業增加研發支出等長期價值導向的投資行為[24] , 以提升長期盈余水平。 同時, 機構投資者也有動機干預企業投資決策, 阻止企業做出為滿足短期收益目標而不顧長遠發展的投資行為。 因為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較高, 當企業業績變差時無法隨意拋售股票, 其在短期內退出企業的難度較大, 會更加關注大股東或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 并監督企業制定長效的生產經營決策以保證收益的持續性。 因此, 機構投資者既有能力又有動機發揮有效的外部監管作用與內部資源調控作用, 減少管理層短視投資行為并提高企業盈余持續性, 起到弱化企業金融化與盈余持續性負向關系的調節作用。
為驗證以上分析, 建立方程(5)檢驗機構投資者持股對企業創新的推動作用; 建立方程(6)檢驗機構投資者持股對盈余持續性的促進作用; 參考相關研究計量模型[17] , 建立方程(7)檢驗機構投資者持股對企業金融化與盈余持續性之間關系的調節作用。 并采用計數(Poisson)模型對方程(5)進行估計, 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對方程(6)、(7)進行估計。
回歸結果見表5。 方程(5)的回歸結果中, inst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 表明機構投資者持股提高了企業的創新能力; 方程(6)的回歸結果中, 交乘項Croat×inst的系數代表了機構投資者持股對盈余持續性的影響, 發現其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 表明機構投資者能夠通過其特有優勢提升企業盈余持續性; 方程(7)的回歸結果中, 機構投資者調節機制的檢驗需重點關注交乘項inst×Croat×fin1的系數, 發現該系數為正并通過顯著性檢驗, 表明機構投資者持股可以緩解企業金融化與盈余持續性的負相關關系。 前文的分析均得到驗證。
在方程(7)的穩健性檢驗中, 交乘項inst×Roat×fin1的系數為正, 并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 與原結論保持一致, 說明研究結論具備較強的可靠性。
(三)基于產權異質性的分析
國有企業作為接受政府直接管轄的主體, 其存在的目的更可能是擴大就業、增強社會穩定性并支持貫徹政府政策, 利潤最大化并不是其首要追求, 在“企業盈利性”與“國家公共性”的權衡下更傾向于后者, 因而其投資決策更加穩健; 非國有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是市場競爭的結果, 投資決策以優先滿足收益最大化為原則, 在金融領域投資回報速度與金額的雙重吸引下, 非國有企業更偏好對金融資產的投資以謀取高額回報。 因而本文認為, 企業金融化與盈余持續性的關系會因產權異質性而存在差異, 二者的負相關關系在非國有企業中顯著, 在國有企業中不顯著。
為此, 本文將1044家樣本公司按產權性質分為國有與非國有兩組, 對方程(1)采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樣本回歸, 結果見表5。 可以發現, 在國有企業組, 交乘項Croat×fin1的系數雖然為負但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在非國有企業組, 交乘項Croat×fin1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 這一結果表明在非國有企業中, 金融化行為對盈余持續性的抑制作用更為明顯, 前文的分析得到驗證。
六、研究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
針對實體企業“脫實向虛”的現狀, 本文基于非金融及房地產行業上市公司數據分析不同動機下的企業金融化行為與盈余持續性的關系, 并進一步考察企業金融化對盈余持續性的傳導路徑與調節機制。 研究發現, 市場套利動機下的企業金融化行為因擠占實業投資對盈余持續性產生抑制作用; 資金儲備動機下的金融化行為雖為企業創造了內源現金流, 但并未對盈余持續性產生有利影響, 反而證實了我國部分企業追逐“以錢生錢”的投資現象。 進一步研究得出, 創新能力下降是金融化行為影響盈余持續性的部分中介因子, 機構投資者持股能夠減弱企業金融化對盈余持續性的抑制作用。 另外, 通過分樣本回歸發現企業金融化行為對盈余持續性的抑制作用在非國有企業中更明顯。
(二)啟示
盡管本文研究表明企業金融化會對盈余持續性造成不利影響, 但綜觀世界各國的金融發展經驗, 經濟金融化是必經階段, 不能將企業金融化行為全盤否定。 為此, 本文提出: (1)深化金融業改革, 規范金融業發展。 政府應進一步放寬金融行業準入政策、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 以降低金融行業的超額收益率。 同時, 要完善金融監管體系, 創新監管方法, 提高金融監管透明度與法治化水平。 (2)加快產業轉型升級, 引導企業回歸本源。 政府應不斷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制定相應政策打造更好的實業投資環境, 加大對創新型企業的扶持力度, 縮小實體領域與金融領域的投資回報差距, 引導企業專注實業。 (3)明確金融投資定位, 重視創新發展。 企業應當將金融投資定位于為經營活動與研發創新提供更為充沛的內源資金, 借助金融活動“反哺”主業, 同時應重視創新活動, 積極引進創新型人才, 提高創新效率。 (4)優化股權結構, 完善內外部治理機制。 企業應適當引入機構股東, 充分發揮機構投資者的治理效能; 制定合理有效的薪酬制度與監管措施, 避免管理層短視投機行為。
【 注 釋 】
① 如何核算實體經濟占GDP比重目前尚有爭議。本文以MPS(物質生產體系)算出的GDP與當年SNA(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算出的GDP之比作為實體經濟占比,依據國家統計局官網《2020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計算得出。
② 依據中國人民銀行官網M1、M2貨幣供應量數據計算得出(http://www.pbc.gov.cn/diaochatongjisi/116219/index.html)。
③ 本文定義企業配置的金融資產為交易性金融資產、衍生金融資產、發放貸款及墊款凈額、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凈額、持有至到期投資凈額與投資性房地產凈額之和。
【 主 要 參 考 文 獻 】
[1] 張成思,張步曇.中國實業投資率下降之謎:經濟金融化視角[ J].經濟研究,2016(12):32 ~ 46.
[2] Greta R. Krippne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J].Socio-Economic Review,2015(3):173 ~ 208.
[3] Sloan G.. Do Stock Prices Fully Reflect Information in Accruals and Cash Flows About Future Earnings?[ J].Accounting Review,1996(3):289 ~ 315.
[4] 欒天虹,袁亞冬.企業金融化、融資約束與資本性投資[ J].南方金融,2019(4):28 ~ 36.
[5] 王紅建,曹瑜強,楊慶,楊箏.實體企業金融化促進還是抑制了企業創新——基于中國制造業上市公司的經驗研究[ J].南開管理評論,2017(1):155 ~ 166.
[6] 劉篤池,賀玉平,王曦.企業金融化對實體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研究[ J].上海經濟研究,2016(8):74 ~ 83.
[7] Tornell A.. Real vs. Financial Investment Can Tobin Taxes Eliminate the Irreversibility Distortion[ 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0(2):419 ~ 444.
[8] 鞠曉生,盧荻,虞義華.融資約束、營運資本管理與企業創新可持續性[ J].經濟研究,2013(1):4 ~ 16.
[9] 杜勇,張歡,陳建英.金融化對實體企業未來主業發展的影響:促進還是抑制[ J].中國工業經濟,2017(12):113 ~ 131.
[10] René M. Stulz. Rethinking Risk Management[ J].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1996(9):8 ~ 25.
[11] Tadesse S.. Financial Architecture Economic Performance:International Evidence[ J].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2002(11):429 ~ 454.
[12] Sean 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rm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Status[ 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99(2):673 ~ 692.
[13] 肖華,張國清.內部控制質量、盈余持續性與公司價值[ J].會計研究,2013(5):73 ~ 80+96.
[14] 嚴武,李明玉.企業金融化一定會擠出實業投資嗎——基于中國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實證分析[ J].當代財經,2020(7):63 ~ 74.
[15] 劉貫春.金融資產配置與企業研發創新:“擠出”還是“擠入”[ J].統計研究,2017 (7):49 ~ 61.
[16] 韓曉明.財務風險與會計盈余質量[ J].財會研究,2011(18):57 ~ 60+62.
[17] 程敏英,鄭詩佳,劉駿.供應商/客戶集中度與企業盈余持續性:保險抑或風險[ J].審計與經濟研究,2019(4):75 ~ 86.
[18] 彭愛武,張新民.企業資源配置戰略與盈余持續性[ J].北京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3):74 ~ 85.
[19] 李常青,張兆偉.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會計盈余指標的有用性[ 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2):114 ~ 121.
[20] Reuben M. Baron, David A. Kenny. The Moderator -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1986(6):1173 ~ 1182.
[21] 馮根福,劉虹,馮照楨,溫軍.股票流動性會促進我國企業技術創新嗎?[ J].金融研究,2017(3):192 ~ 206.
[22] 溫忠麟,張雷,侯杰泰,劉紅云.中介效應檢驗程序及其應用[ J].心理學報,2004(5):614 ~ 620.
[23] 羅正英,李益娟,常昀.民營企業的股權結構對R&D投資行為的傳導效應研究[ J].中國軟科學,2014(3):167 ~ 176.
[24] Sunil Wahal, John J. McConnell. Do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Exacerbate Managerial Myopia[ 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00(6):307 ~ 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