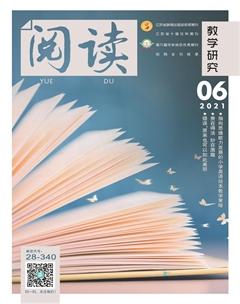閱讀:最美的“遇見”
丁素芬
把教育的力量注入時間的流淌之中,讓時間的流逝產生教育的偉力。
時間的流逝,絕不止于讓人衰老,它還能讓人再生。
——摘自李政濤:《教育與永恒》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個讀書人都有過這樣的“遇見”——總會有那么一些書,讓你一見傾心,念念不忘。或因為作者,或因為書的本身,總之,你就這樣愛上了它。
我讀李政濤教授的著作,就是如此。無論是《做有生命感的教育者》《重建教師的精神宇宙》,還是《傾聽著的教育》《教育與永恒》,文字中都有一種安靜入心的力量。
翻開多年前的閱讀記錄,有一段話再次觸動自己:
夜深,又一次讀您的同一部書,仍然感動不已。生命躍動中的思想碎影,仿佛對話,抵達靈魂。人的存在之信仰,之累,都是生命的必然。初領了“心情微進中年”的深義,只能說,感恩、進步,是此后生命中唯一的權利。
很少有幾本書,可以讓我如此不厭重讀。且每讀一次,心靈依然深深震動。我相信,這是我的書緣。教育常識、生命自覺、精神宇宙、自省復盤……這些階段的關鍵詞眼,是一扇扇通往人生格局的窗和門。由書及人,對李教授的“跟蹤式閱讀”,彌補了我的理論空缺,打開了更遼闊的實踐田野。其詩人般的情懷、教育人的深邃、思想者的哲思、變革家的堅定剛勇,如燈光如風景,引領我向著明亮那方而行。
這些年,我的閱讀方式發生了變化。我越來越強烈地感到,最重要的不是讀了多少書,而是實現了多少轉化。這聽起來似乎有點功利色彩,其實不然。“讀”應該是一個更縱深、更遼闊的概念。于我而言,“讀”關聯著兒童,關聯著思維方式,關聯著自我的課堂追求。如何以更多樣的“讀”打通理論與實踐的通道?如何把“讀”化入常態的教學?
一天,我聽到一個報告,主題是“學科核心素養下的語文教學”,在主講人兩個半小時的演講中,有一個他所講到的看似平常的習慣擊中了我,那就是每天寫閱讀記錄、教學日志,幾十年不間斷。讀讀寫寫,說起來容易,堅持做太難了。試想,若能在最平常的每一天里,堅持以兒童的眼光,以樸素的教育姿態,以對教育常識的極大尊重,讀讀書,寫寫心得,該是多么有意義的事情。
于是,我也嘗試給自己設計一條新的學習路徑。這恰又印證了李政濤教授的觀點:我所經歷的個人成長誤區,是一度讀得太多,寫得太少,被“述而不作”所束縛。后來發現,其實很多道理、想法、體悟,不是讀明白,想明白,而是寫明白,寫清楚的,由此我悟出了“以寫促讀”“以寫清思”“以寫引思”的道理。
在自己認為對的那個點上,需要一股激情投入的傻勁兒、魯莽勁兒和義無反顧。
我喜歡專題閱讀。讀書、讀課、讀人,也讀己。女兒說,我讀過的書別人都不要看了,簡直是“毀書”,任性的批注讓書本“面目全非”。對于愛書顏的人來說,這的確不是一種好習慣。但是,書是自己讀的,何必管那么多呢?讀書讀到會意處,就要動筆寫一寫自己的理解,是認同還是有異議,好像在與作者進行一場面對面的交流,那樣的感覺很棒。
閱讀中,常常產生聯想,這種聯想更像一種靈感。此時,此地,此心境,讀到此句段,腦海中一下子冒出與之相關聯的其他書籍,或是自己曾經有過的想法。如火花般閃現的思想轉瞬即逝,當然要趕緊記錄下來。我聽到過許多老師抱怨:讀過的書總記不住,怎么辦呢?讀書不是背書,為什么都要記住呢?或許真有人有過目不忘的特異功能,我們也不必羨慕,我總相信,眼睛、大腦遇見過的文字會在不經意的某個時刻閃現出來。
于我來說,每天堅持15分鐘晨讀,大有裨益。雜志沒有時間翻閱,清晨正好。碰到喜歡的文章,做個筆記,寫幾句感言,這是真正的閱讀積累文章。不是刻意而為之,自然而然是最好的狀態。我很喜歡讀卷首。好的卷首語,語言凝練,思想深邃,邏輯緊密,從文章學的角度去細讀結構,體悟內涵,是件很有趣味的事。一次讀雜志,讀到特級教師孟曉東的《學生在“生長中”》一文,寫下感言——
“生長中”是以尊重天賦為前提的可持續的過程論。這個過程首先是要賦予兒童學習的權利,而且是個體化的權利。教育在本質上就是要依據學生已有的所思所想來實現生長。面對空無一物的大腦,或是將豐富的個體原有認知結構籠而統之,教育將無所作為。其次,生長中的“主體”有充分的自由,也有潛在的規約。作者強調自由,并不是否認規約,作者以“本質需求”與“非本質需求”來論證自由、規約與生長之間的循環。列夫·托爾斯泰說:“教育的唯一規范是自由。”這是對教育生長樣態的最好注解……
多么迷人的“生長”啊!學生要時刻處于“生長中”,這是教育應然的追求。
像這樣的閱讀批注還有很多。讀一篇好文章,想清楚一個問題,足夠了。
常常有人問我,最近又讀了什么?列個書單吧。其實,我讀得不多,讀得很慢,非要讀出與自己的聯系才肯罷休。我很享受這樣的慢讀、深讀、追蹤讀。讀書、寫作,源于教育,又反哺教學。這個過程,本該是優雅的、專注的。
遇見一本有思想的好書、一段有力量的文字、一群光明俊偉的人,是閱讀的最美的“遇見”。
(作者單位:江蘇省蘇州市高新區科技城實驗小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