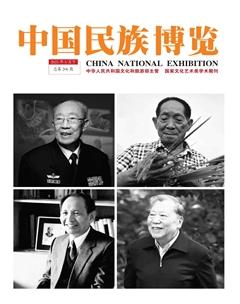邁進西北地區民族音樂種類的文化現場
【摘要】我國西北地區少數民族較多,民族風情獨特,地域特點突出,音樂文化品種豐富。本文對馬希剛所著《西北少數民族音樂文化》一書從結構安排的科學性、內容的全面性,創作的思想性、學術性,美學視角的藝術性、知識性,文化價值的實踐性、永久性以及學術研究的情緣性、學識性多個方面展開了闡釋與評論。一則對其學術研究成果的肯定,二則能夠讓我們對民族音樂的文化類型、各民族間音樂文化的交流與互融等問題有更廣泛更深層次的認識與思考,在民族音樂研究中更加重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使民族音樂有更好的發展。
【關鍵詞】 西北;少數民族;音樂文化;評介
【中圖分類號】J6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1)10-211-03
【本文著錄格式】賽音. 邁進西北地區民族音樂品種的文化現場——馬希剛著《西北少數民族音樂文化》評介[J].中國民族博覽,2021,05(10):211-213.
西北地區是中國少數民族聚居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主要有回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藏族、蒙古族、俄羅斯族等。這里不僅是中國經濟、能源的戰略要地,而且也是傳統音樂的巨大寶庫。據《西北五省四部民間音樂集成》錄載的各種民間音樂品種,如民歌、歌舞、戲曲、說唱、器樂以及宗教音樂大概接近1000種。尤其西北少數民族音樂不但品種豐富而且具有很強的區域性特征和濃重的民族特色。面對這樣的天然資源庫,馬希剛所著《西北少數民族音樂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10月)帶我們邁進西北地區不同民族音樂種類的文化現場,領略各民族鮮明的各具特色和民族風格的傳統音樂文化風貌。他將生活在西北地區少數民族人民的歷史傳統、居住環境、社會狀況、勞動方式、語言風俗、宗教信仰等方面條件的影響下各民族的民族文化、音樂品種的類型、特征及教育問題等方面都做了詳盡的闡釋分析和總結。
《西北少數民族音樂文化》這本書的外觀(如圖所示)設計簡單大方,清新明快,特色突出,有著與眾不同的民族音樂文化特點。整本書的封面以白色為主,左右兩側以直線作為裝點,中間以縱橫交錯的封閉圖形進行點綴,簡約而不簡單。左側下方加入西北少數民族代表性的打擊樂器,這種鼓上寬下窄,中間呈現凹進去的形狀,鼓的表面橫豎都有條紋狀花紋,上端兩側有兩個抓手,制作精致且非常方便攜帶去各個少數民族地區進行交流演出,所以此元素的設計應用凸顯少數民族樂器普及性特點及少數民族音樂交融性的文化含義。文字信息從大到小、從上到下依次為書名、作者以及出版社名稱。封皮內側有作者簡介,封底有內容簡介。從整體來看,這本書的插畫雖然相對簡單,面積占比也比較小,但是與書名起到上下呼應的作用。所謂麻雀雖小,卻五臟俱全,主題鮮明。讀者只需要隨意看上一眼就能夠大體了解到書中寫了什么樣的內容,具有什么樣的特點。這本書不僅適合專業學習音樂的學生對西北少數民族的音樂文化進行深入了解,也為促進西北少數民族音樂文化普及與發展,使其更好的繼承西北傳統音樂,推動國內地域音樂文化與民族音樂文化研究邁向縱深起到積極作用。
統閱全書對其感思評介與學術界諸君分享。
一、內容的全面性、科學性
西北地區少數民族音樂具有中原文化、諸羌文化、西域文化、吐蕃文化等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點,該著對西北地區少數民族音樂文化進行科學的系統研究,既是我國傳統文化建設與發展戰略中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也是滿足學者了解西北地區民族音樂的客觀需求。《西北少數民族音樂文化》全書共有十二章,每章根據所述內容以二、三、六、九節不等建構,整體內容來講亦可歸納為三個大的部分。
第一部分,對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的文化進行了闡述。音樂與文化是分不開的,所以對西北地區少數民族音樂的分析,亦離不開對當地文化的分析。其次,對音樂的分析也離不開對音樂本體理論的掌握,因此對西北少數民族音樂學與相關學科、民族音樂與民間音樂、音樂體系、音樂類別、典型歌種“花兒”的藝術特征、山歌的音樂形態進行了分析。
第二部分,對西北地區的各個少數民族,如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回族、藏族、裕固族、蒙古族、撒拉族以及其他少數民族的文化、多種音樂類型及其文化特征等進行了詳細闡釋,然后選取各民族代表性傳統音樂作品進行了解讀分析。這是對音樂微觀層面的分析,可以幫我們更細致地了解西北地區的少數民族音樂文化。
第三部分,對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的發展、傳播以及教育進行了分析。音樂要不斷地傳承,離不開發展,離不開傳播,更離不開教育。只有這樣,才能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二、創作的思想性、學術性
縱覽《西北少數民族音樂文化》之全文,甚感資料收集全面,結構清晰合理,內容客觀詳實,不但研究視角新穎獨特而且吸取了大量交叉學科的知識及學術前沿的理論,參考了廣泛的資料和文獻。有理有據,有“述”有“作”,層次清楚,體例得當,見解犀利。可從以下方面足見。
第一,采取全方位的文化視角對西北少數民族音樂文化進行研究,即把音樂作為文化類型與行為模式置于其文化背景中加以研究,在形態分析的基礎上對它做出了合理的文化闡釋。
第二,形態剖析另辟蹊徑,從整體著眼,對民歌、歌舞音樂、器樂等基礎知識及所包含的各類體裁,在音樂特征上做了綜合性的剖釋、解析,概括性地提煉、歸納,使每一種體裁各個分類的音樂共性得以清晰地、整體化地呈現,各體裁的音樂個性也因此得以清楚地、標識化地鑒別。
第三,重視音樂作品鑒賞,設有經典代表性作品,樂曲譜例,配以文化背景、音樂形態等特點的分析,不僅生動直觀且形象感人。
第四,將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歷史文化與音樂文化實踐和創造性藝術成就緊密結合分析西北少數民族地區音樂傳播及教育的發展,探索其與特定環境之間多方面的淵源關系。充分彰顯著作撰寫之思想性、學術性、包容性。
三、美學視角的藝術性、知識性
任何社會文化現象,總是以發展著的結構形態存在著,它既是現實的又可追溯為一種歷史的延伸現象,在宏觀世界里將民族音樂與社會生態、人文等關聯研究才能表現出民族音樂與社會、民族音樂與生態、民族音樂與文化的內在聯系。
第一,《西北少數民族音樂文化》的研究能夠站在民族文化的歷史高度,把西北少數民族音樂視為文化生活中千變萬化的方式發展著的精神領域,運用了史學、考古學、民俗學、人類學,以及文獻研究法、比較研究法、分析研究法、個案研究法。將概論性、宏觀性研究與專題性、微觀性研究相結合,進行切合實際的認知和可觀的闡述。同時反映了社會環境、生態以及人文對民族音樂發展所起到的功能及作用。
第二,《西北少數民族音樂文化》是我國傳統音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的文化發展和人民生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這些少數民族音樂不光為生活在那里的人們創造了交流、互通、宣泄情感、放飛心靈的最佳平臺。而且在環境上,在朝山祭神的宗教儀式的召喚上,在情感動力的內驅下,客觀上推動了少數民族音樂的群體發生,淋漓的表現了少數民族音樂自然美、純樸美、野性美、蒼涼美、悠遠美以及形式上的格律美、音韻美等眾多文化方面比較成熟的美學效應與美學特征。這些都能讓我們更加直觀的注視到民族音樂不是靜止的、凝固不變的,隨著時間、空間的變化,其內容和形式都處于不斷演變之中。自然而然的以特有的內在機制影響著人民群眾向社會實踐中真、善、美境界的追求和接近。
第三,在民俗學界、文化人類學界強調文化環境、文化標志物、文化承載“三位一體”的觀察角度方面,《西北少數民族音樂文化》無論是對研究對象的立體考察還是對方法論的理論構筑,都無不體現出民族音樂學科構架、方法論及實踐的運用,使我們對西北少數民族音樂文化景觀有了更新的視野和角度。
四、文化價值的實踐性、永久性
我國音樂文化古老深沉、歷久彌新、豐富多彩,尤其西北地區是眾多音樂文化瑰寶的誕生地,諸多少數民族音樂所帶有的特質都是我國音樂文化中濃墨重彩的存在。它們有著不同的自然環境、社會型態、歷史、宗教、經濟、語言,在長期的生產勞動和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同程度的創造了自身多元的民族文化。然而這種形式上色彩斑斕的變化,以及內容上深厚睿智的積淀正是西北地區歷史文化的記錄。
第一,《西北少數民族音樂文化》反映了各族人民鮮明的民族特色和共同的性格特征、心理素質和審美情趣,體現了民族音樂是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再次證明了從各個角度各個方面對民族音樂進行研究使我國民族音樂研究的歷程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在短短十幾年內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與進展。故而以此促進了各個文化間的相互理解與溝通,加強了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認同感。
第二,《西北少數民族音樂文化》的研究不僅說明了浩如煙海的西北少數民族音樂種類之豐富,形式之多樣,同時也反映了西北地區少數民族同胞的思想理念、情感和思維方式,正是這些思想情感以及思維方式決定了文化的發展方向與文化的創作初衷。它是一種經過歷史沉淀積累,發展穩定且方向統一并獲得普遍廣泛認可的一種思想本質。這種思想本質引導人們對一些事物的審美趨向以及觀點的改變。在哲學、倫理學、宗教學、科學以及藝術學等思想領域中,一樣是引導人類創造文化,并且使文化反映最真實的人類社會生活。具有高度審美價值和人文研究價值。由此更可以看出馬希剛的研究成果在民族音樂學、中國傳統音樂及西北民族音樂相關理論與方法體系應用的集中體現。
第三,這部《西北少數民族音樂文化》之作,是民族音樂研究領域中比較突出的成果之一,對西北地區各民族的音樂文化傳播衍生具有積極的影響和指導意義。當下,作為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許多民族魂寶傳承保護工作十分強調繼承性與普適性,這也是引發民族音樂藝術發生及文化價值的重要要素。《西北少數民族音樂文化》的研究成果正是對民間文藝形式的漸進性、認識價值的永久性的這一科學認識的付諸實踐。
五、學術研究的情緣性、學識性
一個出色的學術研究者不但要有良好的專業素養和極強的思辨能力,還要有博納萬川的胸懷與真摯的情感。馬希剛在著作后記中闡述以西北少數民族音樂文化立作的原因,其中言道:“出于對西北民族大學音樂學院的特色性學科建設的思考及自己作為一個地道的西北人對豐富的西北民族文化和民間音樂執著熱愛的情懷。”當我讀到此處就在想,如果這樣的選題讓西北地區以外的人做,難度反而較大,因為會涉及到地緣、人緣、語緣,這些方面沒有一樣不難的。而對于地道的西北人馬希剛而言則合乎于理,順乎于情,難變為易,劣勢轉為優勢。情懷是動力,質能因動力而展現,有此情懷、責任、精神與初衷值得稱道。
學術研究有如接力賽,只有不斷吸納新思維、新方法、新理論,一個學科才會獲得延續其生命力的能量。馬希剛能夠將此《西北少數民族音樂文化》的學術資源,交給當代學術界,留于后啟之學,不但為民族音樂研究者提供了借鑒學習的經驗,更是具有實踐性和現實意義的。
六、結語
如果我們能夠對中國民族音樂文化做出有深度的結論,它將需要構筑數以萬計的群體融合的經驗,對地方、民族、歷史、經濟、政治、文化以及個性化等因素進行整體關注。同時,這項工作還需要大批像馬希剛這樣有決心和睿智的生力軍去完成。建議在此研究基礎上對西北少數民族音樂建構的變化規律、社會變遷交互影響的規律及民間音樂作為基于小農思維邏輯之上的活態展現與踐行等問題做進一步深入思考與研究以梓增補,期待此著更加完美。
作者簡介:賽音(1973-),男,甘肅蘭州人,碩士研究生,西北民族大學音樂學院院長,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民族音樂、理論作曲。中國音樂家協會理事,甘肅省音樂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