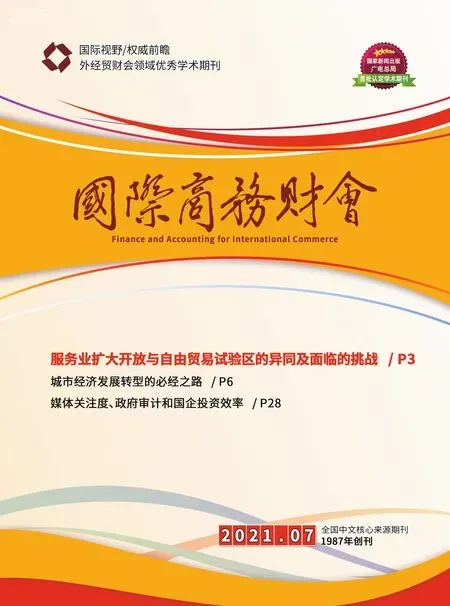關鍵審計事項政策效應文獻綜述
黃圓圓
(深圳市教育局財務核算中心)
一、引言
審計師是資本市場的信息鑒證者,審計報告影響信息使用者對企業財務報表的信賴程度和投資決策,也會影響企業在資本市場的股價表現。審計報告的信息含量和審計溝通價值備受理論界和資本市場的關注。近年來,英國財務報告委員會、歐盟委員會和國際審計與鑒證準則理事會分別在2013年、2014年和2015年相繼修訂了新的審計報告準則,要求注冊會計師在審計報告中披露某些被認定的關鍵審計事項,以此進一步規范審計報告格式和質量。為了與國際審計準則趨同,增加審計報告的信息含量,我國在2016年頒布了《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第1504號——在審計報告中溝通關鍵事項》等12項新審計準則,其中最核心的變化則是在審計報告中新增披露關鍵審計事項。該項準則要求A+H股上市公司自2017年1月起首先在審計業務中實施該規定,而其他所有A股上市企業則于2018年1月起披露關鍵審計事項。
關鍵審計事項的定義為:“注冊會計師根據職業判斷選取與治理層溝通過的事項中認為對本期財務報表審計最為重要的事項。”因此,關鍵審計事項的披露質量不僅取決于審計師的職業能力,也會受到被審計單位的影響。此外,關鍵審計事項的披露內容、數量和詳細程度也并未在準則中規定,因此學者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是否能夠提供增量信息的研究結論尚存爭議。本文梳理了關鍵審計事項披露實施效果的現有相關文獻,探討該準則是否發揮了預期的提高審計報告質量和投資決策效率的作用。
二、政策實施效果
關于審計報告增設關鍵審計事項段的影響,現有研究歸納起來基本體現在對審計質量、信息含量、審計風險、企業投融資決策方面的影響,具體如圖1所示。

圖1 關鍵審計事項實施效果
(一)審計質量
關于關鍵審計事項與審計質量之間的關系,現有研究共有提高、降低和無影響三種觀點。
我國研究學者的結論基本支持關鍵審計事項的披露會提高審計質量這一觀點。王艷艷等(2018)以及路軍和張金丹(2018)的研究認為關鍵審計事項的披露通過兩種途徑提高了審計質量。第一,披露關鍵審計事項提高了審計程序的透明度,報表使用者可以實現對審計師工作的外部監督,有利于加強對審計師的約束并強化其受托責任(Bédard等,2015;Reid等,2019)。許靜靜等(2019)基于2018年A股全面披露關鍵審計事項的研究同樣認為注冊會計師為了滿足新審計準則的要求,會努力提高自身職業素養和執業水平,從而促進其專業勝任能力。此外,注冊會計師出于聲譽和法律風險,會在工作中時刻保持職業懷疑,尤其是審計風險較高的領域,更加積極謹慎地對待重大錯報風險,提高發現錯報的概率,進而有效限制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提高審計質量。第二,新審計準則中規定關鍵審計事項要有助于信息使用者與企業管理層溝通,即其披露在一定程度上會促使管理層與審計人員溝通的意愿更強(柳木華,2018),管理層會按照審計師的意見進一步修改完善財務報告,報告更多高質量的財務信息,從而間接提高了審計質量(張繼勛等,2016;楊明增等,2018;李延喜等,2019)。而鄢翔等(2018)則是利用A+H股的數據,從“溢出效應”角度出發,驗證了關鍵審計事項披露對審計質量的提高。由于A+H股的審計師相對于其他審計師要更早接觸并適應新審計報告要求,這些審計師會先一步形成“學習效應”,設計新的審計流程并更加謹慎,從而提高了審計質量。
另一方面,Asbahr和Ruhnke(2017)的研究證明了關鍵審計事項的披露不僅沒有提高財務報告質量,反而降低了審計質量。這是因為注冊會計師關鍵審計事項的披露,反而可能會放棄對這些事項提出異議或進行調整。即審計師將關鍵審計事項的披露看作相關的免責聲明,認為相關賬戶的審計結果已經說明,因此減少了審計程序,進而導致審計質量的下降(Kachelmeier等,2014)。
此外,Gutierrez等(2018)的研究則發現關鍵審計事項與審計質量之間并沒有顯著關系。這是因為關鍵審計事項的披露極有可能成為樣本化和模式化的陳述,從而使披露信息的價值十分微弱。或者審計師為了降低自身風險,披露一些本身價值不多的財務信息,降低了審計質量。張金丹等(2019)的研究證實了關鍵審計事項的披露并沒有降低公司盈余管理,報表使用者只是因為審計報告更加詳細而在感知層面上感受到了更高的審計質量。
(二)信息增量
新審計準則的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審計報告的信息增量,美國公眾公司會計監管委員會提出,審計報告中增設的關鍵審計事項也許可以為信息來源較少的企業提供信息增量。而審計師在每年的審計報告中提供了以前年度關鍵審計事項沒有的信息才能成為信息增量,即如果后期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與前期有所重復,則關鍵審計事項的信息價值就會大打折扣。國內外學者主要通過投資者交易、分析師盈余預測質量和股價同步性等來驗證關鍵審計事項是否具有信息增量,但研究結論尚存爭議。
1.投資者交易
一方面,有學者的研究證明,關鍵審計事項的披露可以提高審計報告溝通價值,影響投資者的投資決策(Chen等,2014;Carver和 Trinkle,2017)。Christensen等(2014)和Sirois(2017)的研究證明,投資者會關注審計報告中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并因此改變自己的投資決策(Reid 等,2015;王旭東和程安寧,2018)。張繼勛和韓冬梅(2014)的研究同樣支持該結論,他們發現投資者因為增設的關鍵審計事項會加強對審計報告有用性的感知,降低投資者的風險感知并增加投資意愿(Doxey,2014)。陳麗紅等(2019)的研究表明關鍵審計事項的披露降低了盈余價值相關性,即其提供了增量信息,增強了投資者感知的盈余不確定性。王艷艷等(2018)則利用A+H股新審計報告準則為準自然試驗,采取雙重差分法研究發現,相對于未披露關鍵審計事項的公司,披露公司的累計超額收益率在披露前后的變化都顯著提高,說明關鍵審計事項確實提供了增量信息。而李奇鳳和路軍偉(2021)利用所有A股上市公司數據研究也同樣得出,關鍵審計事項的數量和篇幅與中長期窗口累計超額收益率顯著正相關,但這種情況存在于小公司中。說明關鍵審計事項披露只對小公司具有信息補充作用,而大公司審計報告中的信息含量則沒有顯著提高。此外,也有學者認為,關鍵審計事項只會對專業投資者有影響,而非專業投資者則不會(Khler等,2016)。
另一方面,有國外學者認為關鍵審計事項的披露并不能增加信息含量。Guitierrez等(2016)利用英國資本市場數據,實證檢驗發現投資者對增設了關鍵審計事項的審計報告并沒有表現出特別反應,其決策沒有發生變化。Lennox等(2015)的研究認為投資者在之前披露的盈利公告或年報中已經了解到了大部分風險,關鍵審計事項并沒有提供新的信息,因此股票市場的超額收益率沒有顯著變化。Brasel(2016)從另一個層面指出,即使關鍵審計事項在首次披露時可能會吸引投資者的關注,影響其決策。但在連續審計中,可能會出現更多“樣板式”的關鍵審計事項,相關的審計程序也可能越來越標準化,難以保證每一年度的審計報告都會提供新的信息,尤其是經營穩定的企業(Irvine,2014)。
2.分析師盈余預測質量
審計報告作為分析師獲取信息的主要來源之一,新審計準則的實施必然會影響分析師盈余預測的準確性,但提高還是降低分析師預測質量卻有所異議。
已有研究大都支持關鍵審計事項的披露會提高分析師預測的準確性,且披露數量越多,分析師預測質量越高。這是因為在此次審計準則改革前,審計報告在格式和內容上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同質化問題(唐建華,2015),分析師無法通過提供有限信息的審計報告區分企業質量及其經營情況。而新審計準則要求披露關鍵審計事項、持續經營等信息,從文本結構來看,可以分為“事項描述段”和“審計應對段”。“事項段”傳遞了更多公司基本面信息,“應對段”則增進了外部報告使用者對審計程序的了解,這些信息又降低了信息不對稱程度,有助于分析師進一步收集和分析公司特質信息和經營情況(王艷艷等,2018)。趙剛等(2019)、劉圻等(2020)以及高錦萍和高居平(2021)的研究以A+H股為研究對象,發現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為分析師提供了有效增量信息,顯著提高了分析師預測準確性,降低其盈余預測樂觀度。
但也有學者認為關鍵審計事項反而會降低了分析師預測準確度。薛剛等(2020)以A+H股公司為處理組,利用DID模型實證檢驗得出,關鍵審計事項披露降低了分析師預測準確度,且在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中更加顯著。這是因為審計報告中增設關鍵審計事項對管理層產生了壓力,顯著抑制了管理層盈余管理程度,使其無法迎合分析師預測。另一方面,關鍵審計事項降低了使用者對財務報表的信賴度導致分析師獲取信息不足(Kachelmeier等,2014),從而降低了分析師預測質量。
3.股價同步性
王木之和李丹(2019)利用雙重差分模型實證檢驗發現,新審計報告增加了公司特質信息,降低了股價同步性,且在信息不對稱程度較高的企業中更明顯。這是因為關鍵審計事項可以形成可靠信息來源。Christensen等(2014)發現,同一件事項相對于管理層披露,投資者會對由審計師披露的內容產生反應。同時,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可引導投資者更合理分配其有限注意力到更為重要和有價值的地方,從而促進投資者對公司特質信息的了解,降低了股價同步性。
(三)審計風險
國內外學者關于新審計報告對審計風險的研究,基本是從審計師感知到的審計責任和審計定價角度展開。
國際審計與鑒證準則理事會(2015)認為,如果審計人員進行了全面風險評估并采取了相應的審計程序,審計意見的發表是基于獲取的審計證據,那么審計人員的責任不會因為增設關鍵審計事項的披露而改變。對此觀點,一些學者認為披露關鍵審計事項可能會降低審計失敗給審計師帶來的責任,畢竟審計師已經盡到告知提示義務(Brown等,2015;Brasel等,2016);另一些學者則認為“言多必失”,因為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會受到管理層、監管者和投資者等多方的關注和監督,因此反而會增加審計師感知到的審計責任(Emst和Yong,2013;Katz,2014;Gimbar等, 2016)。基于上述問題,韓冬梅和張繼勛(2018)基于心理學理論,采取試驗研究法檢驗發現,關鍵審計事項的披露使得審計師感知的審計責任更小。進一步研究發現,在披露關鍵審計事項的基礎上,對其做出結論性評價時,審計師感知到的責任比沒有做出結論性評價更大。此外,韓冬梅等(2020)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發現,在關鍵審計事項的結論性評價表述為“合理的”情況下,審計師感知的審計責任最大;表述為“可以接受的”情況下,審計感知的審計責任次之;表述為“沒有發現重大問題”的情況下,審計師感知的審計責任最小。而Gimbar等(2016)的研究則得到了與之相反的結論,他們發現如果披露了與重大錯報相關的關鍵審計事項,外界會質疑為什么沒有實施徹底的審計程序以解決已經發現的問題;如果披露了非相關的關鍵審計事項,外界則會質疑審計師為什么沒有察覺重大錯報,即審計師的能力總會遭到質疑。
審計定價取決于審計過程中耗費的直接成本和風險溢價(Simunic,1980)。新審計報告準則要求增設關鍵審計事項等信息,必然帶來了一定的實施和轉換成本,如審計師學習新準則的時間和學習成本。特別是關鍵審計事項主要披露一些可能存在重大錯報風險的領域,導致事務所風險溢價以及審計師與管理層之間的溝通成本也必然會上升。基于上述問題,潘克勤(2020)、楊茜和李濤(2020)、涂建明等(2020)以及周中勝等(2020)利用審計準則變革為準自然試驗,研究發現,關鍵審計事項的披露顯著提升了事務所審計收費,且關鍵審計事項披露數量越多、被審計單位審計風險越大,審計收費越高。
(四)企業投融資決策
信息不對稱是影響企業融資成本的一個重要原因,而關鍵審計事項增加了了解企業信息的可信賴來源,提高了企業信息透明度,因此對公司融資成本必然會產生影響。
一方面,關鍵審計事項作為新增信息,有助于投資者了解企業經營情況,預測企業未來現金流量和財務風險,降低了信息不對稱性,從而減少了投資者要求的風險補償。另一方面,管理層會由于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的壓力,采用更穩健的會計估計和方法。因此新審計報告作為一種有效的外部監督機制,降低了投資者的監督成本,從而降低了企業股權融資成本。而另一方面,關鍵審計事項是否具有信息增量尚且存在爭議,且如果審計師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模板化”趨同,就很難降低企業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此外,關鍵審計事項可能會將企業重大風險披露出來,提高投資者對企業的風險溢價,進而導致股權融資成本的增加。基于上述問題,趙玉潔等(2020)以中國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關鍵審計事項的披露確實含有信息增量,有效降低了企業融資成本,支持了第一種說法。而姜麗莎等(2020)則基于同樣的思路對企業債務融資成本進行了檢驗,研究結論一樣支持了關鍵審計事項可以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使企業債務融資成本下降。但涂建明和朱淵媛(2019)從銀行新增信貸規模這一角度出發,發現關鍵審計事項的數量與銀行新增信貸規模顯著負相關,而這一現象在民營企業中更為顯著。
周蘭和桂許健(2020)的研究則是從企業投資效率出發,認為新審計報告可以降低信息不對稱,提供新增信息幫助投資者了解企業,有效改善逆向選擇的問題(Sirois,2014),有助于企業選擇優質投資項目。同時,關鍵審計事項披露一些重大錯報風險較高的事項,給予治理層與投資者一種風險上的預警,對管理層形成了有效的監督,促使其與股東利益趨于一致,也就會選取有利于提升公司價值的項目投資。因此,他們利用選取2017—2018年中國A股市場數據實證檢驗發現,關鍵審計事項的披露顯著提升了企業投資效率,且兩者之間的關系是以會計穩健性為中介機制實現的。
三、述評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由于我國新審計準則于2016年開始執行,其政策效果還有待后續實施過程中觀察。而相關的研究也因為政策執行時間尚短,尚處于發展階段。如對于關鍵審計事項的披露是否具有信息含量問題,國內外研究對此都尚未得到一致的結論。有的研究認為,關鍵審計事項可以降低信息不對稱,提供了新的可信賴信息來源;有的研究則認為,投資者對于關鍵審計事項并沒有特別的反應,因為在此之前投資者已經從盈利公告等獲悉了大部分風險。甚至,關鍵審計事項對于分析師預測質量的影響也有截然不同的結論。因此,新審計準則的政策效應還有待后續觀察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