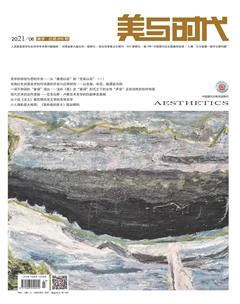“藝術生產”論與當代文藝的產業化
摘? 要:文藝的產業化標志著文藝向工業化、復制化、規模化、標準化的生產方式邁進,并以新的形態大規模地傳播文化產品。馬克思“藝術生產”理論打開了從生產論角度認識藝術的新視域,其對商品、資本、文化等方面的論述顯示藝術生產的社會化、產業化轉向。本雅明和阿多諾圍繞如何看待復制技術對藝術的侵入以及大眾文化問題展開論爭,觸發了對文藝產業化的深層思考。我國當代文藝的產業化發展離不開國內文論界對“藝術生產”的深入研究,同時要處理好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重關系。
關鍵詞:藝術生產;文化工業;文藝的產業化
基金項目:本文系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西方馬克思主義藝術生產論與當代文藝問題研究”(17ZWB003);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文學存在、意識形態與藝術生產”(18FZW056)研究成果。
自從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提出“文化工業”概念以來,藝術參與市場活動的商業邏輯和經濟行為一直受到學界關注和熱議,與之相關的文藝產業變革及產業化形態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對文藝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凸顯文化、科技和產業的有機交融。這一切,顯示馬克思所言的“藝術生產”向經濟、商業的躍入,被納入到工業化、產業化生產的運行之中,成為傳播和消費文化產品的社會經濟行為。本文主要論述“藝術生產”論與當代文藝的產業化問題。這里的“藝術生產”論既包括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藝術生產理論,也包括20世紀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繼承藝術生產論基礎上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其對藝術的商品化、市場化、技術化乃至媒介化的關注凸顯藝術生產作為一門精神創造活動和產業化實踐活動的“顯學”的存在。
一、“藝術生產作為藝術生產”:藝術生產的產業化轉向
將藝術看作特殊的生產形態,進而形成藝術生產理論,是馬克思對文藝理論的重要貢獻。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提出藝術作為生產的特殊形態,同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等生產一樣受社會生產的普遍規律支配[1],這不僅意味著對藝術的考察要以“生產”為基本立足點,而且隱含著對藝術的理解要從其作為精神生產的特殊形式與物質生產的辯證關系中把握。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等著作中,馬克思描述了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關系,強調物質生產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包括藝術生產在內的精神生產以物質生產為基礎,隨著物質生產的改造而改造,貫穿于物質生產的過程。由此,藝術作為精神生產活動與物質生產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這打開了從生產論角度認識藝術的新視域,與馬克思之前的理論家們將對藝術的認識置于社會實踐的彼岸完全不同。
馬克思對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關系的論述顯示了藝術生產的社會化、產業化轉向,這種轉向的主要標志在于“藝術生產”理論的提出。在1857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在物質生產與藝術生產的不平衡關系命題中提出:“當藝術生產一旦作為藝術生產出現,它們就再不能以那種在世界上劃時代的、古典的形式創造出來;因此,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某些有重大意義的藝術形式只有在藝術發展的不發達階段上才是可能的。”[2]理解兩個“藝術生產”的含義有助于深刻認識藝術的本質,前一個“藝術生產”一般指傳統的藝術創作,后一個“藝術生產”指資本主義時期藝術作為商品形態的生產行為。在這個意義上,“藝術生產作為藝術生產”預示著藝術將面向市場,按照工業生產的流程和技術,開始商業化、規模化、社會化的生產活動,實現自身的產業化生產,也標志著藝術走出了“在世界上劃時代的、古典的形式”,被賦予豐富的內涵。“藝術生產”理論對文藝的產業化形成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如果說,在馬克思提出他的‘藝術生產理論的時候,文化還沒有形成為一個產業,馬克思的思想,還只是一種前瞻性的預測,那么,在今天,這種預測,已經以馬克思他們當年所未曾想到過的規模和水平演變成為了活生生的現實。”[3]
藝術生產的產業化轉向還可以從馬克思對“資本”概念的解讀上看出。由于藝術生產與社會物質生產發生著密切關系,對藝術生產的理解,自然離不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在這一視域內,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現象置于資本考察之下,辯證審視資本與社會生產的復雜關系。在《剩余價值理論》中,馬克思區別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認為同一種勞動可以是生產勞動,也可以是非生產勞動,“一個自行賣唱的歌女是非生產勞動者,但是,同一個歌女,被劇院老板雇傭,老板為了賺錢而讓她去唱歌,她就是生產勞動者,因為她生產資本”[4]。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別在于是否同資本發生關系、是否帶來資本的增值,即作家作為雇傭勞動者,能否使著作的書商發財。這種區別顯示資本推動了藝術生產,作為生產性勞動的藝術進入規模化、批量化、產業化生產。由此,馬克思沒有孤立地看待藝術生產現象,而是從商品、資本、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以及審美、文化等多方面剖析藝術生產,顯示產業化的藝術生產方式的形成,為藝術發展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理論范式。
二、機械復制與審美自律:藝術生產的產業化論爭
藝術生產的產業化轉向與近代工業革命相伴隨,尤其是新興科學技術的運用引起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變革,給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各個領域帶來強有力的沖擊。受到技術不斷侵入的藝術活動走出了單純的商品化生產,向工業化、復制化、規模化的生產模式邁進,并以新的形態大規模地傳播文化產品,其生產的潛能得到極大釋放,生產的規模獲得重大提升。技術給藝術生產帶來的一系列變化不能不引起20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關注,尤其隨著30年代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全文刊出,更是助推了研究者們對馬克思藝術生產問題的深入研究。在這一過程中,作為法蘭克福學派成員,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生產”、阿多諾的“文化工業”批判都體現出對機械復制時代藝術生產的關注。當然,圍繞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以及商品拜物教等問題,阿多諾與本雅明在20世紀30年代展開過三次論爭,其中第二次論爭的重點是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問題,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關于對機械復制技術的認識。本雅明和阿多諾雖然都認識到復制技術給傳統藝術帶來巨大變化,但本雅明對機械復制藝術持歡迎態度,以客觀的態度承認之。本雅明認為機械復制技術給電影、新聞、廣播帶來了新的變化。例如傳統口口相傳講故事的藝術雖然行將終結,但本雅明認為不能簡單將其看作“衰敗的癥候”,因為隨著新聞、廣播的興起,“得以在漸漸消亡的東西中看到一種新的美”[5]。電影以精細的分析在視覺與聽覺方面擴大了觀眾對世間事物的注意范圍,加深了觀眾對藝術的統覺能力。與此相反,阿多諾從精英主義立場和審美自律出發,將機械復制藝術視為統治者控制大眾的意識形態工具和文化工業機器。阿多諾認為技術發展使得電影、廣播和雜志制造了一個系統,其審美活動總是對鋼鐵機器的節奏韻律充滿褒揚和贊頌,自身成為文化工業的內容。“電影和廣播不再需要裝扮成藝術了,它們已經變成了公平的交易,為了對它們所精心生產出來的廢品進行評價,真理被轉化成了意識形態。它們把自己稱作是工業”[6]108。在阿多諾看來,技術變成了用于宣傳的工具,使審美陷入極端貧困的狀態,其生產出來的產品源于制造商的意識,根本不是藝術品,而是工業化的商品。
(二)就藝術在社會中的功能形態而言,本雅明指出復制技術雖然貶抑了藝術原作的“此時此地”,粉粹了傳統經典藝術的“靈韻”,使藝術的本真性、儀式性、膜拜性向展示性轉變,但有利于摧毀藝術自主自律的假象,粉碎法西斯的權威意識。“法西斯主義者將首領崇拜強加給民眾,如此來壓榨百姓,正好比施壓于設備器材,強迫實現儀式價值的生產服務。”[7]本雅明重視藝術與政治的關系,從“靈韻”的消亡中看到了復制藝術所蘊藏著的革命潛力,通過藝術政治化抵制法西斯主義“政治運作的美學化”,這無疑突出了藝術的政治救贖功能。阿多諾固然也認為藝術是一種社會現實的精神勞動產品,但“藝術只有具備抵抗社會的力量時才會得以生存。如果藝術拒絕將自己對象化,那么它就成了一種商品”[8]。也就是說,藝術憑藉存在本身與社會保持距離,對社會展開批判。顯然,阿多諾堅守審美自律,對技術摧毀傳統藝術的美和藝術介入社會持批判態度。
(三)關于如何看待大眾文化的興起。本雅明認為技術的發展改變了藝術生產、傳播和接受方式,使得藝術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而是走入到大眾之中,成為被關注和被消費的對象。在《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中,本雅明提出隨著城市生活的發展,“一個文人與他生活的社會之間的同化作用就隨一種時尚發生在街頭。在街頭,他必須使自己準備好應付下一個突然事件,下一句俏皮話或下一個傳聞”[9]。街頭文藝、閑暇文藝、市井閑話、桃色新聞等進入藝術生產者的視野,當然也成為普通民眾娛樂和消遣的對象。這一切預示著當藝術走出神圣性,與商業、商品、消費融于一體,滿足受眾感官消遣需要,文化的工業化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在這個意義上,本雅明所言的技術復制和大眾傳媒帶來的藝術實際上就是大眾文化。與本雅明對大眾文化的態度相比,阿多諾將技術要素視為藝術生產的異化,對大眾文化實施堅定的批判。阿多諾認為通過文化工業的過濾,任何事物都變成了被設計出來的細節,貼上同樣的標簽,包括流行歌曲、電影明星和肥皂劇等在內具有僵化不變的模式。“文化工業的所有要素,卻都是在同樣的機制下,在貼著同樣標簽的行話中生產出來的。”[6]116其結果是民眾陶醉于文化產品的認同及商品拜物教的眩暈之中。
顯然,本雅明和阿多諾對技術與藝術關系的論爭焦點是如何看待復制技術對藝術的侵入以及大眾文化問題。在這方面,本雅明更多著眼于技術本身的政治效力和價值,阿多諾基于文化工業的欺騙性,深入思考的是隱藏在技術背后的社會生產機制和制度。姑且不論他們論爭過程中各自顯露出來的不足,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本雅明對機械復制藝術和大眾文化的思考以及阿多諾對文化工業的批判,都指向了如何看待技術時代文化產業的發展。或者說,他們關于藝術生產的商業化、市場化、工業化、大眾化的論爭觸發了對文藝產業化的深層思考,而“機械復制”“文化工業”“大眾文化”等概念本就是藝術生產產業化的題中應有之義。
三、“藝術生產”論與我國當代文藝產業發展
我國學者對馬克思主義藝術生產論的關注,始于20世紀50年代。到了七、八十年代,隨著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以及理論界出現的馬克思“手稿”熱,藝術生產論再次引起學界的關注。學者們圍繞藝術生產論與藝術反映論、藝術生產論與意識形態論等事關文藝本質的問題展開論爭。90年代以后,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社會經濟重心向消費轉移,藝術生產的商業化、批量化、標準化、市場化及其流通、傳播進入一個高度組織化和規模化的的環境之中,這一切強烈沖擊著傳統的藝術生產模式,也推動著當代文藝的產業化進程。學者們結合市場經濟的發展對藝術的生產、傳播和消費的產業化影響給以合理的解釋,對產業化洪流中的文藝觀念與市場體制變化作出理性的判斷。
文藝的產業化發展離不開物質、技術、生產力、資本等生產要素。進一步說,離不開“生產”這一基本范疇。新時期以來,國內文論界在對“藝術生產”研究過程中,緊扣藝術的“生產”要素,深刻剖析“生產”內涵,科學闡釋藝術生產的本質和功能,為藝術生產的產業化提供理論支撐。何國瑞認為馬克思筆下的“生產”就是“生產者物化”,即藝術家通過他的腦力和體力勞動借助一定的物質載體將他的審美意識對象化,創造出第二自然,表現藝術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10]。這一凝聚和改造表象的生產過程離不開材料、技術、工序,如同物質生產的過程。董學文從建設有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當代形態”的目標出發,提出以“生產”范疇作為邏輯起點,建構文藝學新形態:“從‘生產概念和范疇出發,文藝學將自然地以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這一對概念組合、裂變、演化起,既按著歷史的線索又按著邏輯的線索,產生出二者相統一的一系列文藝科學的范疇群,就可能組織起一個符合歷史規律、符合時代需要的動態、有機、有延伸能力的文藝學理論體系。”[11]在董學文看來,以“生產”為邏輯起點,可以把馬克思主義還原為“經濟學—哲學—文藝學”結構,集中組織起以“藝術生產—藝術作品—藝術消費”為骨架的藝術體系新形態。以“生產活動”作為馬克思主義藝術生產論研究的邏輯起點,其意義在于將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考察置于唯物史觀基礎上,為藝術生產論的中國化提供新的發展范式,也為產業化的藝術生產方式提供理論依據。
當代文藝的產業化發展要處理好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文藝管理體制的改革,我國文藝生產的市場化和規模化迎來繁榮發展的新局面,文藝產業化也成為必然趨勢。“藝術生產者的內心意象,生產的需要和生產的動力及目的不可能憑空產生,它們必然要與消費者(無論是存在的還是假想的)的內心意象、需要和目的相聯系。”[12]面對大眾的藝術消費需求,如何打造更多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的文藝精品,推動文化品牌、文化產業發展,應當成為當前文藝生產者的追求。在這方面,藝術生產兼有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的雙重屬性,與之相關的藝術活動既要獲得商業價值和經濟效益,又要滿足人的精神和審美需要,實現藝術生產的可持續發展。藝術的制作、傳播、消費離不開市場機制和產業化的藝術生產方式運作。產業的基礎是市場,藝術生產的批量化、規模化、標準化要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按照市場發展規律實現。在市場、消費和商業資本的裹挾下,文化產業制作部門在給大眾提供娛樂和消遣的文化產品的同時,更多是遵循商業邏輯,其生產方式在資本驅使下必然受到多種社會因素的制約而呈現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點,即片面追求藝術生產的經濟效益。這勢必將大眾的消費引向低層次的審美趣味以及娛樂消費、奢侈消費,滋生商品拜物教現象,即阿多諾所批判的文化工業。然而,藝術的本質在于其相對獨立的精神價值,即以特殊的精神觀念形態給大眾提供具有審美需求的作品。這就決定了藝術在面對日益增值的經濟效益和產業邏輯的同時,必須考慮審美價值和社會效益,把藝術維系社會的基本價值和理念置于藝術生產的首要位置,使藝術品在滿足市場需求的同時,以高質量內涵促進自身的發展。
當然,這里涉及到如何正確地認識市場對藝術的影響,誠如有學者認為,“市場本身確實是面向大眾的,但不必然是低俗的,也并不必然走向道德主義的消解和享樂主義”[13],其關鍵在于作家本人采用了哪種創作(生產)方式,是否選擇和資本合謀等。也就是說,在承認藝術生產雙重屬性的同時,作家是否恪守文學的精神性和審美性是關鍵。在這方面,文藝批評應積極介入社會實踐,在藝術生產的精神性與實踐性關系中準確引導文藝產業化的發展方向,以“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的文藝精品樹立正確的價值導向,提升藝術生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效益,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
參考文獻:
[1]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中共中央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2.
[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3.
[3]李益蓀.“藝術生產”理論和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馬克思“藝術生產”理論·結語》[J].當代文壇,2007(1):53-55.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冊)[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2.
[5]本雅明.本雅明文選[M].陳永國,馬海良,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294-295.
[6]霍克海默,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哲學斷片[M].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7]本雅明.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論藝術[M].許綺玲,林志明,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100.
[8]阿多諾.美學理論[M].王柯平,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387.
[9]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M].張旭東,魏文生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46.
[10]何國瑞.藝術生產原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53-54.
[11]董學文.文藝學當代形態論——“有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4-5.
[12]陳定家.市場經濟與藝術消費[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6):93-98.
[13]張冰.消費時代文學的生產與危機——兼論馬克思主義藝術生產觀的當代啟示[J].文學評論,2015(6):10-14.
作者簡介:蔣繼華,博士,鹽城工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編輯:豫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