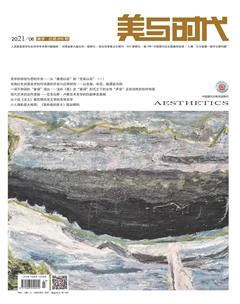《林泉高致》中“時景”的闡釋及啟示
摘? 要:《林泉高致》匯集宋代畫家兼理論家郭熙的思想,由其子郭思編撰而成,是山水畫畫法理論全面豐富的著述。郭熙思想對中國山水畫時間觀和空間觀的確立有重要意義。《林泉高致》明確指出不同客觀物象在不同季節內呈現出不同的狀態風貌。“時景”是《林泉高致》中獨特且重要的思想,是山水畫中重要的表現成分。“時景”一詞可以窺山水畫創作中的時空感,分析郭熙時空感的建構以及運用,了解歷代畫論思想中“時景”的形成發展,分析中國時空感意識的產生的影響,對新時代正確認識和繼承中國山水畫的理論思想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林泉高致;時間觀;空間觀;山水畫;山水畫論
中國山水畫是體現中國藝術家思想與情感的藝術作品,其中蘊含的不僅是中國山川秀麗的俊美景色、悠遠寧靜的意境,更體現物我相忘的哲學情思。中國山水畫創作是景、情、思交織相融的藝術創作活動。繪畫理論是藝術家創作實踐的總結、深化、歸納。繪畫理論也對繪畫創作具有一定的指導與推動作用。《林泉高致》中提出的“山春夏看如此,秋冬看又如此,所謂四時之景不同也”,指不同客觀物象在不同季節內呈現出不同的狀態風貌。本文探索“時景”一詞,一方面指客觀物象四季呈現的不同風貌,一天內朝暮變化而景物有別;另一方面是指由于空間變換而觀察到風貌各異的不同景象,代表時間觀與空間觀的集合。中國山水畫是在特定的二維平面空間內展示無限立體的三維空間。隨著山水畫的發展形成一定的時間、空間表達范式,二者之間的關系緊密不可分割。時空觀的發展對中國山水畫寄托情感、追求意境有著重要作用。“時景”是《林泉高致》中獨特且重要的思想,是山水畫中重要的表現成分,至宋代發展較為成熟,在前代畫論的基礎上進行了更全面細致的闡釋。山水畫中的時空觀一直是學者們研究的對象。或從中西方藝術時空意識比較角度進行,或從中國畫以及山水畫時空意識研究。本文從郭熙山水創作思想精粹中,基于“時景”一詞,以窺山水畫創作中的時空感,分析郭熙時空感的建構以及運用,了解畫論思想中“時景”的形成發展,分析中國時空感意識的產生及意義影響。
一、“時景”在中國畫論中的體現與不同見解
時間的觀念早已在諸多文學家的作品中產生,從朝暮到年月再到四時是中國人對時間認知的逐漸發展。《韻會》中指出:“時,時辰也。十二時也。”這里的“時”是一種計量單位,是古人對一天內晝夜的計數。古人對一天的時間觀念已經較為清晰明確,將其細分為12個不同的時間段。宋代黃庭堅《思親汝州作》中的“五更歸夢二百里,一日思親十二時”,表達對故鄉親人的熱切思念,在夢里回到故鄉,對親人的思念更是一天12個時辰毫不停歇,這里依舊是指一天之內的時間認識。《林泉高致》中的“山朝看如此,暮看又如此,陰睛看又如此,所謂朝暮之變態不同也”,指同樣的山峰景色在一日之內早晚各異、各有其獨特的樣態。這里用“朝暮”來表示一日之內對時間的感知。這幾處的“時”都指日出日落一日之內12個時間段,是小范圍內精確度較高的時間段。同樣,在一年之內,也劃分為不同的時間段,也就是四季。這里的“時”相對于一日之內的“時”范圍較大。《左傳·桓公六年》中有:“謂其三時不害。”這里“三時”是指春夏秋三個農忙季節。四季時間觀念是從“春秋”二季逐漸發展為“春秋冬夏”。許慎《說文解字》中講的“時,四時也”,是指四個不同的季節,具有一定的時間范圍。宋代歐陽修《醉翁亭記》中講:“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歐陽修認為四季的景色各異百態,因而會產生無窮無盡的趣味。《林泉高致》中說:“山春夏看如此,秋冬看又如此,所謂四時之景不同也。”這句話指山的景象在一年不同季節觀看會呈現不同樣貌。歐陽修的“四時之景”與郭熙提出的“四時之景”具有相同的涵義,都明確指出四個季節的時間概念,一年四時的時間觀念已然成熟。故而,“時”的觀念在時間范圍內解釋為一日之時和一年之時。
基于“時”的背景對“時景”的討論,古人也有不同的見解,其涵義大致分為三類。一類是指一年之內不同的時令,季節。顧大成《楚辭九歌解》中有言:“裊裊秋風以下六句,皆間間敘述時景。”綿長不絕的秋風吹起,下面的六句話語,都是在解釋述說秋季的風光景致。此處,時景特指某一個時令與季節。二是指在某一局勢、形勢下的情況。漢代郭憲《漢武洞冥記》中提到“漢武帝未誕之時景”。可以從直觀意義來解讀為在漢武帝還未出生的局勢狀況下,國家處于某一狀況與形勢。同樣的,在唐代詩人鄭谷《蜀中三首》一詩中:“堤月橋燈好時景,漢庭無事不征蠻。”月亮照在堤岸上,亮堂的燈掛滿了橋,這正是別有興致的好形勢,通過月、燈、堤、橋四個景致營造了一種別有意境的氛圍與場合。這里兩處的“時景”都是指一種特定情境范圍的狀況與局勢。三是特指春景,專門由“時景”一詞來指代春景。唐代韋應物的《韋刺史詩集》有一詩中提到“仲春時景好,草木漸舒榮。”這里的時景以及語境專指春季的第二個月里,風光甚好,草木慢慢開始舒展生長,興盛繁茂。詩人元稹一詩《春晚寄楊十二兼呈趙八》中云:“獨此愛時景,曠懷云外心。”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特別喜歡春天這時候的景象,令人心曠神怡、神思飛揚。這兩處對“時景”的運用都是限定在春天這個季節之內。在《林泉高致》一文中,并未明確提出“時景”一詞。在《中國畫論研究》一書中,王世襄將《林泉高致》中論及畫法分為:論畫山畫水、時景、位置、筆墨四項;而在“時景”一項中,又分為:山水云氣、四季畫題、曉晚畫題三類。“時景”部分所涉內容皆為山水云氣之四季曉晚畫法,直觀體現其中的時間觀念,實則亦通過不同時間的變換、不同位置的轉移,才可觀察到全面細致的風貌景致。故本文“時景”探究基于王世襄認為的“時景”內容,但不僅限于此,還要探究《林泉高致》在山水畫中對不同景物的畫法所構建的時間觀及空間觀。
在郭熙之前的山水畫家的繪畫理論中,就有多位畫論家對“時景”進行探討。如梁元帝、王維、以及與郭熙同時代的韓拙的繪畫理論中,王世襄認為皆涉及“時景”之內容,其內容有詳有略。梁元帝有《山水松石格》一篇,“時景”內容為“秋毛冬骨,夏蔭春英,炎緋寒碧,暖日涼星”“霧破山明,云墜而霧清”。這部分內容所描述的為四季氣候不同而呈現的不同景色,四季各有其特點,所述內容是整體大觀的方式,并無更加細致的闡釋。在王維《山水論》中說道:“凡畫山水,須按四時。”文中講明了描繪山水之景,應當遵守不同的時令產生的變化。文中還說明了早景、晚景時的景象、氣霧、日月、江帆的不同姿態,山水、煙霧、云氣因不同的時節,各呈現出不同特色,如春景則是水如藍染,夏景綠水無波,秋景鴻雁秋水,冬景則水淺沙平。值得注意的是,文中也暗示了部分因為所觀視角不同,各個景物產生不同的現象。春景則霧鎖煙籠、夏景則古木蔽天,這不僅體現因時間不同而景象不同,也體現出:春季之時,煙霧溟,二者相互交織纏繞,樹木崇山蒼穹被遮擋隱蔽,當距離此景有較為遙遠的距離時,才可觀察到幾種物象之間的關系與真實樣貌;而夏季卻古木蔽天,樹木枝繁葉茂,只有當站于古木高樹之下或是茂密繁林之處,才會產生天空被遮蔽的景象。這里只是較為簡單地體現山水畫中的空間觀,并未能全面而具體地闡釋山水畫中的時空觀。王維另一篇山水畫論《山水訣》中,據王世襄時景分類僅為“閑云切忌芝草樣”,內容較為簡略,故并不認為是主要的探討對象。在文中王維卻提到“或咫尺之圖,寫千里之景。東西南北,宛爾目前;春夏秋冬,生于筆下”,不僅明確提到了春夏秋冬四時,也開始出現東南西北四個方向方位詞語。東南西北四方觀念也是由東西兩方觀念逐漸發展而來。此篇中并未涉及具體的方位景物之象,但這一語句的出現,說明畫家在山水畫中已然意識到空間方位與時間季節會同時出現;也開始認識到將地大物博的奇秀美景繪于方寸紙面,這是將三維空間思想體現在二維平面,不僅是藝術家對自然山水的切身感悟與規律總結,更是藝術家空間感的表現。到了宋代韓拙的《山水純全集》中提出了“四時之氣”“四時之象”,主要意思則為春云、夏云、秋云、冬云四季不同的云氣在雨停晴天和陰天朦朧兩種氣候下的不同呈現,特點各異。這里雖較之前更加細致地將天氣分為陰晴兩類,詳說云氣的形態,但并未體現山川景物布置的空間觀。
二、《林泉高致》中不同“時景”之闡釋
《林泉高致》相對于前代山水畫論,“時景”論述勝于前代。文中所論山、水、煙嵐云氣等,皆闡發詳盡。山之“時景”闡釋最為詳盡,水及煙嵐云氣次之。
(一)山之“時景”闡釋
《林泉高致》第二篇《山水訓》中首先指出,“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須遠而觀之”。首先說明了畫家看山時的視角,人與山相距較遠時,才能一覽山的全貌與氣勢,這里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物理空間關系已經表明明顯。后又說山水創作須建立“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之處。這里的山層巒疊嶂,縱橫交錯,以一種不斷移動的視點,把多個角度觀察到的不同的景象匯聚于同一幅畫面之中。這里所說并不是僅僅聚焦于某一視點和時間點,而是將眼睛所觀客體與大腦所想象客體融合所共同建構的山水空間,并非真正客觀物象的真實寫照,是一種主體尋求心靈神游、精神寄托的心理空間。在宗炳《畫山水序》中,也提出了主體根據客體物象而創立的心理空間。“萬物融其神思”“暢神而已”都指明了將藝術家的情思與想象寄托在萬物中,期望畫中之物能獲得精神的愉悅,達到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狀態。其次文中體現了不同客體之間的關系,闡明了各個物象之間的空間及層次關系。“山之人物以標道路……山之溪谷斷續以分淺深”,說明山與人物、山與樓閣、山與林木、山與溪谷之間的關系。用人物來標識山中的道路,人物處于山間,表現其道路;用樓閣標識山中的美景圣地,樓閣居于山間顯其意義;用樹木相互遮擋或顯露區分其遠近關系,以溪流在山谷時斷時續區分溪水深淺空間。物與物之間相互依存、相互證明,建立了更加精確細致的客觀空間。“大山堂堂為眾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岡阜林壑”“長松亭亭為眾木之表,所以分布以次藤蘿草木”,在描繪眾山與眾木的時候,并不是依據自然之象的形體相似相近,而是取一山或一木為主,將眾多山與木以合理的比例分布于畫面之上。文中還說明了若是山沒有煙云、水流、林木,就缺乏秀麗、潤媚、活力、生機。重視物與物之間的組合分布關系,才能塑造一個嫻靜幽遠的空間。
后文還更加詳細地闡述了山本體的空間關系:“山有高下”“山有三遠”“山有三大”。山有高有低,高山壯闊厚實,淺山則粗大笨重。正是多種山峰形態不同,氣質各異,才形成對比令人遠望而有深邃幽遠之感。山有“三遠”:高遠、深遠、平遠。基于形態各異的山峰營造的空間,通過對山的仰視、遠視、俯視三種不同的觀察方法,從而產生高遠、深遠、平遠的空間意境。“山大于木,木大于人,山不數十重”,這句依舊是通過山與其他物象的對比營造空間,也說明只有山峰的本身對比,空間較為單調且無生機活力。山不僅通過與多種山峰建構寬闊空間,也通過與山之外其余物象建構小范圍、區域性的空間,多種物象相互依存、互為參照,共同構成山水畫客觀物象空間。“山近看如此,遠數里看又如此”,每次隨著觀看不斷遠近交替、角度變換,看到山不一樣的面貌,謂之“山形步步移”“山形面面看”。利用移動的視角,即“全景式”,使得時間的流逝與空間的延伸相互融合統一。郭熙全文大篇幅敘述山之“時景”,一是建構了主客體的物理空間,二是建構主客體的心理空間,三是建構客體之間的空間。山水畫是畫家依據自然景象與主觀情思相結合創作而得,在山水畫空間中,主體與客體創造的空間起主導作用,客體之間的小區域空間在主客空間的統籌下共同構成了山水畫的空間。幾種空間意識既是各自獨立的,又是相互交織纏繞的。建構的山水空間是運動的、相互依存的,亦是相互統一的。
山的“時景”解析不僅是空間的創造,亦包括隨時間變化山呈現出的風姿百態。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時間觀念與空間觀念聯系緊密,試圖將二者抽離,卻難以完全區分。時間觀在空間觀變換的基礎上,令山之“時景”更為全面豐富。郭熙謂:“春山煙云連綿人欣欣……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春天的山煙云纏綿,夏天的山樹木繁密,秋天的山明朗潔凈,冬天的山陰郁昏暗,因為時節氣候的變換,山呈現出四種不同的氣質。而觀看出山這四種不同的氣質,也暗示了居于不同的空間位置,才可意識到山的不同面貌。春山與冬山需要站于遠處,才可觀其煙云連綿與昏霾翳塞的整體態勢;而嘉木繁陰與明凈搖落須處于山之林木之間,才可感其樹木茂盛而產生的綠蔭,葉落空枝的清凈利爽。文中最為精彩概括的則是春夏秋冬看山有“四時之景”,朝暮陰晴看山亦有“朝暮之變”。基于在山中不斷移動的視點變化,隨著四季氣候朝暮陰晴的變化,對山的面貌認知得更加明確清晰。
(二)煙嵐云氣之“時景”闡釋
郭熙對煙嵐云氣之“時景”認識也較為精彩。“真山水之云氣”“真山水之煙嵐”“真山水之風雨”皆四時不同。郭熙強調在描繪這些物象時,要立足于宏觀的整體氣象,抓住整體意趣,居于遠處,隨著時間的流動觀望才可令煙嵐云氣靈活,景象才能不偏倚,把握其錯綜復雜、起始止息的形式。既有“雨有欲雨,雪有欲雪”,又有早春斜風細雨,夏季飄風急雨,秋日西風驟雨,冬天密雪霾雪,不同季節之中晦明風雨各時景物皆有分別。處于山谷、山澗、林中、隴下、山家、漁舍、艤舟觀雨觀雪,近看遠眺則會有不同意境與情趣。而在一天之內的曉晚,更會因天氣的轉變而景物有別。“晚”分別有春山、雨過、雪殘、疏林、平川、遠水六種不同景致的晚景。畫家用眼觀看、用心體會,將流動的時間與移動的空間相融合,創造了各種豐富別致的“時景”。通過時間在空間中的流動,空間在時間中的延伸,創造出一種心向往之、漫游翱翔的山水世界。郭熙《林泉高致》中對山煙嵐云氣等物象的“全景式”的“時景”描繪,體現了山水畫創作中對時空意識的認知和運用,這種時空觀的產生,在經歷了長時間的發展之后,形成了動態的、相互依存、相互統一的時空關系。
三、“時景”的意義及影響
中國先哲認為,宇宙是原始混沌的,時空是宇宙,宇宙是一個有機整體,天、地、人是合一的。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響,當主體感受客體自然萬物,浩瀚宇宙的精神時,將人融合于宇宙萬物,主客交融,以生命感悟生命,并不限于對客觀事物的描摹。山水畫在表達萬物精神的同時,也是對人精神的表達。人們這種觀念對中國山水畫時空觀的認識產生了較大影響。人們寄情于山水畫之中,為了尋找永恒的時空感,尋找永恒的山水精神。
山水畫在宋代之前,畫面時空表現形式與宋代的有較大差異。早期人類處理時空的方式是“排列式”,認為畫面就是平面的,僅是用一些代表性的景物通過上下、左右依次排列組合,用重復連續的方式來構成畫面的空間,這時時間與空間是混沌一體的。陶器上繪制的圖案較為抽象,陶器是圓形的,上面的圖案既無起點又無終點,追求周而復始的時空感,這也涉及早期人類的時空觀。這些方式不僅體現在原始時期,至漢朝畫像石依舊用此方式表現時空意識。
到了魏晉時期,開始出現“重疊式”的表現方法。阿恩海姆認為:“運用重疊來建立空間,很早以前就是中國風景畫所特有的一種手法。”顧愷之的《洛神賦圖》畫面中通過樹木草叢相互掩映來體現樹木的前后空間關系。圖中通過長卷從右至左的形式,敘述了曹植拜見洛神到洛神離去的故事,這時空間與時間已經相互縱橫交錯、關聯統一。唐代李昭道的《明皇幸蜀圖》已經是較為成熟的山水畫。山石、樹木、云氣等更多的物象進入了畫面之中,依舊是采取物象之間重疊的方式,體現畫面中山水的空間感,并未直接展示四季朝暮等較為準確的時間觀念。
郭熙的山水時空觀較前人不同的是全景式的動態空間觀念,更加細致明確四季朝暮的時間觀念,指出各物象不同的形態風貌,通過動態的觀察方法與流逝的時間來組織真實與理想的景物,再置于二維平面中。依舊采用前人的“天人合一”的方式去感知、認知時空觀,而創作者目難所及之處,則是利用思想散發的無限空間與主客觀時空結合,構造畫面中的山水世界。這時,宋代許多山水畫已經體現出這種移動的時空觀念,描繪現實與理想結合的風景。如郭熙《早春圖》、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范寬《雪景寒林圖》等多位畫家已經應用移動的視點方法,將時間與空間融合、客觀與想象融合,統一交融在畫面整體之中。
郭熙所論及的各景象之“時景”對山水時空的認知影響后世山水畫,創造的山水世界代表人與自然和諧統一融合的境界,也對后世具有啟發指導意義。山水時空的創作者也應重視表現各景物的生命氣質與人的精神氣韻,如王陽明所說的“天下無心外之物”。人與天地共生,人具有自我思想,以感悟感知的心理神游于天地之間,用心體會萬物精神和生命情趣,表現主觀思想和對客觀物象的神韻,達到物我合一的境界。黃公望在創作時,經常去自然中寫生感悟,《富春山居圖》利用全景式描繪出不同的山川景物,讓視點不斷游走、移動,觀看的方式自由無拘。同時還與個人的感受交融,讓心靈悠然游走于山水之間,實現主客體交融,神與物游。元明清山水畫成為了中國繪畫的主流,郭熙“時景”的時空觀,讓山水畫家將虛靜的精神寄托于山水畫中,在動態關聯統一的時空中盡興游走,空間與時間相互轉換,無拘無束的心靈與宇宙合二為一。這一時空觀,并無具體的聚焦點,而是注重內心的觀照與體驗,創作者將景、情、思結合,圍繞自己內心邏輯構建的時空觀繪于紙上,暢游其中。
《林泉高致》中郭熙的時空觀對中國山水畫具有深遠影響。“時景”不僅是對物象時間空間的指涉,更是主體與客觀物體的時空體現。對郭熙思想深入研究,確立中國山水畫的傳統時空觀,對當代山水畫創作有一定的借鑒與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阿恩海姆.藝術與視知覺[M].滕守堯,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2]王世襄.王世襄集:中國畫論研究[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3]周積寅.中國畫論輯要[M].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5.
[4]郭熙,郭思.林泉高致[M].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0.
[5]巫鴻.中國繪畫中的“女性空間”[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
[6]劉文英.中國古代的時空觀念[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
[7]馮民生.中西傳統繪畫空間表現比較研究[D].南京:南京藝術學院,2006.
[8]邱永培.山水畫空間論[D].蕪湖:安徽師范大學,2006.
[9]程明震,陳繪.中西藝術時空意識之比較[J].大連大學學報,2006(5):67-73.
[10]洪潮.四時之景 朝暮之變——淺析中國山水畫中的時間表達[J].美術觀察,2014(7):78-81.
[11]劉成紀.中國美學與傳統國家地理[J].社會科學戰線,2020(1):140-158+281-282.
作者簡介:張穎,北京語言大學藝術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