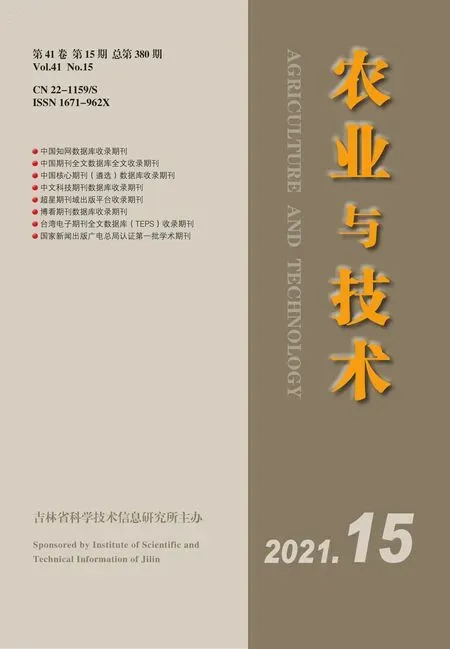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政策工具研究
——基于2012—2020年605份政策文本的分析
甘黎黎帥清華
(1.華東交通大學人文社科學院,江西 南昌 330013;2.南昌航空大學文法學院,江西 南昌 330063)
十九大報告指出,農業面源污染屬于需著力解決的突出環境問題。多年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農業面源污染治理,但仍持續強調加大治理力度(2019、2020中央一號文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治理的政策工具有待完善。選擇合適的政策工具,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1],有利于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效果的提升,有利于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有利于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
1 文獻簡述
國外農業面源污染發生較早,20世紀60年代美國和歐洲少數發達國家開始重視此現象。20世紀80年代,關于農業面源污染的研究由學術邊緣向學術中心轉化。早期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政策工具屬于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1]。但是,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的實施效果并不理想[2]。Shortle J S等學者則發現,采用經濟激勵型政策工具更有利于治理農業面源污染[3]。Segerson認為,環境稅可以治理農業面源污染問題[4]。Xepapadeas沿著此思路提出,集體罰款和隨機罰款這2種非常有名的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政策工具[5]。邁阿密產權交易項目也為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不久,生態補償成為了較新的經濟激勵型政策工具。當然,始于20世紀90年代的自愿型政策工具也展現出了獨特的魅力。3類政策工具的結合才是農業面源污染治理取得良好效果的關鍵[6]。
國內對農業面源污染的關注與國外轉為系統研究的時間基本同步,但多從政策、技術與工程層面上進行分析,如楊金田等、周健、林昭遠等、張維理等、朱兆良等、魏欣等。直到2005年,才有學者從政策工具角度觀察該問題,且成果相對較少。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4個方面。對某類或某種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工具進行研究。側重某類政策工具的研究,如韋寧衛專門探討了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財稅政策工具選擇[9];側重某種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工具的研究,如杜娟則對農業面源污染控制的生態補償機制進行了研究[11];就某種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政策工具進行較深入的分析,如李冉等較深入的分析了畜禽養殖污染防治的政策工具[12],鄭云虹等則基于政府補貼研究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機理[14]。對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工具的影響因素進行了較多研究。如韓洪云等以陜西眉縣為例,對農戶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政策接受意愿進行了實證分析[15];欒若芳等基于農戶受償意愿研究了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生態補償的影響因素[17]。對發達國家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政策工具進行了一些總結和借鑒。如余耀軍等研究了美國面源污染治理措施[19]。對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工具的改進進行了初步探討。如胡中華論述了農業面源污染規制的失靈及其矯正[21];羅倩文和姜松專門研究了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環境保護稅政策改進[22]。
綜合而言,國外相關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相關理論和模型值得反思和借鑒;而國內學者在相關領域也取得了較大進展,縮小了與國外研究的差距。但是,國內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工具的內涵、作用、分類、評估標準等有待進一步明晰,現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經濟激勵型政策工具,缺乏對3類政策工具全面、整體、系統的考察。
2 政策工具的分類和樣本選擇
2.1 政策工具的分類
鑒于立場、偏好、面對問題等存在差異,研究者對于政策工具分類所采取的標準有別,由此而導致政策工具類型繁多。在分類時,分類的標準應屬于共識,易于被大眾接受,同時也應充分考慮政策工具的自身特征及適用性。按資源分類。將政策工具分為權威性政策工具、財政性政策工具、信息型政策工具、組織性政策工具。按選擇分類。選擇意味著政府可以選擇干預,也可以不選擇干預;可以選擇由誰干預,如可以自己親自做,也可以交由市場或社會做。因此,可將市場性政策工具和社會性政策工具納入政策工具的范圍。再將上述根據資源分類的政策工具進行調整,確定本研究的一級政策工具分類:規制性政策工具、市場性政策工具和社會性政策工具。以制度為標準來分類。按制度安排,確定大類政策工具下的次級政策工具。
2.2 樣本選擇
2.2.1 樣本選擇需遵循的要求
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政策文本是指全國人大及常委會、國務院或部門制定的與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相關的各種法規性文件的總稱。文本屬性要求,即其屬于規則性文件,如法律、法規、條例、規劃、決定、辦法、意見等。文本相關性要求,即所選擇的文本必須是與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相關的政策。
2.2.2 政策文本初次檢索
在經過對政府官網、北大法寶等文獻資料的檢索,初步確定2012—2020年相關政策文本605份。
2.2.3 政策文本的編碼與檢驗
確定政策工具的區分要素;針對所選擇的605份文本,由2組成員進行信息抽取與獨立編碼;進行信效度檢驗。進行回溯檢索,保證效度;從現有文本中隨機抽取100份政策文本,對2組成員的文本信息進行對比檢驗,本研究的編碼結果信度值為0.83,編碼結果可信。
3 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政策工具分析
經樣本選擇和提取,605份政策文本中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政策工具共計34種。34種政策工具使用次數總計是12874次,每一個政策文本中政策工具的平均頻數大約是21.28次,這一數值表明政府在制定或執行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政策時的政策工具數偏少。
3.1 規制性政策工具占據絕對的核心地位,使用過多
規制性政策工具使用次數占政策工具使用總頻次的76%,占據優勢地位。從現有政策文本來看,在農業面源污染治理中,政府仍起主導作用;規制性政策工具普遍具有操作性強、容易管理、適宜復雜情況等優勢,是政府最為偏好的政策工具;規制性政策工具內部的諸多具體工具,能對政策執行主體行為進行框定、強化與糾偏。如環境標準、申報許可、環境影響評價能框定政策執行主體朝著既定目標運行,環境考核評價和監督檢查能將政府官員的偏離行為重新拉回到合法軌道中來,實現政策糾偏。
規制性政策工具內部則呈現使用不均衡特點。從圖1可知,環境監督檢查的使用次數占規制性政策工具使用次數的22.95%;環境行政處罰的使用次數占規制性政策工具使用次數的13.21%;申報許可的使用次數占規制性政策工具使用次數的12.60%;環境考核評價的使用次數占規制性政策工具使用次數的11.45%;環境資源規劃的使用次數占規制性政策工具使用次數的9.84%;上述使用次數排名前5的政策工具共占規制性政策工具使用次數的70.05%。
3.2 市場性政策工具
市場性政策工具使用次數占政策工具使用總頻次的5%,使用次數非常少。市場性工具具有節省成本,能提高跨期效率,在水、空氣、固體廢物、有毒有害物質等污染物治理中使用較多的優勢,但市場性政策工具在復雜情況下,由于技術或生態的復雜性,使其處于不利地位。因此,盡管市場性政策工具的使用在增加,但其使用次數占比非常少。
在市場性政策工具內部也呈現使用不均衡特點。從圖2可知,環境稅收的使用次數占市場性政策工具使用的35.18%;環境補貼的使用次數占市場性政策工具使用的21.66%;用者付費的使用次數占市場性政策工具使用的13.19%。排名前3政策工具的使用占市場性政策工具使用的70.03%。
3.3 社會性政策工具
社會性政策工具的使用占比19%,使用較少。社會性政策工具主要依賴社會自愿,適用于最接近最終消費者的可見性污染物和產品銷售受環境聲譽影響較大的企業,適用于復雜情況,因此,社會性政策工具的使用空間非常廣。但是社會性政策工具必須以信息提供和責任立法為必要的先決條件,因此其使用又會受限。
在市場性政策工具內部也呈現使用不均衡特點。從圖3可知,環境監測的使用次數占社會性政策工具使用的38.78%;環境聽證的使用次數占社會性政策工具使用的12.59%;環境信息公開的使用次數占社會性政策工具使用的11.82%;獎勵號召的使用次數占社會性政策工具使用的6.70%;清潔生產的使用次數占社會性政策工具使用的6.50%。排名前5政策工具的使用占社會性政策工具使用的76.31%。“自上而下”信息傳遞的信息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占社會性政策工具使用的87.53%,“自下而上”的公眾參與占12.47%。這說明在我國農業面源污染治理中,政府特別重視信息型政策工具并公開相關環境信息,以引起全社會的關注,激發社會全員積極參與農業面源污染防治;同時,政府也特別偏好宣傳教育、獎勵號召等“自上而下”的社會性政策工具。而從“自下而上”途徑看,公眾參與農村環境污染治理的積極性正逐漸提高,但增速不快,有待加強。
4 優化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工具的建議
4.1 改進已有政策工具與創新政策工具并舉,發揮單兵效應
4.1.1 改進已有的政策工具
需要對已有的政策工具加以修正、調試與優化。由于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我國仍處于改革的轉型時期,對規制性政策工具的偏好短期內不會發生重大的轉移,這就需要進一步完善現有的規制性政策工具,規避其不足,形成一系列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規制性政策工具。鑒于市場性政策工具有不能替代的作用,但在農村環境污染治理中應用較少,需要加強該類政策工具的改進與積極應用。不斷完善信息型政策工具和公眾參與。
4.1.2 創新政策工具
隨著人們對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不斷深入,以及政策工具理論研究與實踐應用的創新發展,治理農業面源污染的新政策工具將不斷涌現。可嘗試的新政策工具包括,在轉變現有預算為生態預算中,專門開展農村生態環境預算;創建內部市場,即在市場可以充分發揮配置資源的領域可以考慮建立內部市場,將提供農業面源污染治理公共物品和服務的政府部門人為地劃分為買賣雙方,形成內部市場;建立將環境信用評價的范圍拓展到農民個人,與農民個人征信掛鉤,增強農民參與環境保護的意識與行動;建立健全農村環境大數據,對農村環境點源和面源排放、環境質量、環境風險、環境安全等進行技術上的識別、評估、預測預警。
4.2 科學配置和整合3類政策工具,發揮整體效應
單一政策工具在解決農業面源污染問題時力有不逮,而現實農業面源污染問題涉及不同利益相關者,只有形成良好的政策工具組合才能填補單個政策工具的缺陷。
應調整3類政策工具的比重,科學配置與整合,發揮不同政策工具之間的協同效應,實現協同增效的目的。應適當減少禁止等規制性政策工具的使用頻率,要更多地使用許可、環境資源規劃、環境影響評價、分區保護等政策工具在農業面源污染治理中的優勢,同時完善更加剛性的環境目標責任、環境監督檢查、環境標準、環境行政處罰、生態保護紅線等政策工具以保證政策的良好實施。漸進式的增加市場性政策工具的使用頻次,使環境稅收、產權交易、生態補償、綠色金融等政策工具有更廣闊的發揮空間。平穩增加社會性政策工具的使用頻次,平衡“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政策工具的比率,既要發揮信息型政策工具的作用,也要讓更多的公眾參與農業面源污染治理。
要形成政府、市場和社會多元共治的格局,推動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效果的進一步提升,最終實現農村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