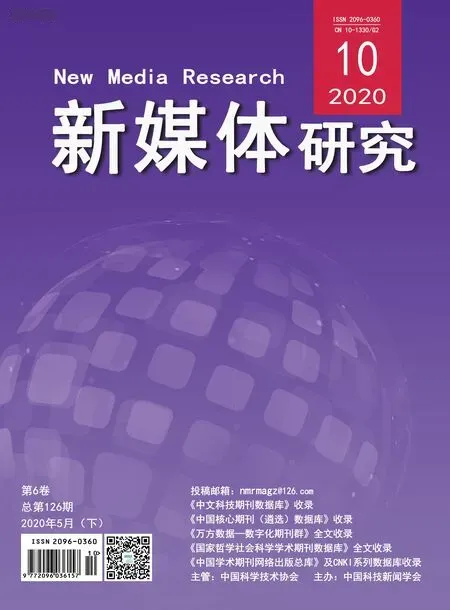選秀狂歡對文化工業的反抗與顛覆
劉洋佳迪
摘 要 “創造營”系列選秀是當今最熱門的選秀節目之一。在發展的過程中,節目內容與制作模式卻被認為出現了文化工業理論所批判的標準化、同質化、商業化等特征,觀眾則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被動地位,成為了被文化工業操縱的對象。文章通過分析“創造營”系列選秀中顛覆性的王菊現象和利路修現象,認為受眾具備一定的能動性,可以通過網絡狂歡顛覆文化工業的規則,并對當代社會文化產生影響。
關鍵詞 文化工業;狂歡理論;“創造營”系列選秀;反抗與顛覆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21)10-0087-05
1 問題的提出
自2005年《超級女聲》開播以來,我國的偶像產業開始繁榮發展。在2018年,隨著《偶像練習生》與《創造101》兩檔選秀綜藝的播出,全民選秀再次開始在娛樂圈進行,2018年也因此被冠以“偶像元年”的稱號。此后,各類選秀節目不斷發展,其中“創造營”系列選秀在同類型節目中脫穎而出,成為當下最熱門的選秀節目之一。“創造營”系列節目以騰訊視頻為播放平臺,先后舉辦了四場選秀節目:《創造101》《創造營2019》《創造營2020》《創造營2021》,并成功打造出了火箭少女101,R1SE男團、硬糖少女303三個偶像團隊。數據顯示,這四場選秀的累計收視量分別為55.82億、41.45億、84.26億、51.34億①。由此可見,“創造營”系列選秀獲得了巨大關注,吸引了許多觀眾的參與。
然而,隨著節目運作走向成熟與我國偶像產業持續發展,很多問題如節目同質化、選拔標準單一化等逐漸出現,節目對受眾的隱性操縱也不斷增強,呈現出許多法蘭克福學派在文化工業理論所批判的現象。但與此同時,打破日益固定的偶像工業體系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如《創造101》中憑借獨立女性形象脫穎而出的王菊和《創造營2021》中因顛覆傳統偶像形象而被關注的利路修。兩次現象吸引了大量粉絲與觀眾的圍觀參與,形成了大規模的網絡狂歡,并以此方式向偶像工業中的固有標準發起了挑戰。基于上述現象,本文通過梳理“創造營”系列選秀的發展,將主要回答以下問題:1)選秀節目中是否存在著對受眾的收編?又是以何種方式實現了這種操縱?2)網絡狂歡是否能成為體現受眾能動性、抵抗偶像文業控制的有效手段?
2 文化工業:控制節目與收編受眾的幕后操手
2.1 研究理論
文化工業理論由阿多諾與霍克海默在《啟蒙辯證法》中提出,將批判矛頭直指資本主義控制下的大眾文化。該理論認為,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的經濟利益與意識形態,大眾文化呈現出標準化、同質化和商業化的特點,淪為了批量生產的產物。文化的交換價值取代了藝術價值,成為了被買賣的工業制品。更為嚴重的是,它通過娛樂實現了對受眾的控制,牢牢占據了人們的空閑時間,讓人逐漸失去獨立思考能力。在文化工業的操縱下,人們沉迷在娛樂中,最終失去了反抗的動機與能力。就算“即使有時候公眾偶爾會反抗快樂工業,這種反抗也是軟弱無力的,因為快樂工業早就算計好了”[ 1 ]。由此一來,藝術的崇高價值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標準化、同質化的文化商品,人們沉迷在娛樂所提供的快樂中,喪失了抵抗的意識,順應了文化工業的控制,成為了完全被動的受眾。
2.2 同質化與商品化:“創造營”系列節目中的文化工業現象
在“創造營”系列的選秀節目中,存在著許多上述理論所提出的問題,偶像工業在實質上成為了文化工業在選秀語境下的衍生物。“創造營”系列選秀改編于韓國的《produce101》節目,自2018年《創造101》播出以來,節目的制作模式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轉變,沿襲了選拔練習生—號召觀眾為之投票—組合成偶像團體出道的制作模式。這種制作模式所選拔出來的偶像團體多為符合“白幼瘦”標準的少女和“小鮮肉”,表現出單一化、同質化的特征,失去了個性化的特點。這一套制作模式現已不斷走向成熟,有助于降低運營風險,并在短時間內獲取經濟效益,而對于這些偶像團體而言,由于其同質化的特征,大多成為了偶像工業流水線上的商品,面臨著快速更新迭代的風險[2]。數據顯示,無論是火箭少女101、R1SE男團還是去年出道的硬糖少女303,其關注度在節目結束后便呈現出下降趨勢,且再也沒有超過總決賽當晚的熱度②。因此,節目的商業價值取代了藝術價值,選拔出的偶像團體成為了流水線上批量生產的商品,成為了文化工業的產物。
2.3 沉迷娛樂與被動消費:選秀節目控制受眾的有效手段
在受眾層面,雖然節目反復強調粉絲的重要性,并以“創始人”稱呼為選手投票的粉絲,但在本質上,粉絲成為了被娛樂節目隱蔽操縱的對象,被無意識地裹挾在以資本為導向選秀節目中。達拉斯·斯麥茲在《傳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中曾提出過“受眾商品論”,認為對于受眾而言,節目所提供的信息、娛樂乃至教育內容是用于吸引人的“免費的午餐”,其根本目的是為了培養他們對于廣告信息的關注度,進而誘使人們購買商品。簡而言之,受眾被媒體當作商品賣給了廣告商[ 3 ]。同樣的邏輯在“創造營”系列選秀中,依然可以得到驗證。節目開播四年來,每一年都會與廣告商進行合作。粉絲購買廣告商提供的商品后,則可以比普通用戶獲得更多的投票機會。為了能讓偶像獲得出道機會,許多粉絲不得不大量購買廣告商品,甚至聯合進行集資。根據現有數據,在《創造營2021》中,最高集資經費已經超過1 000萬③。《創造營2019》決賽播出之時,甚至出現了學生粉絲貸款為偶像集資的現象④。可見在一定程度上,選秀節目本身成為了誘餌式的“免費的午餐”,最終目的是通過將粉絲賣給廣告商攫取商業利益。表面上粉絲贏得了決定選秀結果的權力,但這種權力在本質上是一種“偽能動性”,實際上維護了偶像工業以資本為導向的運營模式。回到文化工業理論的視角,粉絲沉迷在轟轟烈烈的造星活動中,失去了思考與抗爭能力,順應了資本邏輯,淪為了被動的受眾。
3 網絡狂歡:粉絲反抗文化工業的途徑
如上文所述,“創造營”系列中的偶像工業體系不斷走向完備,在本質上是文化工業在選秀語境中的具體表現,節目單一化、同質化、商品化的特征愈發明顯,同時以被動消費和娛樂的方式對受眾進行控制。但縱觀“創造營”系列選秀的發展歷程,顛覆性現象也偶有發生,并打破了偶像同質化的僵局、挑戰了資本邏輯。其中討論度最高、顛覆性最強的選手當屬《創造101》中的王菊和《創造營2021》中的利路修。兩次現象看似出發點不同,實際上則皆以網絡大狂歡的形式,打破了偶像工業中的陳規與標準。因此,本文認為,文化工業控制與操縱雖然強大,但不是絕對的,受眾并非完全喪失了主動性與思考能力,而是可以借助狂歡的力量反抗文化工業的同質化標準、挑戰其中的資本邏輯。
3.1 狂歡:顛覆規則的有力武器
“狂歡”為前蘇聯學者巴赫金提出的重要概念。狹義的狂歡是指中世紀的一個傳統節日,但在巴赫金的理論中,其內涵得到了極大的豐富與延展。狂歡具有全民性、平等性、儀式性和顛覆性的特征[ 4 ]。狂歡節的核心是合二為一的加冕與脫冕儀式,加冕的對象不再是國王,而是與國王有著天壤之別的小丑或奴隸,以此方式來貶低權威。而脫冕意味著另一次加冕,在脫冕時,人們不僅要剝下加冕者身上的華服,還要對他進行譏諷與毆打。該儀式說明了一切權勢都具有“令人發笑的相對性”,同時蘊含著“交替和變更的精神,死亡與新生的精神”,即萬事萬物不是一成不變的[5]。如巴赫金所言,中世紀的人們過著兩種生活,一種是常規的、等級制度森嚴的生活,一種是狂歡式的生活,這種狂歡式的生活以對抗的方式將人們從規則中暫時解放出來,解構了官方權威與意識形態[6]。而本文認為,放眼大眾文化領域,由觀眾構成的網絡狂歡能憑借其顛覆性沖擊文化工業的同質化和商業化,體現受眾的抗爭性與能動性。
3.2 王菊現象:同質化偶像審美標準的挑戰
王菊是2018年《創造101》最飽受爭議的選手之一。在節目初期,她因為皮膚黝黑、身材微胖被認為不符合傳統的女團形象,并因此遭到嘲笑。擁有數十萬粉絲的微博博主“老雞燈兒”在王菊的照片上配文“地獄空蕩蕩,王菊在土創”,將其制作成表情包全網傳播。但隨著節目的播出,王菊現象發生了反轉。在2018年5月26日的節目中,王菊公開表示對獨立的追求。當被問及是否想回到過去符合“白幼瘦”審美的狀態時,王菊表示:“不想回去。因為其實當時,你不知道自己心里美的標準是什么。自從我做模特經紀以來,做自己就是我自己的信條。精神獨立,然后經濟獨立,對一個女性來說,我覺得太重要了。”在節目的拉票環節中,王菊對觀眾坦言道:“有人說我這樣子的不適合做女團,可是做女團的標準是什么,在我這里標準和包袱都已經被我吃掉了,而你們手里握著的是重新定義中國第一女團的權力。”至此,王菊的口碑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其獨立自主、不屈服于主流審美的精神引發了廣泛贊同。同年5月30日,王菊的百度指數突破12萬,遠超節目其他選手,引起了現象級的關注。
在王菊現象持續發酵、最后形成全民性網絡大狂歡的過程中,由粉絲創造的王菊的表情包等發揮了重要作用。針對此類二次加工改造的現象,學者詹金斯曾用“文本盜獵”加以解釋。“盜獵”一詞源于米歇爾·德賽都,用于“將作者和讀者之間的關系描述為持久的對文本的所有權、對意義闡釋控制權的爭奪關系”[ 7 ]。詹金斯將此概念用于大眾文化領域,認為粉絲可以用重讀、加工等方式對原有內容進行“盜獵”,進而構成“參與性文化”。在王菊現象中,第一次盜獵源于其表情包。無論是前期的“地獄空蕩蕩,王菊在土創”還是后期為其拉票的表情包,都使王菊的關注度快速上漲。在第二次盜獵中,粉絲則利用其名字中的“菊”字制造出了許多饒有趣味的“菊花寶典”,將王菊現象推向高潮[8]。粉絲們自稱“陶淵明”,創造出了一系列戲謔的詞句如“菊手投足”(要把王菊投到首位才足夠)“物以類菊”(所有優秀的“陶淵明”都因為喜歡王菊聚集在一起)以及“你一票,我一票,王菊還能繼續跳”等,都憑借其搞笑性質在大眾媒體上廣泛傳播。王菊的百度指數均值在一個月內都維持在三萬以上⑤,最終形成了大規模的網絡狂歡。如詹金斯所言,“粉絲借用大眾文化中的形象,扭轉其原有意義,建構自己的文化和社會身份,從這一行為中粉絲們往往會提出一些在主導媒體中無法言說的想法”[ 7 ]。粉絲以“文本盜獵”的方式,展現了狂歡中的快樂精神,并表達了對王菊本人及其所代表的反抗單一審美精神的支持,使王菊的點贊榜排名從首次公演的墊底一路攀升,甚至一度成為第一名,形成了一場充滿叛逆性質的全民狂歡。
王菊和“白幼瘦”同質化審美下女團成員的關系如同小丑與國王的關系。在這場狂歡中,王菊成為了被加冕的對象,變成了熱度最高的選手之一,充分說明了偶像標準的相對性與流動性,打破了單一的偶像審美。而表情包以及“菊花寶典”作為“文本盜獵”的產物則使得王菊的熱度在一段時間內高居不下,吸引了許多“菊外人”的參與,最終形成了巴赫金所說的“全民性”的大狂歡。王菊本人通過在第六期節目中模仿“地獄空蕩蕩,王菊在土創”的動作加入了本次狂歡,回應“文本盜獵”的產物,在一定程度上也解綁了傳統偶像-粉絲之間嚴格的等級關系,體現了狂歡中的平等和隨意的人際關系。在這場狂歡中,人們用支持王菊的形式,實現了對文化工業中同質化審美標準的反抗和自我審美權力的表達,本質上是對獨立自主精神和多元文化標準的訴求。與此同時,王菊現象也對社會文化產生了一定影響,其獨立精神與形象鼓勵了非常多希望打破陳規束縛的當代女性。至此,在由王菊引發的網絡狂歡中,偶像工業的規則被暫時取消,狂歡節的相對性精神顛覆了文化工業控制下的選秀形態和標準。在網絡狂歡的席卷下,人們不再是被動接受同質化偶像形象、沒有思考能力的受眾,而是通過支持王菊、進行“文本盜獵”等活動反抗了偶像工業的標準化審美。
3.3 利路修現象:固化的造星模式與粉圈邏輯的反抗
在《創造101》中,王菊作為“白幼瘦”審美的對立面成為了被加冕的小丑,而在《創造2021》中,相似的情節再度發生,原本并非練習生的利路修成為了本次選秀中的加冕對象,其獨特的選秀過程也吸引了大批觀眾。利路修為俄羅斯籍選手,本是《創造營2021》的工作人員,卻因為節目選手數量不足被臨時邀請參賽。面對難度頗高的歌曲與舞蹈訓練,利路修的反應與其他選手截然不同,被評論為“被迫上班的打工人”。當別的練習生因為進入了F班(即評級最低的分班)時都情緒低落,而利路修卻表示“F班意味著freedom(自由),應該回家”。其他言語如“希望沒有很多人給我撐腰”等,都和其他符合偶像設定標準、認真練習的選手形成鮮明反差,并因此收獲了意外關注。節目開播以來,其熱度不斷上升,微博熱搜次數高達55次,成為了《創造營2021》討論度最高的選手之一⑥。
利路修之所以能意外走紅,一方面因其“打工人”形象切中了當今社會的焦慮熱點,引起了觀眾強烈的身份認同與共鳴;另一方面,其節目表現也激發了觀眾的逆反心理,具體表現為利路修越是希望自己被盡快淘汰,觀眾就越是給他投票,以此獲得控制他人人生與節目走向的滿足感。此時利路修現象的走向已經與傳統的選秀發生了根本性質的變化,觀眾不再以“打投出道”為導向、被資本邏輯所裹挾,轉而追求滿足獵奇心理的快樂,進而演變為了一場狂歡。其粉絲有意顛覆了許多偶像工業規則,戲謔地自稱“筍絲”⑦,追求“以最少的錢獲得最大的快樂”。官方粉絲后援會明令阻止未成年人花錢投票、不強制成年人投票,在發酵初期甚至將人均集資上限定為一元錢,與“愛他就為他花錢”的現行粉圈邏輯形成對照。其微博超話也堅持以歡樂為出發點,不存在嚴格的發帖格式與內容限制,與其他偶像紀律嚴明的超話氛圍截然不同。越來越多的觀眾被利路修及其粉絲的反差表現所吸引,加入了這場逆向選秀的活動,使利路修現象成為了“全民式”的狂歡。在粉絲們的努力下,利路修的人氣一直高居不下,其微博超話排行榜穩居《創造營2021》所有選手中的第一位,在2021年4月17日的節目中,其名次也從初期的末位變為了10名。粉絲們沉迷在叛逆的狂歡中,以娛樂性取代了官方世界的嚴肅性和神圣性,并通過狂歡的力量顛覆了金錢至上的邏輯和日益固化的粉圈規則。
回顧整個現象,原為普通人的利路修由于機緣巧合進入了《創造營2021》的選秀,其反差化的身份與節目表現吸引了大量圍觀。在身份認同感和獵奇心理的雙重驅使下,粉絲們一定程度上延續了利路修的反叛精神與表現,以阻止利路修實現被淘汰的愿望為投票動機,并在此過程中有意突破了許多粉圈規則。一系列反常規的做法吸引了越來越多人的加入,將利路修現象演變為一場叛逆性質的狂歡。粉絲成功為利路修加冕,在證明偶像標準的流動性的同時表達了對選秀節目差異化的渴望,本質上則是對日漸僵化的制作模式和選秀人設的顛覆與反抗。此時的利路修現象已經成為了巴赫金所說的“翻了個的生活”“反面的生活”[5],一切都與盛行的粉圈規則相反。種種反常規的做法之所以充滿吸引力,也正是因為能讓人沉浸在不需要金錢邏輯、不需要嚴格投票機制的狂歡中,看到了偶像工業的全新的可能性,其中也暗含著人們對僵化的粉圈模式的不滿與抗爭。至此,粉絲和利路修都以劍走偏鋒的方式,構成了一場顛覆了標準化的造星模式和粉圈規則的狂歡。利路修現象也說明,粉絲絕不是文化工業理論中不能獨立思考的被動受眾,也不會完全被文化工業所欺騙、陷入資本主導下被動消費的狀態,而是能以集體狂歡的方式對抗金錢至上的邏輯,為自身爭得一定的主動權力。
4 結語
綜上所述,隨著“創造營”系列選秀在中國市場的流行與火爆,在制作模式走向成熟的同時出現了許多文化工業理論所批判的特征,如節目內容標準化、偶像同質化等。觀眾在觀看選秀節目的過程中,為了幫助偶像順利出道,不得不陷入被動消費的怪圈,表面上看似爭奪了控制選秀結果的主動權,實際上維護了文化工業的資本邏輯。然而,王菊和利路修現象所引發的網絡狂歡卻讓人們看到了改變被動地位、掙脫文化工業限制的可能性。兩場現象的中心人物均和同質化的偶像形象有著巨大差別,并在不同程度上契合了社會痛點問題,進而引發了廣泛關注。在王菊現象中,人們通過為王菊加冕表達了對“白幼瘦”單一化審美的反抗和對多元文化標準的支持,并以“文本盜獵”的形式將整場現象推向高潮,最終演繹為一場網絡狂歡,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大眾審美的革新。而在利路修現象中,人們在叛逆心理的推動下為逆向選秀的利路修投票加冕,象征著對差異化節目內容的渴望和標準化造星模式的反抗。同時,粉絲們反常規的戲謔行為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的加入,挑戰了日益僵化的粉圈規則,最終形成了一場全民的顛覆性狂歡。如美國學者約翰·費斯克所說,粉絲和文化工業之間的斗爭始終存在,文化工業試圖對粉絲進行收編,而粉絲卻可以用反收編的方式對文化工業進行抵抗[9]。王菊和利路修現象讓人們看到了以狂歡的形式顛覆文化工業邏輯的可能性,也佐證了受眾并非完全因為沉迷娛樂而喪失獨立精神與思考能力。誠然,受眾并非處于絕對的優勢地位,狂歡也面臨著消散與結束的風險。在已經結束的王菊現象中,王菊本人并沒有因為顛覆性狂歡就順利出道,傳統的“白幼瘦”審美在后期的選秀中也依然流行。但是,狂歡本身的影響力卻不容否認,它象征著受眾的反抗性訴求以及自身的能動性,讓人看到了流水線偶像工業外的另一種可能性,在一定時間內也對大眾文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與沖擊。無論是在“創造營”系列選秀還是其他的選秀活動中,粉絲和文化工業的沖突會持續存在,二者以收編和反收編的方式進行妥協和抗爭,這種動態關系也將繼續影響社會文化的發展,并為之注入新的活力。
注釋
①數據來源于燈塔專業版App,其中《創造營2021》由于尚未結束,文中數據為2021年4月18日的統計結果。
②數據源于百度指數。
③數據源于桃叭App。截至2021年4月18日,劉宇為《創造營2021》集資經費最高的選手,具體數據為1224.92萬。
④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42370013/。
⑤文中數據為2018年5月15日至6月15日的百度指數。
⑥文中數據為云合數據平臺2021年4月18日的統計結果。
⑦“筍絲”源于網絡用語“奪筍”(多損),用于表達搞笑、戲謔之意。
參考文獻
[1]馬克斯·霍克海默,西奧多·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M].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7-152.
[2]霍連彬.媒體奇觀視角下網絡選秀節目的批判性解讀:以《偶像練習生》為例[J].新媒體研究,2018,4(12):119-121.
[3]Smythe,D.Communications:Blindspot of WesternMarxism[J].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ety Theory,1977,1(3):1-28.
[4]陸道夫.狂歡理論與約翰·菲斯克的大眾文化研究[J].外國文學研究,2002(4):21-27,154-170.
[5]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M].白春仁,顧亞鈴,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6]關慧.狂歡中的契合:巴赫金狂歡理論與大眾文化[J].外語與外語教學,2016(5):132-137,148.
[7]亨利·詹金斯.文本盜獵者:電視粉絲與參與式文化[M].鄭熙青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8]江怡.粉絲文化參與偶像工業的新可能:以《創造101》中的“文本盜獵”事件為例[J].藝術廣角,2020(1):47-53.
[9]約翰·費斯克.粉都的文化經濟[C]//陶東風,楊玲.《粉絲文化讀本》.陸道夫,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