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述與嘆息
文 | 杜鵬

《Rough And Rowdy Ways》鮑勃·迪倫哥倫比亞唱片民謠 2020
在第二遍聆聽鮑勃·迪倫今年六月發行的這張專輯《粗暴和吵鬧的方式》(Rough and Rowdy Ways)時,我正在讀孟悅出版于九十年代初期的著作《歷史與敘述》。鮑勃·迪倫的這張專輯是一張講述者的專輯,而孟悅的這本書則是關于講述的書,同時進行這兩種“閱讀 ”,很容易產生彼此之間的干擾,最后,我的選擇是,把孟悅的這本書放到了一旁,專心去聽這張專輯。
迪倫的這張專輯是他繼2012年的《暴風雨》(Tempest)之后發行的第一張原創錄音室專輯,從專輯的氣質上來講,也與上一張頗為接近,以暗色調為主,配上大量的低聲吟唱。和上一張專輯一樣,這兩張專輯最長的歌曲均講述了一個歷史上的悲劇性事件,上一張的主打歌《暴風雨》講述了泰塔尼克號沉沒的過程,而這一張的主打歌《最卑鄙的謀殺》(Murder Most Foul)講述了肯尼迪總統被刺殺的慘劇。選擇如此沉重的主題作為專輯的主打歌,或許和當下的疫情和全世界各地緊張的政治氛圍有關。
和他的文學前輩波德萊爾、普魯斯特、菲茨杰拉德等人一樣,鮑勃·迪倫作為一名歌者和敘事詩人的同時也是一名“世紀病”患者。他們的共同特征就是在他們的幾乎所有時期的作品中,都帶有一種“過去的已無法挽回,將來的還尚且未知”式的“無可名狀的煩惱”。雖然貴為幾代人心目中的精神偶像,以及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鮑勃·迪倫的一生看似是名利兼收,但是他卻從未停止過自己對于絕望和恐懼的敘述與嘆息。在這張專輯中,雖然有像主打歌Murder Most Foul這樣的對歷史慘劇的詩性敘述,但是更多則是感嘆。在迪倫的感嘆中,既有面向過去的,獻給他的那些死去的偶像們的,比如像《再見,吉米·里德》(Goodbye Jimmy Reed)對他的布魯斯前輩的一次致敬,而《我包羅萬象》(I Contain Multitude)則致敬了惠特曼、布萊克等文學前輩;同時也有面向未來的,像《黑騎士》(Black Rider)這樣的對死神的一次對峙。值得一提的是,在這首《黑騎士》里面,迪倫的演唱和配樂雖然充滿了嘆息和無奈,但是他的歌詞卻充滿了戲謔。他用“I don’t wanna fight,at least not today. Go home to your wife, stop visiting mine.”(我不想干架,至少是今天。回家找你老婆吧,別來騷擾我老婆。)這樣的近似于惡搞的歌詞來面對注定要到來的死神,這使得這首歌充滿了張力,讓原本沉重的調子顯得輕松了不少。沒有人比迪倫更擅長于玩弄評論家的熱情,而這種用最戲謔的方式面對最嚴肅的主題卻是迪倫幾十年來慣用的老把戲,當年他在七十年代,就曾經在巡演的時候,用“下一首歌獻給泰姬陵”這樣的胡說八道賺得不少樂迷和評論家的眼球。而他的諾獎授獎詞又被曝出有“抄襲”和“洗稿”之嫌,這使人不得不以為,這或許也是“迪倫式”的行為藝術中的一部分。
當一個擅長胡說八道的浪子開始一本正經地抒情時,往往也是他最動人的時候。而這張專輯中的《繆斯之母》(Mother of Muses)就是這樣一首至真至誠的歌曲。和他七十年代的名作《永遠年輕》(Forever Young)一樣,這首《繆斯之母》也是首福音歌曲。在這首歌中,迪倫放下他偶像的身段,用吟誦的方式向那靈感的源泉致敬,致敬那最高虛構的存在。歌中像“put me upright,make me walk straight.”(讓我腰板筆挺,昂首而行)這樣的歌詞更像是對他七十年代的名曲《風暴中的庇護所》(Shelter From The Storm)中主題的一次延伸。而這種對過去的延伸在這張專輯中則比比皆是。
總而言之,迪倫的這張新專輯讓我看到了一個重復走過去道路的迪倫,而不是一個嶄新的迪倫。然而對于一個已經78歲的老詩人來講,我們又能要求些什么呢?自我重復并不一定是壞事,也并不一定是精神衰老的標志。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往往是不畏懼重復的。因為他們深知,有感而發的重復不僅不是浪費,反而是一種對自我本體性的加強,一種對個人語調的加強。而迪倫正是這樣一名藝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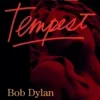
《暴風雨》
鮑勃·迪倫
哥倫比亞唱片 搖滾 2012
《暴風雨》是鮑勃·迪倫的第35張錄音室專輯,并在受到了廣泛的贊譽。像《滾石》這樣的權威音樂雜志也對這張專輯給予了五星的好評。專輯同名歌曲《暴風雨》是一首長達十多分鐘敘事長詩,講述了泰坦尼克號沉沒的慘烈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