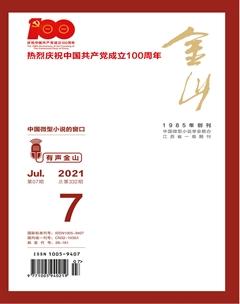詩韻木瀆
雪鷹 劉思陽
編者按:
張建祥是一位“歸來派”詩人,從上世紀80年代的文青,到今天茫然四顧回歸詩壇的寫作者,再通過兩屆詩歌寫作班的學習與訓練,我們看到的是他一路飛進的寫作勢頭和日漸精純的詩寫技藝。“方向很重要”,底蘊與天賦都是為方向服務的。在他的這組詩里,第一首就有脫俗的表現。在詩寫盛大節日之時,能保持“拔河”的藝術端點,同時又實現了情感不動聲色地抒發,將主旨隱含于詩性之下的妙法,是值得肯定的。第二首《枯木賦》整體象征與隱喻結合,讓詩產生了“物”與“人”二者的糾纏與混搭,技藝、內涵與詩性更高一籌。“歸來派”是對一個群體的統稱,他們中有一部分一直沉緬于當年的輝煌,漠視近幾十年來中國詩壇的巨變,深陷因循守舊的泥沼;另一部分則是在短暫的陣痛之后,謙恭地找到了方向與突破口,勇敢地摒棄了自己幾十年來所形成的固化的寫作手法,向詩歌發展的前沿奮起直追。而這部分人通過自身沉淀的底蘊、天賦,加上后天的思考與勤奮,往往詩寫技藝在短期內就能得到迅速飛升,這種精神是令人刮目相看且值得欽佩的。建祥先生無疑是后者中的典型,還有石春國、楊孝洪等,亦屬此類。
劉鵬的這組詩,寫作的自由度更大,抒情酣暢自如,聯想豐富,意象多彩,從詩行間可以感受到他詩寫過程中的興奮與自信。
應紅梅詩寫上的努力,依然體現在凝練與精準兩方面。和她詩中語于西施的那樣,我們得以看到她亦正用自己的想象與詩寫語言,填寫著詩歌創作的新篇。
沐荷的組詩首句一出,就讓我重新認識了她的詩。《一池連花靜默不語》里,詩與人與荷一樣輕盈、曼妙。她的寫作手法雖不算先鋒,但自然、婉約,親切而靈動。
喬一水的努力方向一直未變,但在“采風”這類題材的詩寫中,追求意象的詩,無疑難度更大,角度也需要更新穎。是的,“最硬的詞/都有自己的著落/而我再不能用跪坐/模仿石碑/刻出最后一計”。尋找“硬詞”讓詩骨挺起來,的確是詩人終生的功課。
許健平的三首,基本可代表他當下詩寫的水平,在詩性的統領下敘事、明理、悟道、抒懷。
吳海龍則是只要體驗足夠深刻,就會使他的詩向上一個層次沖刺的作者,在他的這組作品中可以洞察出詞的精準、意象的融合與關聯,正一步步走向醇熟。
冬天的雪,詩寫視角從宏觀到微觀,從喻理到陳情,呈現了她對詩、對文化的理解。
張捷珍的語言既有一股源自自然的清新,又有精心錘煉的況味。她的詩無論氣息、意象、思考都能恰到好處,渾然天成。就像她詩里寫到的:“拜佛不許愿/這些年我一直這么做/佛知道我不想難為它”。寫詩也是如此,虔誠即可,假以時日,終會有回報。
袁煉在本次的作品里也使出了“看家”功夫,觀察的視角、概括的能力使其語言凝煉、精準的程度都略勝一籌。尤其是第一首里的“三頂帽”,虛實搭配,收放自如,情理交融。
毛文文的詩性敘事已具個人風格,想象與意象粘連交融,構成他詩中不經意就流露出的韻味,在他的詩里從不回避自己對吳中、對木瀆的愛。
田由申的三首,也可謂是他近期以來的力作。懷古陳情,以事喻理,前后互文,實現了思考的深度與意象自然融合。
楊孝洪則是把木瀆古鎮當作一本厚重的書,精心閱讀、體悟,并以詩句“劃重點”。
石春國筆下的白玉蘭,不只有乾隆手栽的傳說,它還是一個200多歲的孩子,有慈悲與思想。想象與現實的交合,賦予事物更為豐富的身份與內涵。
秦艷的詩,通過擬人等修辭運用,始終給人一種童話氣息或者寓言的感覺。這與她所從事的職業肯定有關聯。詩中的意象,展示出古今木瀆的不同風貌,有嗟嘆也有期待。
魏貴真語言已呈現出自己的特點,作為一名從山東遠道而來的詩人,南北差異,使其擁有了更敏銳、細微的感知力,她的作品里對江南、對木瀆的愛溢于言表,同時也悟出“大道循環不息止/詩人何處不木瀆”的另類思考與豪情。
此次《金山》文學月刊“走進木瀆”采風交流活動的成功舉辦得到了吳中區政協、木瀆鎮文聯等單位的傾力支持,活動還邀請了《金山》“新時代”詩歌高級寫作班第一、二屆部分學員共同參與交流。從某種角度看,本次作品的集中呈現也可以看作是《金山》詩歌寫作班第一、二屆學習成果的展示與檢閱。當然,部分作品中依舊存在諸如語言的凝煉不夠,氣息不夠順暢,語言散文化傾向等問題,還需要依靠長期堅持不懈地寫作,才能全部克服。但總體來說,我們看到了每個學員詩寫技藝的提升,甚感欣慰!
采風作品中還有柔劍、旁白客等特邀詩人,以及周菊坤、于曉明、貢才興等吳中本土作者的詩作。借此機會,使得這些作品與我們詩歌寫作班學員的作品,同題材、同時間、同欄目呈現,便于大家互相借鑒、學習與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