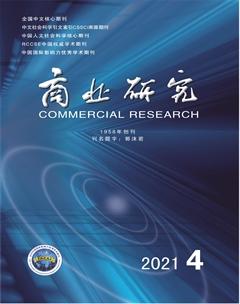中國式分權與經濟增長方式:影響機理與路徑
謝家智 何雯妤
關鍵詞:中國式分權;經濟增長方式;市場分割;產業結構合理化
中圖分類號:F121;F81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148X(2021)04-0098-12
收稿日期:2021-03-23
作者簡介:謝家智(1967-),男,四川西充人,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金融經濟學、中國式分權與金融發展;何雯妤(1996-),女,黑龍江黑河人,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經濟學、中國式分權與金融發展。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金融回歸本源發展的中國式分權制度創新”,項目編號:19XJL005。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制度(體制)改革成為影響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和經濟增長方式的關鍵因素。其中,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財政分權制度改革,充分激活了地方政府發展的積極性,助推了中國的“投資潮涌”現象,促進了經濟的快速擴張。中國的分權制度包括顯性的財政分權制度和隱性的金融分權制度,其中中國式的財政分權制度作用更為明顯。財政分權制度明確了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的劃分,通過政治激勵為主的考核激勵制度,激活地方拓展財源和發展經濟的動力和壓力。財政分權制度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的“大包干”到20世紀90年代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的變化過程。地方政府基于政治激勵動機,努力實現“相對績效優勢”和“超越對手”產生強大的投資發展壓力,對推動中國經濟規模的高速擴張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國式分權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在“為增長而競爭”的政治錦標賽考核機制下,極容易產生非理性的盲目投資行為,加劇要素投入和投資驅動的粗放型發展模式,導致中國經濟出現結構性失衡、效率下降、產能過剩和創新能力不足等問題日益嚴重,同時助長了市場分割和產業結構不合理等現象。因此,如何進一步深化中國式分權改革,探索分權制度真正有效地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發展,形成新的制度比較優勢以此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持續的內在動力,是當今亟須解決的重大問題。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中國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面臨新的發展任務和問題,特別是如何實現高速度的數量增長向高質量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成為新時期經濟發展的新課題。
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形成主要依賴于經濟規模的擴張,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并使之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才是實現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關鍵所在。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通過優化資源配置、影響激勵結構等方式,刺激企業創新和區域技術進步,以此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1]。中國式分權作為重要的制度安排,其對經濟增長方式影響的剖析尤為重要。在現有的中國式分權研究中,多數學者較多關注分權制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大體可分為促進經濟增長和抑制經濟增長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財政分權顯著地促進了經濟增長[2];另外一種觀點則認為財政分權引發了市場分割、重復建設、地方保護主義等多種負面效應,抑制了經濟增長[3]。學界形成了“分權促進論”和“分權抑制論”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一方面,大量研究經驗認為財政分權制度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能夠較好地改善經濟效率。Davoodi等(1999)從長期的角度證明了財政分權能夠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從而影響經濟增長率[4]。林春(2017)從全國和地區兩個層面證明了財政分權對經濟質量改善有顯著的促進作用[5]。另一方面,也有學者認為財政分權容易引起地方政府惡性競爭,對地區全要素生產率造成負向影響,抑制經濟增長方式轉型。Restuccia和Rogerson(2017)指出財政分權下的地方政府競爭行為嚴重扭曲了要素市場的資源配置,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產生負向抑制效應[6]。鄧曉蘭等(2019)通過構建動態的空間面板模型,實證檢驗了財政分權顯著抑制了城市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7]。從上述文獻可以看出:第一,關于中國式分權制度對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較多從財政分權角度出發,但同樣作為中國式分權的金融分權卻被理論界長期忽視[8]。在現有文獻中,關于金融分權的探討主要集中于其產生的經濟影響。這些研究認為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關于金融資源配置權、控制權的博弈深刻影響了地方經濟發展,例如提升金融部門債務效率、促進民間投資、抑制區域科技效率等,但關于金融分權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研究卻十分缺乏。中國經濟增長方式離不開財政資源和金融資源的相互配合,因此僅從單一的財政分權角度出發無法全面反映中國式分權對經濟增長方式的影響效應。第二,現有文獻對中國式分權與經濟增長方式的研究僅僅通過從實證的角度檢驗二者關系,沒有揭示出中國式分權對經濟增長方式的內在機理與傳導機制,也并沒有深入剖析哪些因素可以對中國式分權與經濟增長方式的機理產生影響。
本文將財政分權、金融分權統一納入中國式分權的研究框架,通過理論和實證兩個角度探討中國式分權對經濟增長方式的影響,考察市場分割、產業結構合理化這兩個影響要素對中國式分權和經濟增長方式的作用,分析財政分權和市場分割、金融分權和產業結構的交互作用,進一步歸納完善中國式分權對經濟增長方式的內在機理。
二、機理分析與研究假設
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發展階段,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已經成為新時代全面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必然要求。如何在保持經濟增長規模穩定的情況下,進一步改善經濟發展質量,作為對經濟發展有著重要推動的中國式分權制度,應當繼續提供經濟制度層面保障。中國式分權的基本特征是“政治上集權”、“經濟上分權”,這種模式共同構成了激勵地方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適度的中國式分權通過資源的優化配置能夠顯著改善公共物品供給水平和基礎設施建設,促進經濟規模的擴張和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的提高,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然而,過度的中國式分權扭曲要素配置,造成市場分割、地方保護主義、產業結構扭曲等負向效應,抑制經濟規模的擴張和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的提高,阻礙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發展。因此,對于中國式分權與經濟增長方式的機理分析,應當從正反兩個方面進行論證。
(一)中國式分權與經濟增長方式
1.中國式分權與經濟規模擴張。中國式分權是實現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關鍵力量,在促進經濟規模擴張中有著獨特的作用。首先,中國式分權使得中央政府將一定的財政權力和責任賦予給地方政府,其獲得了對地方經濟較強的支配權力,允許自行決定預算規模與結構,從而通過財稅政策激發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動力,以此促進經濟增長[9]。同時,在以增長為競爭的政治錦標賽考核機制下,地方政府不得不向上負責,滿足中央政府經濟增長目標偏好,努力通過經濟增長來獲得政治晉升機會和空間。其次,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能提供符合居民偏好的公共物品[10],而地方政府官員在為轄區內居民提供服務的同時,也接受著居民更為嚴密的監督。主要因為,地方政府具有地緣優勢,可以直接了解本地居民的真正需求,以此通過財政支出等方式改善基礎設施建設,再加之地方政府在監督之下更有動力為當地居民謀取福利,從而有效地促進經濟規模擴張。最后,經濟規模擴張離不開金融資源的支持,金融分權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地方政府支配金融資源的能力。金融分權的本質體現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對金融資源的激烈爭奪。在財政資源配置確定的情況下,金融分權緩解了地方政府巨大的財政壓力,使其在一定范圍內能夠有效配置和調控金融資源。況且,金融分權程度越高,地方金融機構相對發達,地方融資渠道相對廣泛,民營企業融資較為容易,可用于經濟發展的金融資源相對充足,進而有利于經濟增長。
然而,由于中國的體制和經濟現實與傳統的分權理論假設之間存在差異,部分學者認為當分權的標準假設不成立時,財政分權會抑制經濟增長。一方面,中國式分權造成地方政府與企業合謀行為,進而滋生腐敗尋租等現象,阻礙經濟增長。中國式分權賦予地方政府較大的自主權,但這些權利卻未受到司法約束。若企業為了獲得信息政策等優勢,就會千方百計地與地方政府建立政治關聯。具有政治關聯的企業不僅可以在經濟金融資源方面獲得優勢,還可以受到地方政府市場壟斷的保護力量,即阻止具有潛在競爭性的企業進入本地市場。同時,政企合謀與腐敗現象有著密切聯系。相對于中央政府而言,地方政府更容易滋生腐敗行為。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官員的晉升空間相對于較小,在政治仕途上比中央官員更為曲折。因此,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權更容易受到地方利益集團的影響和干預,導致產生腐敗尋租等行為,進而不利于經濟增長,阻礙經濟規模擴張。另一方面,金融分權程度決定了地區金融資源的豐裕程度,這對經濟增長產生至關重要的作用。為了滿足地方政府對金融資源的需求,從地方性金融機構獲得的債務融資成為地方建設資金來源的重要渠道。然而,這種種行為會引發不良債務和銀行壞賬的產生,若超出地方政府自身承擔能力時,地方政府出于機會主義動機轉嫁給中央政府,極易產生區域性金融風險。區域性金融風險的發生阻礙企業從金融機構獲得良好的金融服務,導致企業增加生產活動的成本,不利于經濟的穩定發展,阻礙經濟規模總量擴大。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a:中國式分權促進經濟規模的擴張。
假設1b:中國式分權阻礙經濟規模的擴張。
2.中國式分權與經濟發展質量。中國式分權在影響著地區經濟發展規模的同時,也深刻影響著地區經濟發展質量。中國式分權作為重要制度安排,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上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首先,中國式分權較好地平衡財政金融資源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分配,打破了政治集權背景下中央政府對財政權力和金融權力的壟斷,能夠促進了資源配置效率提升,實現了要素自由流動,為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良好保障。同時,由于地方政府在信息搜集更具有經濟優勢與時間成本優勢,對于所管轄區內的經濟社會發展更具有專業化了解,能夠提供符合當地居民偏好的公共性服務,加強改善基礎設施建設,有效提高運輸效率,減少轄區內生產要素流動的摩擦成本,進而推動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的提高,從而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其次,“向上負責”是中國式分權的政治體制主要特征,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逐步轉型,中央政府將創新驅動發展這一要素納入到晉升激勵機制中,成為考核地方政府重要標準。因此,為了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滿足以創新驅動為理念的考核要求,地方政府應當按照國家經濟發展戰略,提高財政科技支出比重,為企業創新升級與轉型發展提供完善相應的政策支持和創新環境,激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將更多的財政金融資源投入到企業創新活動中,從而有利于技術進步,而這正是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因素。最后,中國式分權有利于提高各地區開放程度,能夠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提升資源在全球的配置效率,進而有利于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的提升。在分權背景下,為增長而競爭的地方政府對爭奪轄區外流動要素的有著較高的積極性,而FDI所帶來的先進管理經驗和生產技術溢出能夠使企業產生“學習效應”,消化吸收引進的技術,有利于經濟質量的提升。
然而,也有觀點認為,中國式分權在完整性和規范性方面還有很大的不足[11],中國式分權的“要素扭曲”作用容易降低財政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抑制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首先,中國式分權導致地方政府短視近利,抑制財政資源向有利于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領域配置,不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在自上而下的垂直集中官員治理模式下,由于垂直監督成本高且監管難度大,再加之地方政府官員的晉升標尺仍然以轄區內的經濟績效作為主要依據,所以,地方政府利用行政自主權,將發展重點傾向于在短期內能夠快速促進GDP增長的項目上。然而,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的提高主要依賴于技術創新,但技術創新具有高度不確定性,且創新回報周期較長,不能夠在短期內轉化為官員的即得利益[12],因此財政資源和金融資源配置到科技創新領域較為缺乏,抑制了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的提升,不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其次,中國式分權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區域市場分割和重復建設,不利于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分稅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出于增加本級財政收入的需要,維持較為穩定的收入來源,采取市場分割手段保護本地企業發展,違背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原則,阻礙了要素在區域內的自由流動,降低資源配置效率。最后,中國式分權在配置財政金融資源過程中是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金融分權作為中國式分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地方政府通過金融分權掌控國有銀行管理層的晉升機制,進而干預國有銀行的放貸對象和資金金額,造成了效益較低的國有企業卻往往更加容易獲得資金支持,而同等條件下效益較好的民營企業卻難以獲得。所以,長期以來金融分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導致具有潛在成長性質產業因資金短缺舉步維艱,阻礙了經濟高質量發展。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a:中國式分權促進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
假設2b:中國式分權阻礙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
(二)中國式分權與經濟增長方式的機制分析
1.中國式分權與市場分割。市場分割阻礙了生產要素地自由流動,扭曲要素市場資源配置,是阻礙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發展的重要因素。市場分割的類型主要可以歸納為自然性市場分割、技術性市場分割以及制度性市場分割。對于正處于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而言,由經濟、政治等因素造成的制度性市場分割是學術界一致關注的問題。財政分權作為中國式分權改革的重要內容,主要目的是中央試圖通過財政措施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使其成為發展經濟的“援助之手”[13]。然而,在以“為增長而競爭”的特征的政治晉升制度的激勵下,財政分權的負面效應也逐漸顯現出來,毫無疑問,市場分割就是最主要的后果之一。在中國式分權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掌握資源稟賦的豐裕程度直接影響到官員晉升空間、當地的財政收入以及經濟發展。王永欽(2007)指出若自由的市場機制并不能帶來地區間的平衡發展,那么,市場分割和地方保護主義成為地方政府的理性選擇[14]。理論上,市場分割并不是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必要手段,但中國式分權制度為其提供“土壤”環境,如果中央在實行經濟分權的同時,能夠運用有效的法律手段監督產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動,在一定程度上會弱化市場分割的負面影響。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缺少一定的制度約束,地方政府如果資金來源渠道廣泛,出于保護自身利益的需要,容易導致形成“政企合謀”、貿易保護壁壘和地方保護主義等現象。在地區資源錯配成為既定事實的情況下,地方政府通過市場分割這一方式保護轄區內企業發展,增加本級財政收入,成為理性選擇[15]。而中國式分權制度激勵了地方政府實施市場分割這一自利行為[16],再加之當經濟激勵與政治晉升融合時,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會更加激勵,因此,相互市場分割的動機也會更加強烈。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3:中國式分權加劇了市場分割。
2.中國式分權與技術創新。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發展意味著需要理性看待經濟速度放緩,將發展重點轉移到提高經濟質量上。技術創新作為改善經濟質量的關鍵因素,應當重視經濟制度對技術創新的影響。在中國式分權背景下,以市場機制為主導的經濟體制更多表現為地方政府主導區域的經濟建設。在缺少有限的監督機制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可以直接干預國有企業的投資決策。因此,在分權背景下形成的短視近利行為將大量的財政金融資源投向有利于GDP增長的項目上,不斷追求經濟規模擴張,造成微觀主體盲目跟風投資行為,嚴重降低企業從事有關于技術創新生產項目的積極性。同時,中國式分權使得地方政府擁有了較大的自主權,與之伴隨的地方政府同時掌控轄區內適用于經濟發展的大量資源。當地方政府將投資重點放在招商引資、注重發展短平快的項目上時,有限的勞動力、資金等生產要素不能順利地流向新興企業和科技企業,阻礙了創新資源流在區域間的自由流動。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4:中國式分權阻礙了技術創新。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1.基準回歸分析。為了檢驗中國式分權與經濟增長方式的之間的關系,從經濟規模與經濟質量兩個維度進行實證分析。首先,從經濟規模維度出發,根據前文理論機制所分析的基本假設,本文建立模型1:
lnGDPit=α0+α1FDit+α2FINAit+αmControlVariablesit+εit(1)
其次,為了探究中國式分權與經濟增長方式的內在機理,本文加入市場分割和產業結構合理化兩個機制變量,建立模型2:
lnGDPit=β0+β1FDit+β2FINAit+β3SEGit+β4TLit+βmControlVariablesit+εit(2)
最后,本文在模型2的基礎上加入財政分權與市場分割的交互項和金融分權與產業結構合理化的交互項,并進行去中心化處理,建立模型3:
lnGDPit=γ0+γ1FDit+γ2FINAit+γ3SEGit+γ4TLit+γ5FDit*SEGit+γ6FINAit*TLit+γmControlVariablesit+εit(3)
在檢驗經濟規模后,運用同樣的方法將被解釋變量換為經濟質量,建立模型4—模型6:
TFPit=α0+α1FDit+α2FINAit+αmControlVariablesit+εit(4)
TFPit=β0+β1FDit+β2FINAit+β3SEGit+β4TLit+βmControlVariablesit+εit(5)
TFPit=γ0+γ1FDit+γ2FINAit+γ3SEGit+γ4TLit+γ5FDit*SEGit+γ6FINAit*TLit+γmControlVariablesit+εit(6)
其中,i和t分別代表省份和時間,lnGDP代表經濟規模,TFP為全要素生產率,代表經濟質量,FD代表財政分權,FINA代表金融分權,SEG代表市場分割,TL代表產業結構合理化,FD*?SEG代表財政分權與市場分割的交互項,FINA*TL代表金融分權與產業結構合理化的交互項,ControlVariables代表一系列的控制變量,εit為隨機誤差項。
2.進一步分析。在基準回歸驗證了中國式分權對經濟增長方式存在顯著影響的基礎上,本文將從市場分割和技術創新的角度進一步探討中國式分權對經濟增長方式的影響機制,將上述基準模型的被解釋變量分別替換為市場分割和技術創新,若中國式分權能夠顯著影響市場分割和技術創新,則驗證了中國式分權通過這一路徑影響經濟增長方式。
SEGit=λ0+λ1FDit+λ2FIANit+λ3FDit*FIANit+λmControlVariablesit+εit(7)
lnINNit=π0+π1FDit+π2FINAit+π3SEGit+π4TLit+π5FDit*SEGit+π6FINAit*TLit+πmControlVariablesit+εit(8)
(二)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經濟增長方式,經濟規模選用取自然對數后的國內生產總值(lnGDP)表示,經濟質量選用全要素生產率(TFP)表示。關于經濟質量的衡量,雖然我國有部分學者認為全要素生產率不能全面反映經濟質量的內涵,但大多數研究仍然將全要素生產率作為備受青睞的衡量指標。世界銀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認為全要素生產率是用來研究中國經濟質量的重要指標,學術界也有許多學者均采用全要素生產率這一指標衡量經濟質量。因此,鑒于前人研究,本文采用全要素生產率衡量經濟質量。
目前關于測度全要素生產率的方法主要有參數法和非參數法兩類,其中DEA—Malmquist指數方法使用比較廣泛,因此本文運用該方法測算我國各省份的全要素生產率。
(1)投入變量。指勞動投入和資本存量。勞動投入選取各地區就業人口數衡量。資本存量目前沒有官方統計,本文借鑒單豪杰(2008)[17]的計算方法,用永續盤存法進行估算,公式為:Kit=Iit/Pit+(1-δ)Ki,t-1?,其中,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K代表資本存量,I代表固定資本形成總額,P代表固定資產價格投資指數,δ為折舊率,本文采用10.96%。
(2)產出變量。本文選用實際國內生產總值作為產出變量。采用2002年—2016年中國30個省份的國內生產總值和生產總值指數來計算實際國內生產總值。
2.核心解釋變量。
(1)財政分權(FD)。相關分權指標的選擇,不同方法計算的分權程度對于實證結果有較大的影響。?現有文獻主要采用財政收入分權、財政支出分權、地方財政自主度這三種方法衡量財政分權。從中國分稅制改革后的實踐來看,財政分權的核心是政府間稅收收入分配,本質是財政收入分權[18]。因此,本文借鑒相關學者的研究[19],采用財政收入分權用來衡量財政分權程度,同時為保證回歸結果穩健性,用支出分權進行穩健性檢驗,具體公式如下:
財政分權=人均地方財政收入/(人均地方財政收入+人均中央財政收入)
(2)金融分權(FINA)。金融分權指標衡量是本文關注的重點,現階段商業銀行信貸仍然是融資的重要方式,況且,地方政府通過各種方式影響轄區內各大型銀行資金流向,來支持當地經濟發展。因此,本文借鑒何德旭和苗文龍(2016)[20]的計算方法,用各省的銀行貸款比重來刻畫金融分權程度,具體公式如下:
金融分權=各省銀行貸款總額/全國銀行貸款總額
3.機制變量。
(1)市場分割(SEG)。借鑒陸銘等(2009)提出的“價格法”測算各省的市場分割程度[21]。其核心理論是“冰山模型”,即在完全套利的條件下,兩地價格不會完全相等,相對價格會在一定區間內進行變化,只有當某地區的價格扣除交易成本后高于其他地區價格,此時發生套利行為,交易才會正常進行。具體步驟:首先,選用中西藥品、紡織品、服裝鞋帽、家用電器、金銀珠寶、燃料、日用品、食品、書報雜志、飲料煙酒等十種商品為代表,構建相對價格方差Var(Pi/Pj),由于Pi,Pj為市場價格,但在統計年鑒中獲取的原始數據是商品的環比價格,所以用一階差分的方法求出商品的相對價格ΔQkijt=Ln(Pkit/Pkjt)-Ln(Pkit-1/Pkjt-1)。?其次,由于上述公式中商品異質性導致的不可加效應,用去均值的方法將其剔除,具體公式:ΔQkijt=β0+β1ΔQkijt+σ2,剔除ΔQkijt后,殘差的方差反映了由市場分割所帶來的套利區間空間的大小。最后,將相鄰省份間的指數按照省份合并,得到每一個省與其鄰省的市場分割指數SEGit。例如:山東省的市場分割指數就是山東和江蘇之間、山東和河北之間的市場分割指數的均值。
(2)產業結構合理化(TL)。關于產業結構指標的量化,借鑒相關的研究方法[22],采用泰爾指數來測度產業結構合理化,具體公式如下:
TL=∑ni=1(YiY)ln(YiLi/YL)
其中,TL代表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Yi代表i產業的產值,Li代表i產業的就業數,Y代表產業總值,L代表就業總數。如果TL=0,則代表經濟處于均衡狀態,產業結構合理;如果TL≠0,則表示產業結構偏離了均衡狀態,產業結構不合理。
(3)技術創新。現有文獻多數從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兩個方面衡量技術創新能力,但相比于研發活動存在不確定、成功率低等特點,創新產出更能直觀反映一個地區創新能力。因此,本文選用發明專利來衡量技術創新能力,并取自然對數。
4.控制變量。全要素生產率的水平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借鑒現有文獻,本文控制如下變量:①城鎮化水平(UZ):本文用各省常住人口與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城鎮化水平,該比例越高,表明城鎮化水平越高,一般全要素生產率水平越高。②貿易依存度(TRADE):本文采用進出口額之和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貿易依存度與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有緊密聯系,一般與其呈正向變動。③研發強度(RD):本文選用RD投入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研發強度,研發水平的高低是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因素,兩者之間一般呈正相關。④工業化水平(ID):本文采用第二產業產值與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來衡量,一般而言,工業化水平會正向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的提升。⑤市場化程度(MT):本文采用樊綱等(2016)測度的市場化水平進行衡量,該指標覆蓋區間2008-2016年,對于缺失年份數據,本文借鑒多數學者做法,用移動平均法將其所缺數據補齊。
(三)數據來源
鑒于數據的可得性與完整性,本文選取2002—2016年中國30個省份(剔除西藏自治區及港、澳、臺地區)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數據來源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Wind數據庫、EPS數據庫、《中國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和中經網等,部分缺失數據通過手工方式進行搜集補充,主要變量說明和描述性統計見表1。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根據Hausman檢驗,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對中國式分權與經濟增長方式之間的關系進行探究。分兩步進行實證分析:第一,通過基準分析,分別檢驗中國式分權對經濟規模和經濟質量的影響,并逐步加入機制變量和交互項,進一步研究中國式分權與經濟增長方式的內在機理;第二,在中國式分權對經濟增長方式存在顯著影響的基礎上,從市場分割和技術創新的角度進一步深入探究中國式分權對經濟增長方式的影響路徑。
(一)中國式分權與經濟增長方式的影響分析
在控制了影響經濟增長方式的相關因素后,先檢驗中國式分權對經濟規模的影響,結果如表2的模型1—模型3所示:(1)財政分權的回歸系數為正,并均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金融分權回歸系數也為正,并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這初步說明了中國式分權對于經濟規模的擴張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驗證了假設1a。(2)表2模型2加入了市場分割和產業結構合理化這兩個機制變量,回歸結果顯示市場分割的估計系數為負,并且通過了較高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說明了市場分割程度對經濟規模的擴張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這一回歸結果符合預期,一般而言,市場分割具體表現為商品市場分割和要素市場分割,地方政府通過行政手段既減少外來商品流入本地市場的機會,又阻礙了要素資源流出本地,進而扭曲資源配置,抑制經濟規模擴張。(3)產業結構合理化的估計系數為正且通過了顯著性水平檢驗,即產業結構的合理化有利于擴大經濟規模。這一結論也同樣符合預期,可能的原因在于生產要素重置效應是促進經濟規模擴張的關鍵因素,中國目前仍然處于轉型發展時期,潛在的結構紅利優勢有利于促進經濟發展。(4)表2的模型3是一個完整模型的回歸,在表2模型2的基礎上加入了財政分權與市場分割的交互項和金融分權與產業結構合理化的交互項。分析結果顯示財政分權與市場分割的交互項的系數顯著為負,并且通過了10%顯著性水平檢驗。可能的原因在于,財政分權背景下的地方政府有著尋求政治晉升和經濟增長的雙重驅動力,再加之在制度約束上中央政府缺少對地方政府的管制,這為市場分割提供肆意發展的“養分”,從長期經濟發展需要來看,這無疑阻礙了資本、勞動、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地區間內自由流動,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增加商品生產成本,減弱了財政分權對經濟規模擴張的正向影響效應。此外,金融分權與產業結構的交互項的回歸系數為也為負,并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即產業結構負向影響了金融分權對經濟增長方式的正向作用。產生上述結果可能的原因,一是在于金融分權本質是央地政府之間對金融資源的爭奪,而地方政府追求“高投資、高回報”的短視行為極容易造成信貸資金配置扭曲,使得具有創新性質但利潤回收周期較長的企業無法獲得充足的資金;二是國有銀行主導下的融資模式往往將信貸資金配置到國有企業,使大量的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成本高,不利于其生產活動的開展。至此,從長期來看不利于促進產業結構的合理化發展,從而減弱了金融分權對經濟規模擴張的正向影響效應。
通過上述實證分析結果可知,中國式分權顯著地促進了經濟規模的擴張,但對經濟質量是否有相同的影響需要進一步驗證。表2的模型4—模型6顯示了中國式分權對經濟質量的回歸結果。由此可知,財政分權的回歸系數雖然為正,但是并沒有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而金融分權對經濟增長方式的回歸系數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為正。這初步說明了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方式并沒有顯著的影響,但金融分權會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探究其原因,中國式的財政分權并非單獨發揮作用,而是依賴于特定的政治制度,建立于中央垂直集中官員治理的模式之上[23]。在這種制度下所引發的“自上而下的標尺競賽”毫無疑問在短期內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然而,對于改善經濟質量來說,現有的財政分權影響經濟質量的機理路徑與其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并不相同。一方面,在財政分權制度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員的晉升標尺仍然以轄區內的經濟績效為主要依據,為了在政治錦標賽中獲得優勢,地方政府異化財政支出行為,傾向于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其本質仍然是依靠投資促進經濟增長,并未從根本上提高企業的生產率和資源配置效率,反而強化了以要素驅動為特征的粗放型增長方式。而且,財政分權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引發地方政府的惡性競爭。經濟競爭中的“晉升博弈”和“零和博弈”導致了地方官員合作困難,加劇各地方政府的惡性競爭,成為粗放型和扭曲經濟增長的制度根源之一[24]。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分權不僅體現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還表現在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分權。在開放的市場經濟環境中,為彌補市場失靈造成的效率損失,中央政府會在有限權力范圍內賦予地方政府更多的金融資源使用空間,發揮地方政府在本地的信息優勢,能夠因地施策地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激發民間資本活力,充分調動地方經濟由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積極性。綜上所述,財政分權并不能顯著促進經濟質量的提升,但金融分權能夠顯著提升經濟質量。此外,模型4—模型6的機制變量與交互項的回歸結果與模型1—模型3的基本相同,原因與前文所述大體相同,在此不再重復贅述。
(二)進一步分析
1.?中國式分權對市場分割的影響。如前文所述,市場分割作為機制變量顯著地抑制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那么中國式分權對市場分割是否有影響?本文對此問題進行進一步的探討,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首先,由模型7可知,財政分權對市場分割的回歸系數在5%的置信水平下顯著為正,金融分權對市場分割的回歸系數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為正。其次,在模型7的基礎上,加入控制變量,構建模型8,財政分權仍然通過了較高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但金融分權的影響作用并不顯著。最后,再加入財政分權和金融分權的交乘項,構建模型9,考察二者對市場分割的共同影響。結果表明財政分權對市場分割的回歸系數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為正,金融分權也同樣通過了較高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財政分權和金融分權的交乘項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綜上所述,中國式分權加劇了市場分割這一現象,驗證了本文的假設3。
2.中國式分權對技術創新的影響。在基準回歸分析中,中國式分權對于經濟質量改善的作用效果并不明顯,那么中國式分權對技術創新是否有影響?本文通過技術創新這一機制變量進行進一步的探討,表4的模型10—模型12顯示了中國式分權對技術創新的回歸結果。首先,在模型10—模型12中,財政分權和金融分權的回歸系數均為負,并通過了較高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即中國式分權顯著抑制了技術創新,其次,在模型10的基礎上加入了市場分割和產業結構合理化兩個機制變量,構建模型11,市場分割回歸系數為負并通過了10%顯著性水平檢驗;產業結構合理化回歸系數為正且通過了10%顯著性水平檢驗。最后,再加入財政分權和市場分割與金融分權和產業結構合理化的交互項,構建模型12。結果表明,兩個交互項的回歸系數均為負且通過了較高水平的顯著性檢驗。綜上所述,中國式分權顯著抑制了技術創新,驗證了本文的假設4。
(三)穩健性檢驗
由于本文的經濟增長方式包涵經濟規模與經濟質量兩個維度,一方面,在進行經濟規模穩健性檢驗時,將核心解釋變量進行替換;在經濟質量穩健性檢驗則將核心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均進行替換;另一方面,考慮到內生性問題的存在,運用工具變量法進行穩健性檢驗。
1.基于替換變量的穩健性檢驗。一方面將核心解釋變量進行替換,將財政分權的計算用財政支出分權進行衡量,具體公式為:財政分權=人均地方財政支出/(人均地方財政支出+人均中央財政支出);金融分權用各省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占各省和全國金融機構貸款余額比重計算。另一方面,由于經濟質量檢驗的被解釋變量為全要素生產率,因此選擇其他方法重新測度。測算全要素生產率的方法選擇上,有學者認為DEA方法缺少非投入的影響因素、無法進行合適的檢驗,因此,本文用隨機前沿函數法(SFA)重新計算各省的全要素生產率,并將投入變量的資本存量改用張軍(2004)的計算方法重新測度,以此來確保實證結果的穩健性[25]。回歸結果表5和表6關鍵變量的經濟含義和顯著性均與前文回歸結果所保持一致,說明回歸結果較為穩健。
2.基于工具變量的穩健性檢驗。由于模型設定存在遺漏變量和變量之間的雙向因果關系導致的內生性問題的存在,所以回歸結果不一定具有穩健性。為了解決內生性問題,選用核心解釋變量財政分權和金融分權的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使用二階段最小二乘回歸法(2sls)進行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表7中關鍵變量的經濟含義和顯著性均與前文回歸結果所保持一致,說明回歸結果較為穩健。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含義
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階段逐漸步入新常態時期,經濟增長方式的動力轉換成為當今亟須探討和解決的重要現實問題。本文從中國特殊的體制背景視角出發,通過理論與實證兩個方面深入分析中國式分權對經濟增長方式的邏輯和內在機理,得到以下結論:第一,整體而言,中國式分權顯著地促進了經濟規模擴張;但對于經濟質量而言,財政分權的影響并不顯著,金融分權卻促進了經濟質量的改善。從理論角度出發,中國式分權對于經濟規模和經濟質量的影響機理并不相同。中國式分權使得地方政府產生“為增長而競爭”的投資行為是經濟規模擴張的動力之一,但也應當認識到,這種以長期以要素驅動型的增長方式并不能使得中國走高質量、可持續的發展道路,反而抑制了向創新驅動型轉變的發展模式,阻礙了經濟質量的改善。第二,機制分析顯示,市場分割負向影響了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方式之間的關系;同時,產業結構合理化負向影響了金融分權對經濟增長方式之間的關系。市場分割所形成嚴重的地方保護主義、貿易壁壘阻礙了生產要素流動,制約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而金融分權雖然提高了地方政府金融資源的使用權和支配權,但政企合謀、尋租等行為使得真正需要資金的企業難以獲得,導致產業結構不合理,阻礙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第三,進一步分析,中國式分權顯著地加劇了市場分割;中國式分權顯著地抑制了技術創新。市場分割作為財政分權產生不良后果之一,對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造成嚴重影響。同時,中國式分權使得地方政府按照自利性投資偏好發展經濟,忽視技術創新。
本文的政策意義如下:第一,深化中國式分權體制改革,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發展。在經濟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轉變的重要時期,應當加快改善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相背離的現象,努力構建相對有效的管理格局,確保中央政府在合理范圍內賦予地方政府較大的財政、金融資源空間,?進而促使生產要素自由地流向有利于長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領域,激發中國式分權對經濟增長方式的正向影響作用。第二,加快打破市場分割,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市場分割對于中國經濟增長方式有消極的影響作用,并負向影響了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方式的正向作用。因此,應當拋棄地方“諸侯經濟”思想觀,推進市場整合,加快產品與要素在區域之間的自由流動。此外,中國的比較優勢從過去的廉價要素優勢逐漸轉變為國內市場優勢,再加之受世界經濟下行、新冠疫情等多種不確定因素影響,構建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為新發展格局是中國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必然要求。因此,形成自由統一的國內市場才能夠促使中國式分權更好地為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提供服務。第三,建設地方服務型政府,有效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轉變地方政府官員考核機制,破除以?GDP?為核心的晉升激勵模式,將創新指標、社會指標、綠色環保指標等加入官員考核機制中,為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供有力保障。此外,地方政府在干預金融資源時應當遵循市場規律,取消對民營企業的信貸歧視政策,通過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功能以此來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進而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
參考文獻:
[1]?Haber?S.,A.?Razo,and?N.?Maurer.?The?Politics?of?Property?Rights:Political?Instability,Credible?Commitment?and?Economic?Growth?in?Mexico:1876-1929[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3.
[2]?Lin,J.Y.?and?Liu,Z.,?Fiscal?Decentralization?and?Economic?Growth?in?China?[J].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2000,49(1):1-21.
[3]?傅勇,張晏.?中國式分權與財政支出結構偏向:為增長而競爭的代價[J].?管理世界,2007(3):4-12.
[4]?Davoodi,H.,Xie,D.?&?Zou,H..?Fiscal?Decentralization?and?Economic?Growth?in?the?United?States[J].?Journal?of?Urban?Economics,1999,45:39-228.
[5]?林春.財政分權與中國經濟增長質量關系——基于全要素生產率視角[J].財政研究,2017(2):73-83.
[6]?Restuccia,D.,&?R,Rogerson..?The?Causes?and?Costs?of?Misallocation.?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Working?Paper,No.w23422,2017.
[7]?鄧曉蘭,劉若鴻,許晏君.經濟分權、地方政府競爭與城市全要素生產率[J].財政研究,2019(4):23-41.
[8]?洪正,胡勇鋒.中國式金融分權[J].經濟學(季刊),2017,16(2):545-576.
[9]?Qian,Y.?and?Weingast,B.?R.Federalism?as?a?Commitment?to?Preserving?Market?Incentives[J].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997,11(4):83-92.
[10]Oates,W.?E.Searching?for?Leviathan:An?Empirical?Study[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5,75(4):748-757.
[11]周業安,章泉.財政分權、經濟增長和波動[J].管理世界,2008(3):6-15.
[12]吳延兵.財政分權促進技術創新嗎?[J].當代經濟科學,2019,41(3):13-25.
[13]Shleifer,?Andrei.The?grabbing?hand?:?government?pathologies?and?their?cures[M].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8.
[14]王永欽,張晏,章元,等.中國的大國發展道路——論分權式改革的得失[J].經濟研究,2007(1):4-16.
[15]林毅夫,劉培林.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與地區收入差距[J].經濟研究,2003(3):19-25.
[16]陸銘,陳釗,嚴冀.收益遞增、發展戰略與區域經濟的分割[J].經濟研究,2004(1):54-63.
[17]?單豪杰.中國資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年[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8,25(10):17-31.
[18]?呂冰洋,馬光榮,毛捷.分稅與稅率:從政府到企業[J].經濟研究,2016,51(7):13-28.
[19]?詹新宇,劉文彬.中國式財政分權與地方經濟增長目標管理——來自省、市政府工作報告的經驗證據[J].管理世界,2020,36(3):23-39.
[20]?何德旭,苗文龍.財政分權是否影響金融分權——基于省際分權數據空間效應的比較分析[J].經濟研究,2016,51(2):42-55.
[21]?陸銘,陳釗.分割市場的經濟增長——為什么經濟開放可能加劇地方保護?[J].經濟研究,2009,44(3):42-52.
[22]干春暉,鄭若谷,余典范.中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和波動的影響[J].經濟研究,2011,46(5):4-16.
[23]Xu?C.?The?fundamental?institutions?of?Chinas?reforms?and?development[J].?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2011,49(4):1076-1151
[24]周黎安.晉升博弈中政府官員的激勵與合作——兼論我國地方保護主義和重復建設問題長期存在的原因[J].經濟研究,2004(6):33-40.
[25]張軍,吳桂英,張吉鵬.中國省際物質資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經濟研究,2004(10):35-44.
Chinese?Style?Decentralization?and?Economic?Growth?Mode:?Influence
Mechanism?and?Path
XIE?Jia-zhi,HE?Wen-yu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China?is?in?the?key?stage?of?high-quality?economic?development?under?the?new?normal.?Further?deepening?the?reform?of?the?Chinese?style?decentralization?system?and?effectively?promoting?the?transformation?of?economic?growth?mode?have?become?major?practical?problems?to?be?solved.This?paper?unifies?fiscal?decentralization?and?financial?decentralization?into?the?research?framework?of?Chinese?style?decentralization.?Based?on?the?theoretical?analysis?and?provincial?panel?data?from?2002?to?2016,?this?paper?empirically?analyzes?the?relationship?between?Chinese?style?decentralization?and?economic?growth?mode?by?using?fixed?effect?model.?The?findings?are?as?follows:?first,?Chinese?style?decentralization?significantly?promotes?the?expansion?of?economic?scale;??for?economic?quality,?the?impact?of?fiscal?decentralization?is?not?significant,?but?financial?decentralization?promotes?the?improvement?of?economic?quality.Second,?mechanism?analysis?shows?that?market?segmentation?negatively?affects?the?relationship?between?fiscal?decentralization?and?economic?growth?mode;?at?the?same?time,?the?rationalization?of?industrial?structure?has?a?negative?impact?on?the?relationship?between?financial?decentralization?and?economic?growth?mode.Third,?further?analysis?shows?that?Chinese?style?decentralization?significantly?intensifies?market?segmentation,?and?Chinese?style?decentralization?significantly?inhibits?technological?innovation.?This?study?provides?a?new?perspective?for?China?to?accelerate?the?transformation?of?economic?growth?mode,?and?provides?the?corresponding?policy?reference.
Key?words:Chinese?style?decentralization;?economic?growth?mode;?market?segmentation;rationalization?of?industrial?structure
(責任編輯: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