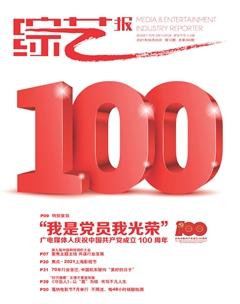主旋律電影的市場化探索“新主流”電影創作密碼
鐘茜


“主旋律”是今年上海電影節的高頻詞。
6月13日,在題為“主旋律電影的市場化探索”的金爵論壇上,制片人梁靜、導演李駿、導演尹力、編劇趙寧宇、導演鄭大圣等,圍繞主旋律電影創作、技術、市場等不同維度,分享經驗體會,對“如何處理技術和藝術的關系”“如何塑造真實鮮活的主流人物”等發表見解。
中國電影由“主旋律”邁向“新主流”的變化有目共睹。與會嘉賓不約而同地表示:主旋律電影其實就是主流電影,主旋律影片之所以越來越受年輕觀眾歡迎,正是因為其表現形式受到觀眾的喜愛。
從主旋律到“新主流”電影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金剛川》編劇趙寧宇認為,中國主旋律電影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20世紀90年代初涌現出一批優秀代表作;到2002年、2003年,電影產業改革,主旋律影片升級,像《張思德》《云水謠》《鐵人》等在敘事及視聽美學上,對我們這代創作者影響很深;當下,一批優秀的中青年電影人投入‘新主流電影創作,各方面成績都非常不錯,并在不斷探索中前進。”在趙寧宇看來,主流電影發展得好,不僅能促進中國電影的整體進步,還能夠推動電影人的自我完善和升級。
說到中國主旋律影片,不得不提到知名導演尹力,趙寧宇所提及的《張思德》《云水謠》《鐵人》正是尹力的代表作。尹力強調,優秀的主旋律電影之所以能夠成功,本質在于跳出了主旋律命題作文思維,回歸電影本體,回歸市場,回歸藝術規律。
從演員到制片人、出品人、董事長,梁靜先后操刀制作《我和我的祖國》《金剛川》和即將上映的《革命者》等主旋律影片。梁靜認為,主旋律電影其實就是主流電影,因為它的價值觀代表了正能量,“在很多國家都有這樣的電影,而且都相對在商業上非常成功,我們還有很多空間可以探索。”
李駿執導的災難片《無限深度》將于年內上映,這是一部在災難背景下,展現新鐵道人如何傳承老鐵道兵精神的電影。李駿同樣認為,主旋律就是符合主流價值觀的電影,《無限深度》彰顯英雄主義,但主要表現的是平民英雄,“是在特殊狀況下普通人迸發出的、無比強大的能量和勇氣,這種價值觀是全世界共通的,也是主流的。”
作為《1921》的聯合導演,鄭大圣也提到了黃建新導演在拍攝《1921》時和他說的話:“與其說是主旋律,不如說是主流電影。”“我們所有電影工作者、創作者都有一個共識,基于電影規律本身,我們更愿意把它理解為主流電影。”
“技術”為“共情”服務
當下的“新主流”大片,大題材、大場面、大制作已成為創作常態,“技術”成了主旋律電影市場化繞不開的關鍵詞。
李駿導演的《無限深度》有1600多個特效鏡頭,“災難片比較考驗技術,為了在視覺上帶給觀眾災難體驗,要運用大量電腦特效,制作難度非常大。”但他認為,觀眾之所以愿意走入影院,是因為共同的情感體驗。“電影院的技術革新,不管是IMAX還是CINITY,都是為了增強觀眾的觀影共情。”
尹力導演對李駿談到的“共情”深有感觸,“無論科技如何進步,不變的是在電影中把普通人的情感調動起來,從而跟觀眾達到共情互動的藝術效果。”
鄭大圣導演親歷了從膠片時代到數字化時代的技術革新,在拍攝《1921》時,黃建新導演仍不停地告誡他:“不要被最新的、最炫的技術所誘惑,為了技術去設計場面或者鏡頭。”黃建新會指著監視器前演員們生動的面孔說:“你看,這是任何高科技達不到的。”鄭大圣由衷地表示,“只有塑造好人物,高新技術才能為影片加分。”
見事件又見人物
在主旋律電影的創作中,如何做到“見事件又見人物”,同樣值得探討。
影片《1921》回到歷史現場,全景式再現平均年齡不到28歲的先輩們;《我和我的祖國》用一個個小人物的故事折射整個大時代的變化;《金剛川》展現炮火下小人物的群像……縱觀近年來主旋律電影的敘事方式,越來越多的影片將大時代背景和小人物經歷有機結合。
鄭大圣以《1921》中的十幾位一大代表為例,談道:“回到歷史現場,他們就是小人物。回到人物本身,我們會更加感佩,他們能在這么年輕的時候,以天下為己任,為四萬萬人的救亡圖存謀出路,這是多么可貴。”
尹力特別以《張思德》《鐵人》為例來強調小人物的重要,“為張思德立傳,就是為最普通的人作傳。千千萬萬默默無聞、訥于言敏于行的小戰士,構成了革命事業的基礎。”
以總制片人身份參與《金剛川》《革命者》創作的梁靜談道:“要讓大家感受到這個時代是由一個個小人物帶動起來的,任何大人物都是從小人物成長起來的。”電影《革命者》講述李大釗追尋正確革命道路的歷程,監制管虎帶著導演徐展雄、編劇團隊,通過不同階層、不同職務、不同社會角色的八個角度,呈現李大釗的真實形象。“為什么現在大家都關注小人物的力量?就是因為這個時代是由一個個小人物建立起來的。”梁靜說。
趙寧宇也認為要挖掘普通人的故事,“除了歷史上有名有姓的人物,普通的戰士、學生、工人、農民等,實際上也有巨大挖掘價值,可能是未來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