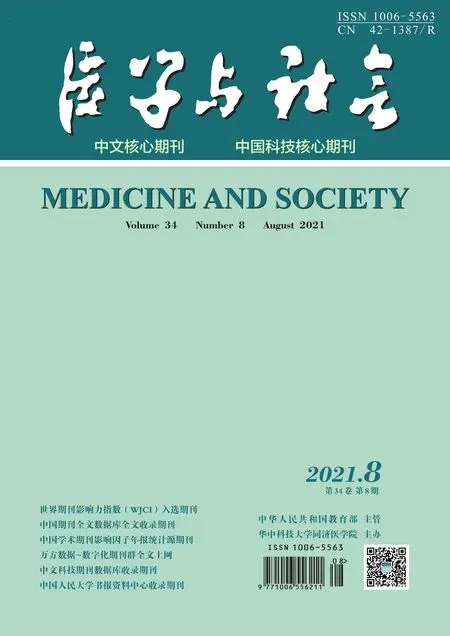藥品帶量采購中國家組織藥品集中采購和使用聯合采購辦公室與中標企業超額供應問題的博弈分析
譚清立,王昊陽
廣東藥科大學醫藥商學院, 廣東中山,528400
藥品帶量采購是近年來我國解決“看病貴”問題的關鍵舉措,實施以來成效顯著[1-3]。國家組織藥品集中采購和使用聯合采購辦公室(以下簡稱“聯采辦”)于2018年11月在11個試點城市開展了第一批“4+7”帶量采購工作,并分別于2020年的1月17日與7月29日完成了第二批、第三批帶量采購的招標工作。第四批帶量采購的招標工作也于2021年1月啟動,對45個品種進行集中采購。
在聯采辦2018年發布的《4+7城市藥品集中采購文件》(GY-YD2018-1)、2019年發布的《全國藥品集中采購文件》(GY-YD2019-2)、2020年發布的《全國藥品集中采購文件》(GY-YD2020-1)以及2021年發布的《全國藥品集中采購文件》(GY-YD2021-1)中,都提到了“醫療機構將優先使用本次藥品集中采購的中選藥品”“在提前完成采購量的情況下,超額部分中選企業仍按中標價進行供應”“采購協議每年一簽,續簽協議時,約定采購量原則上不少于該中選藥品上年的約定采購量”。可見,在中選藥品供應價格不變的前提下,聯采辦對中標企業的持續供應持鼓勵態度。由于最終的實際采購量難以被準確預估,采購協議中并未對中標企業供應量的上限做出規定,在市場有需求的情況下,許多中標企業的供應量往往會超出約定的市場份額。2020年10月27日江西省發布的《落實國家組織藥品集中采購和使用工作情況通報》顯示,在半年不到的時間里,36個品種中已有26個品種完成了約定采購量,其中阿比特龍完成了約定采購量的2433.85%。帶量采購政策下藥品市場對中選品種的消化極其迅速,這也給中標企業的供應帶來了更多機遇與挑戰。
藥品帶量采購政策的落地,擠掉了中標企業的營銷成本,并且對采購量進行了約定,理論上能讓中標企業將更多生產資料投入到創新研發中。但在實際情況下,由于采購的總額難以預估,往往需要中標企業超額地進行藥品供應,使中標企業獲得了更多“以價換量”的機會。若更多的中標企業在超額供應中取得規模效益,中標企業可能會將更多的生產資料投入到藥品的超額供應中,在創新藥物研發上的支出將有所削減。此外,市場的份額有限,若超額供應的中標企業顯著增加,留給未中標企業與未中選品種的市場份額將進一步被擠壓,過快的“洗牌”速度可能會給中標藥企帶來更多供應上的壓力與挑戰,不利于藥品市場創新活力的激發。這些因素可能會對藥品市場的長遠發展產生一定不利的影響。
本文通過研究聯采辦與中標企業在超額供應問題上的利益博弈,分析影響中標企業高層次創新投入和藥品供應投入意愿強弱的因素,為政府引導中標企業進行生產資料的合理配置,從而在滿足藥品市場龐大需求與激發藥品市場創新活力之間尋求一定的平衡提供依據。本研究可為推動藥品帶量采購政策的有效落實、提高我國制藥企業的創新水平、促進藥品市場的持續發展提供一定的理論指導。
1 資料來源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本研究選取2019年我國藥品帶量采購的約定采購量與實際采購量、中選藥品采購量平均占相同通用名藥品采購量的比重等數據作為論據,分析影響聯采辦與中標企業在超額供應問題上決策的因素,并對博弈結果的分析進行論證。所選取指標來自政府部門近年發布的藥品集中帶量采購文件、《關于提高研究開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比例的通知》(財稅〔2018〕9號)、中商產業研究院數據庫等。
1.2 研究方法
本文運用了博弈論分析藥品帶量采購中的超額供應問題。博弈論著重分析博弈雙方的個體的預測行為和實際行為,并研究它們的優化策略。運用博弈論對聯采辦與中標企業在超額供應問題上的利益訴求進行分析,在博弈模型中對雙方策略的相互作用進行一定的量化,對探究聯采辦在超額供應問題上的優化策略具有重要意義。在大多數情況下,雙方的博弈既包含了合作的因子(滿足國民的用藥需求),也包含了沖突的因子(企業希望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聯采辦希望維持藥品市場的長期穩定發展)。此外,雙方對彼此的收益函數缺乏準確的把握。因此,本文使用不完全信息的非合作博弈模型對聯采辦與中標企業的博弈進行分析。
2 博弈分析與模型構建
藥品帶量采購政策的預期效應之一為擠掉藥品銷售費用等水分,以是否通過藥品一致性評價作為參與帶量采購的門檻,倒逼藥企加大研發投入,促進醫藥產業的健康發展。2016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開展仿制藥質量和療效一致性評價的意見》(國辦發〔2016〕8號)提出“通過一致性評價的藥品品種,在醫保支付方面予以適當支持,醫療機構應優先采購并在臨床中優先選用”“同品種藥品通過一致性評價的生產企業達到3家以上的,在藥品集中采購等方面不再選用未通過一致性評價的品種”。據Wind、中康產投中心統計,2016年以來,我國上市藥企的研發支出總額與研發支出增長率都在逐年上升,2016-2018年的研發支出增速分別為24%、28%、43%。仿制藥一致性評價的推進促進了藥企研發投入的增加,創新的主要方向為與原研藥的藥學等效PE(體外藥學一致)與生物等效BE(體內生物利用度一致),并未對活性數據等標準作一定的要求,創新的程度與層次較低[4]。就我國藥企的總體情況而言,推進仿制藥一致性評價可以說是一條從仿制向創新轉型過渡的捷徑,相較于“me-better”“me-first”等創新藥,通過仿制藥一致性評價的研發難度較低,投入耗時較少,風險較小。隨著帶量采購政策的推進,更多的藥企邁過了一致性評價的門檻,參與競標的藥企數量越來越多,價格競爭愈發激烈,中選品種的中標價格持續走低。但近年來帶量采購的范圍有所擴大,競標規則逐漸完善,中標企業可以通過“以量換價”與“超額供應”獲得可觀的收益。由于我國制藥產業的研發起步較晚,基礎薄弱,藥企以生產仿制藥為主,短時間內很難實現大規模的轉型。比起需要8-12年研發時間與5-12億美元研發資金的原研藥,中標企業可能更愿意將時間與成本投入到仿制藥一致性評價與超額供應中,因為其風險較小,收益更為穩定。
另一方面,仿制藥一致性評價的推進有效促進了藥品質量與療效的提高,為帶量采購政策的落實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帶量采購政策的推進以及超額供應規模的擴大也會激發藥企開展一致性評價的興趣,帶動藥企研發費用的上升,在我國藥企研發基礎比較薄弱的前提下,有利于提高我國藥企的整體研發層次。但需要注意的是,若更多的制藥企業只滿足于通過仿制藥一致性評價,爭奪中標企業的名額以享受超額供應的紅利,可能會出現我國藥企在藥品創新研發上的投入不斷增加,但“me-better”“me-first”等高層次創新成果的專利申請數量沒有明顯增加的現象。
隨著藥品帶量采購政策的逐步推進,“以價換量”已成為一個新的利潤增長點。在單位利潤較低的情況下,中標企業希望通過供應更多數量以彌補藥品一致性評價及其他方面不斷上升的成本并獲得利潤,聯采辦也愿意看到帶量采購政策與仿制藥一致性評價進程的互相推進。但中標藥企的總投入是有限的,若中標企業將更多的生產資料投入到一致性評價與中選品種的供應當中,其在高層次藥品創新方面的投入可能會有所下降。
假設在落實藥品帶量采購政策的過程中,聯采辦與中標企業存在博弈的因素。中標企業希望在藥品供應中最大化自身的經濟效益;而聯采辦則希望在推進帶量采購發展的同時提高企業的創新水平,維持藥品市場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根據雙方不同的利益訴求建立以下博弈模型[5-6]。
①參與者:聯采辦,中標企業
②策略選擇:
聯采辦——控制超額供應規模并鼓勵高層次的創新;鼓勵超額供應
中標企業——加大在高層次創新上的投入(me-better藥、me-first藥等);加大在中選品種供應上的投入(仿制藥一致性評價與超額供應)
條件假設:設聯采辦鼓勵高層次藥品創新并控制超額供應規模的宏觀調控成本為C1,在聯采辦鼓勵高層次創新而中標企業加大高層次創新投入時,聯采辦能夠獲得一定的社會效益S(中標企業的高層次創新投入增加,我國藥企的高層次創新能力提高等)。在聯采辦鼓勵高層次創新而控制超額供應規模的條件下,中標企業加大高層次創新投入的總收益為R1+R2+G-T1(R1、R2分別為企業加大高層次創新投入下的藥品供應收益與高層次創新收益,G為政策扶持與補貼,T1為加大高層次創新投入的市場風險),此時聯采辦的收益為S-C1;中標企業加大藥品供應投入的總收益為R3+R4-T2(R3、R4分別為企業加大藥品供應投入下的藥品供應收益與高層次創新收益,T2為聯采辦鼓勵高層次創新并控制超額供應規模時,中標企業加大藥品供應投入的市場風險),此時聯采辦的收益為-C1[7-8]。設聯采辦鼓勵超額供應的宏觀調控成本為C2,由于目前藥品帶量采購中的超額供應規模較大,中標企業持續加大超額供應投入在帶來社會效益的同時也會帶來一定的隱患(中標企業高層次創新的意愿減弱等),為簡化模型,設聯采辦的收益僅為-C2。此時中標企業加大高層次創新投入的收益為R1+R2-T1;中標企業加大藥品供應投入的收益為R3+R4。其中,C1>C2(相較于鼓勵超額供應,鼓勵高層次創新需要更大的政策支出)[9-11]。由此建立以下的博弈矩陣,見表1。

表1 中標企業與聯采辦的博弈矩陣
用β表示聯采辦鼓勵高層次藥品創新并控制超額供應規模的概率,θ表示企業選擇加大高層次藥品創新投入的概率。聯采辦的混合策略為R1=(β,1-β),而中標企業的混合策略R2=(θ,1-θ)[12]。因此,聯采辦的期望收益函數為:
V1(R1,R2)=β[θ(S-C1)+(1-θ)(-C1)]+(1-β)[θ(-C2)+(1-θ)(-C2)]
=βθS-βC1+βC2-C2
V1對β求偏導,令бV1/бβ=0,解得:θ=(C1-C2)/S
(1)
而企業的期望收益函數為:
V2(R1,R2)=θ[β(R1+R2+G-T1)+(1-β)(R1+R2-T1)]+(1-θ)[β(R3+R4-T2)+(1-β)(R3+R4)]
V2對θ求偏導,令бV2/бθ=0,解得:β=[(R3+R4)-(R1+R2)+T1]/(G+T2)
(2)
因此,該模型的納什均衡為:
3 博弈結果的分析與討論
3.1 聯采辦的收益函數分析
式(1)表明,中標企業選擇加大高層次創新投入的概率大小受C1-C2與S的比值影響。由于S為聯采辦鼓勵高層次創新獲得的政策紅利,并非中標企業考慮范圍內的主要因素,因此著重討論C1-C2的值對中標企業策略選擇的影響。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當C1-C2的差值較大時,中標企業加大高層次創新投入的概率較高。即聯采辦在鼓勵高層次創新上投入的政策成本越大,中標企業加大高層次創新投入的概率越大。這表明:更大的政策扶持力度有利于促進中標企業的高層次創新。在激勵政策投入一定的情況下,激勵政策的針對性將成為激勵政策能否取得成效的關鍵因素[13-14]。2018年9月21日發布的《財政部 稅務總局 科技部關于提高研究開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比例的通知》 (財稅〔2018〕99號)中提到,“企業開展創新活動中實際發生的創新費用,未形成無形資產計入當期損益的,在按規定據實扣除的基礎上,在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間,再按照實際發生額的75%在稅前加計扣除;形成無形資產的,在上述期間按照無形資產成本的175%在稅前攤銷”。由于高層次藥物創新會產生更高的創新費用,按比例攤銷成本的稅收政策將更為有效地促進中標藥企的高層次創新,但同時也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政策成本。
3.2 中標企業的收益函數分析
式(2)表明,聯采辦鼓勵高層次創新的概率大小受(R3+R4)-(R1+R2)、G、T2、T1四個值的影響。(R3+R4)-(R1+R2)為中標藥企加大藥品供應投入與加大高層次創新投入的經營收益差,G為政策補貼,T2為聯采辦鼓勵高層次創新并限制超額供應規模時中標企業加大藥品供應投入的風險,T1為中標企業加大高層次創新投入的市場風險。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當[(R3+R4)-(R1+R2)]的值較大時,聯采辦鼓勵創新的概率較大。即當中標企業加大藥品供應投入的經營收益遠大于加大高層次創新投入的經營收益時,聯采辦更有可能鼓勵創新并限制超額供應規模。一方面,2015年以來國家通過發布更多涉及醫保、醫療、醫藥等多個維度的醫藥類政策,建立了許多新的行業標準,朝著與國際接軌的方向邁進,對藥品創新的重視程度明顯提高,并在藥品、流通、醫保等方面出臺了具有針對性的藥品創新激勵政策。在2015年《國務院關于改革藥品醫療器械審評審批制度的意見》(國發〔2015〕44號)中,提出對創新藥實施特殊的審批制度,有效地縮短了創新藥的上市審批時間,提高了審批的效率;2016年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制定的《化學藥品注冊分類改革工作方案》縮小了創新藥的范圍,鼓勵真正意義上的藥品創新,對創新藥設置最長6年的數據保護期與最長5年的專利補償期,推進制藥企業從模仿創新到更高水平創新的升級。另一方面,我國的化學藥物創新基礎比較薄弱,研發投入水平較低,對仿制藥市場的依賴程度較高。Wind、中康產投中心的化學企業投入數據顯示,我國年創新研發費用超過5億元的藥企數量較少,2018年恒瑞集團的創新研發費用達到了26.7億元,位于我國藥企之首,但仍與國外的醫藥巨頭具有明顯的差距。更多的藥企滿足于仿制藥的生產,扎堆現象顯著。由于我國藥品市場的剛需較大,集采擴圍后單個中標企業供應的范圍擴大,藥品需求難以準確預估,使得中標藥企通過超額供應最大化“以價換量”效益的機會較多。同時,藥品一致性評價和生產原料等成本的上升使得中標企業需要在藥品供應投入更多的生產成本,“以價換量”的政策導向又需要中標企業供應更多的量才能獲得更大的規模利潤,中標企業高額的生產供應成本將對其高層次創新投入產生一定的擠壓。若中標企業藥品供應投入的經營收入遠大于進行高層次藥品創新的收入,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標企業的生產資料分配集中于藥品供應。此時聯采辦更有可能對中標企業超額供應的規模做出一定的控制,加大對高層次創新的激勵程度,引導整個藥品市場從以仿制藥生產為主向“仿創結合”過渡。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當G的值較大時,聯采辦鼓勵高層次創新的概率較小。即政策扶持的力度和針對性較強時,聯采辦鼓勵高層次創新并控制超額供應規模的可能性較低。這表明,當先前宏觀調控效果較好時,中標企業在創新和供應的投入分配比較合理。此時,聯采辦會將更多的政策支出投入到藥品質量監管等其他方面上,符合實際的情況。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當T2的值較大時,聯采辦鼓勵創新的概率較小。即中標企業加大藥品供應投入的風險越大,聯采辦加大鼓勵創新力度限制超額供應規模的可能性較低。這表明,當中標企業加大藥品供應投入的風險逐漸提高導致預期收益明顯下降時,超額供應的規模將有所縮小,對藥品市場上的正常供應產生一定影響。這種風險可能是由于如果聯采辦提高了中標企業進行超額供應的門檻(如對進行超額供應的企業提出了更高的質量水平與創新水平要求),將導致符合資格進行超額供應的企業數量減少。此時中選品種供應缺口可能會引發一定的市場波動,對藥品市場造成一定的不利影響。因此聯采辦將對藥品市場進行科學的宏觀調控,引導中標企業將創新投入水平和藥品供應投入水平維持在一個合理的區間。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當T1的值較大時,聯采辦鼓勵高層次創新的概率較大。即中標企業加大高層次創新投入面臨的市場風險越大時,聯采辦加大鼓勵創新力度限制超額供應規模的可能性越高。這表明,在中標企業高層次研發的風險較大時,中標企業在高層次創新上的投入會相對保守。此時,聯采辦會將更多的政策支出投入到高層次藥品研發的政策激勵上。
4 建議
4.1 鼓勵超額供應但適度控制其規模,為未中標企業留下一定的發展空間
由于帶量采購政策實施不久,納入帶量采購的中選品種占總的藥品品類的比例十分有限。在藥品帶量采購政策提高了藥品市場準入門檻的作用下,藥品市場過快的洗牌速度將有可能導致藥企數量銳減。隨著今后納入帶量采購的藥品品種越來越多,藥品市場上的供應企業的數量不足可能會影響到帶量采購政策的推進、藥品供應的穩定以及市場的創新活力[15-16]。
為此,聯采辦可以適當限制中選企業的超額供應規模(如提高中標企業超額供應的門檻或者增加單個品種中標的企業數量等),在提前完成約定采購量的情況下,可將一部分超額采購量劃給通過該品種一致性評價但未入圍的企業,同時對未中選品種的價格與供應數量做出一定的限制[16]。2019年2月19日,上海市醫療保障局、上海市衛生健康委員會、上海市藥品監督管理局聯合發布的《關于本市做好國家組織藥品集中采購和使用試點有關工作的通知》(滬醫保價采〔2019〕3號)中提到了針對未中選品種的兩項限制政策:一是提高使用未中選藥品的個人自負比例,最高提高比例達20%;二是醫療機構可在優先采購中選品種的前提下適量采購價低質優、有療效保證的“未中選藥品”,但其采購數量不能超過中選品種的采購數量。在推進中選品種帶量采購的同時給予未中選企業一定的生存空間,這有利于維持藥品市場的健康發展,為藥企更高層次的創新營造穩定的市場環境。
4.2 加大鼓勵企業進行高層次創新的政策扶持力度與政策針對性
目前,相較于增加高層次的藥品研發投入,我國的大部分藥企更愿意增加在藥品供應上的投入,對于參與藥品帶量采購的中標企業來說更是如此。
為改變我國藥品市場“重供應、輕創新”的局面,聯采辦可針對新藥的創新投資較大、周期較長、機會成本較高以及現有藥品知識產權保護法律不完善、創新方向同質化等重點問題,推出針對性的鼓勵措施。針對國內藥企創新方向同質化等問題,聯采辦可聯合相關部門,在我國藥企涉足較少的藥品創新領域頒布更多的激勵政策,引導藥企在不同領域進行創新,減少藥企的創新扎堆與成果抄襲等不良現象,推進我國藥企創新研發方向的差異化。同時,可由國家相關部門牽頭,每年定期舉行藥物創新學術研討會,邀請國內與國外的醫藥創新巨頭參加會議,就不同藥物領域的創新方向、創新前景等進行討論,增強我國在高層次藥品創新上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此外,還可對藥企的創新成果實行梯度激勵制度,加大對“me-better”“first-in-class”等更高階段創新成果的政策扶持(如更大幅度的稅收減免、更長的專利保護期等),推進我國藥企創新層次的提高[17]。
4.3 將中標藥企的實際供應量多少與其高層次創新投入大小掛鉤
在藥品帶量采購的超額供應規模逐漸擴大的情況下,聯采辦可以聯合有關部門出臺相關政策,將中標企業的實際供應量與其高層次創新投入掛鉤,倒逼中標企業加大在高層次創新上的投入。
通過制定一定的衡量標準,在中標企業的高層次創新投入達到一定的標準時,給予其額外的供應量。中標企業的高層次創新投入越大,分配給其的供應機會越多。若中標企業的預期創新投入較小,則同樣以高層次創新投入的水平為標準,將預計的超額供應量分配給已過評但未入選帶量采購的藥企。將宏觀調控與市場機制相結合,平衡中標企業在高層次上的創新投入與藥品供應上的投入,引導中標企業將其在中選藥品供應中獲得的收益更多地投入到高層次藥物的創新研發中,而不是單一地投入到藥品一致性評價與超額供應中,從而最終促使“藥品供應促進藥品創新的發展,藥品研發反過來推動藥品供應的發展”這一良性循環的形成。
5 結論
在藥企生產資料投入一定的前提下,由于產業基礎薄弱、創新觀念不強、引導相對不足等因素,目前參與藥品帶量采購的大部分中標藥企更傾向于將生產資料投入到中選品種的供應當中。隨著藥品帶量采購政策的深入推進和持續發展,聯采辦應聯合相關部門將激勵高層次創新的政策與控制超額供應規模的政策結合起來,使中標藥企超額供應的規模趨于穩定,引導中標企業將更多的生產資料投入到更高層次的藥品研發當中,尋求供應與創新之間的動態平衡,從而促進我國醫藥產業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