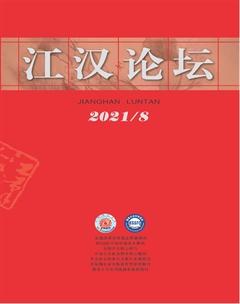《穆天子傳》意象演變及其經典化過程

摘要:南北朝時期《穆天子傳》的經典意象已經確立。謝惠連《雪賦》為后世賦雪詩確立了意象模范,而謝朓樹立“白云謠”離別、思故的典范。唐人賦予典故更豐富的內涵,《穆天子傳》事典、物典的意義逐漸發生了改變。“白云謠”常引申為送遠、懷故、思故之曲,繼而指相思之歌、道家神仙之唱。“白云之期”又指約期,其特指與仙人相會。“黃竹詩”的初始含義指皇帝憫民愛民憂民,后成為愛民之詩,甚至是彰顯帝王圣德之詩,它還是詩人詠雪詩的通稱。《穆天子傳》的經典化過程其實也就是它被接受的過程,與時代學術背景有關。探討《穆天子傳》在傳播與接受過程中的經典意象的確立、典故意義的演變,有助于了解其所處的時代文化,重新審視《穆天子傳》的文學價值。
關鍵詞:《穆天子傳》;白云謠;黃竹詩;經典意象;演變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穆天子傳》綜合研究”(20FZWB016);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項目(JD18067)
中圖分類號:I206.7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854X(2021)08-0080-09
1700多年來,《穆天子傳》不但為陶淵明、謝莊、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王世貞等歷代重要詩人所重視,到了明中后期更是成為以王世貞為首的文學復古派的案頭書。它還以道書、歷史書和地理書的身份,出現在道士、歷史研究者、地理研究者的視野中。《穆天子傳》中的“瑤池”“八駿”“白云謠”等意象激發了作家的情思與詩意,促進了大量文學作品的產生,豐富了古代文學史。此外,詩人閱讀《穆天子傳》后寫的讀書詩、重要文人談論《穆天子傳》的書信、明中后期大量的模仿作品的出現以及清代樸學派對此書的推崇,無不顯示出《穆天子傳》曾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和心理共鳴,能夠滿足讀者的審美需求。我們發現《穆天子傳》的人物形象與典故意象得到開發,其文學價值被挖掘,書中故事被改造等等事例,證明《穆天子傳》在唐前已成為文學經典,具有重要的地位。《穆天子傳》經典化過程關涉到一定時代的社會實踐和文化觀。對其經典化過程進行梳理不僅可以幫助我們從側面了解所關涉的人物的價值觀,還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其所處的時代文化。
一、兩晉時期《穆天子傳》經典意象的確立
兩晉時期戰爭不斷,書籍時有散佚。當時保留下來的文集又幾經兵燹,輾轉于今,已是稀少難見。據已有文獻可知,兩晉時期文人對《穆天子傳》典故的引用較少。到了南北朝時期,皇家圖書館與大世家存有《穆天子傳》。我們通過考察南北朝時期留存下來的文獻,發現以王、謝二大世族與皇家為中心的詩人群體對此書具有濃厚的興趣。南北朝時期,比較著名的皇家詩人群體主要有三:南齊竟陵王蕭子良詩人群體、梁代蕭衍詩人群體、蕭綱詩人群體。實際上這三大詩人群體的主要成員存在著交集,比如梁武帝蕭衍、任昉、沈約。這兩個群體甚至還存在承繼關系,比如蕭衍與蕭綱。王、謝兩大世家的子弟亦屬于這三大群體。郭璞、葛洪之后,這三大群體中的謝惠連、謝莊、江淹、謝朓、王融、任昉、劉勰、徐陵、庾信等人喜讀《穆天子傳》,多援引書中典故。“穆滿八駿”“黃竹詩”“白云謠”等經典往往被認為是在唐代時確立,但實際上并非如此。
“舊時王謝堂前燕”中的“王謝”指的是陳郡謝家和瑯琊王家兩大高門世家,這兩家人才輩出,有較高的政治地位、文化地位,具有代表性,我們以這兩家為樣本來考察《穆天子傳》意象的確立。
(一)《雪賦》為后世賦雪詩確立了意象典范
陳郡謝氏家族以曹魏的典農中郎謝纘為始祖。其子謝衡“以儒素顯”官至太子少傅,謝氏家族在他的帶領下逐步壯大。謝衡參加了討論《穆天子傳》翻譯得失的“束、王之辯”。這說明謝衡本人是研究過《穆天子傳》的。我們通過考察西晉至梁朝時期謝衡后世子孫著作發現,謝氏家族傳留有《穆天子傳》一書。
謝惠連《雪賦》是南朝有名的“物色”小賦,最早見于梁昭明太子所編的《文選》。其《雪賦》兩次引用《穆天子傳》典故,賦曰:“臣聞雪宮建于東國,雪山峙于西域。岐昌發詠于來思,姬滿申歌于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盈尺則呈瑞于豐年,袤丈則表沴于陰德。雪之時義遠矣哉!① 又云:“于是臺如重璧,逵似連璐。”② 周穆王姓姬,名滿。《穆天子傳》卷五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所作詩三章即后人所謂“黃竹詩”。《穆天子傳》卷六載周穆王為盛姬建“重璧之臺”。謝惠連《雪賦》寫盡梁苑大雪之景色,傳為妙文,為世人所稱頌。據《謝宣城集》載謝朓曾和朋友朱孝廉、檀秀才、江朝請、陶功曹各賦雜曲,有朱孝廉者作《白雪曲》轉述謝惠連《雪賦》的內容,詩云:“凝云沒霄漢,從風飛且散。連翩下幽谷,徘徊依井干。既興楚客謠,亦動周王嘆。所恨輕寒質,不迨春歸旦。”③ 周王,指周穆王姬滿。“周王嘆”典出《穆天子傳》卷五周穆王大雪哀民作“黃竹詩”。
《雪賦》篇中引用周穆王大雪哀民的典故為后世賦雪詩確立了意象典范,影響至深。劉璠的《雪賦》云:“已墮白登之指,實愴黃竹之心。”④ “黃竹詩”后成為詠雪之作的代表及代稱。如李世民有《喜雪》詩云:“儻詠幽蘭曲,同歡黃竹篇。”⑤后喻為天子詠詩。正如唐順之云:“亦知圣主揮天藻,不羨周家黃竹詞。”⑥ 此賦影響力可見一斑。
(二)《宋孝武宣貴妃誄并序》開后妃祭文引《穆天子傳》之先例
謝莊,字希逸,劉宋辭賦家。其作《月賦》與族兄謝惠連之《雪賦》并稱南朝小賦“雙璧”。《宋孝武宣貴妃誄并序》亦有引《穆天子傳》典故,例如:“國軫喪淑之傷,家凝■庇之怨。⑦ “涉姑繇而環回,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⑧
《穆天子傳》重“禮樂”,不僅在第五卷提出“禮樂其民”的施政主張,還在第六卷(即汲冢竹書《雜書十九篇》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極力鋪陳后妃的葬禮。盛姬謚為“哀淑人”,穆天子“永念傷心”,時思淑人盛姬,哀傷流涕,故“喪淑之傷”,既是實指齊武帝失殷淑儀之傷,也是借穆天子喪盛姬之痛的典故喻殷淑儀受帝王的寵愛。“姑繇”“樂池”典故亦出自《穆天子傳》。卷二載:“天子西征至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卷六載盛姬亡后,“天子乃殯姬于谷丘之廟”,“葬于樂池之南”。殤祀時,“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圜喪車”。穆王對她情深意重。盛姬死后,其葬禮奢侈,為人詬病:“昔宋桓、盛姬,前史譏其驕惑。”⑨ 但作為深得帝王寵愛的妃子,其榮寵與奢華的葬禮又為后妃所追慕。用這兩個典故來比喻殷淑儀得寵及齊武帝的哀傷極為恰當。《穆天子傳》是后妃喪禮文化的先導,而《宋孝武宣貴妃誄并序》開帝妃祭文引《穆天子傳》之先例。謝莊雖因此文得齊武帝贊賞,卻也因此受到牽連。
(三)謝朓樹立“白云謠”離別、思故的典范
謝朓,字玄暉,曾出任宣城太守,故又稱為“謝宣城”。謝朓之文為世人所稱誦。如梁簡文帝蕭繹《與湘東王書》贊曰:“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⑩謝朓鐘愛《穆天子傳》的“白云謠”,多次在其作品中引此典故,甚至直接化用。如《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箋一首》詩云:“白云在天,龍門不見。”{11} 李善注《文選》時云:“《穆天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12} 李善明其典源自《穆天子傳》。謝氏又在《懷故人》中直接化用“白云謠”,詩云:“我行未千里,山川已間之。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13} 又《送遠曲》云:“北梁辭歡宴,南浦送佳人。方衢控龍馬,平路騁朱輪。瓊筵妙舞絕,桂席羽觴陳。白云丘陵遠,山川時未因。一為清吹激,潺湲傷別巾。”{14}“白云謠”是西王母與穆天子分別時所吟,它是送遠之歌又是懷故之曲。當然,“白云謠”典故并非謝朓首用,474年江淹在《被黜為吳興令辭箋詣建平王》中已引,詩云:“一辭城濠,旦夕就遠。白云在天,山川間之。眷然西顧,涕下若屑。”{15}又有《清思詩》其二云:“白云瑤池曲,上使淚淫淫。”{16} 但謝朓將離別之傷思故之情的意蘊發揮得淋漓盡致,可以說是為后世詩人樹立了離別、思故的用典模范。
(四)“瑤池”新意象——外交場所、宴會之地、神仙之居
王融字元長,山東瑯琊人,其外祖父謝惠宜乃謝惠連之弟。王融以文才與辯才聞名。文以《三月三日曲水序》顯才,而辯才則以譴北朝使者獻劣馬事顯,蕭子顯所修《南齊書》載其事。筆者以為此兩事足可證《穆天子傳》被南北朝詩人所熟知。永明九年三月,齊武帝在芳林園禊宴群臣,命王融作序。序言文藻富麗,為時人所稱贊。序文引用《穆天子傳》典故:“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17};“七萃連鑣,九斿齊軌”{18}。永明十一年,北朝使者房景高、宋弁出使至南齊,王融負責接待,房、宋在北朝時素聞融才名求觀此序,王融示之。后日,宋弁在瑤池堂與王融相見。“瑤池”之名出于《穆天子傳》,是西王母宴請周穆王之地。“瑤池堂”可能是梁朝來訪的外國使者辦公的地方。陸徳明《經典釋文》云:“西王母是西方昏荒國名,又曰西王母神名。”{19} 也就是說“瑤池”第一義指西方之國名,瑤池相會也就可以理解為兩國外交事件,瑤池為外事招待之地。唐時亦有瑤池殿,唐太宗曾御瑤池殿問侍臣“西蕃通來幾時”{20}。“瑤池”的初始含義是指穆天子與西王母宴會之地。后往往指神仙居住之地,這是由西王母第二義衍生出來的,這一意象也是詩人最愛援引的。“瑤池宴”自然是神仙之宴,如胡曾《瑤池》:“阿母瑤池宴穆王,九天仙樂送瓊漿。漫矜八駿行如電,歸到人間國已亡。”{21} 它還指宮廷之宴,如李白《秋夜獨坐懷故山》:“入侍瑤池宴,出陪玉輦行”;韋莊《貴公子》:“瑤池宴罷歸來醉,笑說君王在月宮”{22}。這都是大家比較熟悉的詩歌。
齊武帝對北朝送來的馬不滿意,派王融去交涉。《南齊書》記有其事。王融責問北使違約,而宋弁以馬“不習土地”的借口推脫責任。王融回以穆王周行天下,駿馬如有水土不服,那么造父為王驅車不會一日千里之理反駁:“周穆馬跡遍于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23} 王融所引典故見之《史記》又見之《穆天子傳》。《穆天子傳》云:“天子之馬走千里”,“造父為御”。宋弁能明白王融用典的意義,說明他亦是熟悉典故的出處的。
(五)徐陵、庾信對《穆天子傳》典故的開發
如果說王融、謝惠連、謝朓樹立了“穆滿八駿”“黃竹詩”“白云謠”用典模范,那么徐陵、庾信可以說是將后世引用率較高的物典與事典囊括于詩中。
與王、謝相較,徐、庾對《穆天子傳》的接受在數量上更顯突出。兩人的用典情況為:徐陵《徐孝穆集箋注》9條,庾信《庾子山集注》(清人倪璠注)15條。用典內容包括:西王母觴周穆王于瑤池之事典(5條),如徐陵“所睹黃絹之辭,彌懷白云之頌”,庾信“停鸞宴瑤水,歸路上鴻天”{24};穆王八駿(4條),如庾信《陪駕幸終南山和字文內史》“玉山乘四載,瑤池宴八龍”{25},又如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周王玄圃之前,猶驂八駿”{26};藏書、讀書、曬書之地(4條),如徐陵《玉臺新詠序》“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27},又如徐陵《陳文皇帝哀冊文》“乃詔云臺之史,稽采《咸池》之曲,葉《大雅》于鳴金,同藏書于群玉”{28};黃竹詩(2條),如徐陵《丹陽上庸路碑》“紫庭黃竹之辭,晨露卿云之藻”{29};稀奇之物黃金之膏(3條),如庾信《蒙賜酒》“金膏下帝臺,玉歷在蓬萊”{30};七萃(2條),如庾信《周宗廟歌》“六龍矯首,七萃警途”{31},又如庾信《擬詠懷二十七首》“鼓鞞喧七萃,風塵亂九重”{32};其它(6條),如徐陵《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高詠玄池之野”{33} ,“皇帝以陶唐啟國,致玉版于河宗”{34}。徐、庾兩人詩文多為《藝文類聚》所引。
以上所提詩賦多入昭明太子之《文選》,并隨著《文選》學的興起而流傳后世,間接地推動了《穆天子傳》的傳播。
二、“白云謠”“黃竹詩”等經典意象的演變
我們對《穆天子傳》所有典故印象最深的是“瑤池宴”“白云謠”和“黃竹詩”,這也是唐人引用率較高的典故。麥奎爾在談到大眾傳播的傳遞模式時說:“大眾傳播是一種由受眾興趣和需求所引導的自我控制過程,而這種興趣和需求只有透過對所提供內容的選擇和反應才能了解。”{35} 換句話說,因為有了唐人對“瑤池宴”“白云謠”和“黃竹詩”等經典意象的大力開發,我們才對這些意象產生了生動的記憶。本文的目的是通過梳理“黃竹詩”“白云謠”等的引典情況、意義演變,展示唐人對《穆天子傳》的接受情況,同時讓人們了解這些物典和事典是如何成為經典,從而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讀者的。
(一)充滿魅力、影響最大的歌謠:“白云謠”和“黃竹詩”
筆者利用統計學原理,在梳理唐代詩人引用《穆天子傳》典故情況的基礎上來看哪些才是最具影響力的經典典故。基于研究樣本的數量、質量方面的考慮,筆者選擇收詩48900余首、作者2200余人、能較集中地反映唐代詩作情況的《全唐詩》作為考察對象。
據表1可知,《全唐詩》詩人對《穆天子傳》典故的關注率由高至底依次是“瑤池”“八駿”“穆天子(穆王)”“白云謠”“黃竹詩”“金膏玉果”“黃澤謠”“群玉之山”“七萃之士”“美人盛姬”“藏書冊府”等。其中“瑤池”典故被引94次,“八駿”被引82次,“白云謠”被引42次,“黃竹詩”“黃澤謠”被引35次。事實確實如此,皇帝和大臣們喜引《穆天子傳》典故。如前文所引李世民《喜雪》篇云“儻詠幽蘭曲,同歡黃竹篇”{36}。又如竇庠《奉酬侍御家兄東洛閑居夜晴觀雪》言“綠醋乍熱堪聊酌,黃竹篇成好命題”{37},皮日休詩云“高韻最宜題雪贊,逸才偏稱和云謠”{38}。
并不僅僅如此,敦煌石室藏唐寫本《云謠集雜曲子》便是以“云謠”命名。原本正面是油麥賬牒文卷,有“中和四年正月上座比丘尼體圓等油麥賬牒”“光啟二年丙午歲十二月十五日安國寺上座勝凈等狀”{39} 字樣,也就是說抄者應在光啟二年之后,而著作與選輯時代應在此前。這說明至少在唐僖宗時期普通百姓對“白云謠”是熟悉的。
在整理、研讀資料時,筆者發現“白云謠”“黃竹詩”“瑤池”在唐代讀者積極接受與傳播過程中意義已發生演變。其變化過程并不是簡單明了,它隱藏在眾多的詩歌作品中。它的復雜性在于,其初始意義與演變意義雜糅于同時代詩人作品中。這種復雜性令當今的學者比較困惑,影響了人們對新發現的寫本性質的認定。如任二北認為《云謠集雜曲子》中的“云謠”源自《列子》瑤池宴上西王母為穆王謠之事,而“唱云謠”“歌云謠”中的“云謠”指當時辭集名。{40} 孫其芳反駁任二北的觀點時指出“白云謠”典出《穆天子傳》,它“是神仙之歌,后世遂有不少人借‘云謠指稱美妙的歌辭”{41}。他并沒有辨析“白云謠”初始含義及演變意義,僅以其演變意義指云謠為神仙之歌,略顯武斷。又對于敦煌寫本《瑤池新詠集》性質的認定,亦是學界討論的重心。如榮新江、徐俊指出:“崔仲容生平不詳,《又玄集》《才調集》的題名僅具其名;另一位入選者女詩人程長文在《又玄集》中題名作‘女郎程長文,‘女郎是對年輕女子的統稱,看不出其信仰背景。已經佚失的另外十八個詩人的情況更是無從知曉,因此我們不能推定《瑤池新詠》是一部專門收錄女仙詩人的詩集。”{42} 榮、徐兩人觀點得到王三慶的認同{43}。而王卡則指出該寫本是“迄今已知唐代女冠詩集的最早抄本”{44}。雖然他們的觀點不一,但思考的出發點相同:“白云謠”典故與西王母有關,故此謠充滿了道教信仰色彩。其實“白云謠”并非僅指神仙之歌,它還是思故之曲,這一點前文已有論述。“黃竹詩”的情況也是如此,它雖多指描寫雪景之詩,但還是天子之歌、朝廷之曲。我們在分析作品、給作品定性時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辨析,如此才能得到較可靠的結論。基于此,筆者認為弄清“白云謠”“黃竹詩”初始意義及演變意義很有必要。
(二)“白云謠”的初始意義及演變意義
西王母在瑤池上與穆天子相會,為之歌謠。因首句“白云在天”而被世人名曰“白云謠”。此謠又名云謠、白云篇、白云吟、白云唱、白云詩,出自《穆天子傳》卷三,是作品中最具文學意味的部分。穆天子與西王母暢飲于瑤池。西王母有感于西王母之邦與西周之都相距萬里,山川相阻,何時能再重逢,遂以歌謠的方式問穆天子是否會再來相會:“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45} 其謠含不舍之意,又蘊遠別之思。穆天子應下了約期:“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46} 紀銘于弇山之石而去。是否再來,《傳》中無記。然《竹書紀年》有“十七年,王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期年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的記載。西王母“白云謠”初始意義為:不舍遠別,相約重聚。
“白云謠”常引申為送遠、懷故、思故之曲。王褒《寄梁處周弘讓書》云:“白云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47} 可謂得“白云謠”之精髓。謝朓《送遠曲》:“白云丘陵遠,山川時未因”,可資證明。謝朓、江淹多次在其作品中化用此典故。又劉禹錫《謝恩存問表》云:“元英匝歲,日夜懷歸。白云在天,闕庭難見。”{48} 借用此謠,乃言歸期之難至。
又因穆天子與西王母相約三年后再重聚,所以白云之期又指約期,如杜審言《和韋承慶過義陽公主山池五首》第五首:“青溪留別興,更與白云期。”{49} 通常指友人之約,如白居易《登龍昌上寺望江南山懷錢舍人》詩云:“獨上高寺去,一與白云期。”{50} 白居易點明作詩背景“昔常與錢舍人登青龍寺上方,同望藍田山,各有絕句。錢詩云:‘偶來上寺因高望,松雪分明見舊山。”{51} 又錢起《送張五員外東歸楚州》言:“杳然黃鵠去,未負白云期”{52};于鵠《春山居》云:“獨來多任性,惟與白云期”{53};劉禹錫《送景玄師東歸》曰:“山下偶隨流水出,秋來卻赴白云期”{54};薛逢《送衢州崔員外》說“休指巖西數歸日,知君已負白云期”{55};元稹《憶楊十二》“南山更多興,須作白云期”{56}。而陳子昂《感遇》則云:“荒哉穆天子,好與白云期”{57},特指與仙人相會。白云期系相會之期也,可謂明矣。
繼爾指相思之歌,如曹唐《小游仙》詩云:“玉童私地夸書札,偷寫云謠暗贈人”{58}。由相會之期細分為友人之期、與仙人相會之期。繼而轉義為戀人相思之曲。這種語義的轉變正是《穆天子傳》的接受者們積極主動推動而成。
在唐人眼里,“白云謠”又指道家神仙之唱,屬于游仙詩。在這里,要先說明一個事實,先前唐人對西王母的理解是多義的,西王母為神仙是其一義。唐代道教為三教之首,道士們為了吸引帝王和大臣信仰道教,大力宣傳已經仙化的周穆王見西王母故事。周穆王好神仙之說盛行。韓愈《衢州徐偃王廟碑》云:“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游,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59} 有詩人認為周穆王瑤池見西王母正是屬于游仙詩的內容。如陳羽《步虛詞》引此典故,詩云:“樓殿層層阿母家,昆侖山頂駐紅霞。笙歌出見穆天子,相引笑看琪樹花。”{60}又如鄭元祐《次韻錢伯行游仙體二首》其一云:“憶昔絳河輕就別,至今《黃竹》不成歌。”{61} 因此“白云謠”又被認為是道家神仙之唱。陳羽《步虛詞》說明唐代文人認可道士們的宣傳,相信瑤池會是神仙之會,“白云謠”為神仙之唱。這種帶有宗教意味的詮釋影響了后人的寫作。
詩人對“白云謠”的評價極高,謝榛《四溟詩話》云此謠“辭簡意盡,高古莫及”{62}。“白云謠”與“黃竹詩”后來成為詩人學習古體詩的典范。宋人郭茂倩將之收入《樂府詩集》供人學習。元明清時期,詩人多有模仿之作。
(三)“黃竹詩”的初始意義和演變意義
“黃竹詩”因句首“我徂黃竹”而得名,或稱“黃竹篇”“黃竹歌”“黃竹詠”“黃竹謠”。典出《穆天子傳》卷五:
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
詩三章以哀民,曰:“我徂黃竹, □負閟寒,
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
夕勿忘。我徂黃竹,□負閟寒,帝收九行,嗟
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窮。有
皎者鳥各,翩翩其飛,嗟我公侯,□勿則遷。居
樂甚寡,不如遷土,禮樂其民。”天子曰:“余
一人則淫,不皇萬民。”□登,乃宿于黃竹。{63}
寒冷的冬天下著大雪,有人凍死餓死。穆天子心生憐憫,作詩三章,表達他對百姓饑寒的擔憂,勸誡公侯冢卿要時刻記住造福百姓。當他看到百姓居樂甚寡生活艱辛時欲將其遷走,同時以禮樂來教化他們。穆天子也對自己未能造福百姓而自責不已。文中的穆天子憫民愛民憂民又自省,正如鄭杰文所說:“作者把穆王塑造成一個體恤下屬、關心人民、為百姓謀利益的圣明君主形象,在這個形象上傾注了自己對民主、平等的新型君臣、君民關系和開明君主政治理想的熱切追求。”{64}
據上所述,筆者認為“黃竹詩”的初始含義應是指皇帝憫民愛民憂民。謝榛《歲暮》云:“云物陰陰歲暮時,江河冰凍白鷗饑。三邊將士沖風雪,天子應歌黃竹詩。”{65} 詩人以“黃竹詩”的典故呼吁帝王來關心守邊將士和人民的疾苦。謝榛使用的便是其初始意義。
隋唐時期,“黃竹詩”的意義悄然發生改變。《全唐詩典故辭典》亦列舉此詩的釋義、例句和演變意義。辭書作者沒有梳理“黃竹詩”的流播過程,導致理解不到位,誤解自然而然產生。該書中釋義為:“傳說周穆王曾作四言詩,以首句中的‘黃竹名篇。詩為哀傷風雪中的凍人而作。后因用作詠雪的典故,也用以比喻帝王的詩作。”{66} 此釋義三句中二句有誤。第一句錯在原詩并沒有標題,“黃竹詩”之稱名見于歐陽詢《藝文類聚》、白居易《白氏六帖事類集》、韓鄂《歲華紀麗》。第三句誤在后世引用此典并非僅指帝王之詩作。
下面,我們來談談“黃竹詩”演變意義的產生情況。
首先,“黃竹詩”由哀嘆民生的憫民愛民憂民之詩變成了皇帝愛民之詩,甚至是彰顯帝王圣德之詩。初唐、盛唐間,是“黃竹詩”演變成“詠雪詩”的關鍵時期。自謝惠連《雪賦》為后世樹立引用“黃竹詩”描寫雪景的模范后,唐太宗李世民以天下至尊之勢掀起了詠雪之潮。如宋之問云“一承黃竹詠,長奉白茅居”{67};徐彥伯曰“懸知穆天子,黃竹謾言詩”{68}。詩人應天子之命作詩,引“黃竹詩”典故一是為了歌頌圣主,二是切合時景,三是為了迎合帝王的喜好。大雪紛飛、天寒地凍,普通百姓可能因缺衣少食面臨著死亡;同時,大雪紛飛,預兆豐收,來年百姓將會迎來好收成。《開元占經》云:“《穆天子傳》曰:雪盈數尺年豐。”{69} 瑞雪并不僅是兆豐年之喻,它還是人間帝王有德行得到蒼天的福報呈現形式,正如謝惠連《雪賦》所云:“盈尺則呈瑞于豐年,袤丈則表沴于陰德。雪之時義遠矣哉!”{70} 唐代詩人們常借此典暗喻當今天子為圣主明君,憫民愛民。引“黃竹謠”典故詩人的身份一般是皇帝和大臣,正如王世貞所言“隱士紫芝曲,朝廷黃竹謠”{71}。
接下來的證據能很好地支撐筆者的觀點。734年左右,張九齡觀陳希烈之唐玄宗手跡《喜雪》篇后上呈《觀御制喜雪篇陳誠狀》,文章大力奉承玄宗的德行感動上蒼,降下瑞雪,德行超過漢武帝和周穆王:“臣聞食者萬姓之命,雪為五谷之精,兆且見于祈年,律既和于言志,圣心昭感,天瑞合符。豈比夫漢詠白云,但嗟歡樂;周歌黃竹,徒事巡游而已哉?”{72}
唐玄宗有《喜雪》《野次喜雪》篇,說明玄宗很在意這種能彰顯自身德行的天瑞。大臣們投其所好,與其唱和,如張說就做了兩篇應制詩《奉和喜雪應制》與《應制奉和》。又李邕有《進喜雪詩表》,蘇綰有《奉和姚令公駕幸溫湯喜雪應制》,張九齡有《和姚令公從幸溫湯喜雪》。果然,唐玄宗看后很高興,認為這是君臣唱和一大美事,御批曰:“復緣講讀,便與希烈,未得付卿。今過有稱揚,豈成獻替。所期戮力,保合大和。今付一本,觀唱和之美也。”{73} 玄宗御筆寫若干份賜于張九齡、李林甫,并遣高力士送去。張九齡得到圣制《喜雪》篇后進《謝賜御書喜雪篇狀》,又將玄宗之詩夸贊一番,稱他的文章是“麗天之文,或冀傳誦;垂露之圣,難有偏沾”{74}。玄宗謙虛地說:“比年少雪,遂罕秋成。恐陰律愆期,時無可望。孰云禱久,每事虔誠。雨雪驟盈,喜慰初集。率爾成作,書情而已,方示朝廷。”御批道出他寫喜雪詩的原因,表達了他對百姓收成的擔憂,巧妙地向大臣暗示他是愛民的君主。故唐人應制賦雪詩多歌功頌德之語。
如上所述,穆天子哀民之“黃竹詩”到了唐代則成了皇帝彰顯德行的“喜雪篇”。這種風氣對后世的影響極大。唐后諸朝廷,多逢雪歡歌,成君臣相和美談。據《玉海》卷一九五記載宋代有喜雪宴:嘉祐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賜喜雪燕于中書”;皇祐四年十二月雪未下,宋仁宗趙禎自責說“是朕誠不能感天而惠不能及民”,“是夕得雪。庚寅賜喜雪宴于中書”{75}。喜雪宴上必有應制詩,淳化三年喜雪宴上“凡應制賦詩者三十五人”{76}。足見風氣之盛。皇帝喜歡大臣上呈此類頌德之歌,有《御制瑞雪》詩曰:“應有五車來表瑞,定殊黃竹著為謠。”{77} 大臣們投上所好,如田錫《進瑞雪歌狀》云:“圣制歌行,初蒙陛下宣示;御筵賦詠,亦令臣等進呈。‘白雪‘黃竹之謠,豈憂稼穡;君唱臣和之美,堪載策書。”{78} 他在《進瑞雪歌》時又言:“圣德昭彰動天地,歲歲豐穰為上瑞。明年有閏節氣遲,冬深有雪方及時”{79},認為瑞雪的出現是帝王德行得到上帝的認可和護佑。唐太宗、唐玄宗《喜雪》篇的影響可謂遠矣。
唐太宗和唐玄宗對《穆天子傳》的重視勢必引起大臣對此書的關注。周證圣元年乙未科的試題的出現、張柬之永昌元年在殿試的回答、類書《初學記》、白居易《白氏六帖》對《穆天子傳》的選擇以及唐代詩人的用典皆是對此的反饋。上層人物對此類典故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唐人詩歌創作風氣,因為藝術家“總是在某些社會條件下創作,也是在某種文藝風氣創作。這個風氣影響到他對題材、體裁、風格的去取……”{80} 這也許是唐人使用“黃竹”“白云”典故的原因。
其次,隨著謝惠連《雪賦》與唐太宗《喜雪》篇的流傳,接受者們對“黃竹詩”的關注重心由內容轉向寫作背景。其轉變時間發生在中唐。詩的作者與詩的接受者的身份發生了轉變,不再限于皇帝與大臣之間。例如:竇庠《奉酬侍御家兄東洛閑居夜晴觀雪》言“綠醋乍熱堪聊酌,黃竹篇成好命題。”這首詩是回應其兄竇牟《洛下閑居夜晴觀雪寄四遠諸兄弟》的。由此可知,“黃竹”不僅“垂芳于帝籍”,它還是詩人詠雪詩的通稱。
據此,“黃竹詩”初指皇帝憫民愛民憂民之詩,后成為愛民之詩。又因受謝惠連《雪賦》與唐太宗《喜雪》篇的影響,在中唐以后詩人詠雪時多引此典故。
綜上可知,《穆天子傳》典故“白云謠”“黃竹詩”兩詩的意義在傳播過程中逐漸發生了改變,主要原因是接受者在信息加工后的再次傳播中產生了信息失真和傳播偏向。使接受者產生偏向的原因比較復雜,但接受者受到當時盛行的道教神仙之說的影響而產生特定傾向性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這是我們通過分析歷代詩人對“白云謠”“黃竹詩”意義的認知后得出的結論。
三、《穆天子傳》經典化(接受)過程
《穆天子傳》經典意象的演變體現在其經典化過程中。它在兩晉南北朝時期經過二次整理后,逐漸被社會精英接受。郭璞注釋《爾雅》《山海經》諸書時引用《穆天子傳》開啟了古代學者用此書注《山海經》和《竹書紀年》的傳統。《穆天子傳》在南北朝流傳的重要途徑有二:一是詩人群體之間互相借閱、討論、研究,二是通過佛門寺院、道教道觀向中、下層知識分子傳播。我們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歷代接受者的文字里,周穆王由明君向昏君逐漸轉變的同時其身份亦由歷史人物向道教神仙轉化。而其中《穆天子傳》中的“瑤池宴”“白云謠”“盛姬”并未見之其他歷史文獻,這說明“瑤池宴”“白云謠”“盛姬”皆出于《穆天子傳》,并非來自《漢武內傳》《漢武外傳》等書。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周穆王形象的演變以《穆天子傳》出土時間西晉為界線,西晉前周穆王為歷史人物,之后有的認為是神仙人物。其主要原因是葛洪、王嘉、陶弘景等道士注重援引《穆天子傳》中的典故,極力塑造周穆王尋仙訪道的新形象,并將周穆王納入道教神仙譜系,以此來吸引人間帝王求長生訪仙道。這一時期,以王、謝二大世族與皇家為中心的詩人群體對此書產生濃厚的興趣,《穆天子傳》的文學價值亦被詩人挖掘出來。詩人開始大量援引書中的典故,典故的經典意象也在此時確立。如謝惠連《雪賦》篇中引用周穆王大雪哀民的典故為后世賦雪詩確立了意象模范,謝朓直接、間接引用“白云謠”將離別之傷思故之情的意蘊發揮得淋漓盡致,徐陵、庾信對此書中的物典與事典全面開發直接影響了隋唐詩人對此書的接受。值得一提的是,劉勰注意到此書所含的文體及其價值,有別于同時代的詩人。這些文學史上著名的篇什間接地推動了《穆天子傳》的傳播。
隋唐時期,《穆天子傳》被更多人知曉。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一是因受到皇帝的喜愛,《穆天子傳》成為殿試題目和士子們常用典故的來源;二是《穆天子傳》被更多的學者注疏引用、類書編撰摘錄、引典。其中瑤池宴和“黃竹詩”“白云謠”獲得較高的關注率;三是因更多的人對其進行新的闡釋,賦予典故更豐富的內涵,事典、物典的意義逐漸發生了改變。例如,“黃竹詩”由哀嘆民生的憫民愛民憂民之詩變成了皇帝愛民之詩,甚至是彰顯帝王圣德之詩,中唐以后凡詠雪多引此典故,凡夸贊帝王親政愛民亦多引此詩。可以說,“黃竹詩”是帝王之詩。又如“白云謠”本為相約重聚之歌,后引申為送遠、懷故、思故之曲,繼而指相思之歌、道家神仙之唱。中唐時期,互有聯系的李觀、白居易、元稹、柳宗元、劉叉五人集中寫下《八駿圖》,其詩文背后是詩人對時局的擔憂。其中白居易不但在類書《白氏六帖》中錄有此書的典故,在《八駿圖》《李夫人》等詩文中援引其典,還對盛姬文學形象進行開發,使人們開始注意到了穆天子對盛姬的深情和“帝王之戀”的悲情。這個題材也是現當代學者研究《穆天子傳》的關注重點。另一重要而特殊的接受者是道教與佛教團體,他們帶有偏好的解讀借助《穆天子傳》的故事框架、主人公宣揚自家的教義。其中道士們在葛洪、陶弘景的基礎上不遺余力地進行再次改編、附會、宣傳,在他們的闡釋下瑤池成為神仙居住之地,瑤池宴演變成了道教神仙西王母在瑤池宴請周穆王,愛民憫民恪于職責的圣明之主成了荒廢國事追求成仙的求道者、得道者,結果阻礙了唐以后人們對原書的理解,造成了理解的偏差,或者接受的偏愛。僧人對此書的利用具體表現在附會周穆王是佛跡的見證者和附會《穆天子別傳》載佛滅度時間,如法琳《周書異記》、道宣《律相感通傳》。這些案例表明了《穆天子傳》在唐代已不僅僅是一部文學作品或者史書,它還是佛教與道教斗爭的武器。唐代歌曲集和詩歌集——《云謠集雜曲子》《瑤池新詠》的書名來源就是《穆天子傳》。《穆天子傳》也為日本人喜愛。日本遣隋使團和遣唐使團的學問僧、留學生帶回此書后,在日本精英學者中引起反響。如伊與部馬養在《從駕應詔》詩中提到“瑤池”和“白云篇”,明示他受到《穆天子傳》影響。又731年葛井連廣成奉試對策提到了“黃竹”和“白云”之事例也能說明日本上層對《穆天子傳》已很熟悉。{81}
到了宋代,因為宋代的皇帝多信道教,其中宋徽宗最為突出,他自封為“教主道君皇帝”。有人以周穆王見西王母故事勸他遠游。他還大肆興建道教宮觀、操辦齋醮道場,建立道學制度,設立經局,整理校勘道書。在此風氣下,朝堂中的大臣自然受其影響,重視對《穆天子傳》的接受。其主要表現在與皇帝進行溝通交流時,比如上呈札子奏狀、賦詩,亦會援引《穆天子傳》中的典故。 《穆天子傳》典故還被宋代類書大量摘錄,如李昉《太平御覽》錄97條,吳淑《事類賦》引33處,王應麟《玉海》著錄、征引共56次等。還有詩歌總集專收此書中的歌謠,如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八十七收“黃澤辭”“白云謠”“穆天子謠”,這些都是朝堂應對常引典故。故猜測《穆天子傳》應屬于考試必背內容。郭茂倩的行為又影響了后來的文集編撰者,如左克明《古樂府》卷一“古歌謠辭”就收了“黃澤辭”“白云謠”“穆天子謠”;劉履《風雅翼》卷七“選詩補注七”收錄了“黃澤辭”。《穆天子傳》歷來被用來箋證史書、經書、地理書、樂書。到宋元時期亦不例外。與隋唐時期不同的是,以《穆天子傳》注釋它書的范圍延展至詩歌的箋證。
道教的興盛、文學的復古思潮是《穆天子傳》在明代再次成為經典的重要原因。明世宗朱厚熜好方術鬼神之事,全國興起西王母信仰,同時,周穆王故事亦隨著西王母故事的廣泛傳播為人所知。以王世貞為首的復古派為了重樹康健的文風,重視對古樂府的學習與寫作,《穆天子傳》再一次進入他們的視野,其歌謠便成了他們學習與模擬的對象。復古派不但在書信往來相互酬唱中談論《穆天子傳》,還會在開展社團活動時同題競詩。在他們的帶動下,明中后期知識分子掀起了閱讀、討論、研究《穆天子傳》風潮。他們學習、討論、模仿其中的歌謠“白云謠”諸篇以習古樂府。需求旺盛促使明刊本、抄本、選本頻出。有清一代,樸學興起,乾嘉之間,凡能以《穆天子傳》入題者則為上選,一時讀書、藏書、校注云集。
《穆天子傳》再次被學者關注是民國時期。當時中國文明、中國民族西源說、“白優黃劣”的人種觀流行,為應對此種歪曲學說,部分中國學者以中國古籍所記地理以及文化為論據反駁,提出保存國粹、地理救國等口號。其中最典型的當屬顧實,他在受到西方《穆天子傳》的研究熱潮的影響以及中國文明西源說和“白優黃劣”論的刺激后,決心從《穆天子傳》地理考證入手抵御外國學術侵略,尋找民族自信。受西方學科分類思想的影響,民國時期現代學術分科日益專門化,《穆天子傳》以上古神話或小說古代珍貴之史料、地理志進入研究者視野。
綜觀《穆天子傳》的經典化過程,我們發現,一是此書的傳播與上位者的接受正相關,而且皇帝引用頻率越高,科舉考試、御前應對、學者在著作和詩詞作品中的引用就越頻繁。二是《穆天子傳》中主人公形象與其歌謠是被闡釋最多的,同時也是流傳最廣的。宗教團體是重要闡釋者,經過他們的傳播,后來人們多記住了《穆天子傳》卷三見西王母一事,而不大知曉其他故事。三是《穆天子傳》不僅是文學經典,還是道書經典、史傳經典、地理經典。與之相媲美的只有《山海經》了,不過,《山海經》的文學意味沒有它強,對文人的影響也沒有它廣。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穆天子傳》的現當代研究主要還是集中在地理、歷史、名物等方面,對于它本身的文學性關注還不夠,這也是本文旨趣所在。
注釋:
①②{70}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13,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94、195、194頁。
③{11}{13}{14} 謝朓著、曹融南校注:《謝宣城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55、272、156頁。
④{47} 令狐德棻等:《周書》,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764、732頁。
⑤{21}{22}{36}{37}{38}{49}{52}{53}{55}{57}{58}{60}{67}{68} 彭定求編:《全唐詩》卷1,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0、7427、8000、10、3045、7085、733、2649、3503、6324、893、7348、3896、648、823頁。
⑥ 唐順之:《荊川集》卷2,《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6冊,第204頁。
⑦⑧{17}{18}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46,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793、795、647、651頁。
⑨ 王嘉撰、簫綺錄、齊治平校注:《拾遺記》卷8,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86頁。
⑩ 姚思廉:《梁書》卷43,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691頁。
{12}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40,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569頁。
{15} 江淹著、胡之驥注:《江文通集匯注》卷9,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34頁。
{16} 江淹著、胡之驥注:《江文通集匯注》卷3,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28頁。
{19} 陸德明撰、黃焯匯校、黃延祖重輯:《經典釋文匯校》,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886頁。
{20} 王方慶:《魏鄭公諫錄》卷3,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8頁。
{23} 蕭子顯:《南齊書》卷47,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822頁。
{24} 庾信撰、倪璠注:《庾子山集注》卷5,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94頁。
{25}{32} 庾信撰、倪璠注:《庾子山集注》卷3,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79、246頁。
{26} 庾信撰、倪璠注:《庾子山集注》卷1,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頁。
{27}{29}{33}{34} 徐陵撰、吳兆宜注:《徐孝穆集箋注》卷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64冊,第874、884、876、877頁。
{28} 徐陵撰、吳兆宜注:《徐孝穆集箋注》卷5,《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64冊,第907頁。
{30} 庾信撰、倪璠注:《庾子山集注》卷4,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86頁。
{31} 庾信撰、倪璠注:《庾子山集注》卷6,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469頁。
{35} 丹尼斯·麥奎爾:《麥奎爾大眾傳播》,崔保國、李琨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頁。
{39} 陳人之、顏廷亮編:《云謠集研究匯錄》,《敦煌〈云謠集〉新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頁。
{40} 任二北:《敦煌曲初探》,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年版,第404頁。
{41} 孫其芳:《鳴沙遺音:敦煌詞選評》,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頁。
{42} 榮新江、徐俊:《唐蔡省風編〈瑤池新詠〉重研》,《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頁。
{43} 參見王三慶:《也談蔡省風〈瑤池新詠〉》,《中國古文獻學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19頁。
{44} 參見王卡:《唐代道教女冠詩歌的瑰寶——敦煌本〈瑤池新詠集〉校讀記》,《中國道教》2002年第4期。
{45}{46} 郭璞注、洪頤煊校:《穆天子傳》卷3,平津館刻本,1806年。
{48}{54} 劉禹錫撰、卞孝萱校訂:《劉禹錫集》,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626、402頁。
{50}{51} 白居易著,丁如明、聶世美校點:《白居易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145頁。
{56} 元稹:《元稹集》卷14,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57頁。
{59} 韓愈著、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第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10頁。
{61} 顧嗣立編:《元詩選初集》,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855頁。
{62} 謝榛:《四溟詩話》卷2,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5頁。
{63} 郭璞注、洪頤煊校:《穆天子傳》卷5,平津館刻本,1806年。
{64} 鄭杰文:《論〈穆天子傳〉的認識價值》,《天津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1期。
{65} 謝榛著、朱其鎧等校點:《謝榛全集》,齊魯書社2000年版,第667頁。
{66} 范之麟、吳庚舜主編:《全唐詩典故辭典》, 湖北辭書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2—1813頁。
{69} 瞿曇悉達編:《開元占經》卷101,岳麓書社1994年版,第1053頁。
{71}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25,《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79,第311頁。
{72}{73}{74} 張九齡:《曲江集》卷15,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160—161、160—161、161頁。
{75}{76}{77} 王應麟:《玉海》卷195,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7年版,第3583—3584、3583、583頁。
{78}{79} 田錫著、羅國威校點:《咸平集》,巴蜀書社2008年版,第288—289、194頁。
{80} 錢鐘書:《錢鐘書論學文選》第6卷,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1頁。
{81} 參見劉伏玲、王齊洲:《試探〈穆天子傳〉傳入日本的時間與途徑》,《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
作者簡介:劉伏玲,江西師范大學當代形態文藝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江西南昌,330022。
(責任編輯 ?劉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