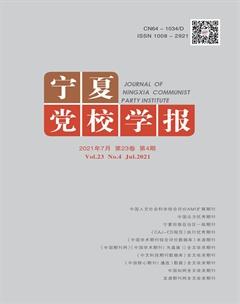中國特色協商文化對協商民主實踐的價值意蘊
王志剛 池忠軍
摘要:中國特色協商文化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我國協商民主實踐中生成的一種文化形式,對我國協商民主實踐具有深厚的價值意蘊。在協商主體方面,中國特色協商文化通過明確人民的協商主體地位、培育協商主體的協商精神、規范協商主體的協商行為,有助于提升協商主體的價值共識;在協商治理方面,中國特色協商文化通過為協商治理注入更多價值理性、推動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有助于增強協商治理的效能;在頂層設計方面,中國特色協商文化通過創新協商民主認知理念、堅定協商民主社會主義方向、完善協商民主體制機制,有助于優化協商民主的頂層設計。
關鍵詞:協商文化;協商民主;協商治理;文化自信
中圖分類號:D62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2991(2021)04-108-008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協商民主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1](P38)。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這一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一方面源于中國共產黨長期的民主實踐探索,另一方面也深受中國特色協商文化的影響。中國特色協商文化是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在不斷深化協商民主實踐、提升協商民主理論認知和強化協商民主文化認同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種文化形式,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具有濃厚的文化滋養和重要的價值引領作用。
當前學界關于中國特色協商文化的研究主要從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與協商民主實踐中的共通因素,闡釋協商文化的歷史淵源和文化底蘊[2],或立足黨在歷史上的民主實踐方式,指出“協商民主得益于‘群眾路線與‘統一戰線兩大革命文化要素的共同催生”[3]。也有學者從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地位功能、精神內涵和實現路徑等方面闡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思想體系[4],或從協商民主概念的界定、思維方法的發展和協商民主的文化自信等方面論證協商民主的理論創新[5]。這些研究的共同點,是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黨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看作是中國特色協商文化的主要構成部分,將民族性、階級性、多元性、開放性和時代性看作協商文化的本質屬性,為全面理解中國特色協商文化提供了借鑒和參考。但是,作為從協商民主實踐中生成的中國特色協商文化,只有充分說明對協商民主實踐的價值意義,才能更全面、深刻地理解其豐富內涵。在新的發展階段,更加堅定文化自信,推動中國特色協商文化發展進步,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滋養中不斷提升協商主體價值共識、增強協商治理效能,進而推動我國協商民主頂層設計的不斷優化,是中國特色協商文化在新時代推進協商民主實踐發展進步的重要價值所在。
一、中國特色協商文化有助于提升協商主體的價值共識
價值共識是協商主體在復雜多元的現代社會就某一公共問題在價值認知上所達成的一致性的觀點和態度。在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多樣化和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對價值共識的達成造成了一定沖擊,但協商民主的根本任務就是在異議中尋求共識,這就有賴于協商主體價值共識的達成。但“價值共識不是脫離各個民族的價值而獨立存在的抽象共相,而是在人類文明進步中、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中逐步形成的對某些基本價值的認可;它是有條件的、歷史的、變化的”[6]。因此,價值共識要置于一定的文化傳統、階級定位和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基礎之上進行討論。中國特色協商文化對協商主體價值共識的提升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明確人民的協商主體地位
任何文化都有相應的文化主體,文化主體關涉的是這一文化“屬于誰”和“為誰服務”的問題。中國特色協商文化作為黨領導人民進行協商民主實踐的產物,除了中國共產黨這個最根本、最核心、最關鍵的主體外,還包括社會各階層、各領域的人民群體,也就是人民是文化主體。
首先,是由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人民民主性質所決定。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人民民主特性要從其生成與發展的實踐歷程進行分析。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反帝、反封、反官僚資本主義,中國共產黨通過建立統一戰線與社會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等開展民主活動,支援人民革命。后又通過人民政協協商成立新中國,并協助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在不斷總結以往協商民主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不斷完善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形式。進入新時代,更是將人民政協上升到國家的制度安排,將其作為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從國家頂層設計的高度肯定其功能和作用。可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在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長期運作實踐中逐步形成和培養起來的一種新型民主政治形態”[7]。縱覽這一發展歷程,中國特色協商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根據不同歷史時期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結合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具體情況不斷進行探索和實踐的結果,是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形式,是捍衛人民民主制度的重要工具。
其次,是由中國特色協商文化的根本使命所決定。中國特色協商文化建設和發展的使命,是為我國協商民主實踐提供動力和支撐,推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廣泛、多層次和制度化發展。其中最關鍵的要素就是培育具有一定協商精神和協商能力的社會主義公民。中國特色協商文化的根本價值在于提升廣大人民群眾的公民意識和權利意識,激發其參與公共生活、參與民主政治的自覺性和能動性,本質上是確保人民當家作主,明確人民的主體地位。由此可知,中國特色協商文化具有鮮明的人民性和階級性,是屬于人民并服務于人民,且為人民所享有的文化形式,這在文化觀念和思想認識上肯定和明確了人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中的主體性地位,為協商民主的制度化發展奠定了政治基礎。
(二)培育協商主體的協商精神
協商民主本質上是協商主體就某一公共問題,通過理性協商和公開對話達成一定共識的民主活動,要求協商主體具備一定的協商精神。協商精神是協商民主的必備要素,對推動協商民主的發展進步具有重要作用。協商精神的培育受協商制度、規則等影響,但更依賴于協商文化所發揮的價值引導作用。
首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協商精神的培育提供歷史底色。“中華民族長期形成的天下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等優秀政治文化”[8]構成協商文化的歷史底色。“天下為公”表達了人民對公正、公道和公平的尊崇,啟示執政者要時刻保有一顆公心,這與中國共產黨沒有自身特殊利益的特質具有內在一致性。“兼容并蓄”是指人要有兼容豁達的品質,內含著顧全大局的集體主義價值傾向,有助于培養民眾和而不同、包容兼聽的協商精神。“求同存異”反映的是我國古代提倡的“和合”文化,是主體間將彼此的差異融合于一個統一體中,以此形成共同認知和基本共識,傳達的文化理念是平和地處理矛盾、分歧以實現彼此融合、相互協調的目的。中國特色協商文化內涵中的優秀傳統觀念和價值理念,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精髓的集中體現。以這些傳統文化的優秀成分滋養、熏陶協商主體的思想認知,有助于引導協商主體在協商民主實踐中形成包容差異、理解他人的協商意識和行為,也是協商主體不可或缺的精神品質。
其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助于提升協商主體的參與精神和公共意識。協商文化內在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公正等價值理念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著鮮明的共通之處,這對于提升協商主體的主體意識,增強其參與精神、履行公共義務和職責具有重要的價值引導作用。正如有學者所言,“加強培育公共協商精神就必須樹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等價值理念,培養公民的主體意識以及積極而負責的權利和義務意識”[9]。
(三)規范協商主體的協商行為
協商主體規范、有序地參與協商是協商民主順利開展的前提條件,也是衡量協商民主制度化的重要標準。隨著協商民主實踐的廣泛深入開展,協商形式層出不窮,無論是公職人員還是普通民眾,人們的協商意識在逐漸增強。面對協商民主發展的新形式、新局面,有必要對社會成員的協商行為進行有效引導,使其在正確的價值引領中規范自身協商行為。
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中國特色協商文化提供了目標指引,也為規范協商主體的協商行為提供了行動指南。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繼承中華文化傳統,立足中國發展實際,這首先有助于提升公職人員的馬克思主義素養,有利于系統、科學地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深刻把握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歷史使命,進而從理論和實踐上深刻理解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特點和優勢。其次,有助于社會成員深入理解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引導社會成員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作為自身的基本要求,貫穿于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等各方面,堅持“為人民服務”這一道德核心,不僅是對公職人員的要求,也是對廣大社會成員的要求。最后,通過構建良好的社會協商環境規范主體的協商行為。協商文化有利于在社會層面形成求同存異、兼容并蓄的協商場域,使在這一場域中從事協商實踐的主體的認知模式和行為方式都受到這些文化理念的規約和引導。協商文化作為社會共有的文化資源,有助于在社會范圍內構建互信互惠的關系網絡,這一關系網絡又有助于推動各協商主體間的合作和共識的達成,由此形成良性的社會循環系統,這個循環系統促使存在利益分歧的各方之間以協商代替對抗,用合作代替沖突。
二、中國特色協商文化有助于增強協商治理效能
協商治理是復雜多元的現代社會應對治理難題的必然選擇。作為各主體間通過溝通、對話和討論等形式達到矛盾化解、相互妥協,最終實現公共利益的實踐形式,協商治理本質上是對人的情感的關照以及在此基礎上尋求社會公共利益實現的途徑。相較于制度規則或技術手段等“硬條件”發揮的保障性作用,協商治理效能的提升更加注重價值理念、思想情感等“軟條件”發揮根本性作用,這是協商文化的基本價值功能所在。
(一)為協商治理注入更多價值理性
協商治理作為一種治理方式,不只是被當作一種純粹的手段僅具有工具理性,更是作為一種倫理價值的評判準則貫穿人民的日常生活,表現出更深層次的價值理性。進入新時代,這一價值理性的評判標準就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國特色協商文化內涵的思想理念對提升和彰顯協商治理這一價值理性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首先,這是由中國特色協商文化的人民屬性決定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與西方協商民主最本質的區別在于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在多元利益格局中通過協商以尋求最大公約數,以切實保障人民基本權利、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為根本價值指向,不是簡單的程序民主和票決民主。這決定了中國特色協商文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為價值取向,強調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治理過程的互動性、治理方式的法治性、治理成果的共享性,更加注重民主民生和公平公正,這與“善治”提倡的“民有、民治、民享”治理模式相契合。同時,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協商治理的價值評判標準,是黨的群眾路線與協商民主相統一的體現。因此,從這一角度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一價值標準也是我國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要求。
其次,這是由中國特色協商文化內在的價值因素決定的。中國特色協商文化內含的平等共存、多元共享、和諧共生等思想理念,有助于緩解社會分離主義傾向,推動治理過程中價值因素和技術因素的融合,為創新和探索社會治理路徑提供參考和借鑒。社會經濟的發展進步伴隨著階層之間、地域之間、城鄉之間差異的逐漸擴大,致使社會結構呈現分離主義傾向。對于這一傾向,有學者基于理性自利人的邏輯去探討社會公平感問題[10],也有學者認為這是各主體基于功利主義致使個體特質凸顯而導致的,并將現代社會看作是帶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個體的集聚[11]。學界關于社會結構分離主義傾向的解讀及應對方式,都反映了一個真實問題,即社會終究不是機械式的、僅由利益結成的組織,而是各主體基于一定的價值規范和文化理念、摻雜著各式各樣的情感組成的共同體。這正是中國特色協商文化發揮化解社會張力、凝聚社會共識的關鍵所在。當前學界討論并提倡的包容性社會治理、完美治理等課題,主張“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系,確立互相認同的包容性發展目標,進而促進生成公平和諧的社會利益關系”[12],強調治理主體通過協商合作,在“上道與下器、戰略與戰術、境界與方法的‘完美統一”中實現美美與共、和合共生的完美境界[13],都是在遵循多元共存、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中尋求社會治理的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辯證統一,本質上都是在強調協商文化對協商治理所發揮的價值功能。
(二)推動公共利益的實現
中國特色協商文化在推動公共利益實現方面,是由其自身的階級屬性決定的。公共利益的實現與否,是評判治理效能的一個重要標準,但首先要說明什么是公共利益。
關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學界尚未達成統一認識,但公共利益絕不是以一種抽象的、觀念性的概念存在于人的想象之中。實際上,公共利益是現實地、具體地存在,它與個人和社會群體息息相關,并表現出一定的群體性和共識性。有學者認為公共利益“依賴于一些由有共同利益和類似的心志能力的人們所組成的群體”[14],且只有通過“調動人們對共同體的存在和健全發展的價值的切近感知而鼓勵他們通過各種方式為其服務”[14]才能得以實現。還有學者認為,公共利益就是“在多元社會的治理過程中,政府與利益相關者在利益和利益分配問題上所達成的共識”[15]。綜合分析學界的討論,其共同之處在于:一是公共利益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即公共利益究竟是誰的利益。二是傾向于從集體主義路徑尋求公共利益的實現。馬克思早在《克羅茨納赫》筆記中就已經通過對市民社會的批判確立了階級的相對公共性的觀念,認為階級社會的公共性總是階級的共同利益的公共性。就此而言,在社會主義中國,公共利益只能是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一價值理念與人民民主專政和黨領導的群眾路線具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對于不同國家、不同階級的公共利益,“關鍵并不在于共同體的不確定性,而在于誰來主張公共利益”[16]。在西方國家,內涵了新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憲政民主以個人利益作為邏輯起點尋求公共利益的實現,從而陷入公共利益的悖論無法自拔。在中國,一方面,作為領導主體的中國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外無自身特殊利益,且“人民民主的政治結構化排除了強勢利益集團的優勢”[17],這從制度上確保了公共決策不受利益集團的操縱。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主導的協商文化內含集體主義的價值取向,這一價值取向有利于啟動社會公眾的價值偏好,使之指向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促使包括個人利益和團體利益在內的社會利益都在人民民主制度的根基上通過集體主義的方法論實現統一。集體主義的價值取向源自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求同存異”“和為貴”等理念,體現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憲法中。“集體主義的出發點是無產階級的整體利益,最高價值目標是自由人聯合體中每個人利益的全面實現”[18]。從集體主義價值取向尋求公共利益的實現,既符合社會善治的一般性規則,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最高理想追求。
三、中國特色協商文化有助于優化協商民主的頂層設計
中國特色協商文化對協商民主實踐的影響涉及個人、社會、國家各個層面。除了對協商主體和協商治理的效果產生影響外,還對國家在協商民主的頂層設計方面有顯著影響。協商民主的頂層設計同樣是一個系統工程,中國特色協商文化對協商民主頂層設計的價值影響主要表現在創新協商民主的認知理念、把握協商民主的發展方向以及推動協商民主體制機制的發展與完善等方面。
(一)在文化傳承中創新對協商民主的認知
中國特色協商文化凸顯人民群眾在協商民主中的主體性地位。在中國歷史上,無論是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還是荀子所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都強調主政者要以民為本,為民做主。植根于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體現了豐富的人文思想和人道主義,啟示后人要重視人民群眾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但我國歷史上傳統的“民本”并不意味著現代的“民主”,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之間的張力需要在繼承中實現創新性發展。立足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中國優秀民本文化的現代轉變集中體現在“以人民為主體的文化自覺、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和兼具全面性與動態性的實現方略”[19]。這與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價值主旨具有內在的一致性。中國特色協商文化作為一種文化形式,歸根結底要落腳在協商主體,即人的身上。“文化都反映著人對人與自身、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歷史以及人與文化傳承之間復雜矛盾的思考,因此任何一種文化現象都離不開人的因素。”[20]協商本質上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思想認知、價值理念等內容的溝通和交匯,只有在充分肯定和尊重人的基礎上,才能真正體現協商的精神、實現協商的目的。中國特色協商文化以全體中國人民為文化主體,在自由平等、公平公正的價值理念中為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服務,在堅持以人為本的同時又實現了人民民主,實現了中國傳統民本思想和社會主義民主思想的統一,從這一角度看,中國特色協商文化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性發展。
要在人民群眾的協商實踐中實現協商文化的發展和繁榮,進而發揮協商文化的價值功能,并反作用于協商民主實踐,推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進一步發展。“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1](P21)堅持人民在協商文化中的主體地位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協商文化是為人民群眾服務。二是人民群眾在推動協商文化發展中起決定性作用。也就是,一方面要把握好中國特色協商文化的人民性和階級性,將其作為培育公共精神、凝聚社會共識的文化形式,另一方面也要充分發揮人民在推動和促進中國特色協商文化發展中的作用,通過不斷豐富和創新人民群眾的協商途徑和協商形式,實現協商文化的發展繁榮,如此才能促使協商文化更好地反作用于協商民主。這種文化思想生成于社會實踐又反作用于社會實踐的認識論,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要求,以此為基礎,科學把握協商文化和協商民主之間的辯證關系,是新時代推進協商民主實踐和協商文化發展的認識論前提。
(二)在文化自信中堅定協商民主的社會主義方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1]。要在文化自信中深化協商民主發展的自覺。樹立多元主體自由平等、公平公正參與協商的理念,加強社會成員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認同感,促進協商民主體制機制的豐富和完善,規范協商主體的協商行為等,都是推動協商民主實踐發展的重要因素。中國特色協商文化以深厚的底蘊、豐富的內涵和開放的姿態,使人民群眾更深入地認識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在中國社會發展實際的基礎上創造出的符合中國國情的民主制度形式,讓人民群眾在與其他不同類型的民主制度或文化形態的對比中,提升文化自信,進而更加擁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協商民主作為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也需要在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中不斷豐富和完善,使之在發揮民主效能、實現人民民主的程度上經得住比較,以此增強人民的認同感和滿意度。
要在文化自信中深化協商民主發展自強。任何文化都是隨著社會實踐的深化和人的認識的提高而不斷向高階段發展進步的。協商民主這一制度形式作為文化的一種,也隨著協商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問題的關鍵在于向什么方向發展,協商民主的發展是否會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是否會一直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關乎協商民主和人民民主性質的根本問題。中國特色協商文化貫穿人民民主這一核心價值理念,體現的是黨心懷天下、追求公義的民族本色和文化使命,反映的是我們黨在尋求民主的道路上對民族文化的高度認同和“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發展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舊,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22]。這一過程是中國特色協商文化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過程。中國特色協商文化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方向指引,遵循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強的發展邏輯,立足黨和人民長期的協商民主實踐歷程,聚焦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面臨的新機遇、新挑戰,不斷對我國協商民主實踐提供精神支撐和智力支持,推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沿著社會主義方向走向更高水平。
(三)在文化交流與互鑒中完善協商民主體制機制
人類社會是在不同文明的交流和互鑒中不斷發展前進的。中國特色協商文化作為一個開放的體系,不是僅局限于某一特定范圍內的文化,而是同時關注其他不同群體、不同民族的優秀文化成分,使自己的社會成員在一定的理論指導下接受多種優秀文化的洗禮,促進社會成員更好地認識世界和認識自身。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統籌推進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23]。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制機制的完善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通過加強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文化交流合作,積極吸收和借鑒其他優秀的民主政治文化,使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在世界民主政治文化的滋養中不斷發展完善。一方面,充分借鑒國外優秀民主政治文化的方法論指導。協商民主體制機制的發展與完善是一個系統工程,關涉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領域體制機制的整合與銜接、各層級的協作和配合。如何在這一過程中處理好整體與部分、系統和要素的關系問題,直接影響協商民主的制度化水平。面對這一新的挑戰,我國協商民主體制機制的完善有必要深入了解其他國家協商政治實踐,總結其中的經驗和教訓以服務我國協商民主實踐發展。另一方面,還要關注西方國家協商實踐中的協商程序制定、協商議題生成、協商代表遴選等方面的方式方法。協商民主概念自提出以來,逐漸被一些國家應用于實踐中,各個國家也根據各自的具體特點建構了適合自身的協商民主運行機制,也在協商民主體制機制方面積累了一定的經驗。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制機制的完善,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總體框架中,積極借鑒國外協商民主實踐中有益的成分,加強協商文化的交流與合作,推動協商民主體制機制的發展與完善。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李承福,周德豐.中國式協商民主的優秀傳統文化底蘊[J].學術探索,2017(08).
[3] 夏澎耘.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文化生成[J].紅旗文稿,2016(06).
[4] 王永香,陸衛明.習近平協商民主思想探析[J].社會主義研究,2016(03).
[5] 劉希良.習近平協商民主思想的理論創新與實踐特色[J].科學社會主義,2016(05).
[6] 陳先達.論普世價值與價值共識[J].哲學研究,2019(04).
[7] 包心鑒.協商民主制度化與國家治理現代化[J].學習與實踐,2014(03).
[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74.
[9] 史為磊,盧旭東.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價值、原則和實現路徑[J].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4(02).
[10] 麻寶斌,杜 平.結構分化、觀念差異與生活經歷——轉型時期社會公平感的影響因素分析[J].江漢論壇,2017(03).
[11] 顧愛華,吳子靖.論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戰略選擇[J].中國行政管理,2016(02).
[12] 徐 倩.包容性治理:社會治理的新思路[J].江蘇社會科學,2015(04).
[13] 楊立華.完美治理:中國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新目標[J].學海,2020(01).
[14] 詹世友.公共領域·公共利益·公共性[J].社會科學,2005(07).
[15] 張成福,李丹婷.公共利益與公共治理[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2(02).
[16] 胡錦光.論我國憲法中的“公共利益”的界定[J].中國法學,2005(01).
[17] 池忠軍.善治的悖論與和諧社會善治的可能性[J].馬克思主義研究,2006(09).
[18] 鐘志凌.馬克思恩格斯集體主義思想及其當代啟示[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03).
[19] 王永力,楊先農.習近平對中國優秀民本文化的三重發展[J].廣西社會科學,2020(04).
[20] 馮 剛,王 振.以文化人在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價值意蘊[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11).
[2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323.
[22] 費孝通.對文化的歷史性和社會性思考[J].思想戰線,2004(02).
[23] 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2.
The Value Connotation of the Consultative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Practices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Wang Zhigang, Chi Zhongjun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Consultative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culture form generated from the proces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d the practices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n our country, which has profound value connotations on the practices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n our country. In terms of the consultative subject, consultative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elps to improve the value consensus of consultive subjects through identifying peoples role as the consultive subjects, cultivating consultive subjects consultive spirit and regulating their consultive behaviors. In terms of consultive governance, consultative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elps to strengthen the efficiency of consultive governance through injecting more value rationality into consultive governance and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public interests. In terms of top-level design, consultative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elps to optimize the top-level design of consultive democracy through innovating cognitive idea of consultive democracy, upholding the socialist direction of consultive democracy and improving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consultive democracy.
Keywords: Consultive Culture; Consultive Democracy; Consultive governance; Confidence in Culture
責任編輯:楊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