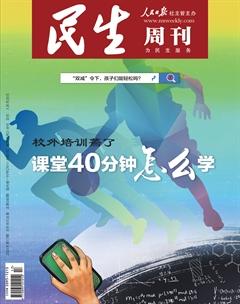與其焦慮,不如擁抱變化
王迪

校外培訓機構不得占用國家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組織學科類培訓。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學科類培訓機構一律不得上市融資,嚴禁資本化運作……
7月24日,“雙減”政策正式落地,嚴格緊縮課后輔導、教育機構等一系列措施,在一些學生家長中掀起不小風浪。
北京、上海、沈陽、廣州、成都等9座城市被列為全國試點城市。家長們如何看待“雙減”政策,對政策落地有哪些期許?《民生周刊》記者采訪了幾位家長。
深得“佛系”媽媽的心
北京朝陽區的李燃,看到“雙減”政策出臺后高呼:簡直深得“佛系”媽媽的心。
李燃用“在劇場看戲”向記者舉例:一個劇場,大家都在看戲。每個人都有座位,大家都能看到演員的演出。忽然,一個觀眾站起來,后面的人為了看到演出,也被迫站起來。最后,所有人都成了站著看戲,所有人都更累了。但得到的,卻是和原來一樣甚至更差的觀劇效果。最可悲的是,雖然大家都累,但很少有人主動選擇坐下來。因為,誰選擇坐下來,誰就啥也看不到。
“這次國家發話了,都坐下看!雖然還是擋不住個別人,但如果大部分人能自覺遵守秩序,總歸沒有之前那么累了,也沒有那么焦慮了。”李燃說。
很多家庭或主動、或被迫地選擇了課外補習,“家長和孩子付出了太多金錢、時間和精力。”在李燃看來,如今教育焦慮愈發嚴重,離不開培訓機構的“推波助瀾”。為了源源不斷地搶招生源,一些培訓機構利用家長攀比、不甘落后的心理,大肆販賣教育焦慮。
“您來,我們培養您孩子;您不來,我們培養您孩子的競爭對手。”在李燃看來,這類赤裸裸的營銷口號以及到處傳播的“雞娃”故事,時刻轟炸著家長們的意志。在如此高壓環境下,不只是父母,孩子更是成為被“壓榨”的對象。
找出路
廣州的張蒙,女兒今年剛剛小升初,順利進入南沙區一所重點中學。
她告訴記者,通常她們母女倆的周末時間,不是在上補習班,就是在上補習班的路上,“我是陪著女兒從小學一路補習到這所重點初中的。”
“雙減”政策出臺,張蒙已經為女兒想好了“出路”—一對一補課。
張蒙覺得,很多家庭還是會有補課需求,畢竟誰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落在后頭。
在北京海淀黃莊地鐵站,以其為圓心一公里范圍內,集合了上百家大大小小的補習機構,由此也誕生了一個特殊群體—海淀黃莊媽媽。
每到周末,來自北京各個區的家長們,從四面八方匯集于此,將孩子送進密集的補習班:奧數、英語、作文……媽媽們熟悉孩子每一項知識的進度,幫助孩子記筆記、刷題,寄希望于補習班提高孩子的成績,只為擺脫小升初隨機派位的命運,考上一所高升學率的中學。
“過去是學習差的上補習班,現在是學習好的上補習班。”有人總結。為什么學習好也上補習班?“因為要競爭名額,連好學生都在補習,你不努力就會落后。”
“有限的名額”,讓媽媽和孩子們都不敢停,只求在激烈的競爭中,把孩子再往上托舉一米。
相比之下,作為海淀家長的徐靖則冷靜許多。她認為,補學科課程,應該是查漏補缺,而非剛需。
“我給孩子報了課外輔導班,初衷是給孩子補短板,對偏科課程培養起興趣,分數不至于拉開太多,也有利于培養孩子的綜合素質。”徐靖告訴記者。
徐靖坦言,沒有家長真正愿意內卷,家長和孩子都累,跟風式“雞娃”的背后,無非還是“唯分數論”的指揮棒。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表示,從嚴監管校外培訓機構,會一定程度遏制“全民培訓”,緩解家長的培訓焦慮。但是,如果不推進教育評價改革,全社會存在唯分數論、唯升學論、唯名校論,就很難把學生從學業負擔中解放出來。
讓孩子成為孩子
有著近10年教育從業經歷的杭州媽媽劉璐,對“雙減”政策有一套自己的觀點。
“首先,我很支持‘雙減。至少和我目前工作相比,我更希望在孩子成長過程中,沒那么多焦慮裹挾我。”
劉璐認為,真正的教育,不在于校外培訓機構,而是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雙結合。好的教育不是靠刷題刷出來的,更不是靠課外培訓“雞娃”雞出來的。
“雙減”政策出臺,傳達了明確的信號:讓教育回歸校內、回歸課堂。
“作為家長,比起奮力‘雞娃,不如從小培養孩子的思維能力,訓練自我驅動力,幫助其養成良好學習習慣,培養其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劉璐認為,好的教育應該是“讓家長做回家長,讓孩子成為孩子”。
對于此次由“雙減”政策引發的風暴,劉璐說,風暴背后,更需要冷靜思考。規范校外培訓機構只是一個開始,未來學校教育能否更高效精準?能否滿足家長多樣化服務需求?新高考改革能否突破“劇場效應”?這些問題才是家長真正關心的。
“與其焦慮于未知的東西,不如擁抱變化,我會密切關注‘雙減政策落地后帶來的變化。”劉璐說。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