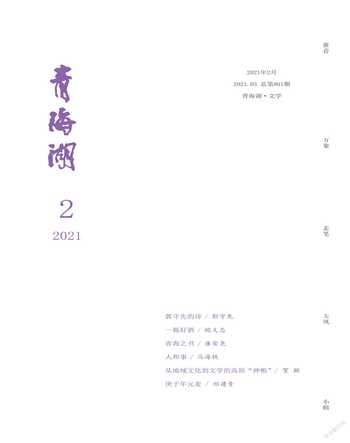青海之書
沿著那條世界著名的、以絲綢命名的偉大之路,很多游人是以敦煌為終點的。對我來說,在敦煌,隨著方向盤的輕輕一偏,尋找那片由勞作者命名的瀚海之旅開始了。
那片平均海拔2800多米、25萬平方公里的高地,像一口朝天張著嘴的旱盆,四面被海拔超過4000米的阿爾金山、昆侖山和祁連山嚴嚴實實地圍著,群山高處的常年積雪,讓這道盆沿四季不絕地散發(fā)銀光,那是向試圖進入這里的人類或動物貼出的白色封條,偶爾有通氣口般的山間小路,崎嶇難行得連動物都懶得穿越,這片高地漸漸變成了人類記憶的死角。人類前往那里的探險腳步,像夜空中偶爾劃過的一兩顆流星,一道流光過后,很快將幽靜歸還于斯。
從新疆境內翻過阿爾金山進入高地北部的烏孜別克族、哈薩克族、維吾爾族的牧人;從青海境內的巴顏喀拉山腳下進入高地的蒙古族、藏族牧民;從甘肅境內的祁連山腳下或敦煌戈壁灘上自北而南進入高地北段的甘肅哈薩克族、裕固族牧民,像一艘艘從不同方位偶爾漂進這荒涼旱海的小舟,駝鈴、羊咩、馬啼聲,很快就被這里巨大的冷寂淹沒。即便是吐谷渾王朝通過這里進入西域的所謂古道,也僅僅是扮演了絲綢之路的備胎角色;即便是國民政府時期修建的青海通往新疆的簡易公路,也沒跑過一輛汽車。
一
電影《你的名字》中的那句臺詞說得好:“我想重新認識你,從你的名字開始。”對一個地方的認知或解讀方式有很多,我對那片高地的認知,是從它的地名開始的。
地理教科書上,盆地叫:柴達木。我曾經在一首詩里寫道:“柴達木,是一棵樹被裁剪出的馴服之路/柴達木,是一條逆淌的植物之河。”事實上,在高地的
邊緣,除了雪山上流下來的雪水養(yǎng)活出面積不大的、低矮的紅柳外,那里并沒有樹,沒有成材的木頭。
是那塊土地的命名者忽悠了我們么?
人類常常依賴自己固有的知識體系,喜歡從自己的文化認知去揣測、理解陌生語境下誕生的地名,甚至會對那些地名產生一種文化上的俯視心理,這很容易滋生傲慢與偏見。
據說,柴達是藏語中才旦的音譯,長壽永固的意思;木是藏語姆的音譯,是漂亮姑娘的意思。合起來,柴達木便是藏族語境中永遠美麗的姑娘。
蒙古族中的和碩特部來到這里后,柴達木這個地名有了新的語意。在和碩特部落的語境中,查、柴、察等相近發(fā)音的詞匯都有白色的意思;達和旦、汗等相近發(fā)音的詞匯有著湖、池的意思,這在內蒙古阿拉善盟境內的鹽湖“查漢池”和青海西北部的鹽湖“察汗”等地名中有著體現(xiàn);木,在蒙古語中是匯聚的意思。柴達木,便有了和碩特蒙古族中“鹽湖密集之地”的語意。
地處青海、新疆和甘肅三省區(qū)交界地帶,周圍又被群山遮掩,讓柴達木成了被上天遺忘的地方:青藏高原在向東北方向低傾時,甩包袱般想把這塊高海拔的干旱之地扔出去,形成一片遼闊的泄洪之地;大地運動中隆起的阿爾金山、祁連山和巴顏喀拉山,像三道大壩,攔截了這片從高處泄來的旱流。
從大興安嶺往西,在陰山以北的遼闊草地上西行,無論是向北至天山南北,還是翻過祁連山后進入青藏高原,所經地域上的藏族和蒙古族等民族的地名認知中,越是嚴酷的環(huán)境,他們越是在一種浪漫、美好的祈愿中,給那些惡劣環(huán)境中的地方,取一些寄托善良愿望的名字。
柴達木,像銀色鹽湖般美艷永在的少女!
然而,柴達木是支在海拔2800米以上的一口大火盆,不分晝夜、不知疲倦地朝天喊渴,來自腹腔內的干熱燒干了它口腔內的植被,盆地邊緣遍布的耐鹽堿、耐干旱的紅柳,是大自然在秋天抹給那張巨嘴的一圈口紅;紅柳叢中,每一峰駱駝低頭吃草的口,就是一臺緩緩移動的小型收割機。
20世紀50年代以前,這個大火盆的腹地內沒有定居的人類,湖水是咸的、地面的大部分區(qū)域是零物質的、山體是被太陽曬得發(fā)紅的雅丹地貌。
命名大地是人類在地球上的一項特權,它的使用卻有著敬畏、熱愛、浪漫、威權仇恨甚至恐懼等緣由。
進入工業(yè)時代,地球上似乎沒有人類喚不醒的地方。沉睡在上帝與人類視野之外的柴達木,被勘探者的腳步、鉆井、運輸車、輸油管道喚醒,它遼闊腹腔內的很多地方,被喚醒者給予新的命名。
對群山、平原、冰川、江河、島嶼甚至星辰的命名者,該擁有多大的權力。有的是長久生活于此的人,根據其地理環(huán)境、物產、地形等取名;有的是路過者,隨意取了個名字,被更多后來的路過者沿用;有的是根據這個地方的經濟發(fā)展,逐步上報經過國家民政部門的認定。有的是農牧民、有的是科學家;有的是勝利的征戰(zhàn)者,有的是占有后的君王。
50年代以前,柴達木腹地那片相當于英國本土面積大的戈壁荒漠上的丘陵、荒灘、溝谷、湖澤、戈壁、沙地、鹽湖,幾乎沒有名字。70多年前,一大批時代的邀約者,從千里之外的不同地方集聚于此,在完成他們的工作過程中,無意中成了這片大地的命名者。從他們嘴里輕輕吐出的地名,像生長在這里的一株株生命力頑強的植物,裝進了柴達木的歷史檔案袋中,讓這片曾經死寂的旱海上的每個島礁都有了帶著故事的名字。
二
我在北京的工作室位于海淀區(qū)學院路的一個園區(qū)內。早上跑步、黃昏散步時,我常常看到馬路東側中國石油大學的牌子;在馬路西側,沿著清華東路向西走得稍遠點,會走到清華大學。如今,一個已經永遠躺在清華大學某年的學生檔案袋里的名字,讓我將中國石油大學和清華大學聯(lián)系在了一起。
時間像層層疊加的沙粒,如果你找到清華大學地質系的學生檔案,“葛泰生”這個名字一定是1952屆學子中閃亮的一塊沙金。那一年,中國開始大規(guī)模的經濟建設,這場建設不同于歷史上的每次大規(guī)模農業(yè)經濟,而是以“工業(yè)血液”之稱的石油來帶動的工業(yè)經濟。毛澤東主席十分憂慮那種需要進口但花錢也買不到的戰(zhàn)略資源:“要進行建設,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飛的,地下跑的,沒有石油都轉不動。”
石油,是克服那種憂慮的一劑良藥。時任國家副主席朱德的焦慮印證了這一點:“一個鋼鐵,一個石油。五百萬噸鋼鐵,五百萬噸石油,就能夠戰(zhàn)勝任何侵略者!”
領導人的擔憂、經由國家戰(zhàn)略演繹,就變成了一種政治號召,青年學子無疑是最迅速的響應者。那一年,23歲的清華大學地質系畢業(yè)生葛泰生,和同時代的大學生一樣,沸騰的青春和熱血和畢業(yè)證的封面一樣,成為旗幟的顏色。“為祖國找石油”成了那個時代一名地質專業(yè)畢業(yè)的大學生最自豪的事情。告別清華園,葛泰生被分配到西北石油管理局勘探處第一地質隊任技術員,參與發(fā)現(xiàn)了延安油田青化砭油礦。
1954年3月1日上午,國家燃料工業(yè)部石油管理總局。初春的陽光照射在院子里的樹木、草坪上,會議室內,一道拉得嚴嚴實實的窗簾,將煦暖的陽光擋在了外面。受康世恩局長的邀請,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在室內正作《從大地構造看我國石油資源的勘探》報告。與會人員的思緒仿佛被李四光的“上帝之眼”帶著,從北京抵達2200多公里外的柴達木盆地,再從地面鉆探般透視地下幾百米,似乎看到一面在地下凝固的黑色之海,一座沉睡的黑色金礦,一團等待燃燒的黑色之火。
在古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為了給人類造福,冒著生命危險從太陽神阿波羅那里偷走了火種,卻被囚禁在高加索山的一個陡峭的懸崖上且讓他永遠不能入睡,疲憊的雙膝也不能彎曲,在他起伏的胸脯上還釘著一顆金剛石的釘子。普羅米修斯是從天上盜紅色火種到人間,開啟人類的原始文明;李四光的講座,讓聆聽的年輕人們心中產生從地下“盜”來黑色之油、開啟中國工業(yè)文明的想法。普羅米修斯的盜火遭到被天神懲罰的命運,中國的這批“盜油者”卻被歷史深深贊許。
李四光作完報告后兩個星期,全國第五次石油勘探會議在西安召開,確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石油勘探任務,明確提出要開展柴達木盆地的石油勘探工作。葛泰生被抽調來擔任5個地質隊中編號為酒泉地質大隊103隊的隊長,前往玉門至敦煌間從事地質勘探。
第二年,葛泰生被調入調查柴達木盆地油田的大軍中。
以當時的交通條件,要前往柴達木盆地進行現(xiàn)代科學勘探,最理想的線路是從甘肅省的敦煌翻越阿爾金山進入。葛泰生和其他隊員,行到敦煌往西120公里的瓜州時,發(fā)現(xiàn)這里就像一個喝醉了酒后歪斜著的大寫Y字的中間部位,上面兩道斜伸出去的兩筆,一筆是從河西走廊北段延伸至新疆的絲綢之路,另一筆是穿越庫姆塔格沙漠抵達新疆境內絲綢之路的南線。從瓜州往西南通向當金山然后走進柴達木盆地方向的,是一條牧人和駱駝、牛羊匆匆來去踩出的秘道。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現(xiàn)代科學勘探,將這條死寂的小道喚醒,后來,小道被拓展成了一條尋找石油、開采石油、運輸石油的“黑金大道”。
80多峰駱駝像新招入伍的士兵,被26名駝工編成隊列,馱著一支遠征柴達木的青春力量,沿著那條秘道前行。駝背上的葛泰生,懷揣著一份1947年的、有關柴達木邊緣的地質報告,里面僅僅提到一個叫油砂山的地方,除此之外,沒有太多其他任何指向性的資料。葛泰生和隊員們順著阿爾金山北麓向西而行,每天只能走十幾公里,高海拔地區(qū)連水都燒不開,多半時間無法做飯,只能啃干餅,喝涼水。行走到第二十八天,才到一個叫索爾庫里(當地人稱為硝爾庫勒)的地方,村子位于新疆若羌縣東南角,是塔里木盆地東南端的庫姆塔格沙漠和柴達木盆地的分界處,距離敦煌已經600多公里。葛泰生一行并沒怎么留心位于這個小村子,也沒在這里住宿,導致了他和一個不該錯過的人在這里錯過。
葛泰生和其他隊員并不知道,7年前,設在蘭州的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中國石油公司甘青分公司探勘處聯(lián)合西北工業(yè)研究所、西北地質調查所組成了柴達木西部地區(qū)調查探勘隊,在索爾庫里找到了最佳的向導,才得以進入柴達木,并繪制出了自己懷揣的那份地質報告。
如果說阿爾金山像一位仰天躺著的巨人的鼻梁,索爾庫里就是鼻尖;高聳的鼻梁上方分別架著塔里木和柴達木兩個盆地構成的眼鏡框。工業(yè)時代前,這兩只眼睛眼神黯淡,少有人知曉。50年代后,隨著柴達木油田和塔里木油田的開發(fā)與建成,這兩個盆地成了發(fā)著黑金之光的“中國之眼”;更像兩個富足的裕鏈,搭在阿爾金山這個駝峰的兩側。
柴達木西部地區(qū)調查探勘隊的隊長周宗浚率隊沒到索爾庫里時,就聽說村子里有位精通哈薩克語、蒙古語、維吾爾語和漢語的烏孜別克族中年男子穆邁努斯·依沙,解放前他曾給負責青海到南疆公路的勘探隊、修路工帶過路,也被從天山流竄到此的烏斯曼殘匪武裝威逼著往柴達木盆地帶過路。那時的柴達木,就意味著難以進入、進去很難出來的地獄,穆邁努斯·依沙無疑就是但丁在《神曲》中塑造的維吉爾那樣一位合格的、通往地獄和煉獄的向導。
在穆邁努斯·依沙帶領下,翻過阿爾金山,進入一片連名字都沒有的茫茫荒野。這段艱難的路途,四分之一的駱駝死在路上,能讓沙漠之舟如此死亡,給隊員帶來多大的恐懼,更大的恐懼是遼闊的荒灘上沒有標志性地標,讓向導穆邁努斯·依沙也不時迷路。泉水在地下休眠,這讓向導也很難發(fā)現(xiàn)水源。寒冷、缺水和迷路三支達摩克利斯之劍時時懸在這些人的頭頂。一片枯黃將天和地連在一起,單調的色彩讓隊員們在駝背上常常處于迷糊狀態(tài)。
一天,剛翻過一個小山頭,走在最前面的穆邁努斯·依沙沖緊隨其后的周宗浚喊道:“看!”
周宗浚和隊員們看到了一片不規(guī)則的紅色,像一瓶無意中碰翻的紅墨水倒在一張黃紙上一樣鋪在荒涼的大地上,也像一道巨大的傷口流出的血凝固在一片枯黃的肌膚上,在灰蒙蒙的天空下顯得非常刺目。周宗浚警惕地問:“那是什么?”
“紅柳!”穆邁努斯·依沙回答道。
紅柳的出現(xiàn),意味著地下會有水。走進長滿紅柳的荒灘上,他們意外地發(fā)現(xiàn)了一眼泉水溢出后凍成的冰。
那一眼泉水就像一縷穿破云層的太陽,拂去了缺水的恐懼,周宗浚和隊員們將那個地方取名為紅柳泉。
在遼闊蒼茫、地表參照物極其缺少的柴達木,一個能留得住的、有生命力的地名,就是給后來者留下的路標或燈塔。90年代末,我第一次進入柴達木采訪時,隨身帶的一本1993年版的《最新實用中國地理圖冊》上,從索爾庫里到紅柳泉之間的幾百公里路上,還沒有一個地名。
紅柳泉,中國最早的一支石油勘探隊,在茫茫柴達木盆地中,帶著克服了缺水恐懼后的喜悅命名的第一個地方。這種如江河源頭般給柴達木大地命名的傳統(tǒng),逐漸在以后的一代代石油勘探者身上得以秉承,形成了一條蓬勃的地名之河。
在紅柳泉,周宗浚無意中聽到穆邁努斯·依沙講的信息:東邊不遠的一處山坡下,有人用紅柳燒火取暖后,想用周圍的土塊掩埋火星,防止風助燃火星燒毀紅柳林。沒想到那種土塊放到火星上去燃燒了起來。會燃燒的土塊?這個念頭在周宗浚的腦海里快速閃過:難道里面含有石油成分?
周宗浚帶領隊員們向穆邁努斯·依沙說的山坡奔去。在大斷層崖頭部位,周宗浚發(fā)現(xiàn)了那種能燃燒的黑色硬塊;他用地質錘隨便一敲,硬度介于土塊和石塊之間的黑色硬塊便落了下來,一股濃厚的但對地質勘探者而言猶如蜜蜂聞到花香一樣的味道,令周宗浚興奮不已,那是中國極其缺少但又急需的石油的味道,是饑餓者盼望著的油餅、面包的味道。周宗浚迫不及待地揣著敲下的幾塊“硬黑土”,快速向山溝里的營地上奔去,像一個已經洞悉了病情的醫(yī)生,需要經過儀器再確診一下。他將“硬黑土”扔進燃燒的紅柳堆,“呼”的一下,立即竄出2米多高的火苗。周宗浚的眼光很快又掃向遍布這類硬塊的大斷層,那是含油豐富的黑色油砂石。周宗浚在當天的實測圖上,寫下了“油砂山”三個字。這是現(xiàn)代中國地質工作者寫進測繪報告中的第一個柴達木盆地內的名字,后來的中國地理版圖上,便有了柴達木盆地西部的“油砂山”。
后來的探測證明,油砂山的含油地層簡直就像浮出海面后凝結的黑色波浪,在海拔2950米的地表上層層疊加出綿延數里的油砂層,最厚處足有50層的樓房
那樣高。地下豐富的油層自然也就阻斷了動植物在這里的生長,讓它在期待開發(fā)的歲月里一直恪守寂荒,等待著現(xiàn)代勘探技術的喚醒,等待著和工業(yè)時代的美麗邂逅。
三
當時的國力條件沒能讓周宗浚的探勘成果變成現(xiàn)實,國民政府很快遺忘掉了遙遠的柴達木。周宗浚沒想到,7年后,中國政府會再次派出的一支油田勘探隊伍深入柴達木,葛泰生就在這支勘探隊中。
1954年的中國,像一輛等待上路油箱卻空著的汽車,對石油的期盼,像莊稼等水、行旅盼店、饑者渴食一樣。找油工作只能突破氣候環(huán)境的各種限制了,和周宗浚的探勘選擇冬天不一樣,葛泰生和隊友選擇了勘探條件更為惡劣的夏天。抵達紅柳泉時,從地下勉強擠出的、含有大量硫酸鎂的水,因為天熱既少又苦,燒開后加不少糖才能將苦澀味壓一壓,方可勉強飲用。隨車帶來的水已經不多了,如果下一個住宿地還沒水的話,就意味面臨著缺水的威脅。半夜時分,幾個隊員開始拉肚子了,有人因為肚子疼得厲害而呻吟、哭泣。帳篷外,氣溫驟然下降,遠處隱約傳來狼嚎,恐懼再次降臨。
第二天早上,大隊長郝清江帶領全體隊員向5公里外的一支駐軍求援。走到土坯壘起來的營房,勘探隊員看到駐軍戰(zhàn)士身上穿的還是棉衣,顏色已經變成了灰色,棉花都露了出來,戰(zhàn)士們長期沒條件理發(fā),頭發(fā)都披到了肩膀上。
這支守軍是甘、青、新三省區(qū)聯(lián)合組織圍剿消滅匪幫之后,單獨駐守在昆侖山和阿爾金山交界地帶的阿拉爾,兩年來只有電臺與外界聯(lián)系,給養(yǎng)長期補充不上。
在和駐軍戰(zhàn)士的交談中,葛泰生才知道,當初,戰(zhàn)士們從索爾庫里請到烏孜別克族向導穆邁努斯·依沙,他心中有一幅柴達木的活地圖進入。剿匪戰(zhàn)士在穆邁努斯·依沙的帶領下,三進三出柴達木盆地。完成剿匪任務后,穆邁努斯·依沙回到了他的家鄉(xiāng)索爾庫里,剿匪戰(zhàn)士留在了青海和新疆交界的阿拉爾。
葛泰生這才明白,他們經過索爾庫里卻沒逗留,錯過的是一個好向導。駐軍立即派專人前往索爾庫里,找到了穆邁努斯·依沙。穆邁努斯·依沙的老伴看到幾十年來在柴達木盆地周邊游走的歲月,讓丈夫從一個青年變成中年再到花甲老人,她不忍丈夫再進茫茫柴達木了。穆邁努斯·依沙告訴妻子:“這些人來找那些能燒著的硬土塊。在柴達木,還有海一樣的鹽,有發(fā)光的寶石。這一次,共產黨是拿著一把金鑰匙來的,我知道柴達木的鎖子在什么地方,我得帶他們去!”
我從那張拍攝于1954年的黑白照片上,如此解讀老人在他生命中最后一次扮演向導角色:照片上有4個人,坐在最前面那峰駱駝上給勘探隊員帶路者,是頭戴烏孜別克族民族氈帽、胡須花白的穆邁努斯·依沙,他左手攥著韁繩,放在大腿上,右手食指伸出指向遠方,左側的兩位勘探隊員順著老人的手指往遠方看去,他們是地質師張維亞和葛泰生,身后不遠處還有一個人騎著駱駝正往這邊趕,那是兩年后被評為青海油田第一個全國先進生產者的馬忠義。這支小隊伍只有8個人,這張照片上就出現(xiàn)了3人。
有了穆邁努斯·依沙這樣熟悉柴達木盆地北緣如熟悉自己掌紋的向導,這支找油隊伍就不再是沒有具體目標的探路者。翻過阿爾金山后,每天的日子幾乎都是復制著前一天的枯燥與單調,天氣的燥熱讓人和駱駝的水分蒸發(fā)量陡增。
荒漠中最可怕的事情接連發(fā)生:先是駱駝因為缺水倒斃,接著是隊伍迷路。
一峰峰饑渴難忍的駱駝因缺水而倒地,無助地向天張著大嘴,渴求著救命的水,低低的呻吟砸得大地上都能冒煙。從敦煌招募到的駝工范建民向葛泰生哀求:“把我們喝的水給它一點吧,只要有水,就能救活它。”
葛泰生將求助的眼光轉向穆邁努斯·依沙,想從他那里得到答案。老向導將眼光投向全隊僅剩下的那兩桶水,然后朝葛泰生默默地、無奈地搖搖頭:這是丟棄駱駝的決定,意味著丟棄隊員和駱駝之間的一份契約。
走出不幾步,范建民就忍不住回頭去看,倒在地上的駱駝一邊掙扎著想站起來,一邊發(fā)出不甘死于荒漠的求助之聲,瞳孔睜得能裝下整個天空的絕望與悲憫。沒有養(yǎng)過駱駝的人,無法理解駝工對駱駝的情感。從敦煌至此的十多天相處,范建民已經把自己牽的駱駝視為朋友,相處得無法分離了。他再次向隊長哀求:“別扔下呀……”
勘探隊員繼續(xù)前行,隊員和駝工們,都不忍心回頭。
傍晚,勘探隊準備扎營、做飯時,駝工范建民顧不上吃飯,拎著半桶水,要返回原路去救那峰駱駝。
穆邁努斯·依沙攔住了他,擔心他會迷路。
一心想救駱駝的范建民指著天上正升起的月亮,自信地說:“一會月亮起來了,月光能照見駝印,能看得見我們白天走的路。”
范建民小看了柴達木的風,即便沒有卷起沙塵的那種細細的看不見的風,也像一個個勤奮而認真的清潔工,很快將白天走過的駝印,清掃得干干凈凈。
那個晚上,全體隊員和駝工都在等待范建民歸來,但他們沒能等到。第二天早上,大家沿著昨天的來路往回返,幾天后,在一片鹽堿灘上發(fā)現(xiàn)了范建民的尸體。柴達木的月光欺騙了他,柴達木的夜風讓他迷路了。
隊員們就地掩埋了范建民。他的軀體雖然埋在了地下,故事卻從一張嘴跑到了另一張嘴,在后來者的口傳歷史中扎下了根。柴達木的開發(fā)歷史檔案里,駝工范建民是第一個為找尋柴達木盆地油田犧牲的人。
穆邁努斯·依沙用烏茲別克語給埋范建民的地方取了個名字:開特米里克,意思是一片山包。
迷路是勘探隊要面對的第一號殺手,缺水則是第二號殺手,這些生命隨時會被命運的繩索吊死在茫茫戈壁中的某一角落,死亡的恐懼像頭頂的太陽,一直罩在頭上。
勘探隊繼續(xù)前行,缺水的威脅隨時都在他們身邊,隊員們早上只用半缸水洗漱,洗臉都成了奢侈的事情。半個月后的一天,他們行到昆侖山下一片海拔2800多米的地方扎下來,這就是周宗浚在7年前鄭重寫在測量圖上的油砂山。
1947年的12月,當時的國民政府派出的柴達木西部地區(qū)調查探勘隊在這里找到了油砂,但那是地表上晾曬著的黑色信號;時隔8年后,新中國派出的葛泰生擔任隊長的101地質隊,發(fā)現(xiàn)了柴達木盆地里的第一個油田:油泉子,這條消息傳到北京時,分管石油工業(yè)的鄧小平副總理發(fā)出這樣的贊賞:“這個油田發(fā)現(xiàn)得好!這個名字起得好!”那一年的12月12日,鉆頭觸及地下650米的地層時,現(xiàn)代鉆探工具和沉睡億年的油層美麗邂逅,黑色的原油像解開束縛的巨龍破土而出,向藍天、大地和鉆探工們露出原色,宣告了柴達木的新時代到來。青海勘探局組織人員用兩個小瓶:一個裝著噴出的原油,一個裝著油泉子的地蠟,專門送給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周恩來稱贊其為“柴達木之寶”。以后的歲月里,在柴達木盆地又有了油嘴子、油墩子、油戈梁、油園溝等油字號的名字。
因為工作需要,葛泰生偕在柴達木油田邂逅的妻子馬念和,于1974年夏天奉調東北遼河油田,曾任副總地質師。
沉睡的土地被它的命名者喚醒,被囚禁于地下的黑色的凝固之海的身影如排浪般涌出大地。地質大隊大隊長郝清江對穆邁努斯·依沙說:“油出來了,但人不能靠喝油生活呀,以后會有更多的勘探人員、采油工人、后勤人員到來,會有更多、更大的出油點出現(xiàn),會建立更大的石油基地,這一切都需要水呀!哪里能找到人能喝的水呢?”
穆邁努斯·依沙帶著找水隊員來到距離油砂山西北12公里的荒灘上,他指著遠處的卡騰能山與阿喀祁漫塔格山說:“那兩座山像一個人的臉頰骨,被夾在中間的地方,像一塊突出的額頭。在蒙古語里,額頭、首領被稱為芒來。聽原來在這里放牧的蒙古族人講,這一帶是元朝末年的寧王卜煙貼木兒的封地,王爺當初把那個地方稱作芒來,后來,人們叫著叫著就傳成了芒崖(發(fā)ai二聲),這里有水!”
不同的命名者,對所命名的對象有著不同的心理期許。人類給一個環(huán)境嚴酷的地方取名時,帶有美麗的期許就是對恐懼的回避或迎對:新中國第一批闖進柴達木的勘探隊員,面對一片連芨芨草都沒有的荒涼戈壁,看到地下油層阻斷土壤的生成和糧食、花朵的生長,而缺少土壤和花朵的土地,該是多么令人恐懼。他們摒棄了沿用芒來的名字,而是取了一個浪漫的名字:花土溝。他們仿佛看到厚厚的油層上長出花草,彩色的花朵搖曳在黑黑的油層之上,搖曳在枯黃的天空下,讓這些花成為地下的黑色石油與藍天白云間的美麗信使,給這片死寂的土地寫下美好的情書。
“花土溝”的名字,標在了新中國的地圖上。
上萬人的石油開采大軍來到了花土溝,逐漸改寫只有干黃的地表和不知疲倦地磕著頭的采油機構成的單調景象。
到1985年,青海省的行政架構中,出現(xiàn)了花土溝鎮(zhèn),這意味著人類的行政力量控制這片荒蕪得連動物都無法生存的死亡之地,再后來,花土溝已經成了一個現(xiàn)代化的集鎮(zhèn),建成了一座6400平方米的現(xiàn)代生態(tài)園,里面有300多種花卉。昔日的老石油們的夢想,在強大、富足的花土溝鎮(zhèn)實現(xiàn)了。花草也在人類的幫助下,克服了生存的恐懼,在這里頑強地亮出生命的力量。
如今,花土溝逐漸被茫崖市的市府所在地替代,從昔日的小鎮(zhèn)集中區(qū)到北邊出現(xiàn)的新區(qū),幾條筆直的道路構成了一個現(xiàn)代化小城的交通脈絡,我特意留心路邊,有幾十年間長成的碗口粗的白楊樹,也有路邊花圃里的花草。文化館、路邊的書店、KTV等場所,也不同程度地開著藝術之花。在整個茫崖市,只留下青海油田花土溝基地、花土溝鎮(zhèn)政府、花土溝長途汽車和花土溝機場這幾個名字。從茫崖開往西寧或格爾木、德令哈、敦煌等地的長途汽車的駕駛臺前,立著的標有起點的白色小牌子上,有的還寫有“花土溝”字樣。(未完待續(xù))
唐榮堯詩人、作家、編劇,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魯迅文學院32屆高研班學員、銀川市作家協(xié)會主席、銀川文學院院長。出版詩集《騰格里之南的幻像》,散文集《王朝湮滅:為西夏帝國叫魂》《西夏帝國傳奇》《王族的背影》《西夏王朝》《神秘的西夏》《寧夏之書》《青海之書》《西夏陵》《大河遠上》《青海湖》《中國新天府》《賀蘭山,一部立著的史詩》《西夏史》《中國回族》《月光下的微笑》《青草間的信仰》《山下》等20部人文專著。目前,在賀蘭山下專事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