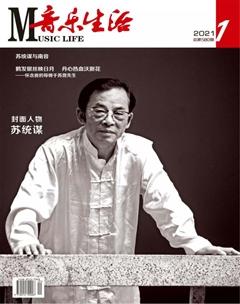數(shù)字“三”在民族音樂(lè)中的文化解讀
“數(shù)字音樂(lè)”在我國(guó)民族音樂(lè)中占據(jù)了一席之地,無(wú)論奇數(shù)一、三、五、七、九,或者偶數(shù)二、四、六、八、十均有涉及[1]。數(shù)字對(duì)我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的體裁、題材、板眼、曲式結(jié)構(gòu)以至于民族樂(lè)器的構(gòu)造、演奏法、音區(qū)劃分等多方面有著深遠(yuǎn)的影響。“數(shù)字文化”對(duì)傳統(tǒng)文學(xué)、風(fēng)俗掌故、哲學(xué)觀念、宗教信仰的交叉包容不斷被中外學(xué)者認(rèn)知。目前我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中“數(shù)字”現(xiàn)象研究主要集中在傳統(tǒng)[2]文學(xué)、修辭學(xué)、宗教文化學(xué)領(lǐng)域,雖有部分學(xué)者開(kāi)始把數(shù)字作為關(guān)注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獨(dú)特的切入點(diǎn),以分析中國(guó)人傳統(tǒng)的思維體系和社會(huì)情景,但作為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民族音樂(lè)中的數(shù)字現(xiàn)象及背后樂(lè)本體分析鮮有涉及。“數(shù)字音樂(lè)”關(guān)聯(lián)著中國(guó)人的傳統(tǒng)思維、經(jīng)驗(yàn)及歷史實(shí)踐,其背后的人文層面亟待厘清。
一、我國(guó)民族音樂(lè)中“三”之現(xiàn)象
筆者在我國(guó)民族音樂(lè)中爬梳出一部分涉及數(shù)字“三”形態(tài)元素的曲目(劇目),包括了琴曲、器樂(lè)合奏、戲曲、曲牌等若干類型,試對(duì)其展開(kāi)樂(lè)本體方面討論。
(一)琴曲中的“三”
大量琴曲形態(tài)學(xué)分析實(shí)例表明,在現(xiàn)存打譜演奏的傳統(tǒng)琴曲中體現(xiàn)出“泛起、中段、泛止”的三段式形態(tài)特征,是“三”在古琴藝術(shù)中的一個(gè)重要表達(dá)。在琴曲結(jié)構(gòu)中“由三個(gè)分段組成的琴曲最小,數(shù)量較多,省去每一個(gè)組成部分只含一個(gè)分段,琴曲的種種構(gòu)成要素都在萌芽狀態(tài),是結(jié)構(gòu)最簡(jiǎn)單的小曲。”聆聽(tīng)經(jīng)驗(yàn)方面,三段式的琴曲演奏過(guò)程即開(kāi)頭散起,節(jié)奏和緩曲調(diào)不明顯,此部分亦為“入調(diào)”,中間段落則是作品核心部分表達(dá),第三部分為入慢,最后由尾聲泛音結(jié)束全曲。古琴演奏上,有“掐撮三聲[3]”作樂(lè)段結(jié)束聲的技法。古琴在演奏當(dāng)中,采用的是復(fù)合律制,即“三律交替”的形式來(lái)表達(dá)音樂(lè)。縱觀琴器表面十三個(gè)“明徽”,每根弦以第七徽為中心宮音,向左的第7—13徽,向右的第7—1徽,自然泛音音階均是“宮—角—徵”的音高序列,即純五度的音程框架中包含大三度、小三度的音程關(guān)系。以七徽為中心,兩邊音高呈對(duì)稱規(guī)律分布,此琴弦震動(dòng)中的聲學(xué)物理現(xiàn)象與“三”之關(guān)系有待思考。
以三個(gè)字命名的琴曲數(shù)量相當(dāng)可觀,其中不少都是著名的古琴大操等。即便是中小型琴曲,如《關(guān)山月》《仙翁操》《鳳求凰》《山居吟》《秋風(fēng)詞》《雉朝飛》等也是廣為流傳的優(yōu)秀曲目。歷代琴論中均有古琴泛音、散音、按音對(duì)應(yīng)天、地、人的敘述,琴曲題名中帶“三”的還有《梅花三弄》《韋編三絕》《陽(yáng)關(guān)三疊》《岳陽(yáng)三醉》《三才引》等。
(二)民間器樂(lè)組合中的“三”
廣東音樂(lè),廣義上包含以廣府文化為中心的珠三角地區(qū)器樂(lè)合奏(粵樂(lè))、以潮汕地區(qū)為中心的潮州音樂(lè)和梅州客家文化為中心的客家漢樂(lè)。從人文視角觀察廣東的區(qū)域性特征:廣府、潮汕、客家呈現(xiàn)出了三足鼎立的格局,三者之間人文特點(diǎn)鮮明、界限清晰。廣東音樂(lè)中“三”的元素,舉例如下:
《三汲浪》(粵樂(lè)傳統(tǒng)樂(lè)曲)、《三醉》(漢調(diào)傳統(tǒng)樂(lè)曲)、《垂楊三復(fù)》(粵樂(lè)、何柳堂)、《三潭印月》(粵樂(lè)、呂文成)、《柳娘三醉》(粵樂(lè)、宋郁文)、《金蓮三疊》(潮州佛樂(lè))《三月三》《三更月》《三點(diǎn)金》《北腔三板》《鳳求凰三板》(潮州音樂(lè))等。
其中器樂(lè)配置上有粵樂(lè)(廣府地區(qū))“三架頭”伴奏:粵胡、秦琴、洋琴;潮州音樂(lè)中缺一不可的“潮樂(lè)三大件”:二弦、椰胡、揚(yáng)琴;客家漢樂(lè)中的“清樂(lè)”伴奏:箏、琵琶、椰胡。今人編著的音樂(lè)譜集著作方面,亦有《廣東漢樂(lè)三百首》《廣東新漢樂(lè)三百首》書(shū)籍[4]出版。
在我國(guó)環(huán)太湖流域,有一個(gè)典型的樂(lè)種“江南絲竹”,其代表性曲目“八大曲”中有著名的“三六體系”,即《老三六》(《原板三六》),和在原始譜基礎(chǔ)上加花形成《中板三六》《花板三六》共計(jì)三首獨(dú)立的樂(lè)曲。在演奏組合編制上,江南絲竹少則有三五人,三人編制組合樂(lè)器有:二胡、曲笛、琵琶。二胡是線條性樂(lè)器,曲笛在二胡的線條上加花點(diǎn)綴,即是行話描述的“糯二胡、花笛子”。琵琶作為能發(fā)出“珠落玉盤(pán)”聲音美學(xué)的顆粒性彈撥樂(lè)器與二胡、曲笛的演奏互為應(yīng)和形成最簡(jiǎn)單質(zhì)樸的“吹、拉、彈”形態(tài)組合。
(三)音樂(lè)典故中的“三”
我國(guó)歷史上與“三”相關(guān)的音樂(lè)典故列舉如下:
“三日繞梁”(即“余聲三日”)出自《列子·湯問(wèn)》:“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guò)雍門(mén),鬻歌假食。既去而馀音繞梁,三日不絕。”韓娥的歌聲,在其人離開(kāi)后仍然能夠在原地余音繚繞、三日不絕。這個(gè)典故以文學(xué)性的描述反映了韓娥高超、動(dòng)人、入情的歌唱技巧。“朱弦三嘆”出自《禮記·樂(lè)記》:“《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孔穎達(dá)疏:“越,謂瑟底孔也,疏通之使聲遲,故云疏越。”這個(gè)典故中承擔(dān)器樂(lè)演奏、伴奏的瑟“朱弦疏越”,譯為白話即瑟張有紅色琴弦,底板上有大面積(疏)的出音孔(越)。這種出音孔設(shè)置的瑟能發(fā)出余韻悠長(zhǎng)的聲音,這種余韻悠長(zhǎng)的器樂(lè)伴奏應(yīng)和人聲相得益彰,形成一唱三嘆的現(xiàn)場(chǎng)效果。“三日不彈”出自清·曹雪芹《紅樓夢(mèng)》第八十六回:“這果真是‘三日不彈,手生荊棘。”這個(gè)典故反應(yīng)了技藝學(xué)習(xí)要遵循“曲不離口、拳不離手”的古訓(xùn),器樂(lè)演奏也要時(shí)刻溫故知新、保持“每日必彈”的良好習(xí)慣,不能有懈怠,這樣才能保持技能水平的不退化。此外,古人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蓋指在音樂(lè)的審美感受中人聲最為可貴美好。又《論語(yǔ)·述而》:“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lè)之至于斯也”朱熹其“蓋心一于是,而不及乎他也。”孔子在齊國(guó)聽(tīng)到《韶》樂(lè),聽(tīng)得入迷陶醉,三個(gè)月當(dāng)中吃飯都沒(méi)覺(jué)查出肉味,可見(jiàn)《韶》樂(lè)的魅力。
(四)民族音樂(lè)中其他可見(jiàn)的“三”
我國(guó)民族音樂(lè)中“三”之現(xiàn)象,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jì)還有:浙江婺劇:曲牌《三五七》;川劇三吹:川劇單列演奏形式,其在正式開(kāi)演前,吹奏的三支嗩吶曲牌,以起開(kāi)場(chǎng)或定場(chǎng)的作用;蘇州評(píng)彈:傳統(tǒng)書(shū)目《三笑》;京韻大鼓:傳統(tǒng)劇目《三堂會(huì)審》;南音:傳統(tǒng)曲目《三千兩金》、《陳三五娘》,京劇文武場(chǎng):京胡、月琴、弦子被稱為“文場(chǎng)三大件”,單皮鼓、大鑼、小鑼稱為“武場(chǎng)三大件”;河北吹歌:常用的樂(lè)器有嗩吶、笛、笙三件,白族“繞三靈”:三腔(腔調(diào)有高、中、低三腔或南腔、北腔、海東腔。);采茶舞:“三絕”矮子步、單袖筒、扇子花;湖南山歌:高腔、平腔、低腔;昆曲伴奏:曲笛、三弦、鼓(點(diǎn)鼓、板鼓);南曲伴奏:簫、管、拍板,曲牌:《金殿樂(lè)三疊》《三轉(zhuǎn)小梁州》《快活三》《鬼三臺(tái)》《三犯白苧歌》……
我國(guó)古典戲曲音樂(lè)論著《唱論》中亦有:“竊聞古之善唱者三人:韓秦娥、沈古之、石存符。……三教所唱,各有所尚:道家唱情,僧家唱性,儒家唱理”的表述。在我國(guó)的民族音樂(lè)形態(tài)學(xué)分析方面“三”有著典型意義,追溯中國(guó)古代音樂(lè)史可發(fā)現(xiàn)民族音樂(lè)在漫長(zhǎng)的歷史時(shí)期主要來(lái)源于中原音樂(lè)、四域音樂(lè)、外國(guó)音樂(lè)三大類型。這三類音樂(lè)通過(guò)相互間的借鑒融合,最終形成了華夏音樂(lè)系統(tǒng)。我們?cè)購(gòu)膫鹘y(tǒng)音樂(lè)的音本體及樂(lè)本體層面考察,這種特征亦無(wú)處不在;例如“一帶一路”沿線的民族音樂(lè)就是一個(gè)典型研究案例。其次我國(guó)古代音樂(lè)史研究[5]有“上古音樂(lè)(先秦)”“中古音樂(lè)(秦漢—隋唐)”“近古音樂(lè)(宋元明清)”的劃分。民族音樂(lè)學(xué)家董維松先生認(rèn)為“頭腹尾式的‘起展落(包括‘起平落、‘起轉(zhuǎn)落等)結(jié)構(gòu),是我國(guó)傳統(tǒng)民族音樂(lè)三部性結(jié)構(gòu)的主要特征,它最普遍、最富有典型性。”[6]劉正維指出“我國(guó)的漢族民間音樂(lè)旋律調(diào)式,系由不同表現(xiàn)性能的徵、羽、宮三色‘三音列連接而成;調(diào)性變化則靠屈調(diào)與揚(yáng)調(diào)。三色‘三音列,美術(shù)界的萬(wàn)紫千紅靠紅黃藍(lán)‘三原色調(diào)配,我國(guó)音樂(lè)的‘色彩大都靠徵羽宮‘三原色調(diào)配。”[7]
自然光通過(guò)三棱鏡的折射化為“紅、橙、黃、綠、青、藍(lán)、紫”七色光譜,而人眼對(duì)“紅、綠、藍(lán)(青)”之光的“三原色”敏感性最為強(qiáng)烈。我國(guó)紫砂壺造型藝術(shù)中的三大基礎(chǔ)壺型:西施壺、供春壺、石瓢壺,“三生萬(wàn)壺”生成了千百種形態(tài)的紫砂壺;我國(guó)民族音樂(lè)亦是在“三”的形態(tài)基礎(chǔ)上衍生出了龐大、完善的藝術(shù)文化體系,“三”在音樂(lè)教育、音樂(lè)美學(xué)、音樂(lè)批評(píng)、音樂(lè)形態(tài)、音樂(lè)鑒賞等方面有著深遠(yuǎn)的影響。[8]
二、民族音樂(lè)中“三”的成因
作為傳承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重要媒介,民族音樂(lè)中蘊(yùn)含了中華民族特有的哲學(xué)、倫理、道德和審美,它與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美學(xué)相結(jié)合。
(一)出自典故、傳說(shuō)
此類數(shù)量龐大如琴曲:《韋編三絕》《岳陽(yáng)三醉》《陽(yáng)關(guān)三疊》等,這類琴曲題材源于歷史故事或諸如《岳陽(yáng)三醉》呂洞賓飛升得道的傳說(shuō)。我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借鑒音樂(lè)藝術(shù)來(lái)表達(dá)的一種樣式,在我國(guó)的傳統(tǒng)戲曲、曲藝中此類劇目尤為繁多。例如:《三打祝家莊》《三請(qǐng)樊梨花》《三借芭蕉扇》《三笑姻緣》等。這些典故在我國(guó)廣為流傳、婦孺皆知。其分別以說(shuō)唱、曲藝、戲曲、文學(xué)等方式來(lái)表現(xiàn)。這些題材的音樂(lè)化運(yùn)用,應(yīng)和了音樂(lè)的教育、教化作用。戲曲(曲藝)在傳統(tǒng)乃至現(xiàn)代社會(huì),這些典故傳說(shuō)依靠音樂(lè)藝術(shù)的表達(dá),在豐富我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的同時(shí)仍然肩負(fù)著基礎(chǔ)的音樂(lè)教育意義。而成語(yǔ)類“一唱三嘆”“三日繞梁”“朱弦三嘆”“三日不彈”等則以“三”[9]之?dāng)?shù)目表述數(shù)字文化在音樂(lè)教育、音樂(lè)欣賞、音樂(lè)傳承等方面的意義。
(二)出自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哲學(xué)觀
古語(yǔ)曰:“天數(shù)極高,地?cái)?shù)極深,盤(pán)古極長(zhǎng)。后乃有三皇。數(shù)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處于九,故天去地九萬(wàn)里。”《春秋繁露·官制象天》指出:“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規(guī),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時(shí),三時(shí)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由此觀之,三而一成,天之大經(jīng)也,以此為天制。”又有明·吳承恩《西游記》第二十七回:“常言道:事不過(guò)三。我若不去,真是個(gè)下流無(wú)恥之徒。”《禮記·禮記上》:“卜筮不過(guò)三。”《論語(yǔ)·公冶長(zhǎng)》:“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曹劌論戰(zhàn)》:“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妙法蓮華經(jīng)》:“法華三車(chē)(羊車(chē)、鹿車(chē)、牛車(chē))”喻法。在佛經(jīng)中高頻出現(xiàn)的蓮花,其表法喻義在于,根部蓮藕生成長(zhǎng)在水底淤泥中,代表六凡境界,莖處在水中表示四圣法界、而蓮花頂出水面,代表中道、不落兩邊。蓮的三部分各有喻義。在八卦圖中,每卦都有三爻。天有日月星三寶;地有水火風(fēng)三寶;人有精氣神三寶。古老術(shù)數(shù)“六爻”之法,即“預(yù)測(cè)人將三枚銅錢(qián)放于手中,雙手緊扣,思其所測(cè)之事,意念所測(cè)信息注入于手中三枚銅錢(qián),合掌搖晃后放入卦盤(pán)中,擲六次而成卦。”我國(guó)文學(xué)中亦有“三字成文”“三單成復(fù)”的傳統(tǒng),《三字經(jīng)》即是其典范。其他相關(guān)表述還見(jiàn):魏蜀吳、中日韓、基督教中圣父、圣子、圣靈,道教三清(太清、上清、玉清)、佛教三寶(佛、法、僧)、東方三圣(藥師佛、日光菩薩、月光菩薩)、西方三圣(釋加牟尼佛、大勢(shì)至菩薩、觀世音菩薩)等。
龐樸則認(rèn)為:中國(guó)人具有“一分為三”的思維模式,此形成了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中約定俗成“三”之傳統(tǒng)。“三”的概念貫穿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各個(gè)方面,其中就包括了中國(guó)民族音樂(lè)中的“三”之普遍現(xiàn)象。其中相當(dāng)數(shù)量的一部分曲目,源自中華民族傳統(tǒng)的哲學(xué)理念及信仰,舉例如下:粵劇《三官堂》、川劇《中三元》、湖南花鼓戲《喜報(bào)三元》、琴曲《三才引》、廣東音樂(lè)《三寶佛》、《金蓮三疊》、道教音樂(lè)《三清勝境》等。這些曲目和儒釋道信仰體系有密切聯(lián)系。如源自道教的福祿壽三星、天地水三官、天地人三才、佛教的佛法僧三寶、儒家科舉“連中三元”等觀念。這類作品往往富于內(nèi)涵、哲理豐富,表現(xiàn)中國(guó)傳統(tǒng)社會(huì)中人們的精神情緒。
(三)出于自然與人文景觀
這部分音樂(lè)曲目也很常見(jiàn),例如譽(yù)滿中外的廣東音樂(lè)《平湖秋月》(即《三潭印月》)是作曲家呂文成于20世紀(jì)30年代中秋時(shí)節(jié)暢游杭州西湖,觸景生情創(chuàng)作的一首富有人文情懷的音樂(lè)作品。另有廣東音樂(lè)《三汲浪》、《垂楊三復(fù)》;琴曲《梅花三弄》、道教音樂(lè)《三清勝境》等。這類作品借自然界的景觀例如月亮、浪花、植物等寓意美好的心境。需要進(jìn)一步指出的是這類自然景象,在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中往往被賦予特殊的意義。譬如“歲寒三友”中高潔的梅花和“三汲浪高魚(yú)化龍”之典故等。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jì),我國(guó)的風(fēng)景名勝,以“三”命名的并不少見(jiàn)。例如江西“三清山”、黃山“三主峰”、故宮“三大殿”、蘇州“盤(pán)門(mén)三景”、杭州“三生石”、曲阜“三孔”、長(zhǎng)江三峽、大理崇圣寺三塔等。這些用“三”數(shù)來(lái)命名的景點(diǎn)與我國(guó)傳統(tǒng)人文觀關(guān)系緊密。
(四)出自人物姓名或稱謂
此類如下:
京劇:《三打陶三春》《三娘教子》、昆曲:《張三借靴》;越劇:《三夫人》;潮劇:《三姐下凡》《陳三兩》《活捉三郎》;晉劇:《三姑鬧婚》《三娘教子》;彩調(diào):《王三打鳥(niǎo)》……
為什么在中國(guó)傳統(tǒng)社會(huì),姓名喜好帶“三”并對(duì)排行老三有特別的偏愛(ài),這是個(gè)非常有趣的問(wèn)題。例如劉三姐是流傳在中國(guó)南部的著名民間傳說(shuō)形象(她還有著不同的稱呼:劉三妹、劉三姑、劉三娘、劉娘、劉仙娘、劉三婆、劉三、劉仙、劉王、農(nóng)梅花……)。[10]劉三姐是否在其家族中排行老三?筆者暫無(wú)發(fā)現(xiàn)有關(guān)敘述資料。相同情況在重慶秀山民歌《黃楊扁擔(dān)》中可見(jiàn)一斑,其歌詞唱到“……柳州的姑娘會(huì)梳頭,大姐梳一個(gè)盤(pán)龍髻;二姐梳一個(gè)插花紐;只有三姐梳的巧,梳一個(gè)獅子滾繡球。”會(huì)梳頭的柳州姑娘,人們對(duì)三姐梳出的“獅子滾繡球”造型尤為贊賞,用一個(gè)“巧”字作為最高評(píng)價(jià);又如道教護(hù)法神、我國(guó)百姓民間信仰中的哪吒三太子(其大哥金吒、二哥木吒)在李家三兄弟中故事最為豐富。哪吒鬧海中,被哪吒打死并剝皮抽筋的恰恰又是東海龍王的三太子敖丙;在《西游記》中的護(hù)送唐僧西天取經(jīng)有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共計(jì)三人,而唐僧騎的白龍馬,原型則為西海龍王三太子敖烈;京劇《玉堂春》中經(jīng)典唱段“蘇三起解”;《紅樓夢(mèng)》中的“紅樓二尤”,后世讀者對(duì)尤三姐人物評(píng)論方面明顯稍多于尤二姐。趙樹(shù)理小說(shuō)《小二黑結(jié)婚》中的“三仙姑”、《水滸傳》中“拼命三郎”石秀、《封神演義》中“三霄仙子”(云霄、碧霄、瓊霄)、儒家有“連中三元”之吉語(yǔ),道教中的“福祿壽”三星、“天地水”三官、佛教中的觀音、善財(cái)、龍女之組合;西方三圣中的阿彌陀佛,大勢(shì)至菩薩,觀世音菩薩……都是我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中以“三”流傳的典型。
三、陽(yáng)數(shù)[11]文化概念下的中國(guó)民族音樂(lè)
如果把研究視野擴(kuò)充至一、三、五、七、九等陽(yáng)數(shù)體系,就會(huì)發(fā)現(xiàn)涉及的民族音樂(lè)作品數(shù)量非常龐大,簡(jiǎn)列如下:
曲牌:《一枝梅》《一枝花》《九連環(huán)》;彈調(diào):《九子鞭》《九蓮燈》;廣東音樂(lè):《七星伴月》《一片飛花》《東風(fēng)第一枝》;南音:《一紙相思》;京劇:《一箭仇》《一兩漆》《三岔口》《趕三關(guān)》《五人義》《七星燈》《七擒孟獲》《九龍杯》;昆曲:《十五貫》《張三借靴》;川劇:《三孝記》《五行柱》《五貴連芳》《九龍柱》;豫劇:《三上轎》《三哭殿》《五世請(qǐng)纓》;越劇:《一錢(qián)太守》《五女拜壽》《三洞房》;呂劇:《五女興唐》;湘劇:《一品忠》;湖南花鼓戲:《西湖三流》《三里灣》;潮劇:《三姐下凡》《陳三磨鏡》;《父子三登科》《三篙恨》《三竿恨》《五子掛帥》《五福連》《七日紅》《活捉三郎》《三鳳求凰》;桂劇:《三毛箭打鳥(niǎo)》《七部吟》;高腔:《三元記》;祁劇《三討站蕩》《三闖擋夏》《三孝堂》;粵劇:《三笑姻緣》《三下南唐》《七國(guó)齊》;《三春審父》《七虎渡金灘》《五郎救弟》《一捧雪》《七賢眷》《三打節(jié)婦碑》《三帥困崤山》《九件衣》《九天玄女》;晉劇:《三關(guān)點(diǎn)帥》《三姑鬧婚》;秦腔:《射九陽(yáng)》《三上殿》《三滴血》《出五關(guān)》……
而傳統(tǒng)音樂(lè)中陰數(shù)[12]體系的題材則少得多,譬如:
廣東音樂(lè):《雙飛蝴蝶》《雙聲恨》;錫劇:《雙推磨》;潮州大鑼鼓:《雙咬鵝》《十仙慶壽》;琴曲《四大景》《神游八極》;山東箏曲:《四段錦》;京劇:《四進(jìn)士》《四郎探母》《六月雪》《八大錘》;南音:《八駿馬》、(潮州弦詩(shī))、《大八板》;琵琶大曲:《十面埋伏》……
從統(tǒng)計(jì)上看,在我國(guó)民間音樂(lè)中,陽(yáng)數(shù)體系數(shù)量大大超過(guò)了陰數(shù)體系。而在一、三、五、七、九這幾個(gè)陽(yáng)數(shù)中,又特別青睞數(shù)字“三”,其中奧義值得探討。
三、結(jié)語(yǔ)
筆者從樂(lè)本體、音本體角度對(duì)我國(guó)民族音樂(lè)中“三”之現(xiàn)象進(jìn)行了解讀,首先在傳統(tǒng)人文教育方面,“三”交織了傳統(tǒng)文化的多樣層面;其次從音樂(lè)形態(tài)學(xué)及樂(lè)器演奏法方面觀察,“三”的觀念深刻融入曲式結(jié)構(gòu)、伴奏配器、板式規(guī)律中。例如傳統(tǒng)樂(lè)理當(dāng)中“同均三宮”、“中國(guó)傳統(tǒng)三種音階[13]”等理論;20世紀(jì)50年代樂(lè)器改革前使用的傳統(tǒng)四相十二品琵琶、三弦十二品、十七品的月琴和秦琴;十六、十七弦箏和均孔笛、舊式六孔簫(前sol后do)等,在這些民族樂(lè)器的傳統(tǒng)演奏法上均有“三個(gè)把位”、“三個(gè)音區(qū)”和“三種音響(散音、按音、泛音;筒音、按音、超吹音等)”;再如曾侯乙編鐘分上、中、下三層,其中42枚鐘發(fā)小三度音程、22枚鐘發(fā)大三度音程[14];五度相生律中每一次相生(do-sol、sol-re、re-la、la-mi、mi-si、si-fa)都包含一個(gè)大三度音程和小三度音程;此自然生成的聲學(xué)現(xiàn)象,或反映出宇宙間某種定律法則,玩味其中都有“三”痕跡;音樂(lè)欣賞在聆聽(tīng)中也存在三個(gè)層次:感官欣賞、情感欣賞、理智欣賞;在學(xué)術(shù)研究上,亦有學(xué)者倡導(dǎo)“三重證據(jù)”[15]作為方法論……總之“三”是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焦點(diǎn)。審視中國(guó)人的哲學(xué)傳統(tǒng)和思維模式,“三”是歷史經(jīng)驗(yàn)和對(duì)世界認(rèn)知及生活實(shí)踐共同作用的產(chǎn)物,“三”的現(xiàn)象既是一種文化證據(jù),更是一種文化內(nèi)核,中國(guó)民族音樂(lè)中蘊(yùn)含的“三”是多重合力形成的文化表達(dá)樣態(tài)。
注釋:
[1]筆者按:例如《一枝花》(山東梆子曲牌)、《雙飛蝴蝶》(廣東音樂(lè))、《梅花三弄》(琴曲)、《四大景》(琴曲、潮州音樂(lè))、《五人義》(京劇傳統(tǒng)劇目)、《六月雪》(京劇傳統(tǒng)劇目)、《三五七》(婺劇亂彈唱腔)、《八極游》(琴曲)、《九連環(huán)》(曲牌)、《十面埋伏》(琵琶大曲)……
[2]王震亞:《古琴曲分析》,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5頁(yè)。
[3]彈法:左名指按弦,用大指于上位“掐起”,右手即一“撮”,左大指又兩掐,右手復(fù)一撮,總名“掐撮三聲”。
[4]可見(jiàn)成果例如廣東省大埔縣文化局廣東漢樂(lè)研究組編:《廣東漢樂(lè)三百首》(內(nèi)部資料),1982年版。
[5]例如楊蔭瀏的著作《中國(guó)古代音樂(lè)史稿》對(duì)我國(guó)音樂(lè)史的分期即是采用此體例。
[6]董維松:《論民族音樂(lè)中的三部性結(jié)構(gòu)》,《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84年第2期。
[7]劉正維:《“三色”析〈二泉映月〉》,《人民音樂(lè)》2018年第4期。
[8]層次性結(jié)構(gòu):微觀的“語(yǔ)言-結(jié)構(gòu)”批評(píng)、中觀的“歷史-美學(xué)”批評(píng)、宏觀的“文化-哲學(xué)”批評(píng),見(jiàn)李詩(shī)原:《音樂(lè)批評(píng)的層次性結(jié)構(gòu)》,《解放軍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2年第1期。其他可見(jiàn)“世界音樂(lè)教育三大體系(匈牙利柯達(dá)伊、德國(guó)奧爾夫、瑞士達(dá)爾克羅茲)”;音樂(lè)美學(xué)研究方面有李西安:《中國(guó)民族音樂(lè)美學(xué)三題》,《樂(lè)府新聲》1985年第1期;李凌:《音樂(lè)美學(xué)三題》,《星海音樂(l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83年第2期等。
[9]筆者按:數(shù)字“三”在我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當(dāng)中,一定程度上是一種虛數(shù)概念,例如成語(yǔ)“三日不彈”“三日繞梁”“一唱三嘆”等中,即是虛數(shù)的表達(dá)。
[10]梁昭:《劉三姐》,《民族藝術(shù)》2018年第4期。
[11]陽(yáng)數(shù)即奇數(shù)、單數(shù),筆者指民族音樂(lè)中冠以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三、十五等“單數(shù)”涵義的作品。在我國(guó)傳統(tǒng)樂(lè)理、傳統(tǒng)律學(xué)研究中,亦有學(xué)者提出“單陽(yáng)雙陰”律呂問(wèn)題討論。譬如黃大同先生在2010年11月18日韓國(guó)首爾舉行的第五屆東亞樂(lè)律學(xué)會(huì)議宣讀的論文《六律六呂的單陽(yáng)雙陰交替十二律形態(tài)研究》較深刻地涉及了這一問(wèn)題。
[12]陰數(shù)即偶數(shù)、雙數(shù)。指民族音樂(lè)中冠以二、四、六、八、十等“雙數(shù)”涵義的作品。
[13]筆者按:黎英海首次提出“中國(guó)傳統(tǒng)三種音階雅樂(lè)音階、清樂(lè)音階、燕樂(lè)音階”的理論。參閱黎英海:《漢族調(diào)式及其和聲》,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年版,第7—36頁(yè)。
[14]“以曾侯乙編鐘為例,其中正鼓音和側(cè)鼓音或成大三度關(guān)系,或成小三度關(guān)系。”可參閱漆明鏡:《論雙音編鐘的音程組合》,《音樂(lè)研究》2007年第3期。
[15]“三重證據(jù)法”的代表性學(xué)者有黃現(xiàn)璠、徐中舒、饒宗頤、楊向奎、鄧少琴等。
徐海龍 廣西民族文化藝術(shù)研究院助理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