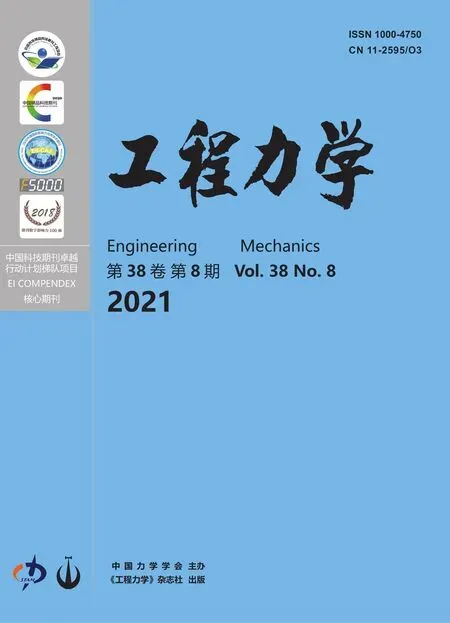近海山地臺風風場特性實測研究
陳伏彬,翁蘭溪,肖 雁,李秋勝
(1.長沙理工大學土木工程學院,湖南,長沙410114;2.中國電建集團福建省電力勘測設計院有限公司,福建,福州350000;3.香港城市大學建筑與土木工程系,香港 999077)
福建沿海地形地貌復雜,屬丘陵、臺地和平原地帶,沿海平原狹窄,海岸帶半島、島嶼眾多。閩東地區的地形特點是山地直接入海,沿海幾乎沒有平原;閩東往南,在鷲峰山-戴云山-博平嶺山帶和海岸線之間的有一條狹窄“平原”地帶,從北到南分布著福州平原、莆仙平原、泉州平原和漳廈平原四大平原;在海岸帶的陸域內從北到南分布著多個半島與眾多海灣。登陸福建的臺風主要有直接登陸(福建沿海為第一登陸地)、登臺入閩(登陸臺灣后再進入福建)[1]。因此,開展福建沿海山地地區的風場特性研究,對提高該區域工程抗風安全具有重要的科學意義與工程應用價值。
國內外眾多研究者開展了臺風實測研究,并取得了豐碩成果。研究表明:臺風與常規的自然風不同,特別是平均風速剖面和湍流度剖面存在一定差異[2],在100 m 近地邊界層中滿足對數率發展[2?3]。孫富學等[4]研究了沿海平坦地貌下的臺風風場特性,指出10 m 高度范圍內平均風速剖面指數遠高于規范建議值;潘晶晶等[5]開展了東南沿海脈動風特性實測研究,分析了不同高度處紊流度與陣風因子的特點;李秋勝等[6?10]及其團隊在臺風現場實測上開展了大量研究工作,深入分析了臺風登陸時的風速剖面、湍流特性以及陣風因子;發現其風速剖面除了滿足對數率分布外,還滿足指數律分布,并給出了近海開闊地貌下的風速剖面指數率取為0.142,與Vickery 等[11]的研究相吻合,所提出的風場參數廣泛應用于工程實踐中[7,12]。現有的臺風實測研究主要在靠近海邊的平坦區域,而像海邊丘陵地帶的靠海山地的實測研究鮮有報道;正如Ishizaki[13]研究所提,不同的臺風之間的風參數存在一定的差異,每個臺風都有其特性。因此,開展山地地貌條件下的臺風風場特性分析尤顯重要。
本文基于福建近海山區兩座100 m 測風塔測得的10 m、30 m、50 m、70 m、80 m 5個高度處的實測風速數據,以10 m 高度平均風速大于10 m/s為強風標準,選取有效風速樣本,應用Bootstrap統計方法,研究山地地區臺風風場的平均風剖面、湍流度剖面的變化規律,研究結果可為福建近海山地地區工程結構抗風設計提供參。
1 近地邊界層風特性
1.1 平均風剖面
Davenport[14]研究指出指數率函數可以很好地擬合平均風速沿高度的變化規律,其表達式如下:

式中:z為高度;U(z)為z高度處的風速;U(zref)為參考高度處的平均風速; α為地面粗糙度指數,也稱風切變指數(風剖面指數)。
對公式進行變換,可以通過實測得到的不同高度處的平均風速確定α:

風切變指數受地表覆被、地形以及障礙物的影響較大,要得到相對準確的風切變指數,需要采用兩個高度的高度比至少為1.5的風速樣本,并且兩個高度風速記錄的時間以及風速儀安裝的橫梁水平長度應相同。
1.2 湍流強度
湍流強度是衡量湍流強弱的相對指標,定義為平均時距內脈動風速的標準差與相應時距內縱向平均風速大小的比值[14]:

式中,I10為10 m 高度名義湍流度,對于B類地貌,規范給定的α 和I10的值分別為0.15和0.14。
1.3 陣風因子
陣風因子可以表示風的脈動強度的大小,其定義為陣風持續期的平均風速的最大值與平均時距內平均風速的比值[14]:

由湍流強度剖面可以建立陣風因子剖面,如下:

其中,中國建筑荷載規范中建議陣風峰值因子的取值為2.5。
2 Boostrap法

3 現場實測及數據選取
3.1 臺風“納沙”和臺風“海棠”
2017年7月30日6時,臺風“納沙”在福清沿海登陸,中心附近最大風力達到12 級(33 m/s),19 h 后(約2017年7月31日3時),臺風“海棠”也在福清沿海再次登陸;形成罕見的雙臺風效應。
3.2 實測系統及場地條件
在臺風“納沙”及“海棠”期間,距離臺風路徑較為接近的風電場主要有閩清上蓮、尤溪湯川、沙縣鄭湖、德化美湖鄉、古田泮洋、古田長坑、屏南黛溪、大田廣平。本文選取數據相對完整的古田長坑(經度:26°51',緯度:119°9')和古田泮洋(經度:26°30',緯度:118°55')兩個測風塔的實測數據進行分析,兩個測風塔相距3.6 km,周邊地貌如圖1所示,古田長坑測風塔在離地面10 m、30、50 m、70 m、80 m 高度處布設安裝了美國NRG 品牌的三杯式風速儀進行風速觀測,古田泮洋站點在離地面10 m、30 m、50 m、70 m 高度布置風速風向儀,風速計風速范圍為0 m/s~70 m/s,風向的測量采用NRG#200P的風向標,采樣頻率為1 Hz,臺風影響期間兩個測風塔進行不間斷測量,總觀測時長144 h,在后續分析中選擇風速較大的時間段進行分析。

圖1 測風塔及周邊500 m 地貌圖Fig.1 Wind tower and its surrounding 500 m landform map
4 結果分析
在建筑結構的設計中,設計人員通常需要預先掌握工程場址的各項基本特性,才能準確把握建筑結構的風荷載。風場的基本特性主要包含平均風速、平均風向、湍流強度、陣風因子、風剖面等。為分析雙臺風登陸過程中的脈動風特性,本文選取10 m 高度處平均風速≥10 m/s的樣本進行湍流強度、陣風因子、風剖面的分析,經過篩選,得到古田泮洋站點的120個有效樣本和古田長坑站點的150個樣本。
4.1 平均風速和平均風向
古田長坑和古田泮洋兩個站點在最高處的風速風向儀實測得到的風速和風向如圖2所示。由圖2(a)可知,古田泮洋站點70 m 高度處的10 min平均風速的最大值為21.4 m/s,而且受臺風“納沙”和臺風“海棠”的影響風速時程分布規律出現明顯的雙“M”型四峰,第一個“雙峰”之間的最小風速為9 m/s;第二個“雙峰”之間的最小風速為5 m/s;平均風向在第一個“雙峰”之間變化范圍為0°~ 140°,在第二個“雙峰”之間變化范圍為140°~ 270°,在雙臺風登陸過程中平均風向出現將近270°的變化。由圖2(b)可知,位于古田長坑站點80 m 處的平均風速的最大值為22.7 m/s,該站點實測得到平均風速時程雖然也有幾個明顯的峰值,但沒有呈現明顯的雙“M”型;受雙臺風的影響,該站點的平均風向從20°變化200°。根據宋麗莉等[18]提出的臺風強風數據的代表性判斷指標:臺風過程中風速大小在8級以上、風速時程呈現M型“雙峰”型且“雙峰”之間的風速出現小于11 m/s情況,風向連續變化120°以上,則可判斷為臺風眼區。根據此標準,可以得出臺風“納沙”的臺風眼區經過古田泮洋站點,臺風“海棠”的臺風眼區并未經過該站點。

圖2 平均風速和平均風向Fig.2 Mean wind speed and mean wind direction
4.2 湍流強度和地面粗糙度指數
圖3給出了古田泮洋站點70 m 高度處和古田長坑站點80 m 高度處不同平均風向下湍流強度的分布規律。
由圖3可以看出,兩個站點的湍流強度基本都在0~0.3波動,不同風向下的湍流強度存在差異:對于古田泮洋站點,在風向角30°附近,湍流強度在0.12~0.16波動,而在風向角300°附近,湍流強度在0.23~0.32波動;對于古田長坑站點,在風向角60°附近,湍流強度在0.14~0.24波動,而在風向角180°附近,湍流強度在0.17~0.24波動;這主要和地貌類型和臺風強度有關,而在中性大氣層中湍流強度主要取決于地面粗糙度[19],因此,在古田泮洋站點和古田長坑站點的不同風向下的湍流強度差異主要由地面粗糙度的不同引起的。為了定性地分析湍流強度和地面粗糙度的關系,下文將進行重點分析。IEC 61400?1提出順風向湍流強度與平均風速有關[20?21],并建立了兩者的計算模型:

圖3 平均風向和湍流強度Fig.3 Mean wind direction and turbulence intensity

式中,a和b為擬合參數。
為了分析雙臺風風場下湍流強度和地貌類型以及平均風速的關系,圖4給出古田泮洋站點10 m高度處湍流強度隨地面粗糙度指數和平均風速的變化規律,從圖4(a)中可以看出,古田泮洋站點10 m 高度處實測的湍流強度平均值為0.22,最大值為0.34,最小值為0.15,湍流強度隨著地面粗糙度指數的增大有增大的趨勢;由圖4(b)可以看出,湍流度有隨著風速增大而略有降低的趨勢,且低風速段湍流度離散性較大,采用式(9)經過最小二乘法擬合得到a=0.23,b在0.13和0.25之間變化,說明在風速10 m/s~14 m/s湍流強度受風速大小的影響,湍流強度隨著風速的增大有減小的趨勢。

圖4 10 m 高度處湍流強度變化規律Fig.4 Variation of turbulenceintensity at height of 10 m
4.3 陣風因子
為研究臺風條件下近地邊界層陣風因子的分布特性,圖5、圖6、圖7和圖8分別給出了古田長坑站點和古田泮洋站點陣風因子隨平均風速、平均風向、湍流強度和地面粗糙度指數的變化規律。由圖5可知,在雙臺風的氣候條件下,古田長坑站點和古田泮洋站點實測得到陣風因子隨著平均風速增大有減小的趨勢,且古田長坑站點的這種趨勢更為明顯,說明隨著距離臺風眼距離越近,陣風因子隨著平均風速增大而減小的趨勢更為明顯。由圖6可知,在雙臺風的氣候條件下,古田長坑站點和古田泮洋站點實測得到陣風因子在不同風向下存在一定的差異,古田泮洋站點的陣風因子的最大值出現在250°附近,最小值出現在30°附近;古田長坑站點的陣風因子的最大值出現在110°附近,最小值出現在90°附近,且古田長坑站點的陣風因子整體大于古田泮洋站點的結果,可以看出陣風因子受不同來流風向的影響較大。由圖7可以看出兩個站點實測得到的陣風因子隨著湍流強度的增加都有明顯增長的趨勢,為了準確定義這種趨勢,Ishizaki[13]提出以下經驗表達式:

圖5 10 m 高度處陣風因子隨平均風速變化規律Fig.5 Variation of gust factor with mean wind speed at height of 10 m

圖6 平均風向和陣風因子Fig.6 Average wind direction and gust factor

圖7 10 m 高度處陣風因子隨湍流強度的變化Fig.7 Variation of gust factor with turbulence intensity at height of 10 m

圖8 10 m 高度處陣風因子隨地面粗糙度指數的變化Fig.8 Variation of the gust factor with theground roughness exponentsat 10 m height

由圖8可知,在雙臺風的氣候條件下,10 m高度處陣風因子隨地面粗糙度指數的增大有增大的趨勢,說明在山區地形中,陣風因子受地面粗糙度的影響較大,在越粗糙的地形條件下,陣風因子的數值越大。
4.4 平均風剖面和湍流度剖面
為了便于對比分析,本文同時分析了季風條件和臺風條件下的風場特性。由于10 m 高度的湍流強度受地面干擾較大,在進行湍流剖面擬合時會出現較大的誤差,為此不建議直接采用實測值進行湍流剖面的擬合,本文根據實測得到的風剖面的地面粗糙度指數對10 m 高度的湍流強度進行最小二乘法進行擬合,得到對應的湍流度,然后結合其他高度的實測湍流強度擬合得到湍流剖面。
4.4.1季風風場
圖9為季風風場中平均風速剖面和湍流剖面。從圖9中可以看出,在90%置信區間為[0.104,0.117]中,平均風速大于等于10 m/s風速樣本的風剖面指數α 均值為0.11,與現行荷載規范GB 50009?2012[15]中A 類地貌條件風剖面指數α 規定值0.12相近;湍流強度擬合的風剖面指數為0.16,大于規范GB 50009?2012[15]中A 類地貌計算值。主要原因可能是:相對平均風速,近地面的湍流參數容易受近地植被擾動作用的影響。

圖9 季風風場Fig.9 Wind field during monsoon
4.4.2臺風風場
由于季風的強風風速樣本基本都在10 m/s~12 m/s變化,為研究雙臺風條件下近地風場的特征并與季風分析結果進行比較,本文取10 m 高度處平均風速大于等于10 m/s數據樣本且以12 m/s為分界線,對古田泮洋站點和古田長坑站點的臺風實測風場結果進行擬合分析,結果分別如圖10和圖11所示。

圖10 古田泮洋站點不同風速下平均風剖面、湍流度剖面和陣風因子剖面Fig.10 Mean wind profile, turbulence profile,and gust factor profileunder different wind velocitiesat Gutian Panyang site


圖11 古田長坑站點不同風速下平均風剖面和湍流度剖面Fig.11 Mean wind profile and turbulence profileunder different wind speed in Gutian Changkeng site
圖10給出了雙臺風影響下古田泮洋站點實測得到的風場的風剖面和湍流剖面參數擬合值,從圖10中可以看出臺風風場平均湍流度,平均風速和陣風因子沿高度變化規律都符合指數律分布,不同風速下平均剖面與GB 50009?2012規范給定值相接近,不同的風速區間對風剖面指數α 的影響不大,其值分別為0.15 和0.16,接近規范規定的0.14的值。臺風風場中各高度處實測的湍流度明顯大于規范推薦值,擬合得到的I10在風速區間[10,12)和[12,15)分別為0.17和0.16。
圖11給出了雙臺風影響下古田長坑站點實測得到的風場的風剖面和湍流剖面參數擬合結果,從圖11中可以看出:平均風速大于12 m/s的風剖面指數α 為0.14,90%的置信區間為[0.127, 0.146],和GB 50009?2012規定的B類地貌較為接近;湍流度的實測結果要大于規范給定值,且在不同高度處湍流強度有較大范圍的波動,且這種波動隨著高度的增加略有減小,這主要是由于越高位置的湍流受地面的影響越小。通過最小二乘法擬合得到的I10在風速區間[10,12) 和[12,15)都是0.17,明顯大于規范結果。
5 結論
本文基于福建兩個測風塔實測得到臺風數據,研究了臺風“納沙”及臺風“海棠”影響下平均風速、湍流度、陣風因子和地面粗糙度指數的變化規律,得到了以下結論:
(1)受臺風“納沙”及臺風“海棠”的影響,實測得到的風速時程具有明顯的雙“M”型四峰,平均風向在雙臺風登陸前后發生了將近260°的變化。
(2)在平均風速10 m/s~14 m/s,雙臺風影響下10 m 高度處的湍流強度最大值為0.34,湍流強度隨著風速的增大有減小的趨勢,但隨著地面粗糙度指數的增大略有增大,陣風因子隨著湍流強度和地面粗糙度指數的增加有明顯增長的趨勢。
(3)指數率模型可以較好地描述臺風“納沙”及臺風“海棠”共同影響下福建沿海地區100 m以內近地層平均風速和湍流強度隨高度的變化規律。
(4)季風風場的風剖面指數α 均值為0.11,接近規范GB 50009?2012 中A 類地貌;臺風風場的風剖面指數α 均值為0.15~0.16,與規范GB 50009?2012中B類地貌相近,但臺風風場中的湍流強度明顯高于常規B類風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