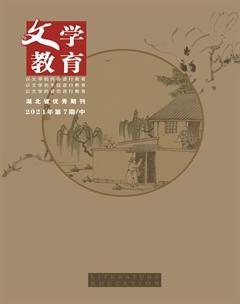淺析程賢章小說中客家地區民風民情
游可心
內容摘要:程賢章是廣東梅州客家地區本土作家的代表,創作了一大批極具客家特色,流淌著客家情懷的小說作品,被稱為“客家文學的擎旗人”,他在創作小說時,除了對客家歷史進行詳盡闡述以外,還將客家文化、客家民風民俗融入了文學作品中,由此為客家文學增添了更深的文化底蘊。本論文將立足于小說文本,分析程賢章小說中包含的客家地區淳樸實在、團結向上、不忘根本的民風。
關鍵詞:程賢章 客家人 客家民俗 客家文學
程賢章是廣東梅州客家地區本土作家的代表,創作了一大批極具客家特色,流淌著客家精神的小說作品。按照羅勇《客家文化特質與客家精神研究》一書的序言中所概括的“客家精神”概念來看,客家精神有三點:“崇先報本、愛國愛鄉精神”、“艱苦奮斗、銳意進取精神”、“團結協作、海納百川精神”。①客家人的吃苦耐勞、正義感、“根”的觀念等團結向上的人文精神,是程賢章小說所要表現的一大重點。
一.客家人的樸素正義感和互助之風
客家人是從中原地區南遷至粵閩等地的,如《圍龍》開頭所述,整個客家人群體遷徙、播種生根需要一個過程,這既耗時耗力,又磨人心志。要克服南遷之路上的重重困難,客家人必須要有團結的精神,這樣才能把勁往一處使。圍龍屋的建造,最初目的是防御外敵,糧食的來源也是自給自足。當時的客家人處在一個比較孤立的境地,為了抵擋這種孤立帶來的不安,團結互助、守望相助的民風便逐漸形成了。
《胭脂河》里這樣描寫客家地區的互助民風:“胭脂河的山民就在這樣稱心如意的房屋里生男育女,傳宗接代。兒女養大了,就來個‘婚連兩姓,緣結百家,誰家閨女出嫁,全村姐妹嫂子就送彩禮,贈花粉……從中午喝到太陽下山,從太陽下山飲到月掛山頭,才各自踏著踉蹌的腳步,打著飽嗝,手里捏著一包吃后分下的肉塊,痛痛快快地回家給小孩們做‘等路的禮物。”②帶“等路”,指的是客家地區出門歸來時給老人、小孩帶禮物的風俗。尋親訪友,不能空手登門;外出歸來,不能空手回家,這樣“等路”者才會皆大歡喜。③透過文中對客家地區人際關系和風俗的描寫,鄰里的和睦、人情的溫暖得以融入人心。
除直接描寫,小說中人物的行為也充分體現了客家人樸素的正義感和互助的風氣。《神仙·老虎·狗》中,內戰時期牛皋受傷,十八歲的地下交通員龍霞常常要給他洗傷口。傷口位置處在盆骨,龍霞不顧男女大防悉心照顧牛皋,只因“這是革命”,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體現在這個年輕的客家姑娘身上。《胭脂河》中,胭脂女為民除害,槍殺了胡一虎,又釋放監獄里的無辜民眾。《挽水西流》中,“烈女”娟妹愿意和田氏一同撫養私生子。其丈夫梁酋生為將孩子留在家,頂下巨額罰款,毅然“過番”下南洋。兩夫妻為了親戚之子,甘愿就此分離,忍受清貧和相思之苦,可謂高風亮節。程賢章筆下的人物,在命運的艱難之下仍不失錚錚鐵骨,秉承著一顆良心,樹立起了“大寫的客家人”形象。
二.客家人的吃苦耐勞精神
客家人的吃苦耐勞,從大遷徙的歷史中就可見一斑。在《圍龍》中描寫的大遷徙里,客家人要從建業(今南京)徒步跋涉到廣東梅州,其路途之遙遠,注定了遷徙的過程不會一帆風順。程旼率領族人遷徙時,要帶上先人骸骨,扶老攜幼,用牛車馬車拉著衣物細軟、鍋碗瓢盆、雞犬牲口,一路南行。”經歷了種種艱難才扎根在廣東梅州的客家人,必然具有“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精神。
客家人吃苦耐勞的精神,鮮明體現在日常農耕勞作之中。臺灣客家文化著名學者陳運棟曾寫道:“由于客家人住的都是窮地方,大家都有地,但大家地都不多,所以沒有專門‘請別人耕田而自己享福的人,也沒有專門被人‘請去耕田的人,大家都要自食其力。”④小農經濟長期以來一直是客家鄉村的主要經濟形式,客家人,尤其是客家婦女每天都承擔著繁重的勞動任務,但小說中的客家人們并不以為苦,反而能從中總結出自己的一套“農業經”。《圍龍》中,娟妹常對天送、醒蓮兄妹說:農家有三寶,菜園是菜籃子,地是油缽子,豬圈是小錢柜。在無青壯年男性的家庭里,兩兄妹亦小小年紀就開始替母親分擔勞動任務。正當天送給番茄施肥時,醒蓮過來搶了糞勺子幫哥哥的忙。兩人的對話充分體現了客家人在勞動中生出的智慧:“一定要在兩株苗之間施肥。”“不可以靠近番茄田澆肥嗎?離太遠,肥料是否可以吸收?”“茄根四面延伸,施下的肥當然可以吸收。”⑤《姐姐明天出嫁》中,秋生哥認為多施肥、用除草劑造成“增產不增收”是不好的,但這與生產隊的大局相悖。姐姐內心經過幾度動搖,最后還是站在秋生哥一邊,不當“女縣令”,文末兩人一同為親手栽的沙田柚樹鋤草施肥,共訴愛語。客家人耐勞、愛勞,在勞動中獲得了口中的糧食和智慧的果實。
對客家人在日常生活和勞作中忍受苦難的能力,程賢章在文中也予以褒揚。《小癩子和“不列級牛”》中,主人公小癩子可謂是客家地區的保爾·柯察金。他為救羊受地主毆打迫害,又深受風濕性關節炎的困擾。他對自己不能勞動耿耿于懷,流淚道:“倒霉也不該在這節骨眼上,人人都干得熱火朝天,我卻成了廢物!”⑥但他的意志力十分頑強,每日吟誦保爾的“生命詩”。病愈后,他認養了一匹瘦弱的“不列級牛”,每日放牛割草。因生病,他放夜草總是十分困難,須得一瘸一拐地到牛棚去;洪水浸村時,他拖著病軀把耕牛搶救出來,為此腿受水泡,瘸腿更加嚴重。但他說:“哪有不受風吹雨打的花木?不經風吹雨打太陽曬,花不紅,果不甜。”⑦小癩子的這番話,把一個笑對苦難的客家人形象展現在讀者眼前。
然而,換一個角度去理解程賢章小說中客家人的吃苦耐勞精神,其情感色彩就會從單純的頌揚,轉向隱含的批判和反思。他的小說中帶有人道主義色彩,表現為對弱者的深刻同情和對他們命運的思考。程賢章作品里的人物都承受著來自生活的不同重壓,按照性別來簡單區分,大部分男性人物,如程武、璨爛、龍種、大野等,承擔的是保衛山河這一類帶有使命感的宏偉任務;而婦女,如田氏、娟妹、胭脂女們等,承擔的卻是來自封建世俗和日常生活的瑣碎重擔,以及更深刻意義上的生命悲劇。客家文化,忠實地傳承了中原地區的文化傳統,包括男尊女卑等腐朽觀念。文氏、田氏這兩位婦女喪偶后寡居,一個靠數銅錢度過長夜,一個和養子做出背德之事后不斷遭受災厄。天送得以出生,是以母親田氏委身于族長熊虎為代價換來的。胭脂女們雖富正義感,力圖除暴安良,卻仍要賠著笑討官老爺們的歡心,她們終究無法擺脫男人玩物這一身份。在當下的文化環境中,客家婦女的吃苦耐勞,逆來順受,也是她們對客家文化中男權話語的自覺認同。作者一方面贊頌她們的高貴,另一方面也通過這種高貴反襯出她們實際地位的低下。
程賢章在小說中描寫人物的勞作和所受苦難時,態度是同情和褒揚皆有之的。正是客家人的這種吃苦耐勞精神,使他們以“客”的身份成功扎根在中國南方,繼而把客家地區建設成今天的模樣。
三.客家人“根”的觀念
認祖歸宗,“不忘本”,這本就是中國古代的人文傳統,源自中原地區的客家民族自然也繼承了這一點。《圍龍》中的老農袁來福,在日本妻子信子得以回國時,同樣收到了去日本定居的邀請,但他不為所動:“我也不阻攔你們去日本尋親,日本是你們的祖國,但中國卻是我的祖國。”⑧天送、醒蓮的四個孩子,分別叫廣輝、東輝、省輝、韓輝,加上未出生的兩個孩子,連起來便是“廣東省韓江水”。“根”在客家人心中勝過一切金銀財寶。
要更深刻地理解客家人“根”的觀念,必須結合他們過去的生存環境來進行思考。客家地區曾有民諺:“寧愿出門做到死,不愿在家吃老米。”被維持溫飽的艱難逼出國門,選擇“過番”的客家年輕男子大有人在。他們離鄉是現實需要,但愛國愛家、懷鄉戀鄉的心理需要亦因此蓬勃生長,他們的“落葉歸根”,歸的是現實中的土地之根,也是心靈之根。出人頭地之后歸來報效家鄉,是許多客家人的做法。《云彩國》中,當年出生在云彩國的璨爛,躲避災禍之后,又回到云彩國當起了開發區主任;他的發小梅華,帶著傷痛出走香港后再歸鄉時,除了返尋“陳三味”,還捐了二百萬港元以建設家鄉的殘疾人服務業。大野本是日本人,但他和姑媽信子蒙袁來福照顧,在客家地區生長多年,他身上早已具有了客家人的優良品質,因而他也算是客家人。大野發誓:“我只要有本錢,就一定回中國投資。”日后他果然兌現了承諾,和天送、醒蓮的兒子韓輝一同在中國投資辦廠。程賢章通過書寫客家人心中“根”的觀念,以及他們尋根、反哺的行為,深化了對客家人懷鄉、戀鄉、愛鄉的表現。客家人雖一開始身為“客”,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客家人的一代代繁衍,他們所到的地方,已經成為了他們的家園,他們的文化也在此生長,這就是他們的“根”。
參考文獻
[1]程賢章.程賢章文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廖紅球,周義,劉日知.廣東文壇常青樹[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3]羅可群.廣東客家文學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
[4]鐘俊昆.客家社會與文化研究:客家文學史綱.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
[5]譚元亨.文學人類學與客家書寫.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14.
[6]周曉平.土風·民情·方言——論程賢章《神仙·老虎·狗》等小說的民間書寫[J].嘉應學院學報,2018,36(03):21-25.
[7]周曉平.歷史印記與文化確認——粵東客家人血淚“過番”與程賢章《挽水西流》[J].嘉應學院學報,2017,35(03):12-18.
[8]陳利群.程賢章長篇小說與客家文化傳統[J].學術研究,1998(12):105-109.
注 釋
①羅勇:《客家文化特質與客家精神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頁.
②程賢章:《胭脂河》,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
③胡希張:《客家文化面面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1頁.
④陳運棟:《客家人》,臺北:聯亞出版社,1981年版,第332頁.
⑤程賢章:《圍龍》,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209頁.
⑥程賢章:《桃花渡》,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頁.
⑦程賢章:《桃花渡》,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頁.
⑧程賢章:《圍龍》,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294頁.
(作者單位: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