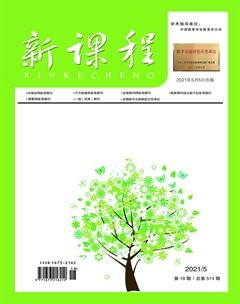毀滅的力量,膨脹的自我
摘 要:《立在地球邊上放號》一詩不光有自由宏闊、雄奇奔放的氣概,還在壯麗浩蕩的意象群下,暗含著對毀滅性力量的贊美。詩人毫無保留地擁抱這股力量,既是由于個人的審美傾向,也是時代思潮的反應。青年人對自我的認知是膨脹變形的,他們相信自己可以擁有征服一切、毀滅一切的絕對力量。解讀詩歌時沒有必要回避文本中毀滅激進的傾向,這種浪漫狂妄的色彩本身就是青春的特別寫照。
關鍵詞:立在地球邊上放號;意象解讀;毀滅力量;自我認知
《立在地球邊上放號》是部編高中語文教材必修上第一單元的文章。這一單元的人文主題是“青春”,《立在地球邊上放號》也是青年郭沫若的青春心語。若只從歌頌青春、贊美力量這一方向來解讀文本,失之太淺,無法引導學生通過意象深入解讀詩歌、理解青春,也很難提高學生對文本、對課堂的興趣。
但這首詩歌本身很有意思,可以說離經叛道。處于青春叛逆期的學生容易被詩歌對青春的別樣演繹所吸引。青春不僅意味著美好、純真、花樣年華,還伴隨著激情、痛苦、變形、破壞乃至毀滅。對青春的吟唱不應回避這些因素,《立在地球邊上放號》的部分價值也在于它如實展現了青年人的激情——膨脹著暴虐、毀滅的力量。
詩中的意象群呈現出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無邊無際的壯闊。詩中“無數的白云”“壯麗的北冰洋的晴景”“無限的太平洋”“滾滾的洪濤”等意象的特點都是極其宏大、純粹、沒有界限。這些意象疊加,構成一幅波瀾壯闊、壯麗奇凌、無可阻擋的畫面。
細細品味這些意象,會發現它們都擁有著毀滅性的力量:白云在天空上“怒涌”,北冰洋遍布冰川冰凌,太平洋積蓄的海嘯狂風要“推倒”地球,眼前滾滾的洪濤可以埋葬一切,絕不是馴服的波浪。這股毀滅的力量狂暴橫肆,并不會在乎被它毀滅的對象是誰,有罪還是無辜。它要持續不斷地毀掉所有、毀掉全世界。
強大到毀滅的力量并不讓人吃驚,暴虐本就是青春的另一重色彩。令人詫異的是作者對這股毀滅力量的態度:沒有遲疑,沒有猶豫,而是全心全意地擁抱。作者用了4次“啊啊”和6次“喲”,通過極其強烈的語氣表達出自己對毀滅力量的按捺不住的向往;將這股力量描繪成“力的繪畫、力的舞蹈、力的音樂、力的詩歌、力的律呂”,用充滿美感的詞匯來形容它,表達了發自內心的贊美與喜悅。
作者郭沫若對狂暴毀滅的欣賞源來有自。在《天狗》中,郭沫若寫道:
“我把月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我把全宇宙來吞了……我剝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嚙我的心肝……我的我要爆了!”他歌頌毀滅的力量,哪怕毀滅了整個宇宙甚至把自己都毀了也毫不猶豫。
郭沫若像獻祭一樣,為了毀滅的力量甘愿獻出所有,原因之一是他崇尚極端強大的力量。《立在地球邊上放號》里,白云、烈日、洪濤、大洋這些所有的意象都有著不可抗拒的威力。詩歌營造了一個陽剛壯美到極致的審美空間,這個力量密度奇高的空間,體現出侵略毀滅的特質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在郭沫若的語境里,毀滅并不是個貶義詞,它帶有新生的味道。《立在地球邊上放號》點出了贊美毀滅的原因:“不斷地毀滅,不斷地創造,不斷地努力喲!”持續地毀滅可以掃除一切障礙和束縛,將過去掃蕩得干干凈凈,給接下來的努力創造留出空間和可能。至于被毀滅的舊世界有沒有價值,這樣做會不會太過激進等問題并不在郭沫若的考慮范圍內。
《立在地球邊上放號》寫于1919年9月10月間,此時郭沫若27歲左右。雖已站在青春的尾巴上,但狂放浪漫的性格特點,風起云涌的時代浪潮都讓他保有了狂飆突進的精神。青年人想擁有改變這個世界的力量,渴望創建一個新天地,迫切地想甩掉一切讓他們感到被約束、被束縛的東西。這種激進的對力量乃至毀滅的推崇,就是時代的青春風貌的顯現。
同時,詩歌對毀滅力量的贊美,也在于敘述者并不畏懼這股力量。從題目中可以看出,敘述者不是一個平凡的、渺小的個體。“立在地球邊上”,說明敘述者站在地球旁,他不是地球哺育的蕓蕓眾生之一,他是與地球平起平坐的個體。在與地球的關系中,他還是主動的一方,他觀察著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我眼前來了滾滾的洪濤”。這類表述明顯構成了“凝視—被凝視”的關系。占據主動的敘述者,并不擔心毀滅的力量無法控制,他有足夠的自信超越這股力量,乃至超越自然,超越地球。
這是無比自信、無比膨脹的自我。在《天狗》中,郭沫若也在反復強調“我是月的光,我是日的光,我是一切星球的光,我是全宇宙的Energy的總量”。這種驕傲狂妄就是五四青年對自我的認知,他們認為自己可以擁有征服一切、毀滅一切的絕對力量。老師引導學生解讀文本時,沒有必要回避里面的激進毀滅的傾向。這是詩歌中意象群的本來特點,這種浪漫狂妄的色彩不僅僅屬于五四那個時代,更屬于青春這個特定的人生階段。
參考文獻:
郭沫若.女神[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50-51.
作者簡介:邱麟淳(1988—),女,文學碩士,高中語文一級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