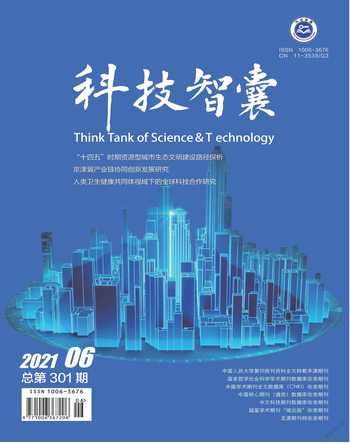“數字+ 需求”驅動社區居民參與共治機制構建研究
黃敘

摘 ?要:隨著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的不斷發展,涉農社區民主化建設逐漸成熟,但居民在參與治理的過程中仍存在著諸多問題與阻礙。文章基于對F社區的調查與實踐,挖掘問題,分析成因,構建“數字+需求”驅動、分類分階段遞推、逐項突破的居民參與融合協同共治機制,以期引導和激發居民需求,實現協同自治,人人自主參與。研究注重機制的普適性和可操作性,為涉農社區居民參與積極性的提升尋找突破口,為其他社區的有效治理開辟新路徑。
關鍵詞:參與機制;分類分階段遞推;逐項突破
中圖分類號:C93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881/j.cnki.1006-3676.2021.06.02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 Governance Driven by “Digital+Demand”
——Based on the Survey of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F Community
Huang Xu
(Jincheng College of Sichuan University,Sichuan,Chengdu,611731)
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politic economy in our society,the construction of democracy in agriculture related communities is gradually mature,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and obstacles in the process of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governance. The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F community,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blems,analyzes the causes,and constructs collaborative co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gration,which is a“digital+demand”driven,classified and promoted by stage and item by item breakthrough,in order to guide and stimulate the needs of residents,realize collaborative autonomy and everyone's independent participation.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universal applicability and operability of the mechanism,looking for a breakthrough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articipation enthusiasm of residents in the agriculture related communities,and opening up new paths for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other communities.
Key words:Participation mechanism;Classified and promoted by Stage;Item by item breakthrough
一、引言
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基層。推動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堅持以黨建為引領,以居民需求為導向,探索“組織聯建、力量聯配、服務聯手、資源聯合”的工作機制,不斷夯實城市發展的基礎。社區是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居民是基本單元中的重要元素。居民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參與是社會治理的本質,其參與程度是衡量社區自治、完善基層民主的重要指標。能否有效地將居民組織起來,決定了基層社會能否成為有自治能力、能夠互助合作、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共同體,決定了基層社會能否實現社會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馮敏良發現缺乏利益關聯性導致居民參與度低。[1]張莉認為,利益關聯性的缺失是因為結構的缺失,應增加制度與資源的支持。[2]向德平、高飛希望通過構建合理的制度來嘗試解決居民參與問題。[3]社區居民參與問題一直是社區實踐調研中最直觀反映出的問題,現有研究已經對這個問題做了大量的探索,但仍然未破解這個難題。[4]因此,突破基層社會治理困境,必須結合實際,尊重基層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注重發揮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優勢。找準突破點,靶向處理,因地制宜地推進基層治理的機制創新以剔除“痛點”。
二、問題的提出
F社區居民主要由原住居民、拆遷后遷入居民、商品小區居民、高校和中學片區的學區房及住宿樓居民等構成,人口多,結構復雜,居民素質差異大,年齡跨度范圍大是其最突出的特征。長期以來,F社區面臨著居民協同治理難度大、溝通協調任務艱巨、居民在除文娛外的社區活動中的參與積極性低等難題。
在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期間,在社區黨群服務中心和社區居委會的支持下,筆者對F社區居民展開了隨機問卷調查,對社區工作人員進行了訪談調查。其中,調查問卷共發放370份,最終回收331份,達到89.46%的回收率,而有效回收問卷為295份,占所有回收問卷的89.12%。筆者的分析數據主要來源于調查問卷。
三、被調查居民的基本特征
在有效問卷的被調查者中男性占50.15%(166人),女性占49.85%(165人)。按年齡劃分:22周歲以下者占4.23%(14人),22~45周歲者占42.30%(140人),46~55周歲者占27.49%(91人),56周歲以上者占25.98%(86人)。按文化程度劃分:初中及以下者占35.95%(119人),中專或高中者占25.38%(84人),大專者占21.15%(70人),本科者占17.22%(57人),研究生及以上占0.30%(1人)。按戶籍所在地劃分:本地戶籍人口占78.85%(261人),外地戶籍人口占21.15%(70人)。按居住時長劃分:1年以下者占2.11%(7人),1~3年者占11.48%(38人),3~5年者占8.46%(28人),5年以上者占77.95%(258人)。
四、社區居民參與情況分析
(一)社區居民對社區管理認同情況分析
社區居民對社區管理的認同程度能體現出社區居民的居住滿意度和歸屬感,這也將決定社區居民的參與和配合程度。社區居民對所在社區管理的滿意者占63.14%(209人),基本滿意者占27.19%(90人),無所謂者占3.02%(10人),不滿意者占4.53%(15人),非常不滿意者占2.11%(7人)。在男性被調查者中,滿意者占63.25%(105人),基本滿意者占25.90%(43人),無所謂者占2.41%(4人),不滿意者占5.42%(9人),非常不滿意者占3.01%(5人);在女性被調查者中,滿意者占63.03%(104人),基本滿意者占28.48%(47人),無所謂者占3.64%(6人),不滿意者占3.64%(6人),非常不滿意者占1.21%(2人)。女性的滿意度較男性的稍高。在占比最高的22~45周歲被調查者中,滿意和基本滿意的有123人,占此年齡段的87.86%,相比其他年齡段是最低的。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119人)對社區管理滿意和基本滿意的有114人,占此文化程度者的95.80%。中專或高中文化程度者(84人)對社區管理滿意和基本滿意的有72人,占此文化程度者的85.71%。大專文化程度者(70人)對社區管理滿意和基本滿意的有59人,占此文化程度者的84.29%。本科以上文化程度者(58人)對社區管理滿意和基本滿意的有54人,占此文化程度者的93.10%。文化程度較低和較高者滿意度比文化程度中等水平者稍高。戶籍屬于本地的被調查者(261人)對社區管理滿意的有176人,占67.43%;戶籍屬于外地的被調查者(70)人對社區管理滿意的有33人,占47.14%。居住1年以下的被調查者(7人)對社區管理滿意的有5人,占71.43%;居住1~3年的被調查者(38人)對社區管理滿意的有16人,占42.11%;居住3~5年的被調查者(28人)對社區管理滿意的有12人,占42.86%;居住5年以上的被調查者(258人),對社區管理滿意的有176人,占68.22%。其中,對社區管理非常不滿意的主要是大專、22~45歲、居住時長5年以上的本地男性。居民普遍認同社區管理工作,但仍存在有待提升的方面。
(二)尋求幫助的渠道選擇情況分析
在尋求解決問題的渠道選擇方面,在本地人中,居住時長1年以下者會找物業管理公司(簡稱“物管”)的占100%,找居委會的占33.33%;居住時長1年以上者找居委會的占73%以上。在外地人中,居住時長1年以下者全都會找派出所;居住時長1~3年者78.95%會找物管,有52.63%找居委會;居住時長3~5年者84.62%會找物管,53.85%找居委會;居住時長5年以上者79.41%找居委會,73.53%找物管。無論戶籍是什么情況,居住時間越長,更多的居民會找居委會解決問題。
(三)獲取信息的渠道分析
在獲取社區信息的渠道中,通過社區宣傳欄得知信息的有259人,占78.25%,占比最高;其次是利用小區業主微信群或社區公眾號,有203人,占比61.33%;再次是通社區工作人員上門通知,有192人,占58.01%;通過鄰居間聊天得知的有186人,占56.19%。在被調查者中通過鄰居間聊天得知的女性106人,男性有80人,男女比例為43:57。利用這個渠道獲得信息的女性比男性更高。22周歲以下的被調查者中有92.86%通過社區工作人員上門通知得知。但無論哪個年齡段,都有75%以上的人會通過社區宣傳欄獲得信息。22~45周歲者中有71.43%的人通過小區業主微信群或社區公眾號獲得信息。46歲以上的被調查者(177人)有96人(占54.24%)在利用小區業主微信群或社區公眾號獲取信息。可見,年紀較大的社區居民基本能較熟練地進行網絡操作。從文化程度的分類不同來看,初中及以下者82.35%通過社區宣傳欄,66.39%通過鄰居間聊天得知;中專或高中以及大專者利用社區宣傳欄的更多,其次是利用小區業主微信群或社區公眾號;本科者有77.19%利用社區宣傳欄,56.14%利用小區業主微信群或社區公眾號,59.65%通過社區工作人員上門通知。研究生及以上學歷1人,利用小區業主微信群或社區公眾號得知。居民在獲取信息的過程中偏向于傳統線下的宣傳欄和線上的電子網絡平臺。居民選擇獲取信息的渠道更注重便捷性和效率,通過鄰里間人與人之間溝通的途徑在弱化。沒了解過的有61人,占18.43%,說明社區居民中存在一小部分居民比較被動,態度比較冷漠。社區需要更多地進行上門告知會有助于這類居民獲取信息。
(四)阻礙居民參與社區活動的因素分析
關于未能參與社區活動的原因調查,有效被調查者的73.72%(244人)因為沒有時間,41.39%(137人)因為不知道,未被通知,30.51%(101人)因為距離太遠,22.96%(76人)對此類事情不感興趣,21.75%(72人)因為社區活動不豐富,11.18%(37人)因為參加活動沒有相應的回報,2.42%(8人)肯定答復都能參加。因而可知,阻礙居民參與活動的主要原因是私人事務對時間的占用。
(五)居民參與社區活動的程度與意愿分析
在所有的社區活動中,政治參與類活動中的社區管理類活動參與度最低。在政治參與類活動、經濟參與類活動中男性被調查者的參與度比女性高,這說明男性居民對涉及自身利益的事務參與積極性更高。在文化參與類活動中,男性與女性參與程度差別不大;在社會參與類活動中,女性被調查者的參與度比男性高。按年齡和文化程度分類的兩種情況,各類社區活動的參與比重結構相近。
從居民參與意愿來看,女性被調查者更支持和關心公益活動,其次是文化娛樂活動,再次是親子活動。在女性被調查者中,22~45周歲者占46.06%(76人),46周歲以上者占48.48%(80人)。男性更支持和關心關愛老人活動,其次是體育健康類活動,再次是文娛活動。在男性被調查者中,22~45周歲者占38.55%(64人),46周歲以上者占58.43%(97人)。46歲以上的被調查者占比過半,這與關愛老人的意愿比較突出有一定關系。
社區居民在一定程度上愿意以公益的形式參與到社區活動中,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給予社區工作更多的支持。對社區管理不滿意和非常不滿意的被調查者提出了不滿意之處:“基本都是形式主義,作秀,拍照,沒實際意義。社區環境衛生狀況差,臟亂差尤為突出,特別是城中村自建小區,安全隱患嚴重。沒有公益文體場所,看得到的全是私人麻將館。”居民更關心社區能否在提升居民素質、法律意識、改善社區居住環境、環境治理、小區建設、停車問題方面有所為。這說明社區居民對有關自己切身利益的社區活動或事務參與意愿更高。
筆者通過對社區工作人員進行訪談發現:社區工作人員對院落的居民情況把握欠缺精準(參與的居民主要就是老年人和小孩,年輕人都在上班),居民對社區的信任度較低(在社區工作開展過程中與物管公司走得比較近時,居民會認為它們有所勾結)。為促進居民參與公共事務和社區治理,應賦權于非政府主體,嵌入或拓展社區社會網絡。另外,適當的動員策略也是推動居民參與的重要因素。[5]
五、F社區提高居民參與度的現有做法
自2019年以來,社區通過項目驅動居民積極參與社區治理工作,協同社會工作服務中心通過外包服務完善社區治理環境。
F社區的具體做法有:在院落支部的配合下,通過“民俗手工”活動和“喜迎新春”活動加強溝通,以改造架空層為老服務獲得居民普遍支持。以立體可視化形式呈現小區特色,通過墻繪等手段將小區精神可視化,使社區更加具有凝聚力,用文化引導居民參與公共事務,幫助居民提升綜合素養,增強居民對社區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2019年11月初,F社區已孵化了9支新的自組織隊伍,通過開展自組織備案培訓會、一對一輔導會、項目培訓會,自組織成員實操能力培訓會、項目評審會,和每月一次聯系溝通解決成員遇到的困難。組織居民骨干到自組織隊伍建設較好的社區參觀學習,通過開展院落特色文娛會演用表演的形式吸引院落內的居民參與其中。
以線上線下發布募捐倡議書、進小區進行擺點宣傳等形式,擴大社區基金的知曉度和影響力。以“公益集市”“微心愿”“社區兒童公益課堂”等形式,實現社區基金的項目化籌款,充分激發轄區活力,形成符合社區特色的基金資助模式,提升社區公益項目自我造血能力。居民在了解了慈善微基金的理念和活動設計后表達了自己的認同,并愿意帶動身邊更多的人參與進來。社區基金的籌款涉及日常捐贈、項目化捐贈、有償參與活動、活動冠名等方式,有效帶動了多方參與。F社區挖掘部分能促進社區基金發展的杠桿角色,通過這部分人群促進基金的普及。從現代社會的社交方式、活動范圍等方面入手,F社區建立了線上線下多渠道的宣傳途徑,根據實際情況選擇更精準有力的宣傳方式。
2019年8—10月,F社區通過沙龍、講座、入戶、設置法治宣傳欄、“模擬法庭”、“同普法治文明曲 共唱治理和諧歌”法治文化會演活動等形式,開展法律知識宣講。F社區用案例和法律相結合的方式,啟發居民解決糾紛的途徑和方式,讓居民了解身邊糾紛所涉及的法律知識并進行專題講解,幫助居民更好地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提高居民參與社區法治治理的能力。
2020年1月,F社區開展“法律護航 關愛弱勢群體”活動,向弱勢群體送去過年物資的同時進行法律宣傳,居民志愿者現身說法,通俗易懂,降低弱勢群體的戒心,幫助其建立法治意識。2020年5月和6月,F社區開展疫情期間防騙講座、小區法治宣傳、法律知識競答等活動,以增強居民法治意識,營造法治的環境和氛圍。部分居民因此從最初的被動接受法律知識到最后成為法律知識的傳播者,成為小區法治建設的新力量。
目前,F社區院落支部、已建的自組織隊伍、志愿者隊伍在帶動居民參與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覆蓋面仍有限。比如,在法律宣傳方面,若能組建居民自己的法律宣傳隊伍,用居民力量去傳播法律,用群眾思維去提高群眾的法律意識將會有更好的效果。
六、“數字+需求”驅動居民參與融合協同共治機制構建建議
圖1 ?“數字+需求”驅動居民參與融合協同共治機制結構
(一)以黨建引領為基礎,充分發揮社區黨委領導核心作用
黨建引領是我國的制度優勢,通過黨建引領,政府、社會各司其職,通過政府的制度性引導和支持,構建內生性和主動性社區參與氛圍和場域,實現政府治理與居民自治的有效銜接。[6]充分發揮社區黨委的領導核心作用,落實黨委人事安排權、重要事項決定權、領導保障權和監督管理權。重點提升組織力,發揮社區黨組織的組織優勢。在社區黨委(黨總支)的組織架構中,將業主委員會、物業公司等社區組織納入社區黨組織統一管理。開展黨小組長、樓棟長“亮身份活動”,做到樓棟建黨、片區建黨,實現黨員負責家庭、黨小組長負責樓棟、黨支部書記負責小區、黨委書記負責社區的黨建工作。將黨的組織工作嵌入社區建設,強化黨組織在基層的領導核心作用,有效激發社區活力。
(二)構建社區工作者隊伍職業體系,提高社區管理與服務水平,增強社區居民居住滿意度
加強教育和培訓,對于初任人員,加強政治素質、職業道德、履職能力、工作作風等方面的教育培訓;建立社區書記輪訓制,其他工作人員定期培訓制。將等級晉升與年度考核結果掛鉤,黨員群眾參與評議社區工作者的工作態度、工作作風、為民服務的情況;建立社區工作人員薪酬體系,形成正常增長機制,除了包括基本薪酬、績效薪酬、獎勵薪酬外,還可以根據個人實際情況,享受一定的職業津貼、學歷津貼等,按勞分配,獎懲分明。進一步提高社區工作人員的能力和素質,提升其服務群眾的水平。
人財物全面下沉,及時了解民意,按需提供支持。兩代表一委員、處級干部、正科級干部等定期下社區走訪,形成一個團隊,每次兩三個人定期走訪。通過多接觸,了解民情民意,及時化解基層矛盾。打造專業化的社區專職工作者隊伍,出臺專職社區工作站管理辦法及薪酬待遇、績效考核等指導意見等,精準提供人力物力財力。
(三)組建專業化的群團組織和社會組織,充分發揮自治組織、社會組織的作用
組建企事業單位、物業、樓長棟長、出租屋業主、居民代表、退休黨員的各類群體聯盟,群策群力;建設院落志愿者隊伍,充分發揮社區黨員志愿者、商戶、學生、熱心居民等青年義工的能動性;培養引導關愛幫扶類的社會組織,通過協會把居民組織起來,如慈善幫扶協會、居民創業幫扶協會、自我管理的出租屋業主協會等。
(四)啟動數字化社區建設,理清治理思路
從信息時代智能互聯大背景出發,充分利用大數據、互聯網、云計算等智能互聯技術,搭建“數據+應用”的集成管理平臺,摸清“家底”,建立社區自建治理數據庫。應積極爭取上級政府的數據共享,結合自身利用人口普查、逐戶巡訪、疫情風控等形成的優勢,熟悉掌握空間地理信息、居民人口信息、法人信息等基礎治理信息,促成規劃構建社區網格,精準細分居民類型,分清調動居民參與積極性的重點類型和難點類型,分類分階段遞推,深入挖掘居民需求,逐項突破,提升居民參與積極性。
(五)利用多元化渠道培育社區居民的公眾參與意識
發動律師、街道干部進行定期宣講,搭建微在線學習平臺,在社區宣傳欄張貼海報,在人流量大的路邊等顯眼處懸掛標語橫幅,利用多元化渠道在專門學習和潛移默化中培育居民法律意識與參與意識。
(六)提升居委會服務水平,充分發揮居委會的紐帶作用
減少居委會的政府性行為規范,加強居委會工作,設立居委會專職文員,提升居委會自治能力;完善居委會內部治理結構,按需設立若干專業委員會,鼓勵群眾威望高、工作能力強、熱心公益事業的居民積極參與社區事務,培養社區事務帶頭人;實行居委會工作述職報告制度,居委會主任每年向轄區居民述職,強化群眾對居委會監督;完善轄區自治組織,推動小區業主委員會的建立,充分發揮物管、樓棟長聯合會等社會組織的作用。
(七)設立社區居民議事組織,了解居民訴求
設立社區居民議事組織,以居民議事會、小區業主懇談會、小區居民決策聽證會等形式,引導社區居民在協商中凝聚共識,拓寬社區居民參與社區自治活動的同時履行社區居務監督委員會的職能。對社區建設規劃、環境、衛生、文化、體育、治安、安全等社區公共事務,各類組織的管理、服務及作風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提出意見建議,商議解決居民關于加強社區公共服務事務的意見建議。對駐社區單位、物業公司、社區社會組織、社區商戶等社區各類組織參與社區建設事務進行商議,收集反映社情民意和居民的訴求。處理不與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相違背的、不涉及黨和國家秘密的、具備可行性和操作性的事項。有提議需求的社區居民和社區居民議事組織成員可以向社區工作人員領取社區居民議事提議表,直接現場提交給社區黨組織、社區居委會,也可通過投遞社區居民議事意見收集箱、撥打辦公電話、發送電子郵件等方式。通過設立多渠道議事途徑為居民和社區居民議事組織成員提供方便。
七、結論
以社區黨建引領為核心基礎,以職業化社區工作隊伍、專業化的群團組織和社會組織為兩翼,建立治理基礎數據庫開展數字化治理,了解和滿足居民訴求。利用“數字+需求”驅動分類型分階段遞推,以問題和訴求為導向,逐項突破,激發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能動性,進一步提升自治力。將頂層設計和基層探索相結合,通過搭建外源的專業性組織和內源的自建組織構架,形成多方參與融合協同共治機制,構建基層治理的新發展格局。
參考文獻:
[1] 馮敏良,“社區參與”的內生邏輯與現實路徑——基于參與—回報理論的分析[J].社會科學輯刊,2014(01):57-62.
[2] 張莉.我國有限社區參與框架探析[J].社會科學戰線,2015(07):264-267.
[3] 向德平,高飛.社區參與的困境與出路——以社區參與理事會的制度化嘗試為例[J].北京社會科學,2013(06):63-71.
[4] 何雪松,侯秋宇.城市社區的居民參與:一個本土的階梯模型[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51(05):33-42,236.
[5] 王詩宗,羅鳳鵬.基層政策動員:推動社區居民參與的可能路徑[J].南京社會科學,2020(04):63-71.
[6] 談小燕.以社區為本的參與式治理:制度主義視角下的城市基層治理創新[J].新視野,2020(03):8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