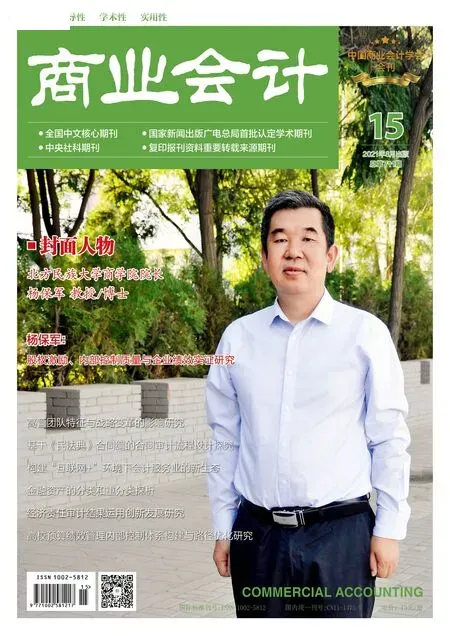政府創新補貼、研發投入與企業創新績效
——基于河南省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
劉亞平(鄭州商學院 河南鞏義 451200)
一、引言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正處于復雜的變化過程中,創新能力尚未滿足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并強調,到2035年要在經濟、科技及綜合國力上有重大提升,經濟的總產量以及來自城鎮和鄉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得到改善,核心技術水平逐漸得到提升,在創新型國家中占據重要的地位。為了增強競爭實力,抵御外部帶來的挑戰,提高創新水平,激發企業的創新積極性,并增加企業的創新績效將變得更加重要。
研發活動有助于增強企業創新實力、提高核心競爭力,能夠促進地區經濟的發展。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企業更加注重研究開發活動,但是由于研發行為成本高、風險大、見效慢,所以很多企業對于研發活動存有顧慮。政府為了促進企業積極進行研發,會通過各種形式,如通過經費補助的直接方式及稅收優惠等間接方式減輕企業資金投入的負擔,以降低企業研發投入最終失敗的風險。根據資金來源的不同,企業研發投入可分為企業自身資金的投入以及來自政府資金的投入,這兩種方式的投入會對企業創新績效產生不同的影響,而且差異較大。此外,高管團隊是企業運營管理的核心,經濟管理相關專業的高管通常更加關注企業的經濟利益與投資回報率。基于上述內容,本文將探討政府創新補貼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以及企業研發投入在二者之間起到的中介作用,并在此基礎上分析高管專業背景的調節效應。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政府創新補貼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有關政府補助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眾多學者對其展開了研究,但是研究結論并未達成一致意見。王一卉(2013)以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為對象,從企業的所有制制度、企業經營時間長短及企業經營所在地的位置三方面,對政府補助與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研究發現,在國有企業中,政府補貼對企業創新績效沒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對于經營時間較短的企業而言,政府補助與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更明顯。Catozzella等(2016)基于意大利的數據樣本,采用雙變量內生轉變模型進行實證檢驗發現,政府補貼對企業的創造力具有消極影響。桂黃寶、李航(2019)基于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上市公司的數據資料,通過建立模型并進行實證檢驗發現,政府補貼與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的創新績效具有負相關關系。有的學者認為政府補貼對企業創新績效具有正面影響。蔣安璇、鄭軍、裴瀟(2019)通過對相關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發現,政府補貼能夠增加企業對研發活動的投入,并且有助于提高企業專利申請的數量,而且媒體的關注有助于增強政府補貼對企業創新投入的激勵效用,進一步提高創新產出。顏曉暢(2019)采用固定效應面板模型對規模較大的制造業企業進行研究發現,來自政府的補貼與企業通過創新產生的效益呈正相關關系,而且創新能力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屈文彬、夏文麗(2020)研究發現,政府補助與企業績效的關系會受到產權性質的影響,在非國企樣本中政府補助對企業績效具有正向促進作用。還有學者認為政府補貼與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不明確。李爽(2016)通過對我國新能源上市企業的研究發現,新能源企業中,創新活動并未受到政府補助的影響。朱衛東、田雨緋、胡雪(2020)以滬深創業板和中小板的制造業上市公司為樣本,分析政府創新資助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創新性的政府補貼與企業績效之間不具有線性關系。本文認為政府創新補助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具有密切的關系,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政府創新補貼有助于企業創新績效的提高。
(二)企業研發投入的中介效應。很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政府補貼、研發投入及企業創新績效三者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大多數學者認為政府給予企業的補助,能夠促進企業增加研究開發投入,可以減少企業研發投入中自身資金的注入;也有學者認為,政府補貼并未促進企業研發投入的增加。丘東、王維才、謝宗曉(2016)從政府補貼對企業創新績效的作用機理角度對研發投入的中介效應進行分析,研究表明企業研發投入具有中介作用。王一卉(2013)通過分析發現,經濟發展較差的地區,政府補貼與研發投入正向關系不顯著,也不能改變企業的績效。賈春香、王婉瑩(2019)以高新技術企業為研究對象,深入分析了不同形式的政府補貼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研究發現政府補貼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具有顯著的關系;研發投入在政府補貼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能夠發揮部分中介效應。丁倫楨、韓書成(2019)將政府補貼進一步細分為與研究開發直接相關以及與研究開發無關的補貼,并進行分類檢驗,研究發現,相比于非研發補貼,研發補貼的中介作用更明顯。梅冰菁、羅劍朝(2020)采用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科技型企業的相關數據庫資料,通過實證檢驗發現,研發投入在政府補貼與創新績效之間能夠起到中介效應。本文從政府補貼明細項目中篩選出與創新相關的項目,認為政府補貼中創新性的補貼能夠增加企業對于研究開發的投入,并有助于增加企業通過創新產生的效益。因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研發投入對政府創新補貼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具有正向調節作用。
(三)高管團隊專業背景的調節作用。部分學者對高管團隊與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展開了研究。Bushee(1998)采用實證的方法,以市場價值超過50億美元的企業為對象展開研究,研究發現企業的創造性受到高級管理人員所學專業的影響。Smith&Tushman(2005)認為,企業在做出戰略決策時,高級管理人員受教育的背景不同,其收集的信息也存在差異,進而決策效果也不同。因此高級管理人員的專業與企業價值之間具有一定的關系,專業性越強,企業市場價值越高。張長江、陳雨晴、溫作民(2020)認為,異質性越高的高管團隊更容易從多種角度、多種渠道獲取準確且多樣化的信息,并通過已有專業知識對信息進行加工整理,從而有助于高管團隊做出有效、實用的戰略決策。高層梯隊理論認為,高管的認知、學習能力及閱歷會對企業經營決策起到一定的作用。周茂春、劉仁越(2020)基于高層梯隊理論以及特質激活理論對我國高新制造業公司進行相關研究,發現高管成員的專業背景與企業創新性之間具有明顯的正向關系,認為高管團隊成員的本科、研究生以及博士專業與企業主營業務契合度越高,企業創新能力越強。綜上,本文認為,高管團隊教育背景的專業性越強,企業創新水平越高,企業價值也越大,同時經管專業背景的高管成員,更加注重投資回報水平,對創新績效的影響更明顯。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3:與其他專業的高管團隊相比,經濟管理相關專業的高管人員比例越高,企業利用政府創新補貼的能力越強,高管專業背景對政府創新補貼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調節作用越明顯。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本文選取的樣本為2015—2019年河南省88家上市公司,分析所用的大部分數據來源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其他數據通過企業財務報告、公司官網、巨潮資訊及同花順等渠道獲得,基于基礎數據,去掉部分異常的數據,同時對變量進行1%的Winsorize處理,最后得到170個樣本數據。
(二)變量定義。
1.因變量。為防止專利數據之間不均衡,對專利數據采取對數的形式,又由于部分企業并非每年都存在專利授權,所以將專利授權數加1,然后再進行標準化,作為創新績效的代理變量。專利授權數采用集團公司中單體公司當年發明、實用新型以及外觀設計的專利授權數量的合計數。
2.自變量。政府創新補貼指企業當年從政府獲取的與創新相關的補貼占當年營業收入的比重,其中政府補貼中與創新項目相關的補貼是從企業年報附注“政府補助”的明細項目中提取出來,并進行收集與整理獲得,包括研究項目政府扶持資金、科技創新項目獎勵、科研撥款、國內外申請專利補助、發明專利獎、重大創新科技經費、技術開發補助、名牌產品獎勵費、技改補貼、科技成果轉化獎勵、新產品財政扶持資金、科技進步獎勵、創新計劃補貼、專項經費補貼、重大科技專項資金、企業知識產權補助資金、發明專利扶持資金、著作權資助、院士及博士后科研資助以及引智專項等項目,將每年的明細項目進行加總,匯總出每年政府創新補助總量,作為當年的政府創新補助。若沒有明細,則通過查詢發文單位或批準機關的文件中關于補助的“說明”“種類”等信息獲得。
3.中介變量。本文采用相關學者的做法,選擇該企業當年的研發投入與當年的營業收入之間的比值作為企業研發投入(R&D)的代理變量。
4.調節變量。以高管團隊中具備經濟管理相關專業的高管人員占高管總人數的比例來反映高管團隊的專業背景。
具體變量定義如下頁表1所示。

表1 變量定義表
(三)模型構建。為了檢驗政府創新補貼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建立如下模型:


為了檢驗企業研發投入在政府創新補貼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中介效應,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研發投入變量,建立如下模型:

為了檢驗高管專業背景對政府創新補貼與企業績效之間的調節作用,在模型(3)的基礎上引入高管專業背景、高管專業背景與政府創新補貼的交互項,建立如下模型: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從表2描述性統計分析可以發現,研發投入以及專利授權數量的極大值與極小值之間差異較為突出,說明企業之間的創新投入以及創新產出具有較大的差異;政府補貼在不同企業中差異不是特別明顯;經濟管理專業的高管人員占比在各個企業中分布較為均勻;控制變量中,企業年齡、第一大股東的持股份額以及固定資產比率的分布也不均勻,說明不同企業經營情況存在差異。

表2 描述性統計分析
(二)相關性分析。為了確保實證檢驗的準確度,采用Pearson方法對本文選取的變量進行相關性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本文選取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低于0.5,表明各個變量之間沒有顯著的線性相關關系。

表3 變量Pearson相關系數表
(三)回歸分析。從表4模型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模型1將企業創新績效(Patent)作為被解釋變量,將政府創新補貼(SUB)作為解釋變量,然后對模型進行回歸,用于解釋假設1,通過分析發現,政府創新補貼的系數為150.3,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企業當年獲得的來自政府的創新性補貼越多,獲得的專利授權數量越多,驗證了假設1。模型(2)和模型(3)用于分析研發投入是否具有中介作用,實證檢驗證明,以研發支出(R&D)作為被解釋變量,政府創新補貼(SUB)作為解釋變量的政府創新補貼的系數為149.2,在10%的水平上顯著;然后以企業創新績效為被解釋變量,在模型(1)的基礎上,引入研發支出中介變量,通過回歸分析發現,政府創新補貼和研發支出的回歸系數分別為135.8和0.0972,分別在5%和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研發支出能夠起到部分中介效應,驗證了假設2。模型(4)是對假設3的檢驗,通過分析發現,高管專業背景的調節效應并不顯著,說明高管的專業背景對政府補貼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沒有起到明顯的作用。

表4 模型回歸結果
(四)穩健性檢驗。由于企業通常通過對生產要素和經濟資源的不斷儲備逐漸實現盈利目標,而通過創新活動給企業帶來收益的風險往往比較高,究其原因,是因為從創新投入到成果轉化并被市場接納,實現創新效益,需要很長的時間。為防止檢驗結果出現偏差,將模型中政府創新補貼變量滯后一期,進一步進行回歸,通過分析發現,回歸結果并未發生較大變化,說明回歸結果依然較為穩健。
五、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本文以2015—2019年河南省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實證分析政府創新補貼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存在的關聯關系;為了研究二者之間關系的內在機理,進一步探討了企業的研發支出在政府創新補貼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中介作用;此外,結合高管專業背景,深入分析高級管理人員的專業背景對政府創新補貼與企業創新績效關系的影響。研究發現,政府創新補貼能夠促進企業創新績效的提升,而且作用顯著;政府創新補貼有助于企業增加研發投入,研發投入又進一步促進企業創新績效的提高,研發支出具有一定的中介效應;高管中具有經濟管理專業的人員所占比重對政府創新補貼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不具有顯著影響。
(二)研究啟示。第一,政府部門可以建立創新補貼機制,加大對企業的創新補貼力度,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最終實現我國創新能力的大幅提升。第二,政府應加強對補貼資金的監督,既要保證創新補貼的數量,還要提高補貼的質量,確保企業將政府補貼用于研發,有效促進企業創新績效的提升。第三,明確政府補貼的分類及使用范圍,加強政府補貼事后評價,提高政府補貼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