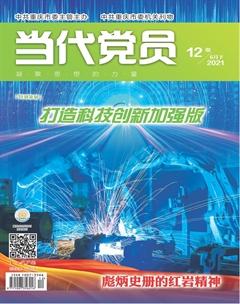深山苗寨,回應最美的期待
陳誠
重慶市目前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家族式苗寨羅家坨苗寨隱藏在渝東南的武陵山深處——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鞍子鎮羅家坨村。
苗寨外是綿延不絕的武陵山,山隔水繞,村民的生活閉塞孤獨。自500多年前羅家坨羅姓始祖羅道蒙由江西入川建寨以來,羅家坨苗寨一直是一個疏離于時代的寨子。早年間,它的疏離是典型性的,典型的農耕生活讓寨子的村民可以自給自足;近年來,它的疏離則具有邊緣化色彩,路況不佳,信息不暢。
改革開放40多年來,苗寨外的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苗寨內的人們還是保持著老習俗:守著一畝三分地,看天耕作,靠地吃飯。寨子里的一些老人,他們去過最遠的地方,是通過山間彎彎繞繞的泥巴路,到達6公里外的鞍子鎮。
困境
羅海是土生土長的羅家坨苗寨人。1995年,羅海和寨子外的女子謝瓊結了婚。
于謝瓊而言,印象最深的是,寨子里的人種地不錯,都是一把好手。
由于沒讀過多少書,羅海兩口子依舊靠種地過日子,每天起早貪黑,侍弄土地。
隨著時代的發展,路修到了羅家坨苗寨。寨子里有些想法的年輕人,都選擇外出務工,北上或者南下,在市場經濟的海洋里,年輕人追風逐浪。年輕人出走后,留下的是上了年紀的老人和上了年歲的苗寨。
1998年,羅海和謝瓊一合計,也準備外出務工,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實在沒有什么奔頭。
沿著僅有半米多寬的泥濘小路,走路1個多小時到鞍子鎮,再坐車坐船,顛簸的客車和搖搖晃晃的客船將羅海和謝瓊帶到了重慶主城區。
由于學歷不高,羅海只能跟著建筑隊做小工,扛鋼筋、挑混凝土,山里人干活不怕苦,羅海很快便有了一筆小積蓄。
然而好景不長,這樣的日子并沒有持續多久。
“家里來電話,說公公患病,需要到醫院檢查。”謝瓊說。
回到羅家坨,謝瓊帶著公公去醫院檢查。這一查,公公罹患膀胱癌,需要化療和長期用藥。
原本兩口子在外務工,孩子便由老人照顧,突如其來的變故迫使兩口子回到苗寨,再度扛起了鋤頭。
“公公患病,除開化療費用,每天還要吃藥,孩子要上學,生活費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謝瓊說。
僅靠務農,支撐不起這么大的開支,羅海一家很快陷入困境之中。擺脫貧困,成了羅海心底的期待。
重生
2007年,彭水在全縣開展文化旅游資源普查,在這次普查中,羅家坨苗寨被發現了。
此次調研中,有一個人的身份很特殊,他叫任廷國,時任鞍子鎮紀委書記,是羅家坨村人。
當時的羅家坨苗寨十分閉塞,村民還保持著最傳統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灌溉農田仍要肩挑背扛地運水。
事實上,正是因為閉塞,羅家坨苗寨才能在過去幾百年始終保持著原汁原味的苗族文化痕跡。寨子外的村民都熱衷于修建新式磚瓦房,甚至放棄了苗族傳統雕窗花的技藝,取而代之的是清一色的玻璃窗、防盜網。
“外面的新房子,已經變了味兒。”在寨子里住了一輩子的老人講。
羅家坨苗寨被發現后,任廷國便開始琢磨怎么保護和開發好這里。
任廷國期待著,通過對苗寨的保護和開發,把羅家坨苗寨發展起來,把苗族文化發揚出去。
“苗寨是苗族文化的載體,如果苗寨沒有了,就意味著民族符號缺失了,民族文化也將失傳。”任廷國說。
怎么來保護羅家坨苗寨?
在任廷國和彭水縣有關部門的推動下,2009年,羅家坨苗寨被國家民委、財政部納入全國少數民族特色村寨保護與發展試點項目。
此后,鞍子鎮政府對苗寨建筑以及寨內的道路、院壩等基礎設施進行了修葺和全面改善,彎彎繞繞的泥巴路變成了水泥硬化路。村民家里也進行改廁、改廚,自來水通到了每一戶。
“對于苗寨的修葺,我們采取‘修舊如舊的方式,遵循‘外貌民族化、內部現代化原則,更加突出苗寨建筑的自身特點。”任廷國說。
2016年,在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定點幫扶和彭水縣委、縣政府的支持下,羅家坨苗寨又分三期進行了提檔升級。
如今,羅家坨苗寨已榮獲“全國少數民族特色村寨”、“重慶市第一批歷史文化名村”、“重慶市第一批傳統村落”、“國家AAA級旅游景區”等稱號。
發展
2011年,羅海家迎來一位“貴客”——任廷國。
“最近生活怎么樣?”見到羅海,任廷國開口詢問。
“還是那樣,身體沒以前好了,娃娃還要上學,經濟壓力大。”羅海說著,語氣有些落寞。
“有沒有興趣開一個農家樂?”
“能搞農家樂肯定好,但是我們這個山上,誰愿意來呢?而且我也沒有本金。”羅海將顧慮告訴了任廷國。
“我們這些年一直在搞苗寨的保護與修復,就是為了發展旅游經濟有載體,現在搞農家樂,正當其時。”任廷國說。
羅海家是一座三合院,穿斗式三層木結構,單檐懸山式屋頂,小青瓦屋面。建筑整體保存完好,窗欞、柱礎等構件造型古樸,直觀地反映了羅家坨苗寨傳統民居的特點,而這也是任廷國看好羅海家發展農家樂的原因。
“房屋改造和內部裝修鎮上有資金補貼,整體而言出不了多少錢。”任廷國繼續說。
聽到任廷國的講述,羅海動了心。在鞍子鎮政府的幫助下,羅海將自家房屋改造為農家樂。
而這,也成為改變羅海一家生活的開端。
隨著羅家坨苗寨的修葺,慕名而來的游客漸漸增多,羅海家也越來越忙碌。
生活環境的改善和旅游的開發,并沒有破壞羅家坨苗寨的原有風俗習慣,羅海家至今仍延續著“鼎罐燒飯”、“腌制臘肉”的苗族習俗,保留著火鋪、石磨、草凳等生活用具。客人多的時候,謝瓊還會拉上好友,一起在院子里跳“踩花山”、唱苗歌。
此外,謝瓊還燒得一手好菜,她從小就會做家鄉菜,臘肉、豆花、糍粑、鼎罐飯、風蘿卜最是拿手。謝瓊的手藝得到了游客的廣泛認可。
“以前,做菜是為了生活,唱歌是娛樂。現在,這些都是掙錢的手藝,是文化的傳承。”謝瓊說。
苗歌
在鞍子鎮的苗歌師傅們眼里,即興唱一首鞍子苗歌,并不是什么難事,莫說是專業的鞍子苗歌表演者,就是在苗寨隨意拉一位上了年紀的老人,也能做到張口即來。
鞍子苗歌中最出名的,便是《嬌阿依》,它是苗族人情歌的專用曲調,大抵便是宋詞中的“詞牌名”。
苗歌的內容,來自苗族人生活中的點點滴滴。生活中的任何場景,從田間地頭到灶頭炕頭,都能成為苗歌的內容。
寨子里76歲的羅興建,唱了一輩子苗歌。如今,他和寨子里另一位老人任正高成為苗歌市級非物質文化傳承人。羅興建也越來越感覺到,有責任和義務將苗歌傳承下去。
鞍子鎮政府也在大力推動苗歌傳承,還在學校開設了苗歌課堂,請去代課的老師,便是羅興建。過去的幾年中,羅興建給彭水縣文化局錄了很多調子,從排子歌、調子歌到嬌阿依,都有。
羅興建期待能將這些苗歌傳承下去,“老祖宗的東西,不能丟”。
羅興建的苗歌記憶,始于小時候的勞作。羅家坨苗寨成“斗”型,站在“斗”兩邊的山坡上,勞作的人們便會開始對歌,羅興建的大伯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每逢對歌,鮮有敗場。
本想讓老人講講學習苗歌的故事,羅興建卻張口唱了起來,當我們驚訝于苗歌奇妙的調子和老人中氣十足的歌聲時,他卻擺了擺手:“這有什么,我們之前還參加過阿依河歌唱表演,唱好幾個小時都不歇氣。”
那是一支由羅家坨苗寨歌者組成的隊伍,羅興建、任正高兩位老人帶著謝瓊、謝清秀、李少娥等人,在阿依河上一唱成名。
歸來途中,羅興建與任正高一路對歌,從彭水縣城一直到鞍子場鎮,紛繁多樣的調子,感染了同行的所有人。
在羅家坨苗寨發展愈發迅速的今天,羅興建最主要的工作便是將唱了一輩子的苗歌傳承下去,偶爾他也會帶著自己教出來的徒弟,在寨子門口唱歌迎賓。對于羅家坨苗寨的發展變化,羅興建的表述則很質樸:“現在走路都不會打濕腳了。”
羅興建能夠描述的快樂,是仍有年輕人愿意學苗歌,是唱歌時胸中散發的那股氣,那是情感的寄托。
回程途中,我所乘坐的車中正在播放流行歌曲《最美的期待》,古老與現代,傳統與未來,突然就在歌聲中碰撞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