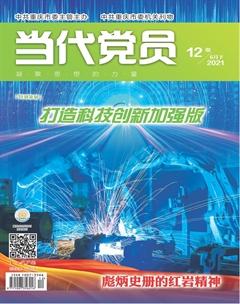自然性、藝術性與人民性的審美統一
李軍


兩次登臨滕王閣,卻難覓落霞孤鶩、秋水長天的意境。我想,如果那個時候的詩人王勃有相機呢?
或許是兩種結果。一則,給我們留下了1300年前的滕王閣的影像記錄;二則,也許我們再也看不到《滕王閣序》這樣的千古名篇了。一波又一波的技術浪潮,將人類從文字識別拉升到影像識別,抽象的美學逐步被具象的認知替代。科學復原著人類對自然事物的認知,卻也解構著人類的想象力。以《天凈沙·秋思》(元·馬致遠)為例。“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枯藤老樹昏鴉,容易拍得到;小橋流水人家,也容易拍得到;古道西風瘦馬,也很容易拍得到;夕陽西下,更容易拍得到;但是,斷腸人在天涯,就顯得沒有那么容易了。恐怕我們再也回不到“飛流直下三千尺”的想象時代了。俱往矣,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須。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可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如若攝影作品能從技術主義現實到人文理想的表達,擴展到大地與精神的共鳴、現實與理想的映照,那么好的作品可能就會出現了。
相機連接物與我,便進入“五系統”
表達系統。表達系統或可稱為視覺系統、鏡像系統。藝術表達是人類的本能。早在20世紀,學者朱光潛、錢鐘書等就對盛極一時的藝術工具論——語言學轉向,展開奮力批駁。他們認為藝術語言和審美意象不可區分,審美意象和審美體驗也密不可分,否則,會摧毀人類詩意。然而,隨著影像技術的不斷發展,人們的藝術語言獲得新的工具并不斷升級,成為當前人類最普遍、最直接的藝術表達。
農耕文明時代,人們將植物和礦物質研磨成顏料,開始描繪五彩世界。工業時代,法國的達蓋爾發明了攝影技術。人們驚訝了,自然世界還可以這樣描繪。1895年,法國人盧米埃爾兄弟第一次用自己發明的放映機放映了《火車到站》影片,人們震驚了,用這樣的東西還能講故事。在影像互聯網時代,影像不僅是藝術的工具,還是社交的工具,以即拍即發的“圖”的形式連接人們的情感。
審美系統。攝影是審美活動。春熙日沐、秋肅風悲,壁立千仞、花香萬里,堅冰銳日、皓月長空,都是人類無處不在的審美體驗。感謝攝影,使人們有如此直接而簡單的途徑和載體去體驗美、表達意、傳達情。
我認為攝影有“五要素、五維度”,即器材是條件,技術是保證,審美是基礎,文化是內涵,機會是關鍵。器材是外部因素,技術是內部因素,審美是基礎因素,文化是根本因素,機會是決定因素。比如拍鳥,什么都具備了,按下快門的一剎那,鳥飛走了。機會決定成敗,這就是布列松的“決定性瞬間”。在諸多因素中,唯獨“審美”具有天賦。久而久之,影像從技術實現到學科實現,再到體系建構,推動影像審美的系統化。
文化系統。人類口頭語言大概形成于3萬年前,文字形成于公元前5000年左右,攝影作為影像語言的存在不足200年。人類從口傳文化、讀寫文化、圖像電子文化再到網絡文化,是文明發育的過程,更是文化塑造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攝影作為影像文化最重要的載體,其最大的貢獻是為人類提供了與工業文明對接的文化符號,開啟了人類讀圖時代。實驗心理學家赤瑞特拉(Treicher)的實驗證明:人類獲取的信息83%來自視覺。實驗還證明,人類對圖像所傳達的豐富信息接受最為充分,保持記憶的時間最為長久。讀圖時代不僅極大地提高了獲取知識的效率,也表達和交流著人們的情感。于風景攝影而言,一幅圖景,一定是先打動你,你才會拍它。久而久之,感動就變成認知,認知就成了文化。
社會系統。當讀圖時代向讀屏時代遷移和躍升,攝影活動的社會屬性便成為普遍屬性。早在東晉時期,文人沒有相機,只有書法和繪畫。永和九年,受會稽(今紹興、蘇州一帶)內史王羲之的邀請,在蘭亭舉行“蘭亭修禊”。四面八方,天下文人墨客在此雅集,寫詩作畫。“修禊”過后,王羲之將此匯集成冊,作《蘭亭集序》一篇,為千古遺墨。歷史上的“修禊”和現代的筆會,都是社會化的產物,如今的攝影節展、各類活動也是社會化的產物。影像社會化是當前全民攝影現象最為重要的特征。
治理系統。不同時代的藝術發展史,折射出這個時代社會發展的特征。當今攝影的文化參與、社交參與,必然反映到經濟社會發展之中,經濟社會發展又為攝影提供了廣闊天地。
4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到清華大學考察時指出,美術、藝術、科學、技術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要發揮美術在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把更多美術元素、藝術元素應用到城鄉規劃建設中,增強城鄉審美韻味、文化品位,把美術成果更好服務于人民群眾的高品質生活需求。三個“相互”(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兩個關鍵詞“應用到”和“服務于”,鮮明地指出藝術與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相互關系,為藝術工作指明了方向。
藝術實踐是如何參與到社會治理中的呢?舉個例子,日暮西垂、晚霞夕照,當你站在北京景山的萬春亭往南看,我認為是全世界最美的黃金中軸線。中間望去,左手為東,右手為西。東邊,現在是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過去是太廟;西邊,現在是中山公園,過去是社稷壇。太陽東起西落,先有列祖列宗,后有江山社稷,反映著當時基于禮治的中華建筑理念,而現在,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一條中軸線,不同的時代,兩種歷史觀。藝術與社會“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再舉一個例子,攝影活動已經成為各地經濟轉型、拉動旅游的重要手段,廣泛的攝影活動已經日趨“應用到”并“服務于”社會轉型中,成為經濟社會發展動力變革中的重要文化因素。
理想國:柏拉圖的烏托邦與陶淵明的桃花源
理想國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提出來的一個政治文化概念。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理想國。柏拉圖的理想國是烏托邦,陶淵明的理想國是桃花源。在西方,學者就是學者,畫師就是畫師。在中國,文人即畫者,畫者即文人。潘天壽曾說過:筆墨取于物,發于心;為物之象,心之跡。今天,我們來到內蒙古畢拉河,共同討論自然生態攝影,意義何在呢?
從趨勢看到未來。審視當今攝影界,一方面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加速分化。表現在其社會系統,去專業化、去機構化、去分工化潮流涌動。人們不再受專業限制,人人都是攝影家,甚至人人都是自媒體。于是,影像社區誕生了。攝影,特別是風景攝影,已經成為人們重要的社交參與。表現在文化系統,攝影日益被市場滲透,被流量駕馭,攝影達人、網紅與攝影家們共同成為攝影潮流新的制造者。表現在治理系統,攝影活動作為經濟轉型的重要文化參與,以“打卡地”的文化形式,給攝影熱持續加溫,也為拉動旅游提供新動能。表現在美學系統,由于影像產品巨量增長,產品過剩,影像語言泛化并且單一,因此,影像加速碎片化、泡沫化,“糖水片”盛行。在這種情況下,攝影個性已經很難形成,攝影主題已經很難尋覓,創作空間被嚴重壓縮,攝影大片已經很難產生。
風格化特征向追求極美和加速兩個極端發展,在風景攝影領域表現為兩大時代的同時來臨。
大片時代。藝術創作、技術和器材最大化結合,極致表達自然生態的豐富性。比如,極地攝影、野生動物攝影、極端氣象攝影等。
魔片時代。影像創作想象力在技術賦能下的超級發揮,驚艷般的手法運用,個性化表達自然萬象的多樣性。我們去參觀羅紅藝術館,羅紅拍攝的作品“巴塔哥尼亞”已是平常攝影家難以企及的,1億像素下巨幅“黃山”讓人有群峰圍繞、穿云破霧之感。我不敢想象未來技術再前行一步會是什么樣子。技術高度逼真復原景象,未來的攝影想象力會不會被終結呢?難怪有一位攝影家跟我說:風光片別拍了,拍不出什么花樣了。技術已經過度參與內容創作了。技術與智能解構著藝術家的想象力,市場和流量也在分散著攝影家的靈感。
技術和藝術不能偏廢。《周易》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材和技術的發展,給我們無限的可能,打開并實現人類的想象力。但是,也要防止為“器”所誤,因“器”廢“道”。警惕技術主義陷阱,防止人工智能把人類的思想吃掉。
藝術與市場難以割裂。過去的人,帶著畫筆走天下,后來,帶著相機走天下,現在,帶著手機走天下。于是,巨量攝影市場形成。這是好事,沒有巨量市場,怎么可能有“人民攝影”?但是,要警惕消費主義,警惕出現“有巨量,缺巨匠”,防止見“影”不見“人”,見“景”不見“民”。什么叫見“影”不見“人”,見“景”不見“民”呢?我們拍畢拉河,除了拍這里的自然風光,還應關注這里的風土人情。比如,如何挖掘和保護達斡爾人、鄂倫春人、鄂溫克人的文化遺存。公元386年,鮮卑人的領袖拓跋珪在這一帶建立了北魏政權。鮮卑族和漢族一步步走向文化融合,從而在隋唐時期形成新的漢族種群,這里有沒有留下文明的“印記”?
野生動物攝影家謝建國說,生態攝影,不同于風景攝影。生態攝影也有風景,但他更關注野生生物與環境的關系。即便是風景攝影,如果有野生動物融入畫面,那就活了,有了靈性。不僅如此,在這次拍攝中,我們觀察到林間濕地有灰鶴飛翔鳴叫。這個季節正是灰鶴的繁殖季,不排除有灰鶴在畢拉河繁殖。迄今為止,國內還沒有灰鶴野外產卵孵化的影像記錄,如果能拍攝到,那就填補了這方面的影像空白。還有,我們發現和傳播畢拉河之美的時候,一定要把鏡頭對準我們一代又一代畢拉河的林場人,他們才是這片優美山地的維護者、保護者,他們是這里最鮮活、最有生命力,也最有正能量的。
讓夢想照進現實。1989年,攝影家于云天憑借組照《九歌》,榮獲第一屆中國攝影金像獎。他的作品如同他的名字一樣,寫盡了日月星辰、碧海云天。他的不少照片拍攝于20世紀80年代,我國改革開放的初期。作品是對黃河文明無盡的贊美,抒發對這片土地的眷戀,表達的是對文明激蕩的曠古憂思,是對祖國山河壯美的大愛,反映了攝影家的藝術追求與祖國情、人民情的血肉聯系。他將自己的作品命名為《九歌》,《九歌·國殤》是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為追悼楚國陣亡士卒的一首挽詩。“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云,矢交墜兮士爭先……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九歌》引起一代人從視覺到心靈的強烈共鳴。他拍攝的作品是風光大片嗎?是,卻又好像不是。是人文大片嗎?似乎不是,又似乎是。當時還沒有自然生態攝影這個概念。自然生態攝影與風景攝影究竟有何區別?我找到了答案——理想國的映照。柏拉圖曾說,無論你從什么時候開始,重要的是開始后就不要停止;無論你從什么時候結束,重要的是結束后就不要悔恨。他用這句話定義理想國——心停靠的地方。
這一代的風光攝影師,是端著相機的徐霞客,是用鏡頭寫詩的屈原。改革開放,理想照進現實,他們視攝影為生命的組成部分,甚至是一種靈魂的存在。在天涯海角中開始自己的思想行走,在大自然中尋覓精神靈性,找到人生的價值和尊嚴。他們的作品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這對我們的啟發是,新時代攝影人,要技術的賦能,不要思想的弱者;要做流量的主人,絕不做市場的奴隸。
文化力,自然生態攝影之根性
自然生態攝影,脫胎于風景攝影,是一個新的攝影概念。其與風景攝影不同之處,在于“生態”二字。通過影像,反映景觀與自然環境和人文的審美關系。
自然生態、景觀文化和文旅經濟,三者是共生的關系。2021年4月,第六屆中國景區創新發展論壇暨中國旅游景區協會第二屆四次會員代表大會召開。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雒樹剛同志有一句話對我啟發很大:景區文旅融合,文化力決定競爭力。借用文化力這個詞,套用在自然生態攝影里,我覺得自然與人文相連,文化力決定生命力。
什么是文化力?1914年5月1日,黃炎培以申報記者的身份第一次到黃山,邀請攝影家呂頤壽隨行拍攝。這次黃山之行,黃炎培寫的《黃山游記》一文,發表在當年的《小說月報》上。攝影家呂頤壽為我們留下黃山最早的真實影像,商務印書館于1914年11月出版了畫冊《中國名勝第一種:黃山》,于是,黃山被廣大國人所認知。黃炎培和呂頤壽造不出黃山,但他們用文字和影像記錄并傳播了黃山。
今天,我們拍攝畢拉河,也要跟隨先人的足跡,以他們為榜樣,創新畢拉河的文化表達,學會復制并創新畢拉河的文化符號。用影像為這片森林“說話”。說什么樣的話呢?“十三五”以來,全國森林旅游產業規模快速壯大,森林旅游游客量達60億人次,平均年游客量達15億人次,森林旅游成為我國林草業重要的支柱產業和極具增長潛力的綠色產業。在產業融合的大背景下,通過攝影平臺助推共謀國家森林公園生態文明建設、生態環境保護,是生態文化旅游發展的重要助推器,在實地體驗互動傳播及消費升級、招商引資等多個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我們要由點及面,發揮影像對新時代綠色文明的文化塑造作用。
可喜的是,年輕一代的攝影人,以他們獨特的藝術行走,參與社會文化建設。我一直在關注環球行攝作家、極地攝影師、自媒體攝影達人羅曉韻。羅曉韻的成長有三個階段,兩部代表作劃分出她的兩次轉型。第一部代表作《冰島迷夢》,表現的是她從攝影達人到攝影潮流制造者的轉型。第二部代表作《格陵蘭消逝的夢》,表現的是她從“攝影大V”到沉靜的攝影思想者的轉型。在她過去的作品里,畫面里的她是風景照片里的視覺中心。現在的羅曉韻,有時也出現在畫面里,但與過去不同,她成了消逝的冰山、瀕臨滅絕的物種和一步步退化的文化族群的注視者。彼時畫面里的羅曉韻不僅是照片上的視點,更是一個對人類生態和文化變遷的關切者、思考者、呼吁者。羅曉韻攝影是此時此地自然生態殘酷變遷的“時間戳”,是此時此刻文明激蕩的“標引符”。于是,在她的作品里有了豐富的思想性。
我第一次采訪她時,是疫情剛過去不久。那時,她在完成第三次轉型,成為紀錄片的拍攝者和獨立制片人。她的第一部紀錄片《余聲》,反映了武漢人民怎樣戰勝疫情、如何在疫情中成長。后來又有了《曉星球,大中國》微紀錄片等。我注意到,她的每一次轉型,都帶來極高的流量。這一點,她可能察覺不出來。她的粉絲在一步一步“跟著走起”。從而,她也把粉絲帶向一個新視角去觀察世界,帶入一種新境界去對話人生,帶向一個新高度去參與建設。我在想,這恰恰是基于網絡和社交文化的影像力量之所在——改變著我,也影響著你。正如她跟我說的:后疫情時代,攝影人特別是風景攝影師,一定要走出自然閉鎖和心理寂寞,主動創設觀察、紀錄和思想主題。
1300年前,先輩沒有照相機,他們用恢弘的文字,給我們留下無比偉大的自然中國。今天我們有相機了,更有了大數據,我們有理由為1300年以后的世界,留下影像意義的自然中國,更有理由留下人文意義的自然中國,以生態攝影之名,向大自然致敬,向偉大的祖國致敬,向這片森林致敬,向這里的人民致敬。
(作者系中國期刊協會副會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傳媒監管局原局長,本文是作者在首屆“自然中國”林業生態攝影研討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