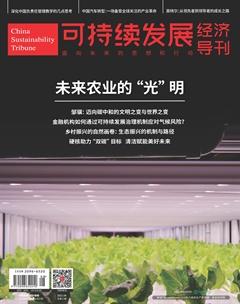創新數字技術,培育綠色低碳生活方式
蔣南青 楊建平
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十四五”時期,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進入了以降碳為重點戰略方向、推動減污降碳協同增效、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實現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由量變到質變的關鍵時期。加快推動生產生活方式綠色轉型,需要通過生活方式綠色革命,倒逼生產方式綠色轉型。本文以如何鼓勵并創造條件支持公民參與綠色低碳消費和生活為主題,嘗試為推動中國公眾參與可持續發展事業貢獻思路。
可持續消費:從消費端解決生態問題
過去十年間,中國的環境污染日漸突出,比如霧霾問題。2015年12月8日,北京首次拉響空氣污染紅色預警,10天后又拉響第二次紅色預警警報,由此引發中國全面打響“藍天保衛戰”的國家戰役,這場戰役最終在國家大力治理下取得勝利。現在,我們遇到的更大的全球性挑戰是氣候變化問題。這是一個長期的、威脅到人類命運的問題。2019年,全球溫室排氣體放達到500億噸,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占到1/3,人均碳排放量自2000年后一直在上升,已經接近每人每年10噸。
當人們更多地將關注放在環境影響問題上時,主宰經濟的生產方式并沒有改變,資源浪費問題也一直存在和發生。另外,除了生產方式的不可持續,從交通、建筑、產品、食品等的全生命周期來看,真正消耗能源和對環境產生影響大比例發生在消費端,例如汽車60%的能源都是消耗在使用階段。因此,自十九大以來,大力推動生產生活方式綠色轉型,已成為政府和公眾的共識。但是,公眾端的綠色低碳轉型依舊面臨知易行難的問題,因為公眾的生活消費水平不斷提升,而這種需求與環境、資源的束縛是有沖突的,沒有合理的政策和激勵機制很難徹底改變現狀。
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1994年的定義,可持續消費和生產(SCP)是指“對服務和相關產品的使用,可以滿足基本需求,帶來更好的生活質量,同時在服務或產品的整個生命周期內盡量減少對自然資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以及廢物和污染物的排放,不威脅到未來后代的需要”。可見,從本質上講,可持續消費就是要與資源消耗脫鉤,即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前提下,盡量減少能源和資源的消耗。
近些年,可持續消費落地中國,方興未艾。在政策層面上,我們也看到各部委相繼推出了許多相關政策,鼓勵綠色消費。例如,2016年十部委首次推出《關于促進綠色消費的指導意見》,我國汽車尾氣排放標準從2009年的國1提升到2020年的國6,是全球最嚴苛的標準,還有最近剛生效的《反食物浪費法》……但是政策的痛點是在消費端很難觸及每個消費者,如出行、垃圾分類、食物浪費等問題。
新消費模式下的綠色循環低碳消費
改變消費者,就要直接面對消費者,而互聯模式正是最大的2C,比如我們每天使用的各種app和小程序。根據商務部《中國電子商務報告2019》,中國電子商務營收為44741億元,十年間增長迅猛。其中,快遞行業、外賣行業都對包裝產生了很大影響,只有少數2C端的平臺在關注循環經濟,在幫助改變個人的行為。可以說,出行是目前做得比較好的領域,比如共享單車、拼車、公交出行等,這些是對于消費者最具可行性的,通過自身行為改變資源效率的模式。未來,數字化技術會給出行給帶來了更多革命性的改變,如車聯、物聯等,我們需要更多地利用這些技術為循環經濟服務。
碳達峰、碳中和的到來為我們提供了新的促進可持續消費的方式和機遇。目前消費端的減排市場行為還處于空白,未來個人消費端的碳交易由于其分散性、微小性和難以記錄,需要采用區塊鏈等技術來保證數據的不可篡改、溯源和個人隱私。而當所有的減排數據匯總時,就需要建立一個第三方來獨立發放碳積分和獎勵。獎勵其實就是很多的權益,是在國家碳市場配額、CCER自愿減排市場外的一個獨立市場,它針對個人減排部分。它不是強制性的,而是一個商業的市場,很多商業性的積分可以轉化為綠色積分,銀行貸款、信用、服務和綠色產品。
商業企業的優惠活動,很多只是一次性的活動,對于綠色沒有量化,通過平臺的定量化,可以把企業所做的綠色公益活動及在供應鏈上的減排量記錄下來,并作為企業的減排量,顯示出企業在可持續發展和社會責任方面的定量化表現,特別是對有綠色產品和綠色服務的企業,可以針對性地向消費者推廣產品和綠色消費的理念,兌換更多相應的服務。
另外,可以用公眾減排的碳推動更多的公益,由于減排量小和個人難以交易,平臺可以將眾多的碳集合起來,發動公益活動,如種樹、塑料回收再生以及垃圾分類等。消費端的減排,與工業端很不同,是嵌入到生活場景中的,而生活場景很多,需要有更多的創新和方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