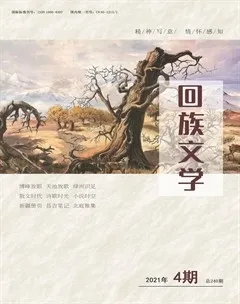當身邊的作家成為參照系
一懷
一
與周俊儒先生真正的接觸,也就是打交道,應該是2003年7月底,那是州上一個文學創作研討會,我多年疏遠了文學場合,所以穿插一段即興發言,提出:文學總是感動人的。文學不是由口號、理論、定義組成的。他在一個人的心中活生生的。真正的生活在別處,這是一種荒謬,一種盲目,一種空虛。其實,你就在生活的中心地帶。這才是永遠的,本質的,真實的。你往何處去?也就是在這個會上,我與周俊儒接近了。其實是會后,我們幾個人一晚上轉換兩三個地方喝酒聊天。這時候我才發現他一個明顯的特點,羸弱之軀掩藏著傾訴之心。之前,我對其模棱兩可語焉不詳。記得有一次在報社走廊與之交錯而過。他穿著工商干部制服,表情莫測。后來得知最早他是武警轉行。我不相信他是一個作家。不像。他半路上拐到文學之路上。尤其是天命之年的他與文學結緣,寫的是童話,出了兩三本書。工商局,制服,五十多歲,童話,這樣的組合,在他身上,是不合時宜的,不能夠對號入座的,我看不出來。這次會后,我們互相之間碰面的機會多了。老周那幾年染酒,抽煙,話多。與我相反。但我逐漸知道了,他青年時代就愛文學,據說手稿在家里的地下室有幾麻袋。讓我想到《地下室手記》。他給人以極大的沉潛感。他不會玩電腦,一直傳統地手寫稿,寫好拿到打字店。耳聞他一個老同學,曾經幫他打稿。他這時候主要是寫童話故事。他對自己的童話,一段時間命之為“綠色童話”。退休,他仍然寫作,涉獵長篇小說,《殘夢》出來了,磚頭厚。我又沒有想到。我的妻子比我先看這本書,一下子就看進去了,給我說了不少有關這本書的話題。我們過去真不了解他。他太不容易了。到2020年底,三卷本長篇小說《野緣》又甩出來了,我更沒有想到,如此厚度的長篇,出自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作家。我對他的職業工作不甚了了,但對他的創作史多少有所了解。周俊儒先生實在是給了我和我們太多的不可想象不可思議。
2003年7月參加全州文學創作研討會的那幾十人,至少五六個人先后離開了這個世界,而周俊儒依然在跑文學馬拉松。
二
巴甫連柯有一句名言:“作家是用手思索的。”周俊儒不斷地在寫,不知不覺地印證了這句話。以這句話為一個標準,周俊儒是不知疲倦的寫作勞模。
國學大師黃侃說:“五十之前不著書。”周俊儒也是五十歲后來居上的。是不是有這樣的思想認識:我五十歲進入寫作場,再不動筆就沒機會了?
據說,塞萬提斯就是五十歲后開始寫作的。我提及周俊儒,竟然想到塞萬提斯,主要是想到了塞萬提斯筆下的堂吉訶德。法朗士說:“我們每個人心里,都有一個堂吉訶德,一個桑丘。我們聽從的是桑丘,但我們敬佩的卻是堂吉訶德。”我有一個預感,周俊儒干文學,是不是有堂吉訶德感?不管別的,始終念茲在茲的都是文學。他豁出去了,誓不罷休。
2021年5月,莫言在北京大學文學講習所成立大會上演講,題為《塞萬提斯的啟示》。他說:“塞萬提斯給予我們的第一個啟示是:要想寫出能反映時代本質并超越時代的作品,作家應該盡可能地拓展自己的生活體驗,更多地深入社會底層,與普通人感同身受。在當今這樣的富裕程度超過歷史上絕大多數時期的情況下,作家要體驗饑餓、勞苦的機會已經大大減少。但生活在基層的人們依然有著種種不如意和難以克服的困難,作為一個寫作者最起碼應該了解這些人的心理和生活狀況,然后才有可能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現實和社會意義。”
不知怎的,我又想到周俊儒。我覺得有一種觸類旁通感。也是推己度人的常識吧。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大數據時代,周俊儒是不是文學之路上冒出來的堂吉訶德式人物之一?
不管那么多,不能為之而為之,不寫自己要寫的,心有不甘啊。
三
非虛構長篇小說《野緣》三卷本,160萬字,這樣的大部頭,厚于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這并不是說,其文學厚度超過了《平凡的世界》。兩者沒有可比性。
路遙英年早逝,遠在邊城的周濤,有一天在報紙上看到路遙去世的消息,看著看著,突然大哭。寫《哭路遙》,發在報上祭奠。周濤自問:“我為什么會如此動情地來哭路遙呢?我們是相交已久的朋友嗎?不是。他是茅盾文學獎的得主,我對他有一種崇拜和敬仰之情嗎?好像也不是。”周濤認為:“耗費如此巨大的精力構筑這樣一部藝術準備尚不充足的長卷,是笨了些。”路遙之死讓周濤生悲。“當這個平凡的世界失去了這個平凡的人時,突然顯示了他真實的意義。”“不管他的作品是否能夠經得起時間的汰選和剝蝕,不管他傾生命之血而完成的這部長卷是否具有藝術的價值,但有一點是明白無誤的:從此,人世間不會有這么一個名為路遙的寫出的哪怕粗糙的文字了。” “一個西北的黃壤中出生的人,用他顯得笨拙的生命給這個職業增加了分量。”
因周俊儒《野緣》,聯想到路遙《平凡的世界》,不由自主,就想到了這一點。
四
《何典》有言:“文章自古無憑據,花樣重新做出來。拾得籃中就是菜,得開懷處且開懷。” 周俊儒也是如此吧。周俊儒吭吭哧哧寫非虛構長篇小說《野緣》三卷本,林林總總、拉拉雜雜、絮絮叨叨,鋪陳到百萬字的三卷本。讓人望而生畏。
刪繁就簡三秋樹。周俊儒卻舍不得刪。拔蘿卜帶泥,都端上來了。《野緣》是不加修整的野草坪。保持一種手稿似的蕪雜瑣碎。
五
周俊儒老黃牛一樣的寫作。
張煒有過430萬字的長篇巨著《你在高原》。他曾經借用毛姆的話表達:偉大的作家必然多產,而多產的作家未必偉大。
張煒在《心儀》一書中向一大批世界級作家致敬。其中這樣評論毛姆的《人性的枷鎖》:“他很少在過去的寫作中表現過如此的淳樸,如此的沉著。當然也顯得瑣細、冗長,特別是用今天的眼光看。但只要耐著性子讀完就會發現,它是莊重沉穩的,有深度的。這本書越往后越好。它寫得太長了,藝術上多少有些平庸氣。好像老牛拉車,盡管緩慢,但畢竟負載的東西很多。”
張煒表示,這是一個稍微談點兒善良、談點兒理想就被嘲笑的時代,大家談得最多的是銷量和點擊量。“但是,這個時代又是需要談偉大作家的,偉大的作家難得不易做,我們若按照偉大作家的規格,做一點兒就很好了。現在搞文藝、搞文學的聰明人太多了,這些人乖巧聰明,喜歡以小博大,以小的勞動博取更大的利益,而稍微冒點兒傻氣的人,就被人稱為‘一根筋,被看作是保守的人。”
在談到如何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時,張煒說,他個人的小聰明,是他成長為偉大作家的障礙。“在未來阻礙我寫作上發展的東西不是技術和閱歷,最大的頑疾是我個人的小聰明、膽怯和投機。我不覺得一個會耍小聰明的人能成為好作家。成為偉大的作家需要很多條件的限制,但是只知道耍小聰明的人不會成為偉大的作家。”
張煒一席話,我認為相當于是周俊儒《野緣》研討會縈繞的一段畫外音。成為我思量的重要眉批。
七十多歲的周俊儒,一直在想搏一把。他貼入基層,經歷磨難,不如意,讓自己面對現實社會,積累出了沉重的《野緣》。他自認為是個人的“終結篇”。
六
周俊儒的《野緣》先鋒嗎?
不先鋒。它不在先鋒文學之列。
它在傳統寫實的作品田野旁逸斜出。
七
周俊儒在踽踽獨行。他仿佛柳青在完成《創業史》。一個人費神費力打造出的浩繁的記錄史,連他自己都懷疑起來,“有誰會看這樣的作品?既然有如此清醒的認識那就別寫嘛,又沒人非要你寫……”我們只能這樣說了,笨也罷,難也罷,累也罷,草也罷,畢竟是 “十年磨一劍”的苦心經營之作。不能一鳴驚人,冷冷清清,都是當今最正常不過的事情。
有不解、誤解或曲解,認為不值得,沒意義,不當一回事,在很多人不屑一顧精神生活的時代,是不足為奇的。
《野緣》寫作是讓周俊儒實現一個百姓作家的自身價值的方式,決絕般的,不惜一切。其實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