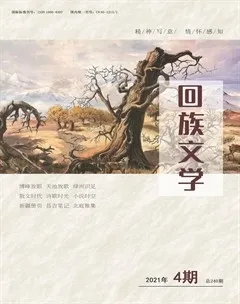農(nóng)業(yè)轉(zhuǎn)型時期人與自然抗?fàn)幍囊磺恍鄩迅?/h1>
2021-09-05 19:35:52楊立新
回族文學(xué) 2021年4期
楊立新
周俊儒先生創(chuàng)作的《野緣》是一部非虛構(gòu)長篇小說,一部貼近當(dāng)下的反映農(nóng)業(yè)大變革的作品,是小說化的家族史。通過一個家族的農(nóng)業(yè)情結(jié),從城里到農(nóng)村辦農(nóng)場,開荒種地,到退耕還林,寫了新時期農(nóng)村開始走向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走向一條節(jié)水、綠色、環(huán)保的艱難探索之路。
《野緣》寫了主人公們面對困境鍥而不舍頑強拼搏的精神,寫了農(nóng)場二十多年間所經(jīng)歷的坎坷曲折,深刻、全面地寫出了新疆農(nóng)村的生活面貌和歷史變遷過程,是全景式地表現(xiàn)中國當(dāng)代城鄉(xiāng)生活的一部長篇小說。
正如周俊儒先生自己所說,“如果簡單說,這是一部勵志的小說”。而我更相信和贊成這是一部反映農(nóng)村改革發(fā)展的波瀾壯闊的恢宏史詩。尤其是農(nóng)業(yè)轉(zhuǎn)型時期,人與大自然抗?fàn)帯⑷伺c命運挑戰(zhàn)的一曲不朽壯歌。
首先,小說《野緣》回答了我國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村面臨的許多深層次問題。作者寫自己的弟弟們跑到窮鄉(xiāng)僻壤去開荒種地,包了8000畝國有鹽堿地,想搞出名堂。從2013年開始寫農(nóng)場的事情,寫得很細(xì)膩,很具體,寫了農(nóng)場十五年的發(fā)展過程,正好也是從第一次退耕還林到第二次退耕還林的過程,從大水漫灌到節(jié)水滴灌的全過程。走的是非虛構(gòu)小說的路子,用紀(jì)實的方式真實記錄了辦農(nóng)場走過的辛酸與艱難。這里,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非要去開荒種地?為什么到了一定程度就必須采用節(jié)水滴灌技術(shù)?為什么到了一定程度就必然走向退耕還林?為什么許多政策的調(diào)整都要從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先試先行?作者直面問題,不回避矛盾,用實事一一作了解答。因此,作者既是農(nóng)村這場變革的親歷者、參與者,更是見證者。《野緣》是如實反映新疆農(nóng)村變革的一個縮影,也從另一個層面揭示了中國社會面臨的根本性問題,仍然是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村問題,只有農(nóng)業(yè)穩(wěn)天下才會興,沒有農(nóng)民的全面小康實現(xiàn),就沒有國富民強民族復(fù)興偉大目標(biāo)的實現(xiàn)。另一個可貴之處在于,《野緣》從開荒、打井、治堿、造田,到后來退耕、還林、節(jié)水、滴灌,從沒把人與自然看成一對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體,而是在艱難探索之中找到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之道,與當(dāng)下治國理政的生態(tài)學(xué)理念高度契合。
二十年間,中國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村發(fā)生的這些重大事情在影視劇里都有所反映,但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上,尤其是長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上還是一片空白,人們的著墨并不多見。而《野緣》這部小說恰好真實、全面、深刻、客觀、理性地反映了這一歷史進程,填補了這一時期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上的空白。尤其是反映新疆人在農(nóng)村這場大變革中所表現(xiàn)岀的思想、行為、作用、責(zé)任和擔(dān)當(dāng),實屬難能可貴。因此,《野緣》的成功,不僅僅是文學(xué)性的,而且是歷史性的。讓我們看到了作者的時代責(zé)任感和歷史擔(dān)當(dāng)。這也再次說明,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根要往下扎,觸角的延伸和關(guān)注度仍然要多放在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村,我們的魂、我們的根、我們的本就在農(nóng)村。
其次,小說《野緣》向世人呈現(xiàn)出新疆人的內(nèi)心世界和豐富情感。包括地域特色、人文地理兩個方面。人文又包括人的社會狀態(tài)、思想狀態(tài)、飲食習(xí)慣、風(fēng)土人情等等;地理包括自然氣候、農(nóng)村環(huán)境、土地耕種、經(jīng)濟狀況等等。這些詞聽起來充滿著干巴巴的學(xué)術(shù)味道,但在生活中卻是生動的、具體的、交織在一起的,簡單說就是一句話:新疆農(nóng)村人是怎么活的,尤其是在艱難困苦中怎么掙扎、怎么與環(huán)境和命運進行抗?fàn)帯V芸∪逑壬鷮懗隽诵陆r(nóng)村人的生存之道、處世之道、交友之道、耕作之道,寫出了新疆的農(nóng)村風(fēng)貌,新疆農(nóng)民的樸實、厚道,新疆人勞動的艱辛,新疆人的執(zhí)著與堅守,新疆人跟土地和農(nóng)業(yè)的深厚情感,寫出了新疆農(nóng)村的一切。
再一個就是書中的算賬,算經(jīng)濟賬。讓我不由得想起新疆曲子和花兒都在唱的那兩句詞,“能干的阿哥是銀耙耙,會過日子的尕妹是金匣匣”。還有人們早已熟爛于心的家風(fēng)傳承:“吃不窮穿不窮,計劃不周才受窮。”無論是傳唱,還是傳承,都牽扯著農(nóng)民算細(xì)賬的問題。周先生說,他寫《野緣》還有一種潛意識,就是學(xué)習(xí)巴爾扎克。他引用了恩格斯的觀點:“我從這里(《人間喜劇》),甚至在經(jīng)濟細(xì)節(jié)方面(如革命的動產(chǎn)和不動產(chǎn)的重新分配)所學(xué)到的東西,也要比上學(xué)時所有職業(yè)的歷史學(xué)家、經(jīng)濟學(xué)家和統(tǒng)計學(xué)家那里學(xué)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正如周先生所說,他在寫作時,把與農(nóng)業(yè)(種地)資金有關(guān)的各種關(guān)系、各種人物都寫進來,特別是在經(jīng)濟細(xì)節(jié)方面,比如資金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中的流轉(zhuǎn)情況,比如從開春種地,種地的錢怎么來,錢又是怎么分解到購買籽種、化肥,犁地、用工、用水、用電等等各個方面,莊稼收獲后資金又是怎么回籠的,虧損造成的欠賬又如何轉(zhuǎn)成高利貸,銀行貸款、借錢、賒賬的利息,高利貸的變化,打井、安滴灌,水費、土管費,地上的融資使用,農(nóng)產(chǎn)品的收購價的變化,打工費用的變化等等。
種地,實際上就是錢的流轉(zhuǎn),錢的走向,錢都到哪兒去了。過去我們老說農(nóng)民小農(nóng)意識如何如何,新疆人大錢掙不來、小錢看不上,就會瞎老婆子算賬,掐著個指頭沒完沒了。讀完《野緣》恐怕要改變有些對自身的看法,賬要從細(xì)處算,做事要從小處著眼,針尖大的窟窿不去堵,必定會有斗大的風(fēng)穿過。水滴石穿、聚沙成堆、涓涓細(xì)流匯成大海,成就了《野緣》的澎湃之勢。這部小說里算了十五年的賬下來,居然從算錢上算出了資金的變化,從而算出來了農(nóng)村的發(fā)展與變化……周先生也自認(rèn)為通過對種地的資金沒完沒了地算賬,細(xì)致、深入地具體算賬,幾乎成了一本農(nóng)村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學(xué)。我不由得發(fā)岀感嘆:好日子真是在算計中度過,沒有家家戶戶的小河滿,哪有全面小康的大河奔流。正是靠著精打細(xì)算,全局謀劃,精準(zhǔn)投入,才使得原來死水一般的農(nóng)場出現(xiàn)了一片勃勃生機。
第三,小說《野緣》向人們傳遞了一種不畏艱難,不向命運低頭,敢于向大自然挑戰(zhàn)的一往無前的奮斗精神。這始終是貫穿這部小說的一條主線。茫茫鹽堿荒地,帶給大多數(shù)人的是荒涼與悲壯。對于楊寶平來說,卻有著特殊的情感。他矢志不渝、拼搏奉獻(xiàn),科學(xué)治堿、綠色發(fā)展,持之以恒推進治理鹽堿。開辦農(nóng)場前期,荒灘種地,屢敗屢進,越挫越勇,反反復(fù)復(fù)做試驗,遇到失敗不氣餒、不服輸、不低頭、不認(rèn)命,及時總結(jié)經(jīng)驗、汲取教訓(xùn),以愚公移山精神,挺直脊梁向大自然宣戰(zhàn),硬是將種啥啥不成的不毛之地,改造成了種啥啥都成的良田,生動書寫了從“鹽堿逼人退”到“人進鹽堿退”的綠色篇章,為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作出重要貢獻(xiàn)。他所掛帥的這支拓荒隊伍,是一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忠實踐行者,是讓鹽堿荒灘變綠洲的不懈奮斗者。小說將主人公楊寶平性格里的不怕吃苦、剛毅堅強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尤其把隱藏在人物性格中的那種鍥而不舍的堅強意志、吃苦耐勞的精神充分表現(xiàn)了出來,使其得到了最大釋放。種地遇到那么多的難事,那么多能使人已經(jīng)陷入絕望,且一時半時都邁不過去的坎,他居然都能堅強應(yīng)對,頑強挺過去,這其中既有治理鹽堿地的傳統(tǒng)智慧,更有講科學(xué)的生動實踐。而失去太多的楊寶平,覺得自己不需要同情、憐憫,他認(rèn)為他的選擇沒錯,他不后悔。這樣一位有追求、有夢想、有個性的守土漢子,堅守著自己的那份初心,認(rèn)準(zhǔn)的道路必須走下去,八頭騾子也難拉回,沒有絲毫退縮,比那犟牛還要犟。楊寶平帶領(lǐng)一撥人,二十多年如一日,馳而不息,久久為功,在與惡劣環(huán)境的不懈斗爭之中,摸索出一條讓鹽堿荒灘披綠生金的發(fā)展之道,彰顯了“誓把荒灘變綠洲”的奮斗精神。
當(dāng)遇到國家相關(guān)開荒政策調(diào)整,退耕還林給農(nóng)場帶來轉(zhuǎn)機時,面對機遇、面對選擇,即便有萬般不舍,最終理性戰(zhàn)勝一切。新疆的農(nóng)民不甘落后,及時更新觀念,服從大局,舍小家顧大家,緊緊抓住機遇,讓林地經(jīng)營和管理進一步帶動農(nóng)牧民脫貧致富,使造林就是“造福”的觀念深入人心。二十多年來,楊寶平接力開荒造田辦農(nóng)場的實踐,鑄就了“不怕困難、苦干實干”的拓荒牛精神,用實際行動詮釋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是小說深化綠色發(fā)展理念、推進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的生動范例,更是以楊寶平為代表的新疆農(nóng)民家國情懷的生動體現(xiàn)。我相信,這部小說,必將激勵鼓舞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治理鹽堿荒灘的大軍。
不忘初心,砥礪奮進。小說《野緣》充滿正能量,緊扣時代主題,緊貼大變革時期農(nóng)村現(xiàn)實,寫岀了新疆人勇立改革潮頭,吃苦耐勞,迎難而上,忘我奮斗的精神,更寫岀了新疆人胸中有大局,眼里有方向,為建設(shè)美麗中國、鄉(xiāng)村振興,實現(xiàn)中華民族永續(xù)發(fā)展貢獻(xiàn)力量的豪邁氣概。栽上一片林,讓大地披綠裝,為子孫后代留下綠蔭,這就是《野緣》的價值所在。
猜你喜歡
國內(nèi)農(nóng)業(yè)今日農(nóng)業(yè)(2022年1期)2022-11-16 21:20:05 國內(nèi)農(nóng)業(yè)今日農(nóng)業(yè)(2022年3期)2022-11-16 13:13:50 國內(nèi)農(nóng)業(yè)今日農(nóng)業(yè)(2022年2期)2022-11-16 12:29:47 叁見影(微篇小說)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2 遛彎兒(微篇小說)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0 勸生接力(微篇小說)紅豆(2022年3期)2022-06-28 07:03:42 擦亮“國”字招牌 發(fā)揮農(nóng)業(yè)領(lǐng)跑作用今日農(nóng)業(yè)(2021年14期)2021-11-25 23:57:29 在新疆(四首)四川文學(xué)(2021年4期)2021-07-22 07:11:54 那些小說教我的事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 02:25:50 新疆多怪絲綢之路(2014年9期)2015-01-22 04:24:46
楊立新
周俊儒先生創(chuàng)作的《野緣》是一部非虛構(gòu)長篇小說,一部貼近當(dāng)下的反映農(nóng)業(yè)大變革的作品,是小說化的家族史。通過一個家族的農(nóng)業(yè)情結(jié),從城里到農(nóng)村辦農(nóng)場,開荒種地,到退耕還林,寫了新時期農(nóng)村開始走向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走向一條節(jié)水、綠色、環(huán)保的艱難探索之路。
《野緣》寫了主人公們面對困境鍥而不舍頑強拼搏的精神,寫了農(nóng)場二十多年間所經(jīng)歷的坎坷曲折,深刻、全面地寫出了新疆農(nóng)村的生活面貌和歷史變遷過程,是全景式地表現(xiàn)中國當(dāng)代城鄉(xiāng)生活的一部長篇小說。
正如周俊儒先生自己所說,“如果簡單說,這是一部勵志的小說”。而我更相信和贊成這是一部反映農(nóng)村改革發(fā)展的波瀾壯闊的恢宏史詩。尤其是農(nóng)業(yè)轉(zhuǎn)型時期,人與大自然抗?fàn)帯⑷伺c命運挑戰(zhàn)的一曲不朽壯歌。
首先,小說《野緣》回答了我國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村面臨的許多深層次問題。作者寫自己的弟弟們跑到窮鄉(xiāng)僻壤去開荒種地,包了8000畝國有鹽堿地,想搞出名堂。從2013年開始寫農(nóng)場的事情,寫得很細(xì)膩,很具體,寫了農(nóng)場十五年的發(fā)展過程,正好也是從第一次退耕還林到第二次退耕還林的過程,從大水漫灌到節(jié)水滴灌的全過程。走的是非虛構(gòu)小說的路子,用紀(jì)實的方式真實記錄了辦農(nóng)場走過的辛酸與艱難。這里,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非要去開荒種地?為什么到了一定程度就必須采用節(jié)水滴灌技術(shù)?為什么到了一定程度就必然走向退耕還林?為什么許多政策的調(diào)整都要從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先試先行?作者直面問題,不回避矛盾,用實事一一作了解答。因此,作者既是農(nóng)村這場變革的親歷者、參與者,更是見證者。《野緣》是如實反映新疆農(nóng)村變革的一個縮影,也從另一個層面揭示了中國社會面臨的根本性問題,仍然是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村問題,只有農(nóng)業(yè)穩(wěn)天下才會興,沒有農(nóng)民的全面小康實現(xiàn),就沒有國富民強民族復(fù)興偉大目標(biāo)的實現(xiàn)。另一個可貴之處在于,《野緣》從開荒、打井、治堿、造田,到后來退耕、還林、節(jié)水、滴灌,從沒把人與自然看成一對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體,而是在艱難探索之中找到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之道,與當(dāng)下治國理政的生態(tài)學(xué)理念高度契合。
二十年間,中國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村發(fā)生的這些重大事情在影視劇里都有所反映,但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上,尤其是長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上還是一片空白,人們的著墨并不多見。而《野緣》這部小說恰好真實、全面、深刻、客觀、理性地反映了這一歷史進程,填補了這一時期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上的空白。尤其是反映新疆人在農(nóng)村這場大變革中所表現(xiàn)岀的思想、行為、作用、責(zé)任和擔(dān)當(dāng),實屬難能可貴。因此,《野緣》的成功,不僅僅是文學(xué)性的,而且是歷史性的。讓我們看到了作者的時代責(zé)任感和歷史擔(dān)當(dāng)。這也再次說明,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根要往下扎,觸角的延伸和關(guān)注度仍然要多放在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村,我們的魂、我們的根、我們的本就在農(nóng)村。
其次,小說《野緣》向世人呈現(xiàn)出新疆人的內(nèi)心世界和豐富情感。包括地域特色、人文地理兩個方面。人文又包括人的社會狀態(tài)、思想狀態(tài)、飲食習(xí)慣、風(fēng)土人情等等;地理包括自然氣候、農(nóng)村環(huán)境、土地耕種、經(jīng)濟狀況等等。這些詞聽起來充滿著干巴巴的學(xué)術(shù)味道,但在生活中卻是生動的、具體的、交織在一起的,簡單說就是一句話:新疆農(nóng)村人是怎么活的,尤其是在艱難困苦中怎么掙扎、怎么與環(huán)境和命運進行抗?fàn)帯V芸∪逑壬鷮懗隽诵陆r(nóng)村人的生存之道、處世之道、交友之道、耕作之道,寫出了新疆的農(nóng)村風(fēng)貌,新疆農(nóng)民的樸實、厚道,新疆人勞動的艱辛,新疆人的執(zhí)著與堅守,新疆人跟土地和農(nóng)業(yè)的深厚情感,寫出了新疆農(nóng)村的一切。
再一個就是書中的算賬,算經(jīng)濟賬。讓我不由得想起新疆曲子和花兒都在唱的那兩句詞,“能干的阿哥是銀耙耙,會過日子的尕妹是金匣匣”。還有人們早已熟爛于心的家風(fēng)傳承:“吃不窮穿不窮,計劃不周才受窮。”無論是傳唱,還是傳承,都牽扯著農(nóng)民算細(xì)賬的問題。周先生說,他寫《野緣》還有一種潛意識,就是學(xué)習(xí)巴爾扎克。他引用了恩格斯的觀點:“我從這里(《人間喜劇》),甚至在經(jīng)濟細(xì)節(jié)方面(如革命的動產(chǎn)和不動產(chǎn)的重新分配)所學(xué)到的東西,也要比上學(xué)時所有職業(yè)的歷史學(xué)家、經(jīng)濟學(xué)家和統(tǒng)計學(xué)家那里學(xué)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正如周先生所說,他在寫作時,把與農(nóng)業(yè)(種地)資金有關(guān)的各種關(guān)系、各種人物都寫進來,特別是在經(jīng)濟細(xì)節(jié)方面,比如資金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中的流轉(zhuǎn)情況,比如從開春種地,種地的錢怎么來,錢又是怎么分解到購買籽種、化肥,犁地、用工、用水、用電等等各個方面,莊稼收獲后資金又是怎么回籠的,虧損造成的欠賬又如何轉(zhuǎn)成高利貸,銀行貸款、借錢、賒賬的利息,高利貸的變化,打井、安滴灌,水費、土管費,地上的融資使用,農(nóng)產(chǎn)品的收購價的變化,打工費用的變化等等。
種地,實際上就是錢的流轉(zhuǎn),錢的走向,錢都到哪兒去了。過去我們老說農(nóng)民小農(nóng)意識如何如何,新疆人大錢掙不來、小錢看不上,就會瞎老婆子算賬,掐著個指頭沒完沒了。讀完《野緣》恐怕要改變有些對自身的看法,賬要從細(xì)處算,做事要從小處著眼,針尖大的窟窿不去堵,必定會有斗大的風(fēng)穿過。水滴石穿、聚沙成堆、涓涓細(xì)流匯成大海,成就了《野緣》的澎湃之勢。這部小說里算了十五年的賬下來,居然從算錢上算出了資金的變化,從而算出來了農(nóng)村的發(fā)展與變化……周先生也自認(rèn)為通過對種地的資金沒完沒了地算賬,細(xì)致、深入地具體算賬,幾乎成了一本農(nóng)村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學(xué)。我不由得發(fā)岀感嘆:好日子真是在算計中度過,沒有家家戶戶的小河滿,哪有全面小康的大河奔流。正是靠著精打細(xì)算,全局謀劃,精準(zhǔn)投入,才使得原來死水一般的農(nóng)場出現(xiàn)了一片勃勃生機。
第三,小說《野緣》向人們傳遞了一種不畏艱難,不向命運低頭,敢于向大自然挑戰(zhàn)的一往無前的奮斗精神。這始終是貫穿這部小說的一條主線。茫茫鹽堿荒地,帶給大多數(shù)人的是荒涼與悲壯。對于楊寶平來說,卻有著特殊的情感。他矢志不渝、拼搏奉獻(xiàn),科學(xué)治堿、綠色發(fā)展,持之以恒推進治理鹽堿。開辦農(nóng)場前期,荒灘種地,屢敗屢進,越挫越勇,反反復(fù)復(fù)做試驗,遇到失敗不氣餒、不服輸、不低頭、不認(rèn)命,及時總結(jié)經(jīng)驗、汲取教訓(xùn),以愚公移山精神,挺直脊梁向大自然宣戰(zhàn),硬是將種啥啥不成的不毛之地,改造成了種啥啥都成的良田,生動書寫了從“鹽堿逼人退”到“人進鹽堿退”的綠色篇章,為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作出重要貢獻(xiàn)。他所掛帥的這支拓荒隊伍,是一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忠實踐行者,是讓鹽堿荒灘變綠洲的不懈奮斗者。小說將主人公楊寶平性格里的不怕吃苦、剛毅堅強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尤其把隱藏在人物性格中的那種鍥而不舍的堅強意志、吃苦耐勞的精神充分表現(xiàn)了出來,使其得到了最大釋放。種地遇到那么多的難事,那么多能使人已經(jīng)陷入絕望,且一時半時都邁不過去的坎,他居然都能堅強應(yīng)對,頑強挺過去,這其中既有治理鹽堿地的傳統(tǒng)智慧,更有講科學(xué)的生動實踐。而失去太多的楊寶平,覺得自己不需要同情、憐憫,他認(rèn)為他的選擇沒錯,他不后悔。這樣一位有追求、有夢想、有個性的守土漢子,堅守著自己的那份初心,認(rèn)準(zhǔn)的道路必須走下去,八頭騾子也難拉回,沒有絲毫退縮,比那犟牛還要犟。楊寶平帶領(lǐng)一撥人,二十多年如一日,馳而不息,久久為功,在與惡劣環(huán)境的不懈斗爭之中,摸索出一條讓鹽堿荒灘披綠生金的發(fā)展之道,彰顯了“誓把荒灘變綠洲”的奮斗精神。
當(dāng)遇到國家相關(guān)開荒政策調(diào)整,退耕還林給農(nóng)場帶來轉(zhuǎn)機時,面對機遇、面對選擇,即便有萬般不舍,最終理性戰(zhàn)勝一切。新疆的農(nóng)民不甘落后,及時更新觀念,服從大局,舍小家顧大家,緊緊抓住機遇,讓林地經(jīng)營和管理進一步帶動農(nóng)牧民脫貧致富,使造林就是“造福”的觀念深入人心。二十多年來,楊寶平接力開荒造田辦農(nóng)場的實踐,鑄就了“不怕困難、苦干實干”的拓荒牛精神,用實際行動詮釋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是小說深化綠色發(fā)展理念、推進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的生動范例,更是以楊寶平為代表的新疆農(nóng)民家國情懷的生動體現(xiàn)。我相信,這部小說,必將激勵鼓舞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治理鹽堿荒灘的大軍。
不忘初心,砥礪奮進。小說《野緣》充滿正能量,緊扣時代主題,緊貼大變革時期農(nóng)村現(xiàn)實,寫岀了新疆人勇立改革潮頭,吃苦耐勞,迎難而上,忘我奮斗的精神,更寫岀了新疆人胸中有大局,眼里有方向,為建設(shè)美麗中國、鄉(xiāng)村振興,實現(xiàn)中華民族永續(xù)發(fā)展貢獻(xiàn)力量的豪邁氣概。栽上一片林,讓大地披綠裝,為子孫后代留下綠蔭,這就是《野緣》的價值所在。